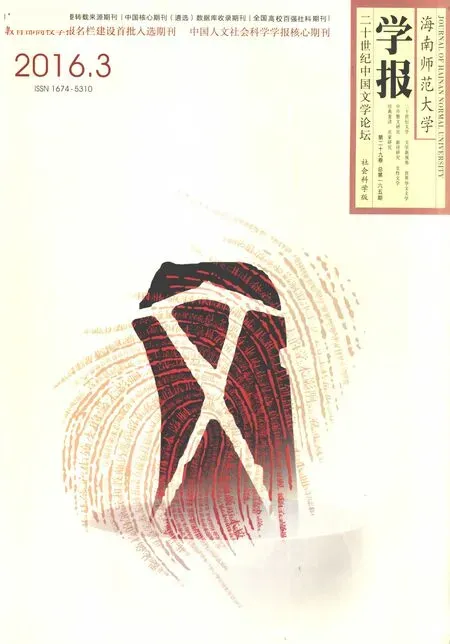“以詩為名”
——談文學研究會與學衡派間的一樁公案
高曉瑞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
“以詩為名”
——談文學研究會與學衡派間的一樁公案
高曉瑞
(西南大學 文學院,重慶 400715)
摘要:《文學旬刊》是文學研究會的機關刊物,文學研究會將其作為自己發表新文學觀念和打擊舊文學的陣地,文學研究會與學衡派之間的論爭也主要是在這里進行的。細查《文學旬刊》,發現這場持久的口誅筆伐竟始于當時南京高師學生編輯出版的報紙“詩學研究號”。透過這段歷史,可以一睹兩派之間的恩怨過節,更可以深入地理解南北學風的差異以及這場論爭對新文學運動的發展產生的影響。
關鍵詞:《文學旬刊》;文學研究會;學衡派;文學論爭
“五四”新文學運動是在陳獨秀、胡適、蔡元培等人的倡導下浩浩蕩蕩地興起的,他們向舊文學投出匕首的陣地是《新青年》。但1919年前后,新青年同人們的編輯方針卻出現了兩種不同的聲音,即胡適的“多研究問題”和陳獨秀的“干預政治”。這種內部分化使得《新青年》越來越向社會批評與政治批評的方向發展,并且從1920年9月第8卷起,它開始成為提倡社會主義運動的刊物,逐步遠離了與新文學緊密相連的初衷。而作為當時國內惟一的大型新文學刊物,《新青年》的分化無疑給當時的文學界造成了一段空窗期,這種留白對于當時以除舊立新為己任的文學青年而言是具有刺激作用的,因為他們渴望對新文學產生一種導向作用。正因為有著獨一無二的責任感和使命感,他們以組成社團的方法來擴大影響力,恰巧促成了文學研究會等新文學社團的成立。所以新文學社團的一個標志便是要“有作為”,“沒有一個社團承認自己的辦社初衷只是閑情逸致的驅使,也沒有一個社團創辦之后的一切作為都圍繞著閑情逸致。”*朱壽桐:《中國現代社團文學史》,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4年,第33-34頁。因此,作為中國現代文學史上成立最早、影響最大的社團之一的文學研究會,在成立初期便自覺地接了此前新青年同人的班,朝舊文學陣營吹響了戰斗的號角。
從社團的角度來講,文學研究會的完備程度在新文學運動初期都是別的社團無法比擬的,它成立時即發表了《文學研究會宣言》《文學研究會簡章》(即章程),還擁有了《小說月報》《文學旬刊》等刊物;在組織程序上,責任分工明確,除了12個發起人以外,還包括“書記干事、會計干事”等,而對于北京以外地區的成員,甚至還訂立一些工作計劃,如“組織讀書會”“設立通信圖書館”*《文學研究會簡章》,《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可見為了握住《新青年》傳下的接力棒,文學研究會成員們可謂是下足了功夫,而他們在被予以重任的同時,也不忘設計新文學未來的走向。在成立之初,便在宣言里高調地打出“將文藝當作高興時的游戲或失意時的消遣的時候,現在已經過去了”*《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的口號,目標對準長久以來把持文壇的鴛鴦蝴蝶派,力圖重整新文學界的格局,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說,文學研究會的創作、理論、翻譯等活動,并不僅僅是為了培養一批獨具特色的作家、批評家,更大的目的是為了對新文學潮流和文壇走向進行建構。在《新青年》同人分化后,我們可以理解在那個新文學剛剛起步的時代學界無首的狀況,因此在文學研究會成立的初期,他們積極向舊文學勢力宣戰。當然,我們也同樣理解了他們與南京高師——東南大學師生間那場關于新詩與古體詩的持久的論爭。
一、“一條瘋狗”:《文學旬刊》上的口誅筆伐
眾所周知,“五四”新文化運動中重要的一項是“反文言”,它宣告了文言文時代的結束和白話文時代的開始,但在文言文傳統歷時持久的中國,這突然的改變對于部分知識分子來說是難以接受的,因而讓白話從一種語言表達到構成文學的基礎,再到如何用白話承擔起改造社會的任務,這經歷了幾代知識分子的思考。從胡適的“話怎么說,就怎么寫”“是什么時代,說什么時代的話”*胡適:《建設的文學革命論》,《胡適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第60頁。,到新潮社的傅斯年提出的“歐化的白話文”*傅斯年:《怎樣寫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這些關于白話文的討論,實際上可以理解為白話被賦予了重大的責任,即傅斯年所說的“借思想改造語言,借語言改造思想”*傅斯年:《怎樣寫白話文?》,《新潮》第1卷第2號,1919年2月1日。,這是與傳統文言文僅為表達自己情懷的作用是不盡相同的。眾位思想家們知道,雖然有白話未必就能產生出新思想、新文學,但是我們首先得有一個新的媒介——白話,“先要做到文學體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來做新思想新精神的運輸品。”*胡適:《〈嘗試集〉自序》,《胡適文集》第9卷,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82頁。所以,白話文在“五四”一代新文學家那里,就成了一項必備的傳播新思想、改造舊思想的工具,人們對于經濟、文化、道德、人生的觀念都改變了,對于一些問題將會有了新的意見和言說,舊皮囊無法裝下新鮮的美酒,“新的思想必須用新的文體以傳達出來,因而便非用白話不可了”。*周作人:《文學革命運動》,《周作人散文全集》第6卷,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第102頁。
既然白話如此重要,那么當文學研究會的骨干人物鄭振鐸看到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仍以宣揚古體詩為本時,我們可以想見他當時迫切想糾正這種思想的心情。所以他在1921年11月3日給周作人的信中如此寫道,“南高師日刊近出一號‘詩學研究號’,所登的都是舊詩,且也有幾個做新詩的人,如吳江冷等,也在里面大做其詩話和七言絕。想不到復古的陳人在現在還有如此之多,而青年之絕無宗旨,時新時舊,尤足令人浩嘆,圣陶、雁冰同我幾個人正想在《文學旬刊》上大罵他們一頓,以代表東南文明之大學,而思想如此陳舊,不可不大呼以促其反省也。寫至此,覺得國內尚遍地皆敵,新文學之前途絕難樂觀,不可不加倍奮斗也。”*鄭振鐸:《鄭振鐸致周作人信》,《中國現代文藝資料叢刊》第五輯,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80年,第353頁。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出刊于1921年10月26日,而遭到文學研究會成員的猛烈批判僅僅就在其出刊后的兩個星期。首先站出來的是化名為斯提的葉圣陶,他在1921年11月12日的《文學旬刊》第十九號上點名道姓地指出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為“骸骨之迷戀”,他指出詩的作用是“批評人生表現人生”,如果人生是變動不息的,那么詩歌就該隨時代變化,不管是在形式上還是思想上,而南京高師那群師生依舊“照抄以前的批評人生表現人生的詩學的研究”,過去的詩留下的精神曾給當時的人以啟示,如“塚墓里的骸骨曾經一度有生命”*斯提:《骸骨之迷戀》,《文學旬刊》第19號,1921年11月12日。,但對于現在的人卻沒有了意義。在葉圣陶眼中,他們在“詩學研究號”中居然推崇舊詩,把精力耗費于已成骸骨的事物上,那就相當于犯了十惡不赦的錯誤了。
這篇犀利的批評一出,立即引起了南京高師師生們的反攻,由此也開創了《文學旬刊》自創刊起最富有戰斗性的一段時期。緊接著在《文學旬刊》第20期,立刻在通訊欄里刊出了薛鴻猷在1921年11月13日致西諦先生的一封信,全文無標點,一邊挑戰似的堅持擬古的特色,一邊要求“糾正斯提之謬誤”*《通訊:薛鴻猷致西諦》,《文學旬刊》第20號,1921年11月21日。。乍一看這種回復無可厚非,但此信后有一編者附記讓大家窺到了玄機:“薛君大稿,題為《一條瘋狗!》。全篇皆意氣用事之辭。本不便刊登……但新舊詩的問題,現在還在爭論之中,迷戀骸骨的人也還不少,我們很想趁此機會很詳細的討論一番。所以決定下期把薛君的大稿刊登出,附以我們的批評。”
就這樣,圍繞著“一條瘋狗”的罵戰就開始了。在《文學旬刊》第21號上,首先就刊出了守廷的《對于〈一條瘋狗〉的答辯》,在題目上似乎就把薛鴻猷對斯提的謾罵不動聲色地還回去,更指出他的這種謾罵根本不值得新文學者的注意,但是現在同薛君一樣的“準遺少”并不算少,所以還是有討論的必要了。守廷首先就指出薛鴻猷對于斯提君的文章的不切實際的理解,指出斯提批評的是《東南大學南高日刊》里“詩學研究號”中的舊詩依舊沿襲古代人的舊形式,并非在罵薛君的“大文”《詩與哲學》。其次,他通讀南高日刊,發現里面所刊載的詩文頗像“前清或前明的落魄秀才,三家村學究的作品”,消沉黯淡的氣息彌漫其中。他還一針見血地指出,這種擬古詩磨滅了作者的創作個性,“讀者能夠知道前一首是誰做的,后一首是誰做的么?這種詩還曾包含作者的人格在里面么?像這種空空泛泛的感懷之作,還會有什么時代精神么?”*守廷:《對于〈一條瘋狗〉的答辯》,《文學旬刊》第21號,1921年12月1日。所以“詩學研究號”占用“詩學研究”這個名字,根本就是名不副實的。而薛君的不分青紅皂白亂罵一氣,不得不讓人感嘆“薛君休矣!”
緊接著守廷長文之后的是薛鴻猷當時回復斯提的那篇《一條瘋狗!》。在文本一開篇就稱斯提的批評為“狂吠一陣罷了”,并洋洋灑灑地提出了自己的詩學觀,條條都為自己以及南京高師諸師生教學古詩文正名。其中幾條為:“(四)我認定我們當在文言詩中,做一番整理的和改革的工夫,在語體詩中,做一番建設的工夫。……決不能因為是前人的作品,就鄙棄之,一筆抹煞,謂之毫無價值,而失學者研究精神。”“(五)我認定一個學府中,對于各家學說,當并容兼蓄,決不能受一種學閥之把持。所以‘詩學研究號’全發表文言詩,改日尚須另刊語體詩,從長討論。”“(九)我們以前人的文學做食品,我們吃了消化了,很可以滋養我們的身體,增長我們的智力。”*薛鴻猷:《一條瘋狗!》,《文學旬刊》第21號,1921年12月1日。這些觀點首先就確定了文言詩不為“骸骨”,反倒具有一定的生命力,而且對現代人有巨大的啟示。其次,還影射文學研究會為“學閥”,稱他們為了自己的主張壓制其他學派,而這個詞在之后不長的時間中,即將被學衡派諸君引用來批胡適。
在這期短短四版的刊物中,罵戰并不止于此。之后連續刊載署名卜向的《詩壇底逆流》,聲明若有人迷戀骸骨,我們本不必在意,但“現在這一二人竟想將他們那嗜好發揮光大,叫大家也迷戀骸骨,我們卻不敢認為妥當”*卜向:《詩壇底逆流》,《文學旬刊》第21號,1921年12月1日。。署名“東”的《看南京日刊里的“七言詩文”》稱讀了他們的舊體詩“不覺起了個惡嘔”*東:《看南京日刊里的“七言詩文”》,《文學旬刊》第21號,1921年12月1日。。而署名“赤”的《由〈一條瘋狗〉而來的感想》更是言辭激烈,聲稱恭候薛君的“第二條瘋狗”*赤:《由〈一條瘋狗〉而來的感想》,《文學旬刊》第21號,1921年12月1日。。
關于新舊詩問題的討論,雙方當然不會這么快就偃旗息鼓。所以在第22期的《文學旬刊》上,首先就刊出了繆鳳林的《旁觀者言》,他站在南京高師的立場上,稱“余覺兩方俱以日刊少數人之詩牽涉學校”這事失之公正,同時稱斯提守廷諸君之論“以偏蓋全”*繆鳳林:《旁觀者言》,《文學旬刊》第22號,1921年12月11日。,所以有必要以“旁觀者”的眼光來論證一下此事。說是旁觀,其實依舊“意氣”,按末尾的編者語來看,其中刪除了幾段“他不必說而說的話……但原文的真意確是毫無失掉”。本期末尾處還登有守廷和歐陽翥的通信,繼續討論“新”與“舊”能否調和,“詩學研究號”中的舊詩是否含有惋惜帝制之意。客觀看來,這一期的爭論相對平緩了很多,但卻在編者后記中隱藏了玄機,“薛鴻猷先生:來信因篇幅關系,且中多意氣之辭,不便登出,乞諒解!”
在之前已經論述過,對文學研究會而言,最重大的任務是要引領新文學走上正軌,同時摒除其發展途中可能出現的各種“倒流”因素,所以在“破”的過程中更要“立”。于是在《文學旬刊》第23號中,先后登出了劉延陵署名Y.L的《論散文詩》、臺靜農的《讀〈旁觀者言〉》、吳文祺的《對于舊體詩的我見》。尤其是吳文祺,在其論文中鮮明地指出:“詩和時代精神相表里的,時代精神既變動不息,那末詩也應當跟著變遷。‘舊壺不能盛新酒’,已死了的文字決不能表微妙的情緒;印板式的詩體,決不能達活潑的想象。”*吳文祺:《對于舊體詩的我見》,《文學旬刊》第23號,1921年12月21日。吳文祺于1917年從南京的金陵大學肄業,對東南一帶學風相對了解,而且擅長語言學,所以除《文學旬刊》第23期外,他還在第25期上發表《駁〈旁觀者言〉》,反對繆鳳林并指出新詩之好壞不在韻律、平仄、格式等問題上,更于1922年2月11日在第28期上撰文《〈又一旁觀者言〉的批評》,廣征博引,表達自己對于現代無韻白話詩的支持。
時至于此,文學研究會與南京高師諸師生間關于新舊詩的論爭,以及由“一條瘋狗”引發的口誅筆伐才稍稍平息下來。而平靜并不意味著兩派的相互承認和妥協,反倒是因為文學研究會把自己的目光轉向了“詩學研究號”這些人背后的更大的一個勢力——學衡派,一群受過歐化教育卻又極力反對新文學運動的守舊者。
二、南北學風: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的“對立”
從1922年起,這段時間的《文學旬刊》《小說月報》上刊登的對于復古派的清算,也基本上是針對學衡派成員的。細查學衡派成員列表,“初期的成員是早期留學哈佛大學的幾位白壁德的學生(梅光迪、吳宓、湯用彤、樓光來)和南京高師)東南大學的師生(老師主要是柳詒徵、胡先骕、王伯沆、王易、劉伯明、汪辟疆此時尚在南昌心遠大學任教授、文科主任。學生主要是繆鳳林、景昌極、張其昀、王煥鑣、徐震堮、束世澂等)以及南京支那內學院的師生”,*沈衛威:《“學衡派”史實及文化立場》,《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第3期。而其中繆鳳林等人皆是在“詩學研究號”事件中與文學研究會筆戰的主力,所以他們基本代表了東南大學整體的學術研究傾向。而從文學研究會這邊來看,“主力”茅盾曾就讀于“北京大學預科”*茅盾:《學生時代》,《我走過的道路》(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7年,第100頁。,鄭振鐸雖然就讀于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卻參與了北京大學舉辦的“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陳福康:《一代才華——鄭振鐸傳》,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18頁。,他們的前輩周作人,當然也是文學研究會成員,更是從1917年開始就任教于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在新文化運動的初期,就開始宣揚白話文,所以這場針對“詩學研究號”的論爭,表面上是文學研究會和南京高師學生之間的對立,某種程度上更可以看成是北大和東南大學這兩所學校之間學術風氣的對立,而學校學術風氣的相悖,更深層次顯示的是地緣文化的差異。
一直以來,學界對社團、學派以及它們相對應的刊物的研究都相當充分,研究者們習慣于從每個社團入手,以時間為維度研究他們的思想變遷、對比彼此之間的差異,卻鮮少從地域文化空間、地緣文化譜系等方面考慮社團文學風格的殊異性。因而當我們重新來看待文學研究會與學衡派之間論爭的這段歷史時,不應直接就從兩派理論主張入手,更應考慮地域這個無形的大手在背后潛移默化的作用,正如郁達夫所言:“我們住在什么地方,就不得不受什么地方的感化。”*郁達夫:《夕陽樓日記》,《創造》(季刊)第1卷第2期,1922年8月25日。而對于中國現代文學而言,這受到影響的不僅僅是作家,更有扎根于各個城市的社團。
先看成立于“五四”時期北京的文學研究會,魯迅先生曾說,“北京是明清的帝都……所以文人之在京者近官。”*魯迅:《“京派”與“海派”》,《申報·自由談》1934年2月3日。不僅明清,在中國歷史上,做官多是靠的種種考試制度,而要參加考試的前提則是有一定的文化積累,知識分子有實現抱負的雄心,則需要做官;官員若需表達心跡,也總以文學的形式來記錄。所以對于北京這樣一個帝都,現代文人受到的最深影響就是以天下為己任的中心意識。如《新青年》的真正發展并產生巨大的影響力是在移師北京,并得到以蔡元培為首的北京大學的推廣之后。《新青年》的推廣者以及接收者都與北京大學有巨大的聯系,潛藏的原因則是知識分子胸懷天下的中心意識。在《新青年》改組后,一手承擔起文學使命的文學研究會則在建社初期就宣布要“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目標是“造成一個公共的圖書館研究室及出版部”和“建立著作工會”,*《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同樣也是這種中心姿態的直觀表現。所以縱觀文學研究會的發展,不管是以“研究”一詞作為自己的社團名詞,還是打著“為人生”的現實主義姿態來啟蒙大眾,更有的是剛成立就以強勢的姿態來對鴛鴦蝴蝶派、學衡派等團體進行筆伐,都可以理解為它的目的是在進行著對整個新文學格局的設計,不斷強化著自己作為一個文學工作者“工會”的形象,以此來據守文壇中心地位。這種對社會改革所自覺擔負起的責任,不能不說有傳統知識分子精神的遺傳。其次,與上海的租界不同,當時北京最為流行的是大學,學院派風氣的盛行是當時北京的一大特色,尤以北京大學之風最盛。學院風氣的一種體現就是打通中外古今的文學,所以文學研究會的宗旨定為“研究介紹世界文學,整理中國舊文學,創造新文學”*《文學研究會簡章》,《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對待別派的態度則取“人生的藝術派”*周作人:《新文學的要求》,《北京晨報》1920年1月8日。,顯示出四平八穩,包羅萬象的氣勢。即使是在打擊舊文學時,也依舊不忘提倡“整理國故”,原因是“完全是為了要滿足歷史上的興趣……并不是向古人去學本領,請古人來收徒弟”*顧頡剛:《我們對于國故應取的態度》,《小說月報》第14卷第1號,1923年1月10日。。這種倡導與復古的學衡派是不同的,它的目的是讓人了解舊文學以更好地為新文學服務。綜上所述,從發起人到所處地域都與北京息息相關的文學研究會,不自覺地就染上了帝都知識分子以天下為己任的理想,也擁有了一種縱橫捭闔、指點江山的氣勢,更擁有了北京大學兼容并包的學術風尚,因而呈現出欣欣向榮的氣勢。
身處南京的東南大學——南京高師師生和學衡派諸人,卻具有了完全不同的學術氣質。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的學術板塊便大致分為兩大傳統,一是以北大為根據地的主張革新的師生,二是以南京高等師范學校(東南大學)為首的對新文學抱有批判態度的一幫人。他們的地域分別與對待新文學態度的差異,儼然成為近代文學史上“南北”與“新舊”的代名詞。細看東南大學的治學之風,首先就是強調文言文、反對白話文;其次是重視古典文學研究、輕視新文學創作;再有推崇固有文化、吸取西方文化來改良傳統文化。這不僅是新文學陣營對他們的指責,更是南京諸人對自我的一種肯定。其實相比于“新舊”而言,北京大學與東南大學之間的差異更在于“激進”與“保守”之間,且不論從20年代到40年代南北學派的幾次分和,就我們討論的學衡派時期的東南大學,也不能完全和甲寅派等純粹的復古派劃上等號。他們的口號是“昌明國粹,融化新知”,即首先是發揚傳統文化中的優良成分,同時也強調吸取外來文化,將中外的精髓同時吸取,摒棄新文化運動者那種模仿西人不得法的錯誤。在破舊立新面前,他們主張的是保守的方法,即“古語有云,利不十,不變法”*胡先骕:《中國文學改良論》(上),《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上海: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1935年,第106頁。,在沒有確定廢文言立白話是否完全有利的時候,不應拋棄文言。白話的產生對文學只是多了一種表述的方式,還遠遠沒有達到要取代文言的地位。某種程度上說,他們對白話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認同的,但這種瞻前顧后的態度對于新文學的倡導者而言是迂腐不堪的,所以兩派之間的對立不可避免。若同樣從城市的角度來講,南京與北京一樣也曾是國都,但卻曾在明代被明成祖朱棣廢棄,顯示出“而今王氣暗銷沉”*歐陽翥:《謁南京古物陳列所》,《國立東南大學南京高師日刊·詩學研究號一》,1921年10月26日。的衰頹之氣,頗有遺少遺老之風。其次,轟轟烈烈的新文化運動雖在北京風起云涌地進行著,但在南京,似乎遠遠沒有受到同等的影響。究其原因,則是因為南北學者之間的不通“聲氣”。早在1923年,尚為東南大學歷史系學生的陳訓慈就敏銳地發現當時學術界的一個問題:“耆學宿儒往往與新進學者各不相謀。又因地域之暌隔,而各地學者常不能共通聲氣”,這實乃“不幸之現象”*叔諒:《中國之史學運動與地學運動》,《史地學報》第2卷第3期,1923年3月。。就是這種各自為王的思想和天各一方的地域差異,導致各地學者“不通聲氣”,也間接促成了他們之間學術的對立。
其實學衡派的保守不是在“五四”運動之后才形成的,早在胡適、梅光迪、胡先骕等在留學美國期間,對立就已經開始了。1915年至1917年間,留學美國的胡適就開始白話詩的實踐,而同在美國留學的梅光迪便開始有了與他截然不同的立場。兩人雖然同宗英美文學,卻由導師觀念不同而各異,“胡適所宗的是科學主義、實驗主義的大師杜威,而梅光迪所宗則是人文主義、文化保守主義、古典主義的大師白璧德(學衡派的主將吳宓、張歆海、湯用彤等都是白氏的門生),新文化派的胡適與文化保守派的梅光迪之間的對立,其背后實質上是當時美國兩大文化派別的對立。”*潘正文:《“文學地理”與現代社團文風》,《文學評論》2011年第5期。所以回國后,胡適率先提出了改革的主張,而梅光迪等人則選擇了保守落寞的南京城來弘揚保存舊文化。而心系舊文學的吳宓在1919年學成歸國后也毅然放棄了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拋出的橄欖枝,自覺來到了東南大學。正在新文學風生水起的時候,他來到南京是否也意味著與北京的背離?而之后在他主導下的學衡派也確實是做到了這一點。
三、“誰的勝利?”:論爭對新文學運動的影響
文學的發展需要一個健康的文化生態環境,這種健康對應的是一個多元共生的局面。任何時代的文學若想要健全地成長,就必定需要這樣一個百花齊放的環境。就“五四”時期新文學的發展而言,出現多種多樣的文學社團、文人派別,他們之間的論爭、制衡都為文學營造了一個良好的生存空間,各派以不同的思想相互碰撞,給后世學人呈現了那個時代絢麗的風采。
文學研究會與學衡派及南京高師師生等人的論爭,雖然就歷史的觀點看起來前者進步,后者保守,兩者對新文學的發展做出的貢獻多寡也是一目了然的,但其實這場論爭不論勝敗,都對現代文學建設起到了積極的作用。正因為他們各自發出了不同的聲音,才形成了不同文學團體之間的相互制衡、優劣互補的局面。若非如此,只有一種單一的聲音占領文學的話語權,則會顯得思想單一、審美單一、題材單一,缺乏文學應有的思想性和活力,因而各種流派之間的相互制衡才顯得如此重要。朱壽桐在其著作中談到了文學高度一致的情況下可能產生的問題:“一是發展缺乏參照……二是容易造成對一定文化資源的惡性開發。”*朱壽桐:《中國現代社團文學史》,第94頁。意思是說,如若一時代的文學只剩下獨門獨派,那么它發出的聲音即使再正確再美妙,缺乏了其他門派的砥礪,它也會逐步走向話語霸權,在自滿自得之中逐漸喪失自己的創造力。其次,由于缺乏其他派別的文學傾向作參照,這種單一的話語則只會按照自己的選擇對文學題材、體裁等進行篩選,即使是再豐饒的礦藏也經不起一而再再而三的開發,在這種惡性循環下,不得不生產出讓人啼笑皆非的作品,如“文革”時期的工農兵文學以及樣板戲。所以我們要承認,文學的健全發展,是離不開多社團、流派彼此之間的論爭和制衡的。
既然社團間的論爭客觀上是對整個新文學運動的發展有利的,那么,我們也應該這樣看待上世紀20年代發生在文學研究會與學衡派之間的這場論戰。在文學研究會成立的初期,舊文學雖已經在“五四”運動的沖擊下面臨巨大的挑戰,卻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仍占有著相當程度的文化市場,而新文學雖然方興未艾,但尚未進入文學中心場。不僅如此,它還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境況,一時間似乎無人反對也無人贊同,因而先驅們自導自演了“雙簧戲”,借以引起文學界的關注。所以文學研究會的產生,一是要鞏固新文學的地位,二則要籠絡新文學的同道者。希望克服中國向來有的“文人相輕”風氣,“結成一個文學中心的團體”*《文學研究會宣言》,《小說月報》第12卷第1號,1921年1月10日。,這種訴求是希望實現各種團體廣泛的聯合,但某種程度上講這種自定義的中心主義,有可能會逐漸消解各個團體的個性色彩。與此同時出現的南京高師和后來的學衡派等人,他們其實并未完全反對新文學運動,“素懷改良文學之志,且與胡適之君之意見多所符合。”*胡先骕:《中國文學改良論》(上),《中國新文學大系》(文學論爭集),第103頁。惟一不同的只是對新文學者們過度偏激的做法采取懷疑的態度。客觀上看,他們的保守也并非完全等同于落后,因而他們實為一種制衡的力量而非反動的力量。當我們在重看這段風氣云涌的歷史論爭時,更應采取一種兼容并包的態度,回到當時的歷史場景客觀地看待兩個社團,他們之間并不能簡單地說誰勝誰負、誰對誰錯。若非要說誰從中獲利,那就只能是有了健全發展空間的整個新文學運動了。
(責任編輯:畢光明)
A Complicated Legal Case between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Xueheng School
GAO Xiao-rui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Wen Xue Xun Kan (Ten-day Literary Review) is not only the official organ of 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and the position where the Association would voice its new literary views and crack down old literature but also the very place at which the Association and Xueheng School debated against each other. By scrutinizing Wen Xue Xun Kan (Ten-day Literary Review), the persistent debate, as is found, arose unexpectedly from a newspaper—“Poetic Study”—edited and published by higher normal college students in Nanjing at that time. By virtue of this phase of history, one can have some idea of the feud between the two literary schools and get an in-depth understanding of differences in the style of study between the northern part and the southern part in China as well as of the impact of such a debate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Cultural Movement.
Key words:Wen Xue Xun Kan (Ten-day Literary Review);the literary research association; Xueheng School; debates in literature
中圖分類號:I 206.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4-5310(2016)-03-0015-06
作者簡介:高曉瑞(1990-),女,四川自貢人,西南大學文學院2015級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
收稿日期:2015-11-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