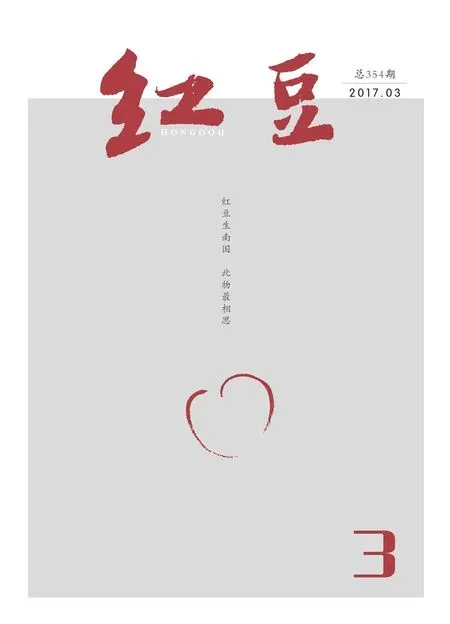味道課
敬一兵,男,學者兼作家。成都天恒仁文化傳媒主編。在《芳草》《延河》《創作與評論》《山東文學》《都市》《邊疆文學》《歲月》《散文選刊》等發表散文若干篇。在全國各類文學大獎賽上多次獲獎。現居四川成都。
味道是走在時間外面的詞匯,是需要用舌頭舔嘗的詞匯,也是味道課的核質和內容。
現在回想起來才發現,我的少年時代是由不同課程串聯起來的一根時間鏈條。
密密麻麻擁擠在一起的房屋和潮水一樣涌向學校的學生,不僅讓這根時間鏈條顯得狹窄有一種婉蜒不知所終的遙遠錯覺,而且還讓我上課的很多情形,連同課本和作業本一道,丟棄在了我走過的時間鏈條上。反而是我在學校以外的地方,比如蒼蠅館子或者糕點鋪上過的味道課,現在還像鮮花那樣綻放在記憶中,鮮明而又生動,和我一起守候著食物的原生味道,以及由味道放大了我少年時代雜食動物的屬性和細節。
臭豆腐是我少年時代雜食動物屬性和細節的主角。
它聞著臭吃著香的奇妙味道,如同荊棘上長出來的倒鉤刺,總是會把我的好奇心、貪吃欲望乃至整個少年時代的夢想牢牢鉤住,不會隨著時過境遷斗轉星移而放松。少年的夢在倒鉤刺上凝固,與臭豆腐相關的記憶場景也在凝固。
像落在棉紙上的水滴悄無聲息向四周浸滲開來一樣,臭豆腐的奇妙味道,成了我走進夢里和過世親人相聚的道路,也成了我和飛逝而去的少年時代重逢的場所。
1970年是我外婆去世一周年的代詞。母親知道這個代詞意味著有許多祭祀活動,等著她千里迢迢趕回老家去參加。但我卻不知道,也有一個味道的倒鉤刺,悄無聲息等在1970年的時間位置上,準備鉤住我的靈魂。
客路青山外,行舟綠水前。趕赴老家的遷徙路途中,母親像毛毛蟲一樣用自己纖弱渺小的肉體丈量著外婆之前走過無數次的道路,還要不斷分出注意力來購買食物滿足我的味蕾需要。看見我的貪婪吃相,母親就會說我的嘴巴是一個無底洞,什么死貓爛耗子的東西都要往里面塞,一點也不像外婆,一塊臭豆腐就成了她一生情有獨鐘的食物味道。
這是我第一次從母親的話語中聽見了臭豆腐這個食物名字。
母親引領我來到了舅舅家里。舅舅一直是和外婆住在一起的。外婆走后,她在小山丘腳下修建的房屋成了舅舅的家。外婆做臭豆腐的工具,零亂地堆放在院墻角邊,上面蒙上了厚厚一層灰。母親給我說這是外婆的心肝寶貝,舅舅不做豆腐但也不敢把這些工具扔掉,害怕外婆的靈魂回來看見工具不在了,會有厄運降臨到他頭上。
夕陽的紅銅色光線,照在屋外架欄上的絲瓜葉、扁豆角和靜悄悄站在墻邊的梨樹上,也照在了堂屋里我的背脊上,還有供奉了外婆靈牌和遺像的神臺上。各種各樣的菜肴端上了飯桌,香噴噴的味道把我的口水都勾引出來了。肚子早就餓扁了的我,卻還不能先吃飯,而是要等舅舅把盛放有臭豆腐的盤子擺上神臺,讓我向外婆的遺像跪拜、叩頭、獻祭和上香后才能動筷子。
親戚和朋友席間說的那些地里缺水了,墳草又長高了,母豬下崽了的話語,我一句都沒有聽進去。對于一個懵懵懂懂的少年來說,所有親戚和朋友都是屬于我母親的,只有臭豆腐才真正屬于我的。
母親發現我直勾勾盯著神臺上的臭豆腐后說,那是外婆最喜歡吃的菜,你不能夠搶外婆吃的菜,知道嗎?舅舅用責怪的眼睛看了一眼我母親后,立即起身走進灶房,不一會兒就端來了一小碗清蒸臭豆腐讓我吃。
小碗里的臭豆腐是乳黃色的,不像我吃過的豆腐是白色的。漂在湯里的油珠子類似透明的小蝌蚪。我的筷子一攪動,它們便如影隨形跟在筷子后面游弋。在我的眼睛里,小碗成了一個童話世界,油珠子成了小精靈,筷子則是它們在碗里守候了很久的魔法師。
我如癡如呆陶醉在幻覺里,舅舅問我是不是嫌臭不想吃的時候,我才從小碗里騰騰冒出來的蒸汽里,聞到了一股腐敗變質般的臭味。我以為豆腐壞了,是舅舅故意用壞了的豆腐來懲罰我的貪嘴行為,所以猶豫著不敢吃它。舅舅似乎明白了我猶豫的原因,對我說你不吃呀,不吃我來把它全吃了!一邊說著,一邊動筷子捻起一塊豆腐放進他嘴巴里,還故意發出嘖嘖的聲音。他的聲音是飄飛的蠱,終于禁不住從舅舅嘴巴里傳來的誘惑聲,我也往嘴里送進了一塊臭豆腐。真是奇怪了,聞著很臭的豆腐,吃進嘴里卻是清香的,細嫩滑爽,簡直跟我吃過的豬腦花的感覺是一樣的。
好吃嗎?好吃!一問一答間臭豆腐全都被我吃完了。
臭豆腐清香的味道在我的嘴巴里四下漫漶,也隨了我的目光四下漫漶。我看我的母親、舅舅和其他親戚,我就覺得他們都浸潤在了清香的味道中,類似開在明媚陽光下的杜鵑花,無論是色澤還是線條都淋漓盡致地袒露出了展眼舒眉的樣子。甚至就連整間堂屋,也有了臭豆腐那種豆質的柔和、婉約與幽古的元素。
上清下濁成天地,清濁相凝便作人。看見堂屋里的人展眼舒眉的樣子與柔和、婉約與幽古的氛圍,我想起了父母時常掛在嘴上的這句話。
大概是從小就受到父母的影響,仗劍逡巡的武俠從來沒有燃起過我沖動的小火焰。反倒是像陶淵明和林逋這類文人隱士的身影,一直在我的心里草長鶯飛。如果不是母親的催促和飯桌上豐盛菜肴岔開了我的注意力,我想我那個時候旁逸斜出的直覺,極有可能引領我將陶淵明和林逋斜戴斗笠的身影,從流連于山水花竹之間獨享其樂與世無爭的隱居生活中抽離出來,發現他們就是一團飄逸的、肉質的臭豆腐味道。
見我對臭豆腐沒有表現出拒絕的情形,舅舅感到十分高興。舅舅不說我還不知道,臭豆腐在他的心中一直就是一面鑒別情感的鏡子。舅舅在這面鏡子里看見了我對臭豆腐持有親近態度的模樣,便認為是外婆的秉性,通過臭豆腐在我的身上得到了傳承和鋪排。
對于舅舅這種近乎神秘的鑒別方式,依我當時的年齡自然無法理解。我只能夠憑直覺發現,外婆、舅舅和我都喜歡吃臭豆腐,所以我們是站在臭豆腐這一邊的。母親不喜歡吃,所以她就站在了臭豆腐的另外一邊,和我們對峙著。
我不可能怨恨自己少年時代的懵懂無知,那是一個自然的生長規律。我只是十分遺憾當時沒有追問舅舅是怎樣想到了把臭豆腐當成鑒別情感的鏡子這個令我十分好奇的問題。倘若我早點追問,我就會早點知道,臭豆腐與其說是食物,還不如確切說成是一座橋梁和一件信物的事實。
花無品第味無貴賤。高下之別或者喜好與否,全憑個人的情感左右。喜歡臭豆腐味道的人,撇開口腹之欲的意義外,大多具有喜歡臭豆腐外陋內秀、聞著臭吃著香這類平中見奇的性質。他們把臭豆腐的這些性質,當成了他們自己為人處世的座右銘。然后又把座右銘當成信物,從喧囂躁動五味雜陳的現實中走出來,踏上架設在今天和清朝康熙年間的臭豆腐橋梁,去尋找隱遁在歷史中的知音。
胡馬依北風,越鳥巢南枝。所謂知音,很大程度上便是懷念的極致和共鳴感。母親不吃臭豆腐,舅舅認為是母親吃多了厭煩了臭豆腐。舅舅始終覺得我母親是一個很容易對人對事厭煩的人,沒有仕女圖中那些彈琴者個個焚香對月的虔誠、耐心和矜持。舅舅并不知道,臭豆腐是我母親心中的一個遁詞。
母親見我在臭豆腐問題上對她表現出了錯愕與驚訝的神情,告訴我說她不吃臭豆腐,并不是不喜歡臭豆腐,而是臭豆腐會觸及到她刻骨銘心的疼痛記憶。
母親的少年時代不是在學堂里度過的,而是從跟著我外婆一起給地主家磨豆腐的日子里熬過來的。如果說日子是一條路,那么我母親少年時代走過的路,就是一條味道的路。路的末端,通向了至高無上的母愛真味。
外婆每天都要帶著我母親,把當天磨出來的豆腐拿到集鎮上去賣。通向集鎮的路雨天泥濘溜滑,晴天塵土飛揚,一點不像外婆心里的那條臭豆腐的道路,沒有四伏的危機讓人擔憂。那個時候外婆最大的擔憂就是害怕地主懷疑她私下把豆腐拿回家中。豆腐的數量地主是知道的,價格也是由他規定的。賣不完的豆腐,都必須拿回去讓地主過目。
這樣一來,就有一些賣剩的豆腐,因為放置的時間久了,生出濃密的灰白色細絨毛一樣的東西(后來我才知道,這細絨毛一樣的東西叫霉菌),并散發出一陣陣臭味(霉菌發酵的結果)。生霉發臭的豆腐地主不要了,才會讓外婆把這些發霉變臭的豆腐拿出去丟掉。外婆一生清貧,當然舍不得丟掉發臭的豆腐,而是借機讓我的母親偷偷把這些豆腐拿回家里留著她們自己吃。
我母親最初面對這樣的豆腐表現出了懷疑的神情。外婆當時也像舅舅對我一樣,一句話不說,把那些豆腐放鍋里蒸熟后,撒上一點鹽巴和蔥花,一邊吃,一邊從嘴里發出嘖嘖的聲音。外婆無聲的示范,讓我母親明白了這東西是可以吃的,并且她吃后也和我一樣覺得這東西好吃。
小雨潤物細無聲。臭豆腐的味道滑過我母親的舌頭進入她身體的過程,好像就是母親與臭豆腐簽下了一份心靈契約的過程。從此,母親和臭豆腐成了無須說的知音。
難怪我做作業不專心鬼畫桃符的時候,母親總是要用吃東西的比喻來教育我說,青菜蘿卜的味道和雞鴨魚肉的味道一樣都是十分鮮美的。認認真真細嚼慢咽后,都會嘗出令人陶醉的真正滋味。原來,這些感受都是緣于母親兒時對臭豆腐的鐘愛與親近。
母親之前從來不給我說臭豆腐的事情。仿佛臭豆腐已經在母親茫茫蕩漾著的記憶中,變成了飄飛的吉光片羽難以捕獲。然而,一旦母親在回憶中捕獲到了它們,母親的述說就會滔滔不絕。
母親說外婆讓她偷偷拿回家的臭豆腐有多有少。多的時候,晚上回家外婆就會把豆腐擠得扁扁的,然后一層一層整整齊齊碼放在潮濕的布上,那濕布上事先已密密實實鋪了一層稻稈,放完以后上面鋪上一層厚厚的稻稈,再用濕布包裹好就可以放上好幾天。外婆做這些活路的時候,總是嘮叨說這既是臭豆腐的保存方法,也是臭豆腐的制作方法。我母親從外婆做事細致的態度上,慢慢領悟出了她的行為,其實就是精心與精致的象征。
外婆總是把積攢下來的臭豆腐,送給和她同樣清貧的左右鄰舍。母親記得有天晚上她跟了外婆去給別人送臭豆腐,不知道從何處突然躥出一條野狗對著她們狂吠不止。我母親越是害怕,那野狗越是猖狂,一下子就朝我母親撲來。在這緊急關頭,是外婆挺身擋在了母親的前面,才讓我的母親躲過了一場災難。
事情的真相終于在我面前水落石出——母親聞到臭豆腐的味道,就會覺得那是外婆穿過臭豆腐的味道,從另外一個遙遠世界向她伸出來的一只手。和這只手相握,母親不僅能夠體會到外婆的溫暖,還會不由自主感傷外婆一生的清苦和悲哀。
母親回避臭豆腐的行為,并不是如我理解的那樣站在了外婆的對立面上。恰恰相反,這是母親敬畏臭豆腐,而敬畏臭豆腐就是敬畏我的外婆,還有屬于外婆生活環境里的黃豆和供黃豆生長所需的陽光、氣候、地氣和雨露的一種深刻表現。在我母親的眼睛里,臭豆腐的味道和讓她感到溫暖與傷感的元素,都是外婆的情感經歷和安貧樂道守真的品性,沿循臭豆腐的道路,在母親的記憶秩序上暗暗鋪排的結果。
味道的鋪排與平坦地勢上的河流一樣,都是一種緩慢的流淌過程。
舅舅和我母親的處境不同,包括地理位置、生活方式特別是勞動性質不同所形成的身份差異。這些不同之處導致了外婆一如安貧樂道守真的品性涓流,在路經舅舅這段身體上的河床時,要么因了舅舅的懈怠或者漠視沒有形成堰塘讓味道涓流停頓片刻,要么因了他的固執或者主觀臆斷上的偏頗形成的鵝卵石,對涓流造成了阻擋。
差異是一種對峙,區別和界限。它的一個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差別達到不可調和的地步時,就會產生分道揚鑣的結果。情形就像河床里越堆越高的亂石灘,最終導致一條河水分岔成了兩條支流。
我現在都還記得,在舅舅家吃完晚飯后我就睡著了。天麻麻亮的時候,我才被一些響動聲驚醒,發現自己已經從堂屋的凳子上,轉移到了床上。堂屋里只剩下舅舅和我母親在準備上墳的事情。舅舅見我揉了眼睛坐在床上,趕緊興奮地跑過來,問我在夢里聽見外婆說了什么話。我說我沒有做夢。舅舅聽我這樣回答,有些失望。
在舅舅和他周圍上了年紀的那些人的印象里,一個孩子如果在神臺邊睡著了,一定是祖先在顯靈,然后向這個孩子傳遞祖先的某種意圖或者心愿。舅舅一直認為,祖先就住在神臺上的靈牌里,而不是住在墳墓里,并且祖先一般是不會和大人們說話的,只和他們的孩子說話。他把臭豆腐擺放在外婆的靈牌面前,就是希望外婆在吃臭豆腐的時候,一不留神就說出了她走之前還沒有說完的話。
當時我只是覺得舅舅的這些舉動很好玩。等我明白舅舅懷疑他和我母親在地位上、身份上和經濟上的差異,都是因為外婆有些話只給我母親說了而沒有給他說的結果造成的,從而在內心里對外婆對我母親耿耿于懷的緣由時,我已經走進了大學的課堂。
舅舅仗著自己在村子里比別人腦袋更靈光的特點,先是在下海經商的那個年代里組建了一支建筑包工隊。因為他們不懂技術又沒有工程墊支的本錢,在老家折騰了幾年都沒有起色。后來跨越千山萬水跑到我母親居住的城市來求我父母利用關系給他們找點活路干,最終還是不了了之草草收場。
舅舅畢竟是一個腦袋靈光的人,不甘心失敗也無顏見江東父老,于是改行做起了餐飲生意。
開初一段時間他的餐飲生意還是比較火紅的,特別是油炸臭豆腐這道菜很受食客歡迎。可是好景不長,鈔票如同一個嫵媚妖嬈的女人鉤走了他的魂。情多志難堅定。他選擇了鈔票放棄了臭豆腐的味道。他親手用臭豆腐壘起來的味道風景線,因他以次充好和投機取巧使用地溝油煎炸臭豆腐,而以次充好和使用地溝油就是對臭豆腐味道的背叛,終于像天塌下來一般轟然崩潰在了他的面前。他的餐館門可羅雀都不說了,關鍵是被衛生防疫部門查出他使用了地溝油,重罰之下他只有卷了鋪蓋走人。
有了靈光的腦袋還要打錯算盤,雖然不至于罪不可赦,但他在鈔票和臭豆腐的味道面前做出厚此薄彼的選擇情形,褻瀆了外婆安貧樂道守真的品性,親手在他和外婆、臭豆腐之間劃上了一條對峙的界限。
臭豆腐是舅舅曾經握在手里的一把金鑰匙。他知道這把鑰匙可以為他開啟一扇財富的大門,但卻不知道財富的大門開啟的同時,另外一扇隱形的災難之門也被悄悄打開了。形影相隨的情形,如同輕煙漫入輕煙之中。
被我嗅覺拒絕的臭味和讓我在咀嚼間味覺產生出清香滋味這兩個極端情形,都似一曲無聲的歌謠在我的口腔里縈繞、跌宕和徘徊,又在臭豆腐中或者我的腸胃里悄然隱遁。它們把我的嘴巴當成了互通款曲的地方。吃一塊臭豆腐,便可知“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這句話的精心與精致的來由。
或許正是因了香與臭的味道如此精心與精致地互通款曲,臭豆腐才以另外一種形式進入了外婆的心靈世界。從外婆精心制作臭豆腐,還有小心翼翼用潮濕的布和稻稈包裹儲存臭豆腐的舉動中,都能夠看出臭豆腐進入她心靈世界的痕跡和她對臭豆腐的虔誠心情。
香與臭的味道傾軋糾結在臭豆腐身上,在性質上屬于物質的一種自然回歸。外婆一生安貧樂道守真的品性,則是她在精神上的一種自然回歸,也是臭豆腐的味道在她身上的一種精心與精致的泛化。清香雋永,令人流連。不難想象,外婆因為心中一直有臭豆腐的味道在縈繞,身心自然而然被賦予了君子氣質高雅的神形,比之她周圍的農婦和我的舅舅,顯然多出了出塵的味道。
不曉得外婆在臭豆腐的味道中,是不是已經用懷念的方式,回歸到了她早已逝去了的童年時光里,是不是又一次帶著純樸的笑臉一頭撲進了她父母的懷抱中?
臭豆腐讓外婆回歸了自然。在外婆的墳頭上我磕一次頭,這個印象就會深刻一次。
“味道”這兩個字看似具有遠水縈紆而至和云繄縈繞的飄逸感,實際上味道的飄逸感,都是從長期的蟄伏中蘇醒后的表現形式。它看不見摸不著的詭異縱深度,就是一個證明。
不僅如此,味道詭異的縱深度還仿佛潛伏在草叢中的蛇,隨時都有可能冷不丁地用自己柔軟的身體,纏繞在圖謀不軌者的脖子上,將其篡改味道本真的企圖降服或者徹底扼殺。
舅舅用地溝油來煎炸臭豆腐,不僅觸犯了花下不宜焚香,猶茶中不宜置果,否則味奪香損的大忌,還讓原本天然的臭豆腐滋生了江湖味道,所以他成了被臭豆腐味道的詭異縱深度,徹底降服在了他發財路上的一個人。
精心與精致的鋪排過程,讓舅舅覺得有臭豆腐的地方就有臭腐神奇的靈氣,就可以由他恣意調遣和指揮。舅舅把外婆的精心與精致,投放在地溝油中油炸,把臭豆腐的性質變成了聞著香吃著臭的味道,也把自己變成了與外婆背道而馳的人。與外婆背道而馳,其實就是與臭豆腐的味道背道而馳。
看幾番神奇臭腐,夏裘冬葛。
臭豆腐的味道,還有地溝油,成了整治我舅舅的刑具。
如今舅舅是怎樣一個情形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
臭腐神奇。這是舅舅給我上的最為生動的一堂味道課。
責任編輯 盧悅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