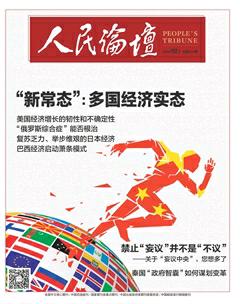學者掛職緣何仍是“鳳毛麟角”
毛壽龍+李梅
【摘要】學術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學者在政府部門掛職的最大的阻力。學者去政府部門掛職,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學者當作官員來使用。如果把學者當作擁有特定知識的人,那么學者掛職的通道就會多了一些,政府也可以系統地利用學者的知識。
【關鍵詞】專家學者 掛職 智囊
【中圖分類號】D62 【文獻標識碼】A
在北京市政府部門和市屬國有企業掛職的八名在京高校學者,在掛職期間擔任副局級領導職務,主要負責協助分管某項工作,同時可以參加局長辦公會等同等級行政和領導班子會議,參與重大事項、重要工作的討論和決策,參加重要的會議、調研活動等。從這可以看出,他們起的作用基本上是智囊的作用。兩年前,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姚輝等六名專家學者以交流掛職的形式,擔任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長等副廳級崗位職務。他們到最高法院掛職,主要是參加司法解釋起草、重大疑難案件研討等活動。他們做的工作是實質性的工作,并不是協助作用。
學者到政府部門掛職,是一個成本少、收獲多,政府和學者都能夠雙贏的舉措
高校學者到政府實際部門掛職,其目的是要培養卓越人才。也就是說,讓學者能夠理論聯系實際,不斷豐富和完善學者的理論。對于學者來說,這的確是很難得的機會。從方法論上來說,這個屬于參與式調查,是全方位的,沒有任何預先設計的調研,而且一去就是一年、兩年,還從事實際的工作,這種方法傳統上是人類學才用的方法。這種調研,對于學者來說,是非常寶貴的機會,對學術的進步,應該說是全方位的。尤其重要的是,對于學者自身的成長也是非常寶貴的機會。
對于政府實際部門來說,專家學者也是非常重要的資源。一般來說,政府部門習慣于從管理的方便和效率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其結果是,很多公共性的改革,都很難推進,或者即使從法律上規定了,但實際上會遇到很多具體的阻礙。學者對于具體管理可能接觸不多,但對于很多政府管理問題的公共性方面、價值方面,具有豐富的知識和體會。這些知識,政府官員雖可以去高校聽老師講課,但把學者請到政府部門,隨時求教、指點,可以讓政府部門隨時了解到學者的看法,從而更好地把握這些方面的問題,避免決策失誤。
所以,學者到政府部門掛職,實際上是一個成本少、收獲多,政府和學者都能夠雙贏的舉措,值得進一步開拓。從目前信息來看,學者到政府部門掛職,不是多了,而是少了。現在見諸報端的也就是這些學者,而且一般還局限于高校里學科帶頭人。偶爾也有年輕學者到基層掛職的消息,但總體上來說,不論規模還是數量,還是太少,但此舉值得進一步推廣。
這應該是比較積極的評價,現在見諸報端的評價,基本上對掛職學者和政府部門的評價也是積極的。媒體上比較消極的評價是,學者進入政府部門后,可能會喪失獨立性。因為學者過去對實際部門很不了解,學的東西很多都是書本上的,一旦進入政府部門了解了很多東西后,尤其是看到了過去看不到的好東西,首先就先想著自己如何學習、如何吸收、如何消化,反而感覺到自己過去很多東西都是書生氣的看法,結果學者在官場耳濡目染一兩年后,逐步變得像政府官員,從而失去了學者的本色。
學者、官員處于不同的秩序,不要把學者當作官員來使用
這樣說來,學者去政府部門掛職,顯然是一個好事情,但是為什么新中國成立67年了,改革開放38年了,學者掛職政府部門的事情還是鳳毛麟角,而不是較為普通的事情呢?這里有非常多的原因。從某個意義上來說,這和學者、官員處于不同的秩序有很大的關系。
從學者角度來說,其職業是科研和教書。這是一個非常扁平化的結構。雖然學者有教授、副教授、講師、助教的身份等級差異,但是他們都直接面向學生。不同等級的學者,只是一個職稱的差異,學校管理上的行政化對學者沒有多大的影響。所以,學者所處的秩序,是一個比較松軟的等級秩序,這種等級相互之間的位差不大,而且還經常受到各種因素的沖擊。很多學者在學校里是普通教授,但在學校外面卻是呼風喚雨的大牌學者。更重要的是,隨著科研教育事業的發展,其身份和等級的數量是擴展性的,而不是有嚴格的數量控制。很多高校,教授、副教授、講師的數量基本上是差不多的,甚至年輕的講師還要少一些,整個學校與其說是一個金字塔結構,不如說是眾多的金字塔結構。
從官員的角度來說,其職業是行政管理和公共服務。作為一個大國來說,官員的金字塔結構,以及等級身份的嚴謹性,遠遠勝于學術領域。每一個實體性政府,比如鎮政府、市政府、省政府,都是一個個的金字塔,而全國更是一個巨大的金字塔,每一個官員都可以在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
從管理上來說,學者過去教授是副廳級以上級別待遇,現在基本上降低為處級、乃至副處級以上級別待遇,副教授、講師,級別待遇依次下降。在學校里,學校一般是司局級、個別校長書記高配副部待遇不帶級,直接管理學者的學院一般是處級級別。所以,從管理上來說,教授要在處級以下,否則學院怎么管理?但是,從高校對于兼職教授的聘請角度來說,一些著名高校,要聘請一個合格的兼職教授,不成文的規定是,必須是副部級以上才考慮,司局級基本不考慮,處級連門都沒有。從這個角度來說,教授如果反過來去政府部門掛職,應該掛副部級是比較合適的。不過,從目前的實踐來看,教授幾乎沒有去政府部門直接掛職副部級的,而是副司局級。這和過去計劃經濟時期的級別是一樣的。
但是,學者的學問是沒有級別的。很多學者研究國家級的問題,如果要掛職,給總理當顧問可能比較合適。如果研究的是社區管理的問題,那就給業委會主任當顧問比較合適。顯然,這兩種掛職都不會發生。因此學者在中國干部管理等級體系里,副司局級是一個比較合理的定位。但是,在這個位置上,學者所研究的學問,可能只占很少的比例。更何況,副司局級這個崗位,在官僚體系里面本來就非常少,除非這個崗位增加編制,否則有可能擋住政府部門內部很多官員的升遷道路。一個學者待一年、兩年,對學者來說有學問上的好處,但對很多等著要升遷的官員來說,卻可能永遠失去了升遷的機會。這對于政府部門來說是代價巨大的,因為很可能導致這個官員喪失工作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政府部門永遠失去了一個可以長期任職的副司局級官員,乃至因為年齡原因,更可能是失去了一個高級官員。
所以,學術秩序和政府秩序的不匹配,可能是學者在政府部門掛職的最大的阻力。現在很多學者雖然沒有掛職的經歷,但有很多給政府官員講課和給政府部門做科研的經歷,也有很多去政府部門調研、咨詢的經歷。這種經歷,給學者的感覺是,自己的級別實際上是和自己接觸的政府部門的級別有關系。因此,學者去政府部門掛職,是好事,但最好不要把學者當作官員來使用。學者職稱可能是有級別的,但其學問是沒有級別的。如果把教授確定為副司局級,掛職的通道就會變得非常小,學者就失去了很多掛職的機會,高級別政府或者低級別政府也失去了很多利用學者知識的機會;如果把教授確定為擁有特定知識的人,那么學者掛職的通道就多了好多,政府也就可以系統地利用學者的知識。
(作者分別為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財政與公共政策研究所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參考文獻】
① 《清華北大8名黨外高知到北京政府部門掛職“廳官”》,人民網,2014年12月15日。
責編/高驪 申唯佳(見習)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