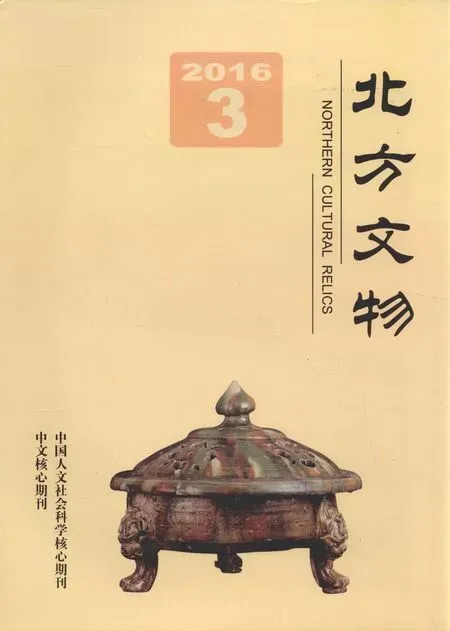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發掘的主要收獲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發掘的主要收獲
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七三一部隊舊址 細菌實驗室 特設監獄 “四方樓”考古
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 俗稱 “四方樓”) 是七三一部隊舊址中最為核心的要害部門,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可以在相當程度上尋找出七三一部隊直接的犯罪證據和毀滅犯罪事實的證據,同時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與施工工藝,為研究日偽時期建筑特點提供第一手資料。“四方樓”發掘,是首次按照考古工作規程對七三一舊址進行的科學揭露,揭開了七三一部隊舊址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嶄新的一頁。在發掘中,對各種遺跡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文字、繪圖、測量、照相、錄像記錄,為今后室內資料整理、報告編寫乃至研究、保護、復原、展示等,提供了詳盡的科學依據。爆破穴點和焚燒灰坑的發現,是日本侵略者毀滅犯罪證據的直接證據,是不可多得的無可爭辯的第一手例證。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下文簡稱“七三一部隊”)總部舊址,位于黑龍江省哈爾濱市平房區新疆大街47號,北距市中心16.8公里,地理坐標北緯45°35′,東經126°40′。其是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期間及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細菌戰遺跡;是以戰爭為目的進行細菌武器研究、實驗和制造的大本營,以危害人類和自然為代價發動細菌戰爭的策源地。
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 俗稱 “四方樓”) 位于七三一部隊舊址核心區南部中央,方向為北偏西 9°53′23″。南距本部大樓71米,北距病毒研究室35米,東距鍋爐房77米,西距野口班15米(圖一)。
一
平房屯清代稱“義和屯”,隸屬于阿勒楚喀副都統。1933年,日本關東軍修筑拉濱鐵路,在平房屯附近設置“平房站”。1936年春季,“東鄉部隊” (對外稱“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突然設營駐扎,并大興土木,“四方樓”應始建于當年。
“關東軍防疫給水部”的營建,是一項極為機密的工程,被稱為“特殊工業”,因此只能由日本關東軍御用的建設株式會社設計與施工。當時兼任關東軍司令部軍醫部部長的石井四郎在長春進行了招標,最后決定由4個建設株式會社承建。1938年平房細菌基地基本竣工,1940年工程結束。由此這里不但成為關東軍首屈一指的軍事重鎮,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細菌實驗基地。如果說七三一部隊本部大樓是其指揮策劃中心的話,那么“四方樓”就是其細菌實驗和罪行實施的最為核心抑或要害場所;從罪證角度講,后者較前者顯然更為重要。也正因如此,當1945年8月七三一部隊潰逃時,動用工兵部隊炸毀的建筑物中,首當其沖的就是“四方樓”。通過對該遺址的發掘與研究,不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尋找出七三一部隊直接的犯罪證據和毀滅犯罪事實的證據,同時亦可以搞清其建筑格局與施工工藝,為研究日偽時期建筑特點提供第一手資料。因此,在對七三一部隊舊址的系列發掘中,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的揭露乃首選。

圖一 七三一部隊本部核心區“四方樓”位置圖 1.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 2.本部大樓 3.病毒實驗室 4.動力班鍋爐房 5.野口班 6.特殊武器制造廠 7.瓦斯發生室 8.地下瓦斯儲藏室 9.航空班
盡管當年“四方樓”被日軍嚴重炸毀,但從歷史照片上觀察,其廢墟地面以上的殘垣斷壁仍清晰可辨。歷經70年的滄桑,如今“四方樓”廢墟的地上部分已蕩然無存,地下基礎部分亦受到不同程度的損毀。“四方樓”現有地面的一部分系2000年挖掘后回填平整所致,上面移植了草坪;其北半大部被后來所建工廠的水泥地面覆蓋;在遺址中部偏西留有一條長約80、寬約40、深約2.5~3米的探溝,第7棟基礎大部裸露;另東北角與東南角及第3棟中央亦暴露在外。揭開地表后發現,遺址基本上被建筑垃圾所覆蓋,其中主要是現代磚頭瓦塊與原有各種建筑構件,間雜白瓷片和玻璃容器碎片等,平均厚度1米多,部分達2米以上。位于第3棟的現代工廠的大煙囪直接坐落在原有錐形基礎構件上;個別新的混凝土建筑構件長約30多米,重達幾十噸;第6棟南部的基礎被現代上水管道破壞殆盡。
在黑龍江省文化廳的統一指導下,2013年10月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等編制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保護規劃》,據此,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與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共同編制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考古工作規劃》,隨后相繼制定了《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2014—2015年度考古調查、勘探、發掘計劃》和《2014—2015年度七三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考古工作實施方案》。2014—2015年度計劃完成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中心走廊、鍋爐房及回水池、動物焚尸爐和細菌彈殼廠6處遺址的調查勘探與發掘。
2014年3—5月,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多次對七三一部隊相關遺址進行了實地考察。此次發掘前,在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西南角外60米處埋設了“七三一部隊舊址永久性坐標基點”,采用象限法布10×10米探方,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遺址位于第一象限內。
國家文物局對七三一部隊舊址的發掘保護和展示極為關注,局領導曾親臨現場部署指導。黑龍江省文化廳和哈爾濱市平房區政府亦非常重視,專門成立了發掘領導機構,并指派富有經驗的考古專家擔任現場領隊。
在黑龍江省文化廳和哈爾濱市平房區政府的直接領導下,2014年5—11月,由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領銜,會同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罪證陳列館、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學院、東北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對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基址進行了全面揭露。
二
“四方樓”實際呈長方形,地下基礎東西長151.4米,南北寬101.3米,總占地面積15336.82平方米;以地上外墻計算,東西長150.14米,南北寬100.02米,約總占地面積15017平方米。由細菌實驗室、特設監獄、中央走廊及四個庭院構成 (圖版四,1) 。
(一) 細菌實驗室
細菌實驗室為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進行細菌研究、生產、儲藏的主要場所。其主體為四周合圍封閉式的長方形平頂磚混三層樓房,分為四棟,其南側稱為第3棟,順時針西側為第4棟,北側為第5棟,東側為第6棟。
現存細菌實驗室已完全不見地上建筑,最高處僅為第6棟殘存的約2平方米的當時一層地面,因此本次發掘揭露的遺跡全部為地下基礎部分。建筑基礎部分可歸類為三種: 柱下獨立基礎、柱下聯合基礎和墻下條形基礎。柱下獨立基礎和柱下聯合基礎具體形式均為鋼筋混凝土錐臺式擴展基礎,但放坡形式存在差異,前者為四面放坡形式,后者為兩面放坡形式。墻下條形基礎由兩部分組成: 墻下鋼筋混凝土條形基礎和墻下磚砌條形基礎。為滿足承載力的需求,減小基礎不均勻沉降等原因,本建筑墻下條形基礎形式為鋼筋混凝土地板上采用磚砌放大腳。放大腳形式為: 基礎底面比墻體寬,呈階梯形逐級收分。
第3棟與第5棟平行,長度跨度相對較大,格局基本一致,采用雙排柱內框架式結構,即中間走廊兩側房間;第4棟與第6棟平行,長度跨度相對較小,格局基本一致,采用單廊磚混結構。據記載,當時環繞細菌實驗室一樓走廊鋪設窄幅鐵軌以運輸重要實驗設備。
據發掘得知,第3棟與第5棟的中央部分,為相對獨立的不同形制的中心建筑,前者南半為方形,北半向外伸出,端部呈半圓形;后者大體呈方形。
經實測,細菌實驗室占地面積(包括第3棟和第5棟的中心建筑)為6393.4平方米。
1.第3棟基址
第3棟位于“四方樓”南側,分為主體建筑和中心建筑兩部分。主體建筑東西橫向,與北側的第5棟平行對應,兩端與第4棟和第6棟南部連接,東西長151.29米,南北跨度15.3米。其平面布局:中間設走廊,兩側為房間,另南北兩側置地溝間。
中心建筑南北縱向,分為南北兩個部分,南半部略為方形,基本與第3棟重合;北半部略窄向外凸出,端部呈半圓形,整體風格與主體建筑相異。南北通長31.3米,南半部東西寬18米,北半部東西寬15.1米(含中心走廊寬度),面積539.6平方米。以中央走廊為中心,將中心建筑一分為二,即東半部與西半部,兩部分格局大體一致,均被東西走向的寬約1.5米或2米的條形基礎及墻體分割成大小不一的空間。
2.第4棟基址
第4棟是細菌實驗室西側建筑,南北走向,與東側的第6棟平行對應,其南與第3棟、北與第5棟相連,中央東西向通道與第7棟相通。南北長70.9米,東西跨度10.3米。
第4棟與第3棟的建筑格局明顯不同,為一側房間,另側走廊。
3.第5棟基址
第5棟位于“四方樓”北側,基礎部分保存程度相對較好,建筑格局與第3棟大體一致。主體部分東西走向,與第3棟平行對應,兩端南部與第4棟和第6棟連接,東西長151.31米,南北跨度15.3米。
與第3棟一樣,第5棟亦有中心建筑,但形制與規模上有別。第5棟中心建筑略呈方形,南北16.8米,東西18米,北部凸出于主體建筑1.5米。
4.第6棟基址
第6棟是細菌實驗室西側建筑,南北走向,與西側的第4棟平行對應,其南與第3棟、北與第5棟相連,中央東西向通道與第8棟相通。南北長70.7米,東西跨度10.3米。
第6棟與第3棟和第5棟的建筑格局明顯不同,而與第4棟基本一致,即一側房間,另側走廊。
(二) 特設監獄
特設監獄即第7棟和第8棟,系關押經“特別移送”,作為“實驗材料”的人的秘密場所。分別橫置于(東西走向,與第3棟和第5棟平行)細菌實驗室合圍之西部和東部正中。據歷史文獻和照片,特設監獄的地上部分為長方形坡頂磚混二層樓房。經發掘得知,其地下部分有中心通道,一側與中心走廊連接,另側分別與第4棟和第6棟相通。
第7棟東西長46.37米,南北跨度為14.5米;第8棟東西長46.33米,南北跨度為14.5米。根據其地下基礎結構,推測地上二層的建筑結構應為中心設置走廊,兩側為大小不一的房間(牢房)。
在第7棟的西北角和第8棟的東北角分別設置有長方形特殊設備間,其墻體具有防水防潮功能;另兩棟的北外側分別設置有分流井。
(三) 中央走廊及地下通道
中央走廊是南北貫穿本部大樓、細菌實驗室和病毒實驗室的主要通道,長度約260余米(因病毒實驗室尚未揭露,無法精確其北所及),寬度2.75米(根據現存南段地上兩層實測)。分為南、中、北三段: 南段為本部大樓至“四方樓”,地上兩層,地下一層;中段即與“四方樓”重合部分,為平頂磚混結構,地上三層,地下一層,將“四方樓”隔離成東西兩部分;北段為 “四方樓”至病毒實驗室,地上地下各一層。
1945年8月,日軍敗退時將“四方樓”炸毀,中心走廊雖亦難于幸免,但殘存情況相對稍好。從20世紀50年代的影像資料中,可以較為清晰地看出中心走廊南段大部分尚存。中段北側殘留約70余米,是為平頂三層,頂上東西兩邊各有一條高約0.6~0.8米的低矮護墻;其北端有一高出平頂的二層碉樓,據歷史照片比對,其南端亦有一相同形式之碉樓,兩座碉樓相互對應,居高臨下,是為細菌實驗室及其特設監獄的制高點;從側面外墻觀察,二層和三層每隔10米左右有一個窗口。如今中心走廊中段及北段的地上部分已不復存在,本次揭露的系中心走廊中段的地下通道。
中心走廊中段的地下通道南北全長103.2米,寬2.32~2.56米,系“四方樓”給水排水、供暖輸電等的主干線,同時也是核心區內聯系本部大樓等各個部門的地下網絡中樞。
(四) 庭院
以南北走向的中心走廊為中心,可將細菌實驗室合圍的院落分割為對稱的近方形的東院和西院;又以東西走向的第7棟和第8棟為中心,分別將東院和西院分割成長方形的南半與北半兩部分。
就該遺址現存地層而言,只有庭院部分保存相對較好,其中第三層黃色墊土較硬,應為當時的活動地面。據實測,當時庭院活動地面的高度,較細菌實驗室一樓的水泥地面低0.23米。
第7棟和第8棟北外側發現的兩個分流井,以及第7棟南外側和第4棟東外側發現的三個焚燒掩埋坑,實際均位于“四方樓”的庭院內。為了盡量保持庭院的完整性,發掘中并沒有對庭院進行全部揭露,不排除還有其他地下遺跡的可能性。
三
本次發掘出土各種遺物1000余件。其中包括鐵器、玻璃器、銅器、陶瓷、鋁和鉛制品等,以鐵器和玻璃器為大宗。
鐵器有建筑構件,如窗框、門栓、箍筋、把鉤子等;機械設備,如齒輪、傳動鏈、軸杠、螺桿、閥門、設備架、大型容器殘片等;生產工具,如緊線器、鍬、鏟、撬棍、扳手、錘子、管鉗子、釬子等;水暖器材,如暖氣片、上水管線、管卡子、掛鉤、地漏、管箍、吊環、篦子;電器器材,如開關罩盒、線盒、線管、燈罩;武器,如炮彈殼等。鋁制品有細菌培養箱插片、細菌培養盒等。鉛制品有器具封堵。銅器有藥匙、環等。鋼制品有針頭、箱扣等。陶瓷有瓷磚、絕緣部件、插座壺等。
下面挑部分器物予以介紹,器物編號前統一省略2014P731。
SF3∶4,鐵緊線器,完整。 一端為鐵鉤,中間為緊線裝置,另一端為管卡子。通長25.8、直徑3.2厘米(圖二,1;圖版四,2)。
SF3∶17,鐵炮彈殼,系迫擊炮彈殼體。中間爆開外翻,兩端有圓孔。通長32、孔徑1.6厘米(圖二,3;圖版三,5)。
SF3∶44,鋼注射針頭,完整。通長4.6厘米(圖二,6)。
SF3∶46,銅藥匙,完整。通長5.4厘米(圖二,2)。
SFZ∶1,鐵線盒,殘,圓角正方體,線盒蓋不見。底部有6個小孔,直徑0.5厘米,側面有2個圓孔,直徑2.8厘米。邊長10.6、高4厘米,線盒壁厚0.4厘米(圖二,7;圖版四,4)。
SF6∶15,鐵設備架,殘。整體呈方形,底座四角為豎向槽鋼,槽鋼間由兩根橫向直徑為2.4厘米圓鋼相連。縱向由一根槽鋼構件連接在豎向槽鋼上,縱向槽鋼上有多處螺絲構件。長60、寬54.4、高26.4厘米(圖二,5;圖版三,6)。

圖二 出土的金屬器1. 鐵緊線器(SF3∶4) 2.銅藥匙(SF3∶46) 3.鐵炮彈殼(SF3∶17) 4.鐵地漏(SF6∶24) 5.鐵設備架(SF6∶15) 6.鋼注射針頭(SF3∶44) 7.鐵線盒(SFZ∶1) 8.鋼箱體扣(SF5∶21)
SF5∶21,鋼箱體扣,完整。扁體,銀色,中間由軸連接,在細菌培養箱上常見相同遺物。通長10.9、寬4.3、厚0.2厘米(圖二,8;圖版四,3)。
SF6∶24,鐵地漏,殘。整體呈深盆狀,中間為螺旋漏網。口徑21.6、底徑11.6、高10厘米(圖二,4;圖版四,5)。
玻璃器大都與實驗相關,常見各式溶劑瓶、瓶塞、導管、注射器、試管、攪棒等,另少見燒杯、漏斗等。
SF7∶49,玻璃漏斗,下端殘斷。無色透明,器壁有圖案。口直徑7.5、殘高12.7厘米(圖三,1)。
SF5∶27,玻璃殘器。透明,呈圓柱體,中空,尾部呈圓球狀,器表有刻度,刻度的對側有一層白底。通長13.8、直徑0.75厘米(圖三,2)。
SF5∶29,玻璃注射器,殘斷。注射管為青色,助推器為青色。注射管上有刻度以及英文字母等。殘長8.7、管直徑0.8厘米(圖三,4)。
SF5∶37,玻璃試管,無色透明,圓柱體,圜底。長12.1、直徑1.5厘米(圖三,3)。
SF5∶41,玻璃瓶,完整。無色透明,圓柱體,敞口圓唇,束頸直腹,凹底。口徑3.3、底頸6.5、高13.1厘米(圖三,8)。
SF3:59,玻璃瓶,完整。無色透明,圓口束頸,溜肩直腹,凹底。口徑2.4、腹徑4.5、高6.5厘米(圖三,6)。

圖三 出土玻璃器1.漏斗(SF7∶49) 2.玻璃殘器(SF5∶27) 3.試管(SF5∶37) 4.注射器(SF5∶29) 5.攪棒(SF5∶34) 6、8.瓶(SF3∶59 SF5∶41) 7.瓶塞(SF5∶57)
SF5∶57,玻璃瓶塞,完整。呈“丁”字形圓柱體,深棕色透明。塞頂部呈圓餅狀慢凸起,其下為磨砂圓錐體,塞體中空。通高5.1、蓋直徑8.2厘米(圖三,7)。
SF5∶34,玻璃攪棒,完整,無色透明,圓柱體,下端有一小圓球。長9.7、直徑0.25厘米(圖三,5)。
四
本次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考古發掘的主要收獲及認識,初步歸納如下。
(一) 揭露完整,數據精確。
在以往的資料介紹和研究中,對“四方樓”的形式與格局、特別是尺寸數據,相當程度上是根據當時人的模糊追憶抑或研究者的揣測,因此可信度較低。通過本次發掘,一方面對“四方樓”地下基礎部分進行了完整揭露,搞清了其整體格局;另方面采用先進儀器對其行了實測,全方位地獲取了其精確數據。
例如對于特設監獄的第7棟和第8棟的格局,以往有許多推測抑或猜想:其中個別人認為其是一側走廊、另側房間(牢房);雖然多數人認為其是中間走廊、兩側房間(牢房),但推定兩側為對應6個大小基本均等的房間,故每棟兩層應為24個房間,而兩棟是48個房間。然而實際情況,首先是房間數量有誤,另房間大小有別,除每側設一特大房間外,其余小房間的大小亦不盡一致。這種房間大小的區別,或許意味著其使用功能上的不同,即關押對象的某種差異。
(二) 細菌實驗室中第3棟與第5棟“中心建筑”的辨識,是本次發掘的新發現之一。
這種分別介于兩棟中央的“中心建筑”,既與第3棟和第5棟主體建筑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又有相對的獨立性,當有其特殊的功能,推測其與細菌研制和活體實驗無直接關系,或許與管理抑或警備密切相關。另外,僅就第3棟與第5棟的“中心建筑”比較而言,前者規模宏大、結構復雜且向內深突,顯而易見其作用大于后者。
值得注意的是,據歷史照片和文獻記載,在“中心建筑”之上各有一高出于三層樓頂的兩小層碉樓,推測此為“四方樓”的制高點,以便居高臨下進行警戒與監視。
(三) 對“四方樓”上水下水系統及設施等有了較為清晰的了解。
上水與下水管道位于同一地溝(管道間)內,上水管為金屬制,較細,以鐵鉤懸掛固定于一側墻壁之上;下水管為水泥制(內有鋼筋),粗大,以磚砌矮墻作為支腳置于另側墻壁之下。在第3棟和第5棟的下水管道線上,間隔有若干下水井,便于觀察與檢修;在下水井底部,常見順下水管線沖出而沉淀的實驗玻璃器皿碎片。“四方樓”排水系統的主干線,位于中央走廊地下通道的底部中央。
另在第7棟和第8棟北外側,各有兩條外側以混凝土包裹的鑄鐵管道通向分流井。分流井為長方形,其形式較為復雜,可分為三層。
(四) 確認出室內一層地面和室外活動地面。
室外活動地面主要是根據庭院的堆積得以確認的,其第三層為淺黃色堅實墊土,厚約25~30厘米,表面略黑薄硬,此即當時室外活動地面。
因“四方樓”遺址破壞嚴重,地上部分已蕩然無存,所以一層室內地面的確認相對難度較大。在發掘中,我們注意到第3棟東側管道間上有一塊斜向塌落的混凝土地板,將其向上扶平,即應是當時室內一層地面的高度,這是僅存的具有說服力的證據。經實地測量,當時實驗室一層室內地面較室外活動地面,高出約23厘米。
(五)“四方樓”布局獨特,防范周密。
高大堅固的細菌實驗室將特設監獄禁錮其中,就被關押者而言,即便僥幸逃出特設監獄,也難脫離細菌實驗室的合圍;進一步講即便其萬幸沖出細菌實驗室,也難逾越核心區的高墻電網。可以推斷當時被關押犯人脫逃的可能性幾近為零,由此不難看出“四方樓”設計者的用心。
從表面上看,第7棟和第8棟似與其他建筑并無干系,實則其地下通道東西橫貫“四方樓”,甚至穿越第6棟伸向樓外。七三一部隊總部的地下通道四通八達,除布置水電管道和檢修等功能外,當有其秘而不宣的特殊用途。
(六) 爆破穴點和焚燒掩埋坑的發現,是本次“四方樓”考古發掘的又一亮點。
1945年8月日軍臨撤退前,曾匆忙采取各種方式就近銷毀實驗設備,并將細菌實驗室炸毀。在第3棟、第4棟、第7棟以及第5棟附近,發現6處實驗設備燃燒掩埋坑,內有木炭,間雜大量的玻璃試管、導管和燒瓶等。另在第3棟、第5棟、第6棟和第8棟等,發現若干處爆破穴點,坑內填滿殘磚碎瓦,其中出土了炮彈、扭曲變形的大型金屬設備殘片和暖氣殘片等;附近的條形基礎被炸斷,兩側斷口拱起,斷面鋼筋清晰可見;錐形基礎被掀起,其鋼筋裸露向上豎起;多處墻體不同程度向外傾斜。
爆破穴點和焚燒灰坑的發現,是日軍侵略者毀滅罪證的直接證據,是不可多得的無可爭辯的第一手例證。盡管其用盡手段極力掩蓋銷毀犯罪證據,但其不爭的罪行終究會在正義的陽光下暴露無遺。
(七) 出土遺物數量較大,類別豐富,為研究與展示提供了豐富的第一手資料。
本次發掘出土遺物超過千件,包括鐵器、銅器、玻璃器、鋁和鉛以及陶瓷制品等,其中鐵器和玻璃器繁多。鐵器有各種建筑構件、機械設備(包括機電設備和制造設備)、生產工具、水暖器材、電器器材以及武器(炮彈)等。玻璃器大都為各種實驗、注射器皿,是侵華日軍進行細菌研制和活體實驗的直接證據。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在一些掩埋坑中,出土了大量完好的灌滿溶液的實驗用玻璃瓶子。瓶子外面原本均應貼有說明,但絕大多數都已腐蝕或脫落,雖然如此,仍可從個別瓶子上辨認出“赤痢”、“XX毒”等字樣。這些瓶子里究竟含有何種毒液,尚待化驗核實,其屬性的解讀,或許會傳遞出意想不到的重大信息。
(八) 合作發掘與多學科交叉研究意義重大。
由于該建筑基址的特殊性和復雜性,要求發掘者除了具備一般考古學知識與技能外,同時必須對建筑學、尤其是建筑結構與建筑工藝學方面的知識具有相當程度的了解和把握,如此才能滿足發掘與科研的需要。與哈爾濱工業大學土木工程學院合作發掘與研究的意義在于: 其一,以技術為先導,全面客觀地展現“四方樓”的建筑工藝與歷史價值;其二,了解日偽時期建筑結構工藝特點,積累寶貴經驗與翔實數據;其三,通過各種建筑材料測定與分析,可以為七三一部隊舊址保護與復原提供科學依據;其四,可以保證發掘質量和提高專題考古報告的科學價值;其五,為即將開展的七三一部隊舊址其他項目發掘提供可參照的數據;其六,為今后發掘保護近現代建筑文化遺產提供經驗與借鑒。
(九) 重視科學性和技術性研究成效顯著。
近年來,隨著我國越來越重視文物保護建筑的價值,相關領域的研究多著重于文物保護建筑的藝術性和人文性的研究,而對科學性和技術性的研究相對薄弱。本次針對“四方樓”建筑技術特點,主要從以下三個方面進行了探討。
1. 通過實地調查、建筑材料性能現場分析、建筑材料性能實驗分析以及與國內外建筑材料性能對比分析等方法,對“四方樓”所用建筑材料性能進行分析和研究,獲得了其建筑材料的多項性能指標,并進行了合理的比較與評估。
2. 通過結構技術的實地調查、數據記錄與統計、相關資料的查閱,并根據舊址現存建筑結構進行合理分析與反推,同時與我國結構技術對比分析,挖掘“四方樓”結構設計理念與結構技術水平,并對其作出了科學合理的總結與評價。
3. 通過實地調查,依據殘存建筑的工法工藝,并結合建筑材料性能的研究結果,分析研究“四方樓”所采用的施工工法和各項建筑工藝,并對其進行了解釋與說明。
(十)合理評估20世紀30年代中后期日本在建筑工業方面的水準和能力,從工程技術角度揭示我國與日本在建筑技術方面的差距。
從舊址現場實際調查結果和實測數據中能夠看出,20世紀20—30年代日本的鋼筋混凝土結構的做法和我國現在做法有很多相同之處,說明當時日本對鋼筋混凝土結構的理解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同時也說明了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該領域的領先性。
“四方樓”3棟和5棟采用雙排柱內框架結構,其基礎、梁、板和柱配筋較完備,可滿足結構較好的性能要求。因日本常年發生地震,其建筑結構在抗震設防方面發展速度快,結構形式和配筋形式先進,如此配筋方式和配筋量可能是考慮地震對建筑結構的影響而設計,也有可能是考慮該建筑的重要性以及戰爭防護的需求。
黑龍江地區土層為季節性凍土,季節性凍土在冬季凍結而夏季融化,其所造成的影響是:冬季土凍結時引起土體膨脹和隆起,形成凍脹現象。夏季凍結土解凍時造成土體飽和及軟化,強度降低,建筑物下陷。“四方樓”建筑的防凍措施是將地基基礎的埋深控制在凍土層以下,采用這種措施防止季節性凍土對建筑的不良影響。排水管道的防凍也采用相同的方式,這與我國當前的防凍做法是相同的,可見當時日本在防止土體凍害方面積累了有效的經驗。
通過建筑材料性能的現場檢測和建筑材料性能的分析,了解到20世紀30年代日本在建筑材料、建筑工業以及建造技術方面的實際情況和生產能力,同時感受到技術整體進步對于國家綜合實力提升的重要性。
“四方樓”設計構思完善,布局周密合理,施工嚴謹務實,基礎堅固安全,設備脈絡清晰,功能實用完備。通過對“四方樓”的全面揭露,一方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到當時日本較為先進的建筑技術,另一方面亦不難看出侵略者對“四方樓”的重視程度和深謀遠慮的戰爭野心。
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舊址的發掘,是在國家文物局的周密籌劃和大力支持、黑龍江省文化廳的直接領導和統一協調下,為配合相關大遺址保護的前期工作項目之一,具有很強的計劃性和操作性。其《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考古工作規劃》是在《侵華日軍第七三一部隊舊址保護規劃》基礎上形成的,二者有機地結合互補,發掘乃是保護的必要前提抑或重要一環。“四方樓”發掘,是首次按照考古工作規程對七三一部隊舊址進行的科學揭露,揭開了七三一部隊舊址考古工作和歷史研究的嶄新的一頁。在發掘中,對各種遺跡現象進行了較為全面的文字、繪圖、測量、照相、錄像記錄,為今后室內資料整理、報告編寫乃至研究、保護、復原、展示等,提供了詳盡的第一手資料。
本文為“四方樓”發掘的階段性研究成果,其各種數據及結論當以今后的正式報告為準。
執筆: 李陳奇 魏明江 尤洪才 關燕妮
〔責任編輯、校對 田索菲〕
The Bacteriological Laboratory and the Special Jail sites (called “the four floor”) are the core and key departments of the 731 Forces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We may found the direct incriminating evidences ,the destructing marks, also we may know its architecture pattern and the construction technology through excavating, it will provide the first-hand data for studying the building of the Time Ruled by Japanese Invaders. It is the first time that we followed the archaeological operation procedures to do the excavating work in our archaeological and historical research field. All the records including the character, drawing , photographic and record materials will help us to sort the data, write the report, and do some researching , protecting , restoring and exhibiting works. The breaking point and burning pit found here, is the direct evidence that the Japanese invaders tried to destroy the criminal evidence, and it is the first case beyond question.
Main Excavations on the Bacteriological Laboratory and the Special Jail of the 731 Forces by the Japanese Invaders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K871.6
A
1001-0483(2016)03-0017-09
本文系黑龍江省哲學社會科學《“七三一”細菌實驗室及特設監獄考古發掘與建筑格局研究》項目中期研究成果,項目批準號為15KGB01。
〔主要作者簡介〕 李陳奇,男,1955年生,1982年1月畢業于吉林大學考古學專業,黑龍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省重點學科帶頭人,郵編150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