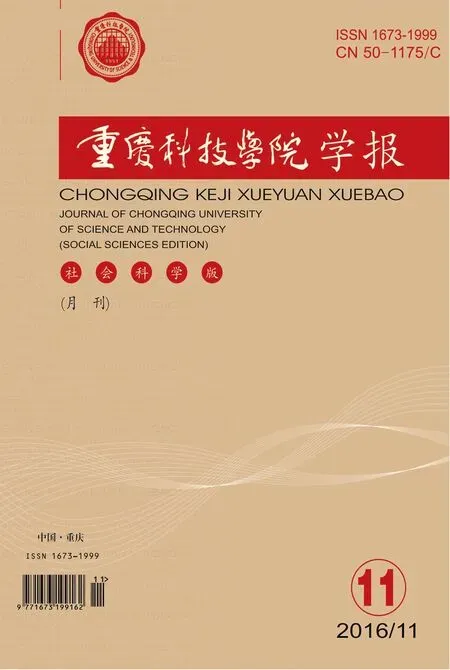論蕅益智旭對“天命之謂性”的闡釋
黃世福
論蕅益智旭對“天命之謂性”的闡釋
黃世福
《中庸》提出的“天命之謂性”一直是儒學的重要思想主張。蕅益智旭以出家人特有的方式對“天命之謂性”命題進行了詮釋。他將儒家所說的“天”區分為蒼蒼之天、主善罰惡之天、本原之天,主張生之謂性、性體用說、性善惡論以及性相近之說。智旭是站在佛教世界觀的立場上詮釋儒學“天命之謂性”,其本義是在介紹佛學,藉儒說佛,會通儒佛。
儒學;佛學;心性論;天命之謂性
蕅益智旭(1599—1655),明代四大高僧之一,幼時癡迷于儒學,飽讀儒書,深諳儒學精髓,后來剃度出家,潛心佛學。然而,他在佛學上取得豐碩成果后,又重拾儒學,以佛解儒,藉儒說佛,會通儒佛。這一心路歷程所體現出的思想特色,在蕅益智旭對心性問題的理解上也有所體現。智旭說:“世間之人,誰不談心說性?然語言雖同,旨趣碩異。”[1]1434
心性論問題是中國哲學的基本理論范疇。《中庸》提出了“天命之謂性”,此后一直是儒學的重要思想主張。智旭說:“天命謂性,自是子思以下一切后儒通計。”[1]1436
一、本原之天
“天”是中國古代哲學的重要范疇,智旭在批駁天主教的過程中對儒學所謂“天”作了系統的闡述。
“吾儒所謂天者,有三焉:一者望而蒼蒼之天,所謂昭昭之多,及其無窮者是也。二者統御世間主善罰惡之天,即《詩》《易》《中庸》所稱上帝是也。彼惟知此而已,此之天帝但治世而非生世,譬如帝王但治民而非生民也,乃謬計為生人生物之主,則大謬矣。三者本有靈明之性,無始無終,不生不滅,名之為天。此乃天地萬物本原,名之為命。”[2]1597
智旭認為,儒家所說的“天”的含義有3種。一是指蒼蒼之天。其所謂“望而蒼蒼之天”即蒼天,是與地相對之自然之天、宇宙之天,此天蒼茫無際,遙不可及。二是指主善罰惡之天,也即《詩》《易》《中庸》所謂的上帝。此天為神格化、人格化之天,用以主持人間公道,人間治理。此天治世而不生世,比如帝王治民而不生民。如果認為此天是生人、生物之主宰,那就大錯特錯。智旭認為,中國唐代以前所說的天,主要指主善罰惡之天。“然唐漢以前溯至三代,皆未嘗不謂天地神明,有靈有赫。”[1]1435“若據此土所稱天命,如商《書》云‘帝臣不蔽,簡在帝心’,周《詩》云‘文王在上,于昭于天’等,不過皆指帝釋天王,正是居須彌頂,統治人間,賞善罰惡之主。”[1]1434三是本原之天。此天“本有靈明之性,無始無終,不生不滅”,為天地萬物本原,也可稱之為“命”。
智旭認為,《中庸》“天命之謂性”之“天”,不是自然之天,也不是主善罰惡的上帝之天;“天命之謂性”之“命”,既不是通過自身教化可改變的,也不是天賦的。“故《中庸》云‘天命之謂性’,天非蒼蒼之天,亦非上帝之天也;命非諄諄之命,亦非賦畀之解也。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正深證此本性耳……此真天地萬物本原,而實無喜怒,無造作,無賞罰,無聲臭。但此天然性德之中,法爾具足,理氣體用。”[2]1598-1599
在智旭看來,“天命”雖然無喜怒、無造作、無賞罰、無聲臭,但其天然本性之中,自然具足,理氣體用,是天地萬物的真正本原。
二、生之謂性
智旭認為,《中庸》“天命之謂性”一說與印度“大自在天”能生萬物的觀點類似。“《中庸》推其原曰:‘天命之謂性’,則與西域所計大自在天能生萬物者相類。”[1]1433由此,導出了“生之謂性”的話題。
“生之謂性”是中國古代儒學之觀點,有“與生俱來”本性之意。荀子有“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董仲舒主張“如其生之自然之資謂之性”,王充有所謂“性本自然”,韓愈說“性也者與生俱生”,這些都是“生之謂性”的不同表述。程顥的表達更具體,他說:“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纟因缊,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3]告子主張生之謂性,但智旭對他的主張頗有微詞:“告子謂生之謂性,而亦不指云何為生。”[1]1433認為告子未對性作出具體解釋。唯獨《中庸》“天命之謂性”和西域“大自在天能生萬物”對此作了具體表述。
印度人談及“性”,有多種稱謂,其中就有“大自在天”一說。“大自在天”為世間萬物、一切萬化之本原。“西域性計,乃有多途:曰時,曰方,曰微塵,曰冥諦,曰神我,曰大自在天,乃至別計地水火風等,為一切萬化之原,稱之為性。”[1]1433眾生及萬物由大自在天產生,“見諸眾生從此天出,便計此天能生一切
也”[1]1433。
與儒家將“生之謂性”理解為與生俱來的本性不同,智旭解釋“生之謂性”時,將“能生萬物”之“大自在天”理解為萬物之本原,他所理解的“生之謂性”被稱為本體之“性”。
三、性體用說
智旭在《中庸直指》中指出:“不生不滅之理,名之為天。虛妄生滅之原,名之為命。生滅與不生滅和合,而成阿賴耶識,遂為萬法之本,故謂之性。蓋天是性體,命是功能,功能與體,不一不異,猶波與水也”。[4]186-187智旭將不生不滅之理稱作“天”,虛妄生滅之原稱為“命”。天與命和合而成阿賴耶識,阿賴耶識是萬法之本,稱之為“性”。所以天是性之本體,命是本體之功能。功能與本體,不一不異,就如同波浪與水之間的關系一樣。此處的“性”是體用合一的,天是性之體,命是性之用。
宋代以后,儒佛道三教走向合一。從某種程度上說,宋明理學就是在吸收佛教心性理論的基礎上產生的。智旭說:“直至宋儒,見佛書中,以種種天神而為侍從。恐謂渠等奉天,便出佛門之下。故竊涅槃第一義天,此經大涅槃天之意,強飾其詞曰:‘天,即理也。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夫使天即是理,鬼神即良能者,則冬至圜丘,夏至方澤,乃至春秋社稷山川等祀,即是祭理祭良能乎?”[1]1434-1435智旭認為宋明理氣學說來源于佛教涅槃心性學說。宋明理學將佛教“涅槃第一義天”解釋為“理”,將鬼神解釋為“二氣之良能”。在此,“天”演化為“理”,“命”演化為“氣”,“天是性之體、命是性之用”之說最終轉變為“以理為體、以氣為用”。
四、性善惡論
儒家的人性論大致可分為4類,即性善論、性惡論、性無善惡論、性有善惡論。孟子道性善,荀子道性惡,告子認為性無善惡,董仲舒、王充主張性有善有惡,韓愈則明確宣揚“性三品”。傳統儒家認為,只要經過“內養外化”,人皆可向善,“人人皆可為堯舜”。智旭在人性論問題上的觀點是矛盾的,一方面認為性“非善非惡”,性無善惡;另一方面又主張“性具善惡”,有善有惡。
在人性論問題上,智旭首先運用體用觀巧妙地說明了性“非善非惡”,同時又“可善可惡”。
他說:“天是性體,命是功能,功能與體,不一不異,猶波與水也。體則非善非惡,功能則可善可惡。譬如鏡體非妍非媸,而光能照現妍媸。今性亦爾,率其善種而發為善行,則名君子之道;率其惡種而發為惡行,則名小人之道。道,猶路也。路有大小,無人不由,故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然善種發行時,性便舉體而為善;惡種發行時,性亦舉體而為惡。如鏡現妍時,舉體成妍;鏡現媸時,舉體成媸。妍媸非實,善惡亦然,無性緣生,不可思議”。[4]187本體之天無所謂善惡,其功能則可善可惡。比如鏡子本身無所謂美丑,但卻能照現美丑。“性”也是如此,從其善的一面出發,“性”本體會導致善行,稱為君子之道;從其惡的一面出發,“性”本體則行惡,即是小人之道。此即儒家所謂的率性之謂道。正如美丑一樣,善惡是因緣和合而生,緣散則滅,并無實體,故稱“無性緣生”。智旭又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是明不變隨緣,從真如門,而開生滅門也。”[4]224本體之天雖然不變,但可隨緣而現萬有。他從本體到相對差別的現象觀察說明性與善惡之間的關系。可見,智旭是以體用論性:性之體,非善非惡;性之用,可善可惡。這與王安石的“性本情用”和“性無善惡”思想非常相似。王安石以體用論性。他說:“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于外而存于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于外而見于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5]234喜、怒、哀、樂、好、惡、欲,既是性又是情,在內心未發時為性,已發于外而付諸行動的為情。性是情之本、之體,情是性之用,性和情是統一的。不同的是智旭站在佛教的立場,主張滅情或絕欲。王安石還探討了善惡的來源問題。“性生乎情,有情然后善惡形焉,而性不可以善惡言也。”[5]235性無善無惡,而情則可善可惡。這與智旭“體則非善非惡,功能則可善可惡”有一定相似之處。
理學家為了闡明人性善惡的原因,通常將性一分為二。例如,張載分性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是人有形體前本來具有的,是善性;“氣質之性”則是人有形體之后才有的,是有善有惡之性。與此類似,朱熹有“天命之性”和“氣質之性”之說,認為“天命之性”是至善的,“氣質之性”有善惡的不同。可見智旭與理學家論性有很大的不同。智旭不贊成理學家的觀點,故曰:“天命之謂性,紫陽之解甚謬。”[2]1606
智旭又主張性具善惡、有善有惡。
他說:“若謂性非善惡,不礙善惡,則善惡從何處來,溷擾于性?既顯性后,善惡復歸何處。且正現善惡時,非善惡之性,避至何處,為復斷滅?善惡去時,非善惡之性,又從何來,為復更生邪?若謂善惡無性,隨妄緣有,既無其性,誰隨緣者?既隨緣必有能隨所隨,所隨即迷悟染凈,能隨豈非性善性惡?又即彼所隨迷悟染凈之緣,為在性外在性內。若在性外,性不遍常;若不離性,那云非具。詎知無性之性,正善惡實性。設性中不具善惡,縱遇迷悟染凈等緣,決不能現修中善惡,如沙無油性,縱遇壓緣,終不出油。請即就喻以申明之”。[2]486-487智旭認為,如果性本身不具有善惡兩種特質,則現實的善惡現象沒有出處。現實善惡現象與性之善惡是緊密相連的。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智旭得出明確結論:“性具善惡”。他說:“不變之性,正由全具善惡,故能舉體隨緣,而善惡二修,正由全攬真性,故復舉體不變。不變舉體隨緣,故稱理具三千。隨緣舉體不變,故稱事造三千。又理具只是具于事造,事造只是造于理具,故雖稱兩重,亦非六千。雖云兩重,即重重無盡也。”[2]490-491性是“體”,是“理”。“體”隨緣而有善惡,“理”具而能造善惡之事,其根源在于“性具善惡”。
智旭在人性論上的矛盾是由于受其佛性論觀點的影響。在佛性論上,智旭堅持一切眾生皆有佛性。“蠢動含靈,皆有佛性,皆得作佛,無論大小升降,本覺平等,終無有二。”[2]671人人皆可成佛。但究竟何為佛性?智旭說:“體性平等諸地,同以本源清凈佛性為所依體”[6]。“沙門以勤息為義,乃出家之都名,不改名性,即指自性清凈心”[7]1745。又說:“菩提,涅槃,真如,佛性,菴摩羅識,空如來藏,大圓鏡智,是七種名。稱謂雖別,清靜圓滿,體性堅凝。如金剛王,常住不壞。”[1]2052智旭雖然沒有對佛性作出明確回答,但從上文可知佛性的重要特性為“清靜”。佛教不以善惡論佛性,而是以“清凈”論佛性。正由于此原因,智旭在人性善惡觀上舉棋不定。無論對佛性本身作何理解,智旭在佛性問題上的成佛愿望與其在人性問題上的成圣訴求所表現出的向善追求是一致的。
五、性相近
“性相近也,習相遠也”,這是孔子關于人性論的重要觀點。智旭認為,“性近習遠,方是不變隨緣之義。孟子道性善,只說人道之性,以救時耳”[4]352。他說:“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似指不變者為性,指隨緣者為習。孟子乃于習性之中,偏指人性為善,故與犬牛不同,則是佛門五戒十善方得人身意耳。”[1]1435-1436“不變隨緣”,指雖隨緣而現萬有,但其本體不變。不變者為“性”,隨緣者為“習”。在佛教看來,順性而修,則一切眾生皆可成佛,故曰相近。隨自己的習性而放任自流,則雖性相近,最終的結果卻相差甚遠。
在智旭看來,性雖相近,但隨緣的過程中修行功夫卻不可忽視。“沙門以勤息為義,乃出家之都名,不改名性,即指自性清凈心。一期果報,五陰名質。有其質者,必稟其性,所謂性相近也。所緣名讬,造進為修。隨于染凈緣,成逆順二修,遂有十界差別之果,所謂習相遠也。”[7]1745
智旭還進一步以體用論解釋“不變隨緣”及“性相近、習相遠”。他說:“可見不變之理常自隨緣,習相遠也……隨緣之習理元不變,性相近也。若以不變之體,隨隨緣之用,則世間但有天圜乃至木果等可指陳耳,安得別有所謂乾?故《大佛頂經》云無是見者。若以隨緣之用,歸不變之體,則惟是一乾健之德耳,豈更有天圜乃至木果之差別哉!故《大佛頂經》云無非見者。于此會得,方知孔子道脈。”[4]933-934認為不變之性為體,隨緣之習為用,明確“以不變之體,隨隨緣之用”以及“以隨緣之用,歸不變之體”之關系,乃為“知孔子道脈”。
六、結語
蕅益智旭雖剃度為僧,但他卻深諳儒學之精髓。智旭對儒學“天命之謂性”的命題以出家人特有的方式進行詮釋,形成了他的心性論。但是,智旭畢竟是以佛教世界觀為指導來詮釋儒學的理論范疇,實際上無助于儒學本義的厘清。智旭系統詮釋儒學范疇的本義是在介紹佛學,是藉儒說佛,會通儒佛,用以教化眾生。
智旭闡釋儒學,會通儒佛之舉,對于儒學基本知識之推廣還是有益的。智旭對儒學思想之真諦確有實解,但未能達到儒學理論創作之境。智旭闡釋儒學,對宣傳佛教義理也是有益的,可起到教化推廣之作用,但尚未進入佛教義理創作層面。智旭闡釋儒學,既有功于儒學,也有功于佛學,但無功于整個理論會通與義理創新。佛教并非人倫價值觀、現世的社會科學,而是一門提出多重世界觀及輪回生命觀的宗教哲學,因此,僅能在若干義理格式及倫理德目上與儒學互相溝通引用,當論究哲學立場及稍有沖突的價值議題時,智旭就會從佛教的世界觀、價值觀的角度來批判儒家了[8]。
[1]蕅益大師全集:第2冊[G].福建莆田廣化寺影印本.
[2]蕅益大師全集:第6冊[G].福建莆田廣化寺影印本.
[3]河南程氏遺書[G].王孝魚,點校.北京:中華書局,2004:120.
[4]蕅益大師全集:第7冊[G].福建莆田廣化寺影印本.
[5]王安石.性情[G]//王安石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6]蕅益大師全集:第4冊[G].福建莆田廣化寺影印本.
[7]蕅益大師全集:第5冊[G].福建莆田廣化寺影印本.
[8]黃世福.蕅益智旭視界中的“格物致知”[J].江淮論壇,2016(3).
(編輯:王苑嶺)
B920
A
1673-1999(2016)11-0005-03
黃世福(1967-),男,博士,中共安徽省委黨校(安徽合肥230022)哲學教研部副教授,研究方向為佛教哲學與中國傳統文化、黨的宗教政策。
2016-1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