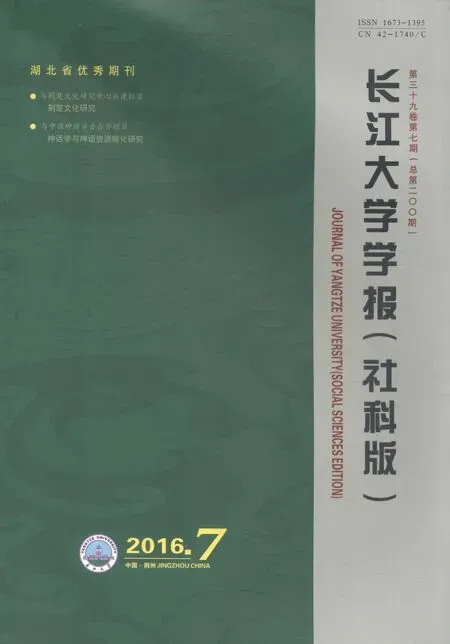超越神話學的神話研究
——劉宗迪《山海經》和神話研究述評
郭佳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
超越神話學的神話研究
——劉宗迪《山海經》和神話研究述評
郭佳
(山東大學 儒學高等研究院,山東 濟南 250100)
劉宗迪先生的《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一書,僅是對《山海經》一個部分的研究。劉宗迪指出,《山海經》中《海經》與《山經》是兩篇性質迥異并曾在戰國時期獨立流傳的文本,故對《海經》與《山經》只能做區別的研究而非一概論之。本書正標題“失落的天書”指的是隱藏在《海經》文本背后、早已不為世人所知的一幅古月令圖。這幅面目模糊不清的古圖不是人們想當然認為的有關山川方國的地圖,而是天文歷法之圖。從副標題“《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以及本書目錄所涉及的內容可以看出,他的研究不限于對《山海經》一書的解謎,而是通過《海經》文本析出古月令圖,通過古月令圖闡述古代的天文知識與歷法制度,再通過天文歷法及儀式慶典這一對古人而言最基本也最重要,但對今人而言早已陌生的領域,重建古代華夏的知識體系與世界觀。
失落的天書;古月令圖;天文歷法;儀式慶典;地理想象;地理構建
劉宗迪先生的《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一書(以下簡稱《失落的天書》)即將第二次再版。縱觀當代《山海經》研究,他的相關著述可謂其中既嚴謹又別出心裁、獨樹一幟的成果之一,其口碑與影響從其再三出版便可得知。實際上,《失落的天書》僅是作者對《山海經》一個部分的研究。通過文本分析與篇目考證,劉宗迪指出,《山海經》中《海經》與《山經》是兩篇性質迥異并曾在戰國時期獨立流傳的文本,故對《海經》與《山經》只能做區別的研究而非一概論之,《失落的天書》就是對《海經》專門而全面的觀照。首先,本書正標題“失落的天書”指的是隱藏在《海經》文本背后、早已不為世人所知的一幅古月令圖。《山海經》依圖而作的觀點早已有之,作者進一步揭示了只有《海經》才是述圖之作,這幅面目模糊不清的古圖不是人們想當然認為的有關山川方國的地圖,而是天文歷法之圖。其次,從副標題“《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以及本書目錄所涉及的內容可以看出,他的研究不限于對《山海經》一書的解謎,而是有著更宏大的學術目標,即通過《海經》文本析出古月令圖,通過古月令圖闡述古代的天文知識與歷法制度,再通過天文歷法及儀式慶典這一對古人而言最基本也最重要,但對今人而言早已陌生的領域,重建古代華夏的知識體系與世界觀。
一、研究路徑
劉宗迪對《山海經》的研究之所以顯得特立獨行,原因在于他沒有按照學術界最普遍的兩種路徑——地理學與神話學——進行解讀:既沒有遵循傳統視野,將《山海經》籠統地視為地理博物之書;也沒有遵循現代視野,從文學與神話學的角度看待《山海經》。在他看來,一方面,古代乃至現當代將《山海經》視為客觀真實之記錄并據以考證地理歷史的研究,因信其無疑而無法清醒認識這些“怪異”記載背后的文化傳統;另一方面,基于西方神話學與人類學的研究,把《山海經》的存在歸結為原始思維作祟,因斥其虛妄而又將這些“怪異”記載的知識價值一筆勾銷。不同于上述兩條路徑,劉宗迪選擇了文化史、知識史的視角,或者說民俗學的研究視角。這條路徑看似新奇卻并非前無古人,其學術思想之淵源正是來自其師鐘敬文先生,書中“謹以此書緬懷鐘敬文先生”的扉頁正表達了對師承的銘記與尊敬。鐘敬文先生關于《山海經》的幾篇文章沒有受到學界的重視,但身為弟子,劉宗迪對其研究成果、研究計劃以及學術價值了然于心:“鐘敬文先生《山海經》研究的勝義主要體現在他是第一個認識到《山海經》一書屬于古代民眾知識范疇,從而超出傳統的經史之學以及因經史之學而帶來的偏見,也避免了現代神話學和人類學對于傳統的傲慢和無知,他從民俗學的角度對此書進行理解和闡釋,從而為《山海經》研究開辟了一個全新的學術視野。”[1](P239)可見,鐘敬文先生開創的這條路徑,把《山海經》當作古代民眾的知識和信仰進行理解和研究,這種民俗學的眼光將學者置身于《山海經》所處的文化傳統之中,真正做到同情地了解,并揭示其中因后世太多“局外人”費心闡釋反致遺失的普遍知識。不過不管是鐘敬文先生,還是有著相似研究路徑的日本學者伊藤清司,都只重點關注相對清晰明了的《山經》,而將更為怪誕和令人迷惑的《海經》懸置一旁,因而劉宗迪便嘗試進一步把這一文化史、知識史的眼光帶進了《海經》的研究。[2]
在古典文獻與文化的范疇提及古代的民眾知識或普遍知識,必定會使很多人感到陌生。這主要是因為傳統學術只關注經史及諸子之書中所承載的有關修身治國之道的主流知識,民眾知識一類從來都只落在正統視野之外。但是,比起相對狹隘的主流話語,紛繁復雜、包羅萬象的民眾知識更貼近古人的真實生活和思想狀態,它上包天文下括地理,遍及歷史譜系、信仰祭祀、工農醫藥等各方面,而縱覽先秦古籍,這些知識在《山海經》中得到了最充分的反映。其實,鐘敬文先生從民俗學角度出發,對古典文獻與文化中民眾知識的強調,與李零先生對古代文化中數術方技之學的重視可謂異曲同工。以天文歷法、陰陽五行與風水占卜為中心的數術之學,以及以醫藥養生為中心的方技之學,外加工藝學和農藝學等知識即李零先生所謂的“以數術方技之學為核心的各種實用文化”,這些知識和文化正是劉宗迪所強調的民眾知識的主要構成部分。李零認為,一直以來學界對中國古代文化的認識存在偏頗,因為受漢以后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影響,古往今來的學者們“往往注意的只是從百家爭鳴到儒家定于一尊這一過程,而很少考慮在先秦諸子‘之前’和‘之下’還有以數術方技之學為核心的各種實用文化”。[3](P11~12)各種實用文化或曰民眾知識之所以消失在后人的視野中,源頭就在于漢代儒家對先秦文獻的重構,在《漢書·藝文志》所呈現出來的“儒經>子書>兵書、數術、方技”的文化結構中,數術方技之學不僅地位最低,而且后世保存下來的只有“術數略”的《山海經》與“方技略”的《黃帝內經》。
但事實上,各種實用文化或曰民眾知識在先秦文化中的地位絕不似今日所見:一方面,近年來,隨著考古發現的不斷推進,大量戰國時期與數術方技有關的簡帛文獻,如日書、占書等,重見天日,這使各領域的學者們日漸意識到以數術方技為主的實用文化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所占的重要地位;另一方面,數術方技之書不僅數量多、影響大,而且向前可以追溯至西周時期諸種重要官學。舉數術之學為例,天文歷法等知識在春秋戰國時期與陰陽家相關,在西周時期則與直置于王權之下的史卜系統相關。可以說,《山海經》所承載的這條知識和文化的線索,在先秦時期不僅有廣大的基礎,更有深厚的淵源,而如果我們根據漢以后的文化結構去探討古代文化,必定會產生李零所強調的“逆溯的誤差”。對于這一點,劉宗迪也有深刻的認識,而知識史、文化史的視角,或曰民俗學的視角,正是他克服“逆溯的誤差”,回到原有的文化傳統去認識《山海經》的法寶。
二、《海經》古圖真諦之一:天文歷法
翻閱《失落的天書》,給人印象最深的大概就是書中大量有關中國上古天文知識與歷法制度的內容。首先,《大荒經》中東西向屹立的七對“日月出入之山”,正是以山峰為參照的原始天文觀測體系。七對日月山循環反復,既與依據月亮朔望分十二個月有關,又與依據太陽周年視運動分二十四節氣有關。不僅如此,根據作者的分析,《大荒經》中還有關于陰陽合歷和冬至置閏成歲的記載,以及春秋分朝日、致月的記載(春秋分的天文觀測活動是上古歷法制度和計時制度的校定基準)。此外,作者還推測,天上二十八星宿系統或許正是地上這七對“日月出入之山”的天文觀測體系的后續發展,這也恰好可以說明后世以二十八星宿配屬九州列國的分野制度的最初緣由。其次,《大荒經》中還有與殷墟卜辭和《尚書·堯典》呼應的“四方風”和“四方神”。作者根據馮時先生的訓詁考證,即“四方神”的名字意為二分二至、“四方風”的名字意為四節之物候的結論,專門論述了《大荒經》中的四方神和四方風實為四時神和四時風,它們反映的是上古物候歷中以風為變化之參照的基本情況。此外,《海外經》中的四方神,與諸如《呂氏春秋·十二紀》、《禮記·月令》等文獻中的四時神相似,而四時神的名號“句芒”、“祝融”、“蓐收”、“玄冥”即源于對四時物候的認知,因而《海外經》中的四方神也實為四時神。由此,《失落的天書》明確指出,《大荒經》及《海外經》背后實際上就是一幅按照空間結構展開的時序圖畫,它們正是后世月令文獻中四時配四方體制的濫觴。再次,《大荒經》與《海外經》中有關于龍星紀時的體現,上古大火紀時的記載遍及先秦文獻,對其研究最為詳備的當屬龐樸先生關于“火歷”的論述,作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開創性地在《海經》中發掘龍星紀時。他認為,龍作為華夏的圣物,僅是一種文化意象,是天文歷法的體現。因此,《海經》中出現的各種龍身怪物極有可能是天上龍星的反映,比如鼎鼎大名“風雨是謁”、“視為晝,瞑為夜,吹為冬,呼為夏”的燭龍,象征的是具有重要授時功能的秋冬之交的龍星。另外諸如夔龍、應龍、相柳等,也象征著不同時節天上的龍星,并帶有各自時節的特征。
除了上述三點,《失落的天書》中還有很多有關天文知識和歷法制度的論述,這些論述的背后有著天文史學家、考古天文學家、文史學家的大量研究成果作為基礎。劉宗迪指出,這些學者的研究雖然專門深入,但他們的研究對象都沒有以《山海經》為主,因而導致《海經》與上古天文歷法的關聯一直沒有得到發現和證實,而《失落的天書》正是致力于研究《海經》與上古天文歷法的關聯,這兩者之間相互印證、相輔相成。除此之外,他還非常重視運用我國少數民族的口頭與文獻資料參比上古的知識和文化。西南少數民族,特別是彝族的天文歷法以及神話傳說,為今人理解上古天文歷法提供了許多生動鮮活的證據。例如,陳久金等合著的《彝族天文學史》提到四川涼山彝族民間有依據山峰作為坐標系的觀測天象的授時方法,可以與《大荒經》中的“日月出入之山”對照理解;又如,彝族關于歲時之神用季候風劃分四季的神話傳說,可以說明原始物候歷中風的重要性,由此也說明了《海經》中的四方神和四方風與之體現的正是同一種歷法源流。
在劉宗迪看來,天文歷法對于上古知識和文化的形成與發展至關重要,這不僅因為它向上關系到王權的天命授予、向下關系到民眾的農業生產,更因為從哲學層面看,天文歷法是華夏先民世界觀與宇宙觀形成的基礎。在時空觀的問題上,劉宗迪深受康德哲學的影響,他指出:“歷法不僅是一連串排列有序按部就班的日子,它實際上通過對時間節律的劃分命名和對空間方位的劃分布局,對整個世界進行了根本性的建構,它序列了時間,構筑了空間,而時間和空間是人類世界觀的兩個基本方面,德國哲學家康德稱之為人類知覺的兩個基本直觀形式,人類對世界的領會、對經驗的組織、對活動的安排、對社會生活的參與,都需要以特定的時間和空間概念為前提。”[4](P239)時間和空間兩個概念是人類認知的前提,是人類世界觀的基礎,不過不像康德認為時空是先驗的存在,他更強調時間和空間是人文構建的產物,而天文觀測和歷法制定就是構建時空觀最基本和最有效的途徑,因此,天文歷法是人們理解世界和宇宙最關鍵的依據之一。由此,作者還在《失落的天書》中論證了,中國上古天文歷法所展現出來的以“五”分類并組織世界的時空觀,正是后世“五行說”的文化源頭和知識原型。天文歷法在上古知識與文化范疇內如此重要,《山海經》作為一部反映古代民眾知識與信仰的典籍,其中包含有大篇幅關于天文歷法的記載不可謂不水到渠成。
三、《海經》古圖真諦之二:儀式慶典
在《失落的天書》中,劉宗迪不僅論證了天文歷法與《海經》的關聯,還詳細闡述了與之最密切相關的儀式慶典在《海經》中的體現。在上古社會,天文知識與歷法制度的運用,在世俗生活中主要體現為節氣的確定以及相應儀式慶典的舉行,因此,作者在關注天文歷法的同時,還關注與農時周期相關的節氣及儀式慶典。他認為,農耕時代人們生產和生活的節律與大自然的節律息息相關,天文觀測和歷法制定確定了大自然的節律,同時也確定了人們勞作休息的節律。由于大自然的節律正是由一個個節氣體現出來,因而古人每逢重要節氣就會舉行隆重的儀式和盛大的慶典,這就是人們共同的歲時習俗的養成。《失落的天書》證實了《海經》古圖與現存的月令文獻一脈相承,因而推論《海經》在四方描述的“怪異”場面極有可能就是月令文獻中記載的四時物候行事。然而這種還原在理論上容易成立,想要落實到具體細節卻十分困難,因此《失落的天書》中僅就《海外東經》和《海外南經》中的一些記載與月令文獻中春夏季的物候和行事進行了對比研究。例如,作者認為《海外東經》中黑齒國和雨師妾的條目與兩者之間扶桑樹的條目構成了一個關于仲春活動的整體場景,扶桑樹是春分測日的表木,而黑齒國與雨師妾一男一女的巫師形象反映的可能是仲春春社的祈雨儀式;《海外東經》與《大荒東經》記載青丘國的九尾狐,可能是仲春春社以會合男女、祈求子孫的郊媒儀式的反映。又如,作者認為《海外南經》中有關交脛國的描述,是孟夏雩禜儀式中焚巫尫以求雨的儀式場面;《海外南經》與《大荒南經》記載的歌舞升平的臷國,反映的是孟夏雩禜儀式中伴隨的狂歡活動,即民眾載歌載舞、歡暢宴飲的慶典場面。此外,劉宗迪還顛覆學界的普遍論斷,認為《海經》中有關西王母的記載為古代西王母記載的源頭,而其實質與秋季的烝嘗儀式密切相關,其原型是秋收慶典烝嘗祭祖儀式上扮演始祖母的神尸。
植根于古代農時周期的節氣與儀式慶典,即后世傳統節日與節日民俗事象的源頭。關于節氣到節日的演變和發展過程,劉宗迪在《失落的天書》中有零散的提及,之后更作《傳統歷法與節日的變遷》一文進行了專門論述。他認為,原始的天文物候歷對應著節氣,精確的成文歷法對應著節日,故節氣是節日的前身,觀象授時時期的儀式慶典是后來節日民俗事象的前身。當代許多民俗學者研究中國傳統節日,并致力于探究節日和節日民俗的起源和意義,在劉宗迪看來,只有將傳統節日以及節日中那些源遠流長的民俗事象和觀念追溯到其對應的節氣以及儀式慶典上,即與農時周期的淵源關系上,才能對節日的起源和意義做出正確的解釋。[1](P203)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七夕》一書正是將這一節日研究的理論和方法落實到個例的成果。人間的生活生產節律需要標志著歲月流轉的天上星象來昭示,天上星象也正是人間民俗事象的反映。正如古代七月孟秋,女人要進行紡線織布的活動,因此便將此時正中天的一顆亮星命名為織女星,織女星上升到最高處,就標志著七月孟秋的到來以及紡線織布活動的開始。傳統節日與原始天文學和節氣活動的淵源,在七夕這一節日中得到了充分體現。
在概括了《失落的天書》中關于天文歷法及儀式慶典的論述之后,不得不提及的還有其中關于神話的論述。隨著現代神話觀念的引入,《山海經》一直就被視為中國古代神話之淵藪,從文學與神話學的角度研究《山海經》早已成為學界共識。不過,劉宗迪認為這樣的研究流于偏見和膚淺,實際上,神話與口頭傳統相關。“脫離了古老的口頭傳統,我們只能從《海經》文字中窺見中國古代神話的只鱗片爪,在此意義上,說《山海經》一書是‘中國神話的淵藪’,并不恰當,它其實只是這個神話淵藪上漂浮的碎片,真正的神話淵藪是原始天文學和歷法知識傳統。”[4](P235~236)神話與口頭傳統的關系此處暫且按下不表,而神話源于天文歷法的基本觀點則引導作者把《海經》中出現的大量神話溯源到原始天文歷法及儀式慶典之上。例如,前文提及的《海經》中有關龍身怪物的神話,是天上龍星運行四季的反映;《海經》中扶桑十日神話是春分觀象授時活動的反映,三足烏神話的原型是兼具測日和測風功能的相風鳥,而春分樹立之表木,不僅可以測日、測風,還能兼為射箭之靶,因此后羿射日神話反映的則是仲春鄉射活動;夸父逐日神話是冬至觀測太陽運行活動的反映;西王母神話與秋季豐收的儀式慶典有關,昆侖神話與作為原始天文觀象臺的明堂有關。此外,作者還把《海經》中關于大禹治水平土的神話理解為現實生活生產中司空平治土地、修整堤防、疏浚水道等農田水利建設活動的反映。
劉宗迪這一對于中國古代神話的基本觀點深受劍橋神話學派,即“儀式—神話”學派的影響,他曾翻譯過其中著名學者哈里森的著作《古代藝術與儀式》。神話學史上的劍橋學派基于對希臘宗教和神話的研究,主張所有神話都源于對原始儀式的敘述和解釋:原始儀式包含兩個層面,作為表演的行事層面和作為敘事的話語層面,行事層面在后世演變為戲劇,而話語層面就是后世所謂神話。雖然這一盛行于20世紀初的神話學理論后來被基于田野作業的功能主義神話學取代,但劉宗迪顯然對劍橋學派的儀式—神話理論持有更高的評價。他認為,神話學說的基本功能就是要揭示神話在現實生活中的文化原型,并重建由平凡到神奇的演變過程。“儀式—神話學派將神話敘事與儀式行事相印證,舉凡諸神怪異的形象、超逸的故事以及神話世界恢弘的時空構造,都在凡世儀式的行事中得以妥帖的落實,這一點,是其他各種神話學理論——包括最‘先進’的結構主義——無法達到的。”[1](P116)由此可見,他對《山海經》中大量神話的闡釋,正是秉承了劍橋學派的理論觀點,致力于為看似荒誕無稽的中國上古神話敘事尋找現實中的落腳點。
四、《海經》的文本呈現:戰國的地理想象與秦漢的地理構建
根據《失落的天書》的基本觀點,《海經》原本是一幅寫照四時物候與行事場景的月令圖,但在訴諸文字之后卻變成了一部描繪山川方國的地理書,從時間之圖變成了空間之書,其性質發生了根本的轉變,而這一轉變就發生在學界普遍認同的《山海經》的成書年代——戰國時期。一方面,研究先秦文獻不得不再三注意的是口頭傳統與書面傳統的轉變及相互作用的問題,戰國時期口頭傳統的瓦解正是劉宗迪用來解釋《海經》古圖被誤解成為《海經》文本的關鍵所在。他認為,文字的產生雖然久遠,但文字真正流通、普及正發生在戰國時期,這導致簡帛書寫代替口頭語言,成為繼承和傳播集體記憶與知識的主要手段,因而流傳于口頭傳統中、依賴于口頭知識與文化背景的古月令圖雖然得以保存,但其意義由于脫離了原初的語境,使得戰國文人無法理解并望文生義。[2]另一方面,劉宗迪認為,《海經》的古月令圖之所以被誤解為地圖,有其歷史的必然性。戰國時期政治上諸侯爭雄、知識上百家爭鳴,諸王與知識分子的視野得到前所未有的拓展,并有著國家大一統的宏大構想。如果說《周禮》是當時學者對國家政治制度的構建,那么《山海經》可以算是當時學者對國家地理格局的想象,而這種地理想象正是基于那幅早已陌生的、描繪著四方光怪陸離景象的古月令圖之上。[2]由此可見,《海經》并不是真實地理的再現,而是戰國時期人們地理觀和民族觀的再現,它在古月令圖,即華夏源遠流長的時空觀基礎上構成了當時人們想象周邊世界的模式。在他看來,先秦文獻諸如《禹貢》、《楚辭》、《呂氏春秋》等展現出的地理觀和民族觀多受《山海經》影響,作為中國政治地理始祖的《禹貢》,其對世界邊緣的描述正來自《海經》的周邊世界模式;另外,稷下學派鄒衍的學說中,不僅“五行說”展現了《海經》古月令圖的時空觀,其“大九州說”也正是繼承了《山海經》從內向外層層外推的世界模式。[5]
在傳統觀點看來,《海經》所描述的是真實的地理無疑,因為其中出現了很多見于古代文獻和地理史料的地名,為此古今學者們一直試圖從這些地名入手,考證《海經》所涉及的地域范圍。但是,劉宗迪卻指出,《海經》中出現的真實地名并不足以證明《海經》地理的真實性,這些見于歷史文獻中的真實地名可以分為三種情況:一是后人竄入的真實地名,例如毆、閩、桂林、朝鮮、蓬萊、大夏、月支等,多見于成書最晚的《海內經》四篇;二是本非地名,但經后人依托而成為真實地名,例如昆侖、交趾、蒼梧、南海、儋耳等;三是在《海經》由古圖轉換為文本時,因述圖者誤解而附會為方國地理的名稱,例如西周之國等。[4](P281~282)在這三種情況中,劉宗迪主要對第二種“真實地名”的產生過程進行了詳細的論證。他認為這些地名其實最初源于《海經》,它們在《海經》文本中并不是指向某個地方的專名,但因為秦漢時期《海經》被誤讀為地理志,人們認為它是對華夏周邊世界的實錄,故用其中的地名命名全新的地域,后人但見熟悉的地名頻繁出現于《海經》,又更加認定其為地理之書,如此循環陷入認識的誤區。秦漢時期用《海經》命名新發現和開辟之地的情況,最典型的要屬漢武帝“按古圖書”將張騫出使西域所呈報的一座河水所出的大山命名為昆侖,還將新平定、待治理的越地分別命名為南海、蒼梧、交趾、儋耳等。*對昆侖命名的論述詳見《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515~517頁;對交趾命名的論述詳見《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中華書局2010年版,第347~349頁。由此,戰國時期《海經》所呈現出來的對周邊世界的想象模式,便在秦漢時期的地理開拓中得到了真正的落實。顯而易見,劉宗迪對于《海經》地理學的論述與傳統觀點可謂背道而馳,按他自己的解釋,這是受了顧頡剛先生“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的影響。顧頡剛先生的這一著名學說關注的是上古歷史的問題,劉宗迪在此理論方法的基礎上引申出他對地理學的看法:“具體到地理學上,‘層累地造成的古史說’就意味著歷史上的一些真實存在的地名,很可能只是古人誤解歷史傳說乃至神話故事并據以想象和命名世界的產物;具體到《山海經》地理學,這個學說則意味著,《山海經》中的地名可能原本只是子虛烏有的神話地理,而后來地理史料中出現的相同地名,并不足以證明《山海經》地理學的真實性,恰恰相反,這些所謂‘真實地名’只是古人輕信《山海經》而根據其中原本子虛的神話地理想象和命名真實世界的結果。我們不妨模仿顧頡剛先生,稱這種地理學知識的生產為‘層累地造成的地理學’。”[1](P291)
五、結語
總體來說,《失落的天書》是一部跳出了固有模式,極具想象力和解釋力的著作。作者既有過于常人的思維天賦,又有扎實的古代文獻功底,還全面掌握了中西理論方法,而流暢明了的語言寫作技巧更使得本應繁冗枯燥的學術性著作變得可讀性極強。就本書存在的缺點而言,有意見指出,作者研究《海經》主要專注于天文歷法以及世界觀、宇宙觀等宏大問題,對遍布文本中的怪異記載缺少逐一詳細的解釋,有避實就虛的嫌疑。劉宗迪就此質疑做了說明,他認為研究《海經》不應被其中五花八門的“怪物”所吸引,而應重點著眼于文本的記載體例和整體結構。[1](P284~286)事實上,也正是這種從大局著眼的方法之運用,使得作者能夠發現《海經》文本背后的古月令圖。不過在筆者看來,先從整體上確定《海經》的性質,再把所有的“怪異”內容按這一性質進行闡釋,難免有主觀構建之嫌。例如,在《失落的天書》把《海經》四方怪異描述解釋為月令文獻中的四時物候行事之時,讀者就能發現不是文本中所有的條目都能被納入這一解釋體系,而作者選擇性的強調與忽略增加了其論述觀點的不客觀成分。又如,在以天文歷法及儀式慶典為主旨的大框架下,作者將《海經》中出現的所有神話敘事看作是上古天文學或原始儀式慶典的反映,然而某一神話敘事不止存在于《海經》,《海經》中的這一神話敘事也并不確定就是所有相關文獻的源頭,因此,單按《海經》的天文歷法框架解釋神話必然存在偏頗之處。但是,必須承認的是,學術研究無法做到絕對的客觀,或者說所有的理論都是主觀構建的產物,只是主觀成分多一點還是客觀成分多一點的區別,而《失落的天書》的特點與長處也就在于,它劈破鴻蒙般地構建出前人研究從未涉及的一種全新觀點,它自成一家之言,并對中國古代學術史、思想史和文化史的研究具有啟發性的意義。
《失落的天書》是劉宗迪研究《海經》的成果,其對于《山經》的研究也正在逐步推進,其研究路徑和基調在《失落的天書》最后一章最后一節“《山經》與《管子》的地理學”,以及“怪物志、本草修辭以及福柯的笑聲”一文中可以略見端倪。他認為,《山經》與《海經》一樣,極有可能出自稷下學派,它的性質是兼具自然和人文景觀的地理資源調查報告。另外,在以博物志為主旨的框架下,劉宗迪運用語言學和符號學,探討了《山經》中有關動植物的描述問題。如果說《海經》中的“怪物”出現于成書者對古月令圖的誤解,那么《山經》中的“怪物”則出現于后世讀者對古人描述動植物的話語系統的陌生。讓我們期待劉宗迪關于《山經》的“地書”早日問世。
[1]劉宗迪.古典的草根[C].北京:三聯書店,2010.
[2]廖明君,劉宗迪.《山海經》與上古學術傳統——劉宗迪博士訪談錄[J].民族藝術,2003(4).
[3]李零.中國方式正考[M].北京:中華書局,2006.
[4]劉宗迪.失落的天書——《山海經》與古代華夏世界觀[M].北京:中華書局,2010.
[5]呂微,等.神話:想象與實證——《山海經》研究座談會發言選載[J].文化研究,2004(4).
特約編輯 孫正國
責任編輯 強琛E-mail:qiangchen42@163.com
A Study of Mythology beyond Mythology——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on Mythology and Liu Zongdi’s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
Guo Jia
(Institute of Confucianism,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250100)
Mr.Liu Zongdi’s Lost Sealed Book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 and ancient Chinese view of the world,is only a part of the study on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Liu Zongdi pointed out that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Mythical Legends of Seas in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 are different in nature,and had independently spread in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so we cannot generalize them.This book is titled Lost Sealed Book refers the picture of ancient lunar that hidden behind Mythical Legends of Seas and it is not known to the world.The indistinct picture is not a map of mountains and rivers that people take for granted,but the map of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From the subtitle and the content involved book catalogue can be seen,his research is not limited to Mythical Legends of Mountains and Seas,but analyzing the ancient lunar order by Mythical Legends of Seas,elaborating the ancient astronomical knowledge and the calendar system by the ancient lunar order,and reconstructing Chinese knowledge system and world view through the astronomical calendar and ceremony for the ancients also the most important and the most basic,but already to people unfamiliar areas.
Lost Sealed Book;the ancient lunar order;astronomical calendar;ceremonial celebration;geographical imagination
2016-06-10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05BZW068)
郭佳(1986-),女,福建福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神話學研究。
B932
A
1673-1395 (2016)07-001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