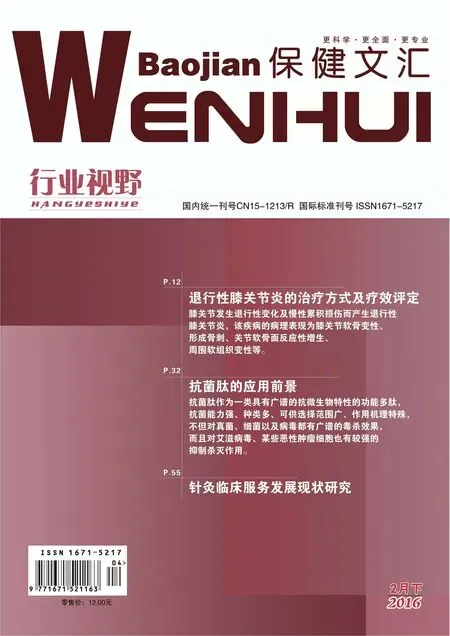誰是“生存者”?
●阮淑貞
誰是“生存者”?
●阮淑貞
“我組認為,離島的應該是‘宇航員’,他受過長期的訓練,身心素質好,定能熬過難關,回到陸地。實現人類遠征火星的偉大夢想。”另一位同學反駁:“在目前,艾滋病肆虐全球,若能攻破這個醫學難題,就能幫助很多生命,很多的家庭!比起尋覓遙遠外星,讓醫生離島能馬上利于全人類。是操作性強的選擇!”這一幕是“生存者”活動課中,關于“離島的人”的辯論現場。
這節心理活動課是為高二理科學生設計的。該班學生對理科學習熱情高,但文科學習感到吃力,學習被動,對抽象概念掌握較慢,甚至出現失去學習信心的現象。為此我的教學設計圍繞“努力讓學生在思考、討論過程中提高自我效能感,在游戲中澄清價值觀”而展開。
“今天,我們一起來做游戲,每個小組要有結果和匯報。”隨著情景的引入,同學們開始進入狀態。
這個游戲名為“生存者”。游戲背景是“某飛機墜落在荒島上,只有不到十人存活。這時逃生工具只有一個只能容納一人的橡皮氣球吊籃,沒有水和食物。人物包括“孕婦:懷胎8個月”、“發明家:正在研究新能源(可再生無污染)汽車”、“醫學家:今年研究艾滋病的治療方案,已取得突破性進展”、“宇航員:即將遠征火星,尋找適合人類居住的新星球”、“生態學家:負責熱帶雨林搶救工作”、“流浪漢”。
每個組員抽取一個角色,然后以角色的立場闡述自己的觀點,要求大家開展討論,并根據討論的完整,組內一致決定可離島的人。此后匯報結果。
呈現故事背景的時候,我特意放慢速度,力求同學們能看明白了、聽清楚了。從后面的課堂表現看,教師如何引導學生“正確審題”是十分重要的。
通過觀察、細聽同學們的討論,發現同學們有許多獨特的開放的思想。十五分鐘過去了,進入小組匯報的階段,匯報期間其他同學可以質疑、提問、辯論。
因為期待同學們持質疑探究的精神投入游戲中,我在一旁聆聽著,把時間交給主角:同學們。
第一小組發言了。“我組認為,生存者應該是懷胎八月的孕婦!基于人道主義,一定要走!這是兩條人命啊!”
反對聲音馬上出來。“當然不行,孕婦乘坐氣球吊籃,能堅持到陸地嗎?如果發生危險怎么辦?”
“我也贊成孕婦不要走,你看,留在島上還有醫生幫忙接生呢!”
全場一片掌聲!
“說得有道理!那么還有發明家、宇航員、流浪漢、生態學家,誰走呢?” 其他小組也提出疑問。
我心里想,這個思路很好!有同學開始逆向思維了。
“應該是這樣的,孕婦和醫生留下,發明家可以發明一些工具或物件,幫助大伙在荒島上求生,所以發明家是不可以走的。”
“嗯。”許多同學連連點頭!
“還有,要在荒島上生存下去,需要生態學家,他在熱帶雨林搶救工作組中工作,他有在這種環境下生存的本領,這點一定能幫助大家活下去!”
“有道理。”
至此,我發現同學們沒有提到“流浪漢”,為什么呢?于是作了一個引導:“每個角色都有自己的特點,還有一個角色,我們想到了什么?”
“流浪漢有什么用啊?這樣會浪費了一個機會。”全場這時出現竊竊私語的聲音。
我微笑著說:“這代表了一部分人的觀點,其他小組贊同嗎?還是有自己的判斷?”我鼓勵更多的同學發表意見。
“我們組恰恰相反,讓流浪漢離島。”這時一片嘩然!這位同學繼續說:“大家細想,當氣球到了高空,溫度低、加上食物的供應很有限,這個時候誰活下去的可能性最高?”
聽到這,班里頓時鴉雀無聲。這是思維碰撞的好機會,“大家的思路都有各自的邏輯,我們是否可以發掘更多的線索?聽取更多的聲音?”我示意這位同學說下去。
“我們考慮島上的各個角色,發現是匹配的,比如孕婦需要醫生。在荒島環境下生存,決定生態學家和發明家要留下來以爭取水和食物,不然沒有人能活在島上。至于宇航員和流浪漢,誰能有離島的能力?我們相信是經歷過饑寒交迫、想到大城市做黃金夢的流浪漢。”
有一個聲音忽然跳出來;“即使流浪漢回去了,又有什么意義呢?他對社會沒有什么貢獻!甚至沒有受過教育,沒有離島的價值。”
“對,從人的價值上看,宇航員更值得離島!他也有更好的道德品質。”另一個同學也同意。在此,部分同學用道德品質的假設作為價值的判斷。有人低聲表示不同意使用“道德”來判斷“流浪漢”不如“宇航員”。
我微笑著向大家說,“價值的體現,你們在政治科哲學部分的‘價值與價值觀’是怎樣理解的?嘗試運用到這個案例中?”
于是同學們回顧“價值”、“價值觀”、“人的價值”等知識點。
一個清晰的聲音響起,只見一位女同學站起來說:“人的價值是分兩種,一種是‘社會價值’指的是‘貢獻’,一種是‘自我價值’指的是‘索取’。我們知道,人的社會地位不同、認識事物的角度不同、按條件不同、就會形成不同的價值判斷。所以,我們說宇航員比流浪漢更有價值,是基于自己的立場,可無論是站在哪個角色思考,最終依歸站在廣大人民立場上選擇才是對的!因此,我認為,流浪漢和宇航員一樣,只要是為大家負責的,就是適宜的‘生存者’!”語畢,班里響起熱烈的掌聲!能有如此邏輯性的回答,正是知識遷移的表現。
游戲仍未結束,后面的討論出現了新的視角:從思考哪“一個角色”過渡至“全體成員”。
思索一會后,一名學生舉手發言:“其實,我們組的決定是,誰都不走!”
“啊?!”全班愕然了。
“既然大家都無法確定離島后能安全著陸,那么我們何不先在島上活下來,靜待救援呢?!這是保守的方法,但一旦被尋找到,大家都安然離島!”
新的觀點出來了!大家再次雀躍起來,爭著要發表意見。
這時一位學生“咳咳”兩聲,把同學們的注意力轉移到他身上,“其實,綜合了眾多同學的意見,我想到一個問題,回到一開始老師提供的故事背景、游戲規則,我們有沒有陷入一個思維定勢中呢?到底‘生存者’是不是僅指一個人?故事中提到的‘生存者’,為什么不能是‘全體成員’?不管我們讓誰離島,我們都拽著希望。‘離島’只是一個機會,重要的是離島的人能讓組織來拯救所有人!”話音一落,班里響起熱烈的掌聲!
至此,這一場氣氛熱烈的活動課落下帷幕。課后延伸是布置學生把思考與啟發寫下來。這樣我能更深入地了解學生的思想,又能檢視教學中的不足。
反思這節課,在不斷的討論、質疑、辯論中,同學們經歷了一個價值觀澄清的過程。在課堂中,學生體會了思維的碰撞、明確了價值觀的導向作用。打個比方,我打開了一扇窗,讓同學們看外面的風景,同時悄悄設下一扇門,留著突破局限的可能。那“生存者到底是一員還是全員”就是一個思維突破口。當思辨到此,同學們已能從“社會價值”、“自我價值”深入澄清價值觀。每個小組的最終答案,可以是不一樣的,這又是價值觀導向的一種體現。
在高中心理活動課教學中,關于高二的教育研究相對較少。高一適應了高中的學習、生活節奏,高三進入沖刺階段,因此高二正是高中生涯中承上啟下的年級,是準備上高三,調整心態的關鍵時期。同時高二階段是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逐步形成并趨于穩定的時期。在此階段若能給予高中生一個符合年齡特征的發展平臺,則可堅信:“每顆心都有自我成長的渴望,每個孩子都是獨一無二的花”,而我們是陽光下最幸福的園丁。
(作者單位:廣州市真光中學)
阮淑貞,心理健康中學一級,專職心理教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