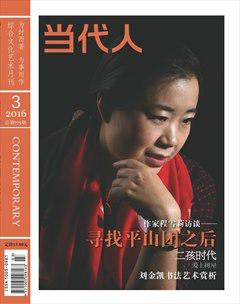老堅決
1980年的一天,省文藝組的幾個人正在院里大柳樹下晨練,一個蒙白毛巾的半大老頭急匆匆走進來,直奔家屬樓而去。李滿天看著那人的背影說:“老堅決又來找老堅決了。”
外來的老堅決叫雷金河,小名喳子,晉縣周家莊不脫產的公社書記。院里的老堅決叫張慶田,解放初從省委宣傳部下放到晉縣當副區長,在周家莊安家落戶。兩個人摽在一起搞農業合作化,一個前臺指揮,一個幕后參謀,把個周家莊搞得轟轟烈烈,有聲有色,周家莊雷金河與五公耿長鎖、西鋪王國藩齊名,成為河北乃至全國三個農業先進典型。兩個人志同道合,配合默契,是因為“朋友就是另一個我”。共同的脾氣性格是不盲從,敢抗上。
雷金河堅決。五八年大躍進,強迫命令瞎指揮,豐產方要插籬笆,高產田要澆狗肉湯,小麥要放畝產五六千斤的衛星,拆社員的房子蓋公社劇場,都被他一個一個頂回去了。三年困難餓肚子,他根據多年的經驗,實行一套調動生產積極性的管理方法,大隊對小隊,小隊對社員,實行“包工、包產、包開支,超產獎勵”,簡稱“三包一獎”。1960年冬天全國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我參加了,在霸縣工作團。在簡報上看到批判周家莊搞資本主義、物質掛帥。第二年中央頒布“人民公社六十條”,規定體制是以隊為基礎,生產隊核算。周家莊實行的是大隊核算,需要立即改正。雷金河想不通。給周恩來寫信,中央書記處負責人彭真奉命親臨周家莊,地委書記和行署專員一左一右。小喳子面無懼色,據理力爭。彭真說:“你提的問題我不能回答,讓他們(地委)解決吧。”小喳子嬉皮笑臉地說:“就算判死刑,來個緩期執行吧。”一句話把彭真說笑了,對人說:“這人有頭腦。”小喳子總算過了這一關,“三包一獎”保留下來了。
張慶田堅決。一是堅決執行“作家深入生活”的指示,從1952年到1960年,一個猛子扎下去八年,對農業合作化和雷金河這個人物十分熟悉,寫了長篇小說《滄石路畔》。二是不顧“歌頌與暴露是作家的試金石”的告誡,以雷金河為原型,寫了短篇小說《老堅決外傳》,塑造了一個實事求是,敢開頂風船的典型人物,外號“老堅決”,名字叫甄仁,等于宣告素材來自真人真事。小說一出世就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在1964年大連小說會上,受到茅盾、趙樹理的肯定。不久康生認定“利用小說反黨是一大發明”,向作家開刀。張慶田首當其沖,先說是“中間人物”論,后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大毒草”。“文革”伊始,他和康濯、李滿天就被當做河北的“三家村”,成為大批判的重點。
中午張慶田送客回來,又被李滿天和我碰上。他說小喳子磨扇壓住手了,又面臨一道難關。安徽省聯產承包風行全國,我們這一帶行動落后,領導有壓力,又搞起一陣風,說不搞一刀切了,實際上切一刀。華北地區是革命老區,抗日戰爭時就興起互助合作。全國勞動模范多,山西第一,河北第二。有些老典型,搞了四十年農業合作化,對集體經濟有了感情。冷不丁叫散伙單干,適應不了。大勢所趨,別無選擇,聽說耿長鎖還大哭了一場。為了幫助雷金河轉彎子,上邊派來干部同吃同住同勞動,大有做不通工作不罷休之勢。省里有位領導還說:“周家莊還不散,就派個工作組去。”雷喳子還聽說,如今全省的釘子戶,只剩下周家莊和前南峪兩家了。
張慶田又給小喳子出主意,畢竟時代不同了,民主的氣氛比過去濃了。這次不要上書了,依靠群眾。小崗村是二十戶社員按手印,要分,咱也交給一個個生產隊表決。結果周家莊百分之百的戶也摁了手印,不分。因為生產生活水平明顯高于周圍,不分是民心所向。最后彭真和主管農業的杜潤生都表了態:“要實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老堅決又過了一關。
回頭看來,雷金河這次又“堅決”對了。像億萬農民分田到戶改變了命運一樣,周家莊發展集體經濟也未嘗不可。前幾天我又到周家莊,雖然雷金河和張慶田已經不在人世,他們精神的物質的遺產還在。如今的周家莊,寬闊的馬路,整齊的民居,儼然一座現代化的小城鎮。生產和文化有了較大的發展,一萬三千口人,四千名勞動力,三千人務工,一千人務農,去年農工商總產值五點六億元,人均收人八千二百六十二元,位于當地先進水平,農民享受著十一項福利待遇。眼前的農業觀光園,更是景色迷人,布谷聲聲,柳條絲絲,桃花灼紅,梨花雪白,油菜金黃,玉蘭淡紫,花香襲人,蜂飛蝶舞。林海中的紅領巾如跳動的火焰,公園里的湖水碧波蕩漾,農家食堂前游人熙熙攘攘,大鍋菜和黃窩頭冒著饞人的香味,等待著大家品嘗小康生活的滋味。路旁并立兩棵高高的白楊,身上長滿了“眼睛”,貪婪地守望著這里發生的一切。它們該是那一對生死不渝的朋友,那兩個風浪中的難兄難弟的化身,那兩個讓人永遠記住的老堅決。【作者堯山壁,河北隆堯人,1965年成為專職作家,1986年起任河北省作協主席,河北大學教授,文學創作一級,享受國務院津貼專家。曾任《河北文學》(《當代人》雜志前身)編輯。】
編輯:劉亞榮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