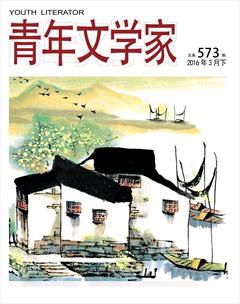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文人集團與賦體文學興盛之關系探微
摘 要:賦文體作為我國文學史上特有而古老的文學樣式之一,它的萌芽、繁榮、衍變都在文學史上留下了絢爛軌跡。同時不難發現賦文體的興盛與其同時代存在的文人集團的集體創作活動密切相關。文章試從特定歷史時空下文人集團的文學活動促使了賦文體的興盛進行論述。
關鍵詞:賦體文學;文人集團;興盛
作者簡介:陳志丹(1986-),女,河南省安陽縣人,單位:河南師范大學新聯學院,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兩漢文學。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6)-09-0-02
一、賦體文學溯源
賦體文學作為我國所特有而古老的一種文學樣式,萌芽于戰國,鼎盛于漢代,且在漫長的中國文學史中不斷涌現經典之作,呈現出頑強的生命力。在以詩、詞、歌、賦并稱的中國傳統文學體裁中,賦體文學占據著不可小覷的地位,且在很長一段時間以文壇霸主姿態示人。
(漢)許慎《說文解字》“賦,斂也,從貝武聲,方過切。”由此可知“賦”本義是貢賦,古代的時候人們將賦稅上交國家陳于庭上。且上古時敷、布、鋪同聲、同韻,因此賦有時也具有鋪陳之意。賦,引申入文學,誦詩述志或引詩言志皆稱為賦,《左傳》中多有如是記載。“不歌而誦謂之賦”、“使公卿至于列士獻詩,瞽獻曲,史獻書,師箴,瞍賦,朦誦,百工諫”“賦”即賦詩,賦詩皆不和樂。而現存最早以賦名篇的文學作品是戰國末期荀子的《賦篇》,《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也曾記載:“先王之賦頌,鐘鼎之銘”,故而可知戰國末期賦體文學已茁壯萌芽破土出世。
關于賦體文學起源學術界歷來莫衷一是、眾說紛紜,主要有古詩之流說、縱橫家說、隱語說、戰國諸子說等,臺灣學者陳韻竹在《論賦之起源》中如是論述:
在文學發展的長河中,任何一種新文類的發生與形成,其淵源都不會是單一的,“賦”亦是如此。新的文類必須在一種適宜的文化環境土壤中孕育,并汲取此前許多文學體裁的藝術技巧和語言樣式為養分,經過相當時間的成長,遂漸發展成自己的面貌與姿態,其中既是時代各種思想觀念的交融發酵,又是審美情趣的沉淀積累,最后表現為某種特定的語言組構形態,而這種作為某一文體外在語言組構形態的特征,便是區別于其他文體的形態標志。任何一種新文體的產生,它作為一種結果,必然是此前已經存在的諸多與之相關的要素共同作用的產物,也就是說,這種演進軌跡不是呈現為單一的直線型,它應當是多源頭的錯綜交織匯流。
陳先生論述甚是妥帖,任何一種文體的誕生,要具備適宜它生長的眾多因素才可以,然其最為重要的一個因素——市場需求,即賦體文學的最初功用——逞辭炫才、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同時確認了其創作主體、創作場景的特殊性。
二、齊稷下文人集團與賦之初現
《史記·田敬仲完世家》中記載:“宣王喜文學游說之士,自如鄒衍、淳于髡、田駢、接予、慎到、環淵之徒七十六人,皆賜列第,為上大夫,不治而議論。是以齊稷下學士復盛,且數百千人。”烜赫一時的稷下學宮中有一位對賦體文出現有卓越貢獻的學者——荀子,“年五十始來游學于齊”,且很受重視,在齊襄王時,“最為老師”“三為祭酒”。且《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也有相似的記載:“自鄒衍與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予、田駢、騶奭之徒,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豈可勝道哉。”
不論齊國國君出于政需還是受到當時招賢納士禮賢之風的影響,他把眾多不同學派的學士召集起來,為他們各抒己論,提供了自由辯論的場所平臺,讓其充分發揮自身的才能“各著書言治亂之事”。荀子《賦篇》作為我國第一篇以賦命名的文學作品,在這個學術開放自由,切磋技藝的創作氛圍中,不可不受其影響。加之齊楚之地特殊的文化和時代背景,一種新的文學樣式賦體文學誕生,并將長期稱霸我國文壇,這不無稷下文人集團的集體創作活動之功。
三、楚宮廷文人集團與賦之成熟
楚宮廷文人集團以宋玉、景差、唐勒等人為代表對賦體文學的大力創作是賦之成熟的關鍵。
楚襄王既登陽云之臺,令諸大夫景差、唐勒、宋玉等并造《大言賦》,賦畢而宋玉受賞。王曰:“……然則上坐者未足明賞,賢人有能為《小言賦》者,賜之云夢之田。”景差曰……唐勒曰……宋玉曰……王曰:“善,賜以云夢之田。
(《小言賦》)
楚襄王與唐勒、景差、宋玉游于陽云之臺。王曰:“能為寡人大言者上座。”王因唏曰……至唐勒,曰……至景差,曰……至宋玉,曰……(《大言賦》)
唐勒與宋玉言御襄王前,唐勒先稱曰……宋玉曰……
《諷賦》言:“楚襄王時,宋玉休歸,唐勒讒之于王。”王謂玉曰……玉曰……
綜上史料可知:國君的愛好、參與及出面組織競才類的文學創作活動促進了賦體的成熟,也體現出賦體文學之初的功用——逞才炫學,大小言賦中所呈現的文人集體文學創作活動“同賦一物”更是呈現出激烈的競賽因子,在獲勝物質上的獎勵外更使文人得到心理精神上的滿足。
四、梁園賓客集團與賦之盛行
賦體文學的真正盛行是從漢武帝時始,武帝之前中央朝廷漢景帝不喜好辭賦,所以具有賦學才能的文學之士不受重視,紛紛離去而被諸侯王所接納。在這些諸侯藩王中以吳王、淮南王、梁孝王三人尤為著名。
“漢興,諸侯王皆自治民聘賢,吳王招致四方游士,陽與吳嚴忌、枚乘等俱仕吳,皆以文辯著名。”
“淮南王安,為人好書,鼓琴,不喜弋獵狗馬馳騁,亦欲以行陰德推循百姓,流名譽。招致賓客方術之士數千人……”
“(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杰,自山以東游說之士莫不畢至。齊人羊勝、公孫詭、鄒陽之屬。”
在這些諸侯國的賓客中,不少人具備很高的文學才能。《漢書·藝文志》中曾記載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和“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賦作頗為繁盛,蔚為大觀,可惜大多散佚。吳王和梁孝王兩個藩國相繼出現鼎盛時期,使得一些文人經歷先游吳、后入梁的生命體驗。例如景帝時期的鄒陽、枚乘、嚴忌,“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孝王游”及“復游梁,梁客皆善屬辭賦,(枚)乘尤高”,據《漢書·藝文志》中記載,枚乘賦九篇,莊夫子(嚴忌)賦二十四篇,但鑒于史料有限已不可考證具體作品作于何地,現存世的枚乘作品僅《七發》一篇,然其在賦史的地位不容小覷,被視為漢大賦的濫觴之作,奠定了散體大賦的基礎。與其并行游吳的還有“朱買臣賦三篇”“嚴助賦三十五篇”,今皆已散佚殆盡。《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漢景帝不喜好辭賦,恰逢此時梁孝王來朝見漢景帝,跟隨在梁孝王身邊的有學之士有齊人鄒陽、淮陰枚乘、吳莊忌夫子等人“(司馬)相如見而悅之。因病免,客游梁”。據《漢書·藝文志》中記載“司馬相如賦二十九篇”,現可考存世者有七篇。司馬相如在賦史上的地位是不可被超越的,其賦作奠定了聘辭大賦的基本模式,并使賦文體長期稱霸我國文壇,鮮有能與之相匹敵者。
漢初的各諸侯國中文人集團賓客繼承了春秋戰國時期游士們的錚錚傲骨和相對自由的人身,如鄒陽、枚乘、嚴忌在吳國不受重視諫言無果,毅然決絕“皆去之梁,從孝王游”。當然各諸侯王的禮賢招攬與延納也是一方面原因,但這些文士更為看重是,居此既不能實現自我價值“去之”游他處。此時賦家更為追求精神上的同氣相求與切磋賦藝的愿景,才積極主動地參與文人集團,共同參與當時流行的賦體文學創作。如烜赫一時并為后世文人時時懷念的梁孝王文人集團,其賓客“皆善屬辭賦”。其中最負盛名的有枚乘、司馬相如等人,且對賦體文學的繁榮做出了巨大的貢獻。
史料記載,枚乘一生所好鐘于辭賦,隨心而行,追求賦趣相投的“英俊并游”。司馬相如亦是窮則獨善其身個時選擇了,與自己賦趣相投的梁園賓客。而相如卻也不負這個人才濟濟、以竟才炫學為能事的文人集團,創作出了漢大賦的典范之作亦自己的成名作——《子虛賦》。《史記·司馬相如列傳》記載梁孝王讓司馬相如與諸生同舍,“相如得與諸生游士居數歲,乃著《子虛》之賦。”也正是由于這篇諸侯游獵賦偶然間被漢武帝發現賞識,才得以為漢賦的鼎盛伏下契機。
“(漢)武帝春秋二十九年乃得皇子,群臣喜,故皋與東方朔作《皇太子生賦》及《立皇子禖祝》,受詔所為,皆不從故事,重皇子也”,由此可知作賦在當時的盛行,為同題作賦,其結果“皋為賦善于朔也”。這種文人集團集體創作活動對賦文體的發展、衍變具有不可抹煞的功績。
綜上論及,齊稷下文人集團對賦之初現,楚宮廷文人集團對賦之成熟,梁孝王文人集團、漢武帝言語侍從對賦之盛行,無不起到不可小覷之功。
參考文獻:
[1](漢)司馬遷撰.史記[M].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9月第1版.
[2](東漢)班固撰.漢書[M].鄭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10月第1版.
[3]郭英德.中國古代文人集團與文學風貌[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11月第1版.
[4]郭建勛.先唐辭賦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5]曹虹.中國辭賦源流綜述[M].北京:中華書局,2005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