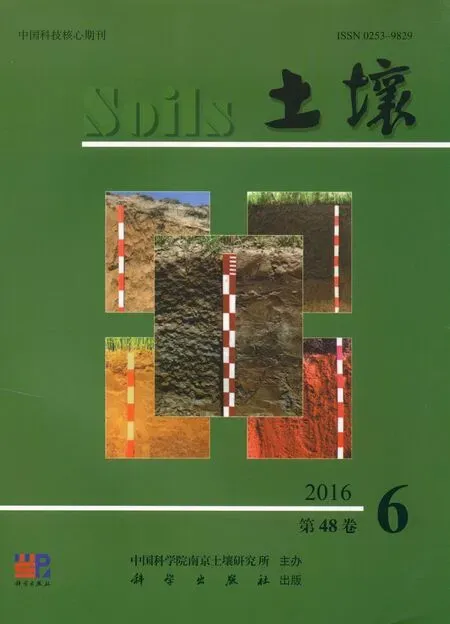連作障礙發生機理研究進展①
侯 慧,董 坤,楊智仙,董 艷*,湯 利,鄭 毅,4
(1 云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昆明 650201;2 云南農業大學食品科技學院,昆明 650201;3 云南大學,昆明 650091;4 西南林業大學,昆明 650224)
連作障礙發生機理研究進展①
侯 慧1,董 坤2,楊智仙3,董 艷1*,湯 利1,鄭 毅1,4
(1 云南農業大學資源與環境學院,昆明 650201;2 云南農業大學食品科技學院,昆明 650201;3 云南大學,昆明 650091;4 西南林業大學,昆明 650224)
隨著集約化種植程度的不斷提高,作物連作導致產量和品質下降,土傳病害嚴重發生,嚴重制約了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連作障礙發生機理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之一。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從多方面、多角度對連作障礙進行了研究,但這些研究多集中于單一因素分析,缺乏對不同因子內在相互關系和本質的了解,未能深入揭示連作障礙發生的真正原因。深入認識連作障礙的成因及各要素間的互作關系是防控作物土傳病原微生物生長、緩解連作障礙、實現農藥使用量零增長的基礎。本文從土壤理化性狀及生物學性狀惡化、植物生理抗性下降和連作自毒作用等方面系統綜述了連作障礙發生機理,分析了連作障礙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并對該領域未來的研究方向進行了展望,以期為尋找安全、環保和有效的緩解措施提供理論依據。
連作障礙;土傳病害;自毒作用;根際微生物
經濟和技術的飛速發展,使高產品種單一連作種植在我國嚴重發生,商品化生產加劇了作物連作現象的發生[1]。作物連作以高投入和高產出為特點,且對農藥的依賴程度較高,隨之而來的連作障礙問題日益突出,其中以土傳病害發生和作物生長受抑為主要表現,連作障礙已成為農業可持續發展的重大問題之一[2]。從發病面積和相對比例上看,目前我國是世界上作物土傳病害發生率最高和最嚴重的國家,我國農藥使用量持續增加與土傳病害的頻繁發生密切相關,實現農藥使用量零增長,甚至負增長目標,首先必須防控作物土傳病害的農藥使用量[1]。因此探究作物連作障礙的成因及尋求克服或緩解措施已成為亟待解決的問題[3–4]。作物連作現象在時間和空間上有很大的跨度,一方面,早在公元前 300 年就出現了連作現象,隨之而來的連作障礙也不可避免;另一方面,連作在世界各地普遍存在,在亞洲的日本、中國和印度等地均有較大面積的分布[5]。許多大田作物、經濟作物、園藝植物(包括瓜果類蔬菜和觀賞花卉)和中草藥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連作障礙問題,尤其以中草藥和蔬菜作物發生連作障礙較為普遍且嚴重[6]。
連作障礙是長期以來困擾農業生產的復雜問題,作物連作障礙形成機理與防治一直是國內外學者研究的熱點。多年來國內外許多學者分別從土壤物理、化學、生物學和化感作用等方面對連作障礙的機理進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很有意義的結論。本文根據近年來國內外學者在連作障礙方面的研究進展,概述了作物連作障礙的危害及成因的最新研究進展,并分析了連作障礙各形成因素間的相互關系,對進一步深入認識連作障礙發生原因及形成機理具有重要作用,旨在為促進作物生長并減輕土傳病害發生、實現農藥使用量零增長、促進我國農業可持續發展提供理論依據。
1 連作的危害
1.1 連作種植對作物生長的影響
連作種植不同程度地影響了作物的植株形態、葉片的光合生理特性和活性氧代謝。作物株高降低、葉面積減小、葉綠素含量降低、光合速率下降等是作物對連作的負反饋。通常這種效應與作物連作年限相關,連作年限的增加將加劇上述危害。如三七連作 2 年后種子的發芽率和發芽指數最低,且顯著低于對照[7]。隨連作年限延長,辣椒地上部干鮮重顯著下降,株高、莖粗均呈下降趨勢,且在連作 8 年差異達到顯著水平[8]。作物連作不僅抑制地上部的發育,而且阻礙作物地下部的生長。根系作為作物水分及土壤營養元素的吸收器官也影響著氨基酸和激素等重要代謝物質的合成,作物根系能夠對外界脅迫做出反應并反饋給地上部,直接影響作物的生長和營養狀況及產量水平。長時間連作條件下,馬鈴薯植株根系活力和總吸收面積顯著下降,使根系對養分及水分吸收能力減弱,減少了代謝物質的合成,進而影響塊莖膨大和干物質填充,這共同影響了塊莖產量的形成和地上部植株的正常生長發育[9]。連作土壤中的根皮苷、間苯三酚、根皮素、對羥基苯甲酸和肉桂酸均抑制了平邑甜茶幼苗的生長,且對根系的影響程度高于地上部分,表現為根系中保護酶活性降低,根冠比降低,增加了過氧化氫 (H2O2)、超氧陰離子自由基 (O2·–) 以及丙二醛 (MDA) 含量,線粒體膜通透性轉換孔 (MPTP)開放程度增大,線粒體膜電位降低,細胞色素Cyt c/a比值下降[10]。
1.2 連作種植對作物病害發生的影響
現代單一作物種植模式下,作物生長期病原微生物的生長和繁殖速率遠高于傳統種植模式。隨寄主作物連作年限的增加,病原微生物數量終將超過發病臨界值,導致土傳病害發生。同一作物連續種植時,因無病原微生物數量的自然衰減過程,在更短的種植時間內,土傳病原微生物的數量即可達到使作物致病的臨界水平[1]。當歸、丹參、黃瓜、茄子、蠶豆、花生、小麥、番茄、西瓜、煙草等多種作物和中藥材連作種植均可導致土傳病害嚴重發生,致使作物產量下降、品質變劣。西洋參和人參連作后土傳病害銹腐病、疫霉病和根腐病顯著高于正茬[11]。蘭州百合長期連作后導致由尖孢鐮刀菌引起的蘭州百合枯萎病嚴重發生,是導致蘭州百合土傳病害高發的重要因素[12]。茄子黃萎病、枯萎病和青枯病等土傳病害隨連作年限增加逐年加重[13]。 我們前期對蠶豆連作障礙的研究結果也證實,隨連作年限增加,蠶豆枯萎病發病率越來越高。同種作物在不同生育時期往往也表現為不同的病害頻發,花生連作條件下,根腐病在苗期多發,且發病率隨連作年限成倍增加;花果期多葉斑病,病株率近100%;隨連作年限的延長,結莢成熟期的青枯病、白絹病則也從無到有[14]。土傳病害嚴重發生是連作種植最直接、最明顯的障礙因子。很多研究表明對連作土壤進行土壤滅菌是減輕再植病害的有效手段,說明連作條件下土壤中病原物激增是引起再植病害的重要因素之一[15]。
2 連作障礙的成因
近幾十年來,很多學者從土壤學、作物營養學、微生物學和栽培學等多個學科入手,對蔬菜、果樹、中藥材等多種作物的連作障礙問題進行了大量研究并取得了顯著進展。不同作物連作障礙發生的原因差別很大,但主要來自土壤[16]。多年來國內外研究者對連作障礙的形成機理進行了研究并取得顯著進展,這些研究涉及土壤養分虧缺、土壤pH和物理性狀變化、土壤微生物區系和多樣性變化、土傳病害和化感自毒物質積累等內容[17–21]。在連作障礙的眾多因素中,土傳病害一直是連作障礙的研究重點[17,22],多年來被認為是大多數作物產生連作障礙的主要原因之一。除土壤因素外,連作作物自身的抗性也對土傳病害的發生產生影響,因此很多研究者也從作物相關防御酶活性、根系分泌物差異等方面開展了相應的研究[23–24]。更為重要的是,連作障礙各形成因素間還具有相互影響,進一步加劇連作障礙的發生。本文分別從土壤環境、作物生理抗性和自毒作用等方面及這些因素相互作用對連作障礙形成的影響進行概述。
2.1 土壤方面
2.1.1 土壤養分失衡,抑制作物養分吸收 由于土壤中原有礦質營養元素的種類及含量是固定的,加之作物對其具有特定的吸收規律,隨連作年限的增加,作物需求較多的元素在土壤中越來越少,而其他不被作物吸收的元素越來越多,造成土壤養分失衡。研究表明,隨種植年限增加,土壤有機質、全氮和全磷顯著下降,土壤速效磷和速效鉀均顯著增加,而土壤堿解氮含量很低[25]。棉花連作后土壤堿解氮含量嚴重超標,土壤有效鉀含量下降,表明棉花連作使土壤中氮、磷、鉀比例失調[26]。三七連作栽培使土壤中無機元素富集,再加之過度施用化學肥料,更易導致土壤表層某些元素的集聚或缺素,同時營養元素富集還會滋長病原真菌積累,加重土壤病害,抑制三七植株生長,最終加劇三七連作障礙的發生[27–28]。花生連作條件下,某些有效養分,特別是微量元素的缺乏,一方面降低了植物的抗病性,誘導根系分泌物增加,而這其中可能包括了抑制花生生長的化感物質;另一方面造成微生物區系變化,因為有效養分與土壤微生物區系密切相關[29]。表明連作障礙的發生可能與某些養分的含量降低有關。
2.1.2 土壤生物學性狀惡化 盡管引起連作障礙的原因較多,但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土壤微生物區系和多樣性失調,有益微生物減少,病原微生物富集而引發植物的各種土傳病害[16]。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多樣性及微生物區系變化直接影響土壤的健康狀況,進而影響作物的生長狀況[30–31]。連作障礙與上壤微生物的種類、數量和多樣性密切相關。連作擾亂了土壤微生物生態平衡,改變土壤微生物種群和功能。地黃連作后根際累積了大量酚酸類物質導致土壤微生物生態環境改變[32–33]。花生連作引起土壤中微生物選擇性富集,細菌數量總體下降,真菌數量顯著上升,病原菌數量急劇增大,土壤微生物從細菌主導型向真菌主導型轉化,使病原菌更容易侵染植物而引發作物的各種土傳病害[20]。花生長期連作顯著增加了土壤病原菌的豐度,而這些增加以犧牲土壤中一些有益真菌為代價[34]。Ying等[35]對人參連作障礙土壤微生物群落研究發現,隨連作年限的增加,土壤中有害菌積累遞增,有益微生物數量遞減。隨連作年限的增加,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指數和豐富度指數均降低,原因是連作土壤連續種植單一作物,根系分泌物種類單一,為微生物提供的營養相對單一、根系活動對微生物的激活作用也相對較小,激活的微生物種類單一,導致微生物多樣性較低[36]。煙草根際細菌群落多樣性指數和豐富度指數隨連作年限的增加呈現先增后減的趨勢,連作 4年后細菌群落的多樣性水平顯著降低[37]。黃瓜連作第11茬后微生物碳代謝能力顯著下降,微生物多樣性水平顯著降低,偏好羧酸類碳源的微生物種群得到富集,對單一碳源的高利用碳源數顯著低于1茬,說明連作11茬后的營養基質中微生物種群結構發生了單一化趨勢而影響了黃瓜的正常生長[38]。
除直接測定土壤微生物區系及多樣性變化外,土壤酶活性的測定亦能反映土壤生態系統中營養元素轉化能力及土壤生物活性變化,可用于衡量土壤的健康狀況。土壤酶活性增強意味著土壤生物活性提高,能增強植株的抗性。單一作物持續連作會使蔗糖酶、脲酶、磷酸酶等土壤酶活性隨連作時間延長而下降[39]。隨花生連作年限增加,過氧化氫酶活性下降,使根系的毒害作用加重而引起連作障礙[40]。三七連作后土壤中關鍵酶的活性下降,造成土壤解毒能力降低,這可能將間接加劇土壤中自毒物質的積累,抑制植物生長,誘導連作障礙發生[28]。
可見,連作障礙發生與根際生物學性狀惡化密切相關,連作引起的土壤理化性狀改變及作物根系分泌物和殘茬在土壤中的長期存留均可導致土壤生物學性狀的變化,直接影響作物生長及抗病能力而導致連作障礙發生[34]。
2.2 作物生理抗性下降
連作不但惡化作物生長的土壤環境,還直接降低寄主作物的自身抗性。連作條件下累積的自毒物質可通過影響寄主作物的生理生化過程而降低寄主作物對病原菌的抵抗能力。
過氧化物酶(POD)及過氧化氫酶(CAT)是作物防御體系中的重要酶類,當作物遭到逆境脅迫時,POD和CAT可通過清除作物體內過量的活性氧和細胞中的過氧化氫,使作物產生耐受性,提高抗逆境能力。研究表明,作物的POD 和 CAT 活性隨連作年限的增加呈下降趨勢,導致膜系統的結構和功能受到損傷,植物對病原菌的抵抗能力下降,病害易發[9]。
作物膜質過氧化的程度和水平一般用膜質過氧化作用的產物丙二醛(MDA)的含量來衡量,膜質過氧化的程度及水平與作物膜質損傷密切相關。研究表明,作物連作產生的自毒物質不同濃度外源添加均促進了作物幼苗根系中MDA的合成,使MDA含量升高,從而降低根系活力,破壞細胞質膜的穩定性和完整性,作物對病原菌的抵抗能力下降[41]。隨連作年限增加,作物MDA含量在整個生育期內總體上呈升高趨勢[25]。連作馬鈴薯葉片 MDA 含量增加導致保護酶系統遭到破壞,使活性氧自由基大量攻擊細胞質膜系統,導致細胞的正常功能受到極大削弱[9]。可見,連作破壞了作物抗氧化系統而不能有效清除自由基,造成自由基過量積累,導致一系列膜功能障礙,進一步加劇連作障礙發生。
2.3 連作自毒作用
連作障礙嚴重制約了現代農業的可持續發展,大量研究表明自毒物質產生的自毒作用是導致作物連作障礙的主要因子之一。
2.3.1 自毒物質產生的途徑 作物可通過不同途徑向環境中釋放化感自毒物質,直接或間接地影響自身的生長,其中地上部揮發和淋溶、根系分泌及殘茬腐解是自毒物質最主要的產生途徑。揮發和淋溶:作物地上部主要通過揮發和淋溶產生自毒物質,在一定條件下,揮發和淋溶能夠相互轉化,共同發生。揮發多發生在干旱高溫時期,自毒物質通過作物體表器官揮發釋放到空氣中,直接或間接作用于同種或同科作物。雜草勝紅薊的新鮮葉片含有揮發物和揮發油,能夠抑制受試幼苗的生長[42]。淋溶易在多雨潮濕時期發生,作物體表含有的自毒物質通過雨、霧淋溶被釋放到周圍環境中抑制自身或其他作物生長。李紹文等[43]的研究表明桉樹葉片產生的酚類物質被淋洗下來會抑制亞麻的生長。
根系分泌:連作條件下作物根系會分泌化感自毒物質到根際土壤中,對作物產生直接毒害作用,有些需要通過與土壤微生物互作間接影響作物生長。研究發現黃瓜、大豆、煙草、地黃和西洋參等忌連作作物的連作障礙現象與根系分泌物中的化感物質密切相關[44]。肖靖秀[45]通過 HPLC檢測出蠶豆根系分泌物中含有羥基苯甲酸、香草酸和丁香酸等自毒物質。Wu等[21]從蘭州百合根系分泌物中檢測鄰苯二甲酸等多種化感物質。棉花根系分泌物含有沒食子酸、綠原酸、香草酸和香豆酸等自毒物質[46]。
植物殘體腐解:植物殘體釋放自毒物質主要有直接和間接兩個途徑,直接途徑是植物殘體腐爛后直接釋放出自毒物質,而間接途徑是通過土壤微生物的分解作用而釋放出自毒物質。不同作物殘體腐解釋放的自毒物質種類和含量不同。李坤等[47]的研究表明葡萄根系腐解物中含有苯甲酸、苯丙酸和水楊酸3種酚酸類自毒物質。即使是同種作物,殘體腐解不同階段釋放的自毒物質種類和含量也不同。趙先龍[48]的研究表明,在玉米秸稈腐解60、120和180天腐解液中均檢測出對經基苯甲酸、苯甲酸、丁香酸、鄰苯二甲酸、香草酸和阿魏酸等自毒物質,但在60天腐解液中的種類最多,除檢測到上述6種酚酸外,還檢測到香豆酸、苯丙酸、丁二酸、十四碳酸、肉桂酸等自毒物質。
2.3.2 自毒物質的種類 研究發現,萜類和酚類是高等植物的主要化感物質。萜類化感物質在高等植物多以揮發油的形式存在,主要包括單萜、雙萜、倍半萜、三萜及多萜等。萜類化感物質多通過揮發和根系分泌等途徑進入土壤,具有很強的化感活性,往往較低的濃度即能表現出很強的抑制作用[49]。酚酸類物質為芳香環上帶有活性羧基的有機酸,是目前研究最多、活性較強的一類化感物質[50–51]。研究者均把酚酸類物質作為化感自毒作用研究的重點,成為公認的化感自毒物質[44,52]。酚酸類化感物質主要包括羥基苯甲酸和肉桂酸衍生物、黃酮類、醌類和單寧五大類[53]。研究者已從多種連作障礙作物的多種組織和根系分泌物中分離出十余種酚酸類化感物質,其中阿魏酸、對羥基苯甲酸、肉桂酸和香草醛等均被認為是最主要的酚酸類物質[50,54]。導致不同作物發生連作障礙的酚酸種類不同,且自毒物質的來源也不同,自毒效應也因自毒物質濃度不同而異。He等[55]從西洋參須根中分離到反式肉桂酸、對香豆酸、阿魏酸、香草酸、香草醛、水楊酸、丁香酸、苯甲酸和對羥基苯甲酸這9種酚酸類自毒物質,它們對西洋參胚根生長具有抑制作用。本課題組在前期研究中從蠶豆根系分泌物中分離出了阿魏酸、香草酸、苯甲酸、丁香酸、水楊酸和對羥基苯甲酸等自毒物質,并且以肉桂酸的含量最高。同種作物的不同部位自毒物質含量也不同。王勇等[56]的研究表明,核桃樹體內自毒物質的分布隨器官組織的不同而有差異,其中枝條韌皮部>葉片>芽體>枝條木質部,且不同核桃品種間自毒物質含量也存在差異性。
2.3.3 自毒物質對種子萌發和作物生長的影響 自毒物質通過抑制作物的種子萌發來影響其生長發育。Yan等[57]研究表明,酚酸類自毒物質對作物種子萌發具有較強的抑制活性。蒙古黃芪植株水浸液對其自身植株生長、種子萌發均有抑制作用,自毒作用明顯[58]。對羥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豆酸對花生發芽有顯著的影響,且這種影響效應與酚酸物質的種類及濃度有關[59]。除影響作物種子萌發外,自毒物質還對作物生長產生抑制效應。水培溶液中添加 p-香豆酸能顯著抑制西洋參植株地上部分的生長,展葉率、株高、冠幅均明顯下降,高濃度時約85% 葉片不能完全展開,葉片生長受到嚴重抑制[60]。廣藿香不同濃度的莖、葉和根提取物顯著降低了廣藿香的株高和根重[61]。自毒物質不僅抑制作物地上部的生長,而且還阻礙地下部的發育。土壤中酚酸類物質的積累使西洋參根系受到一種逆境脅迫,根皮苷、根皮素、對羥基苯甲酸以及肉桂酸處理顯著降低了西洋參的根冠比,證明了這些酚酸類化合物對西洋參根系的影響程度大于地上部分[60]。酚酸類物質脅迫下,蘋果幼苗總根長和平均根直徑均有所下降,這些指標的下降導致根系對養分吸收能力降低,最終使蘋果地下部干物質積累量的減少[10]。研究表明,自毒物質對作物生長的影響表現出濃度效應,即自毒物質積累濃度越高對作物的抑制效應越強[62]。
2.4 連作障礙各因素的相互關系
很多學者認為產生連作障礙的原因錯綜復雜,是作物–土壤兩個系統內部諸多因素綜合作用的外觀表現[34]。連作障礙的形成并非只是單一因素作用的結果,而是存在著多因子間的輔助或協同效應。
2.4.1 連作自毒物質與土傳病害發生的關系 大量研究表明,作物連作自毒作用與土傳病害發生密切相關。近年來的研究結果表明,凡是容易引起自毒作用的作物一般也易引起土傳病害產生而導致連作障礙[23,63]。自毒物質降低了黃瓜生長能力和抵抗力,與多年累積的病原菌共同作用,形成嚴重的土傳病害,是連作障礙產生的重要原因[64]。茄子根系分泌物中自毒物質香草醛和肉桂酸助長了茄子黃萎病的發生[65]。自毒物質對羥基苯甲酸、香草酸和香豆酸助長了花生枯萎病的發生[66]。苯甲酸和肉桂酸處理顯著提高西瓜幼苗枯萎病的發病率,隨苯甲酸和肉桂酸處理濃度提高,西瓜枯萎病病情指數和死苗率逐漸上升[66]。隨酚酸類物質處理濃度升高,土壤尖孢鐮刀菌和甜瓜疫霉菌數量呈持續上升趨勢,導致黃瓜枯萎病發生[67]。
自毒物質通過對病原菌直接表現出刺激作用,促進病原菌增殖而助長土傳病害的發生。作物根系分泌物和殘茬腐解物可為連作土傳病原菌提供碳源,從而促進病原菌繁殖或孢子萌發,減弱或消除了某些有益菌的拮抗作用,使有害菌增殖,從而造成病害的嚴重發生[16,51]。連作西瓜植株腐解物積累大大刺激了尖孢鐮刀菌的生長,尖孢鐮刀菌的數量顯著增加,且感病品種比抗病品種更容易促進其生長[63]。對連作百合的研究表明,連作百合自毒物質鄰苯二甲酸顯著刺激了病原菌產毒并提高了病程相關水解酶的活性,從而促進了百合枯萎病的發生[12]。
自毒物質加劇土傳病害發生的能力與自毒物質的種類和濃度密切相關。在草莓腐爛組織和土壤中含量較高的香豆酸,低濃度 (50 mg/L) 處理顯著促進了草莓冠腐病病原菌菌絲的生長并提高了冠腐病的病情指數,而高濃度 (>200 mg/L) 處理顯著抑制了病原菌菌絲生長,對冠腐病危害無顯著影響[68]。隨甜瓜根系殘茬腐解液處理濃度的提高,枯萎病菌的產孢量和菌絲長度顯著增加,孢子萌發率顯著提高[69]。黃瓜根系分泌物中的自毒物質對尖孢鐮刀菌菌絲生長和孢子萌發具有不同程度的促進作用,其中肉桂酸、阿魏酸、苯甲酸對甜瓜枯萎病病情指數有顯著的促進作用,處理濃度越高,甜瓜枯萎病發生越嚴重[70],表明化感自毒物質具有促進土傳病害發生的效果[71–72]。
2.4.2 連作自毒物質與土壤微生物的關系 隨著對根際微生態環境中植物–土壤–微生物相互作用各過程的深入了解,研究者認為土傳病害的發生和植株發育不良是作物連作障礙發生的直觀表象,但其致病的根本原因是根系分泌物和腐解物中酚酸類化感物質引起的土壤微生物區系失衡,最終導致土壤中病原菌激增而引發嚴重的土傳病害[19]。化感自毒物質是土壤微生物群落演變的重要推動者,長期連作條件下,土壤中積累了大量的植物分泌物和腐解物,其釋放的酚酸不斷累積,極大地控制著土壤中優勢微生物種群[16],因此自毒物質酚酸與土壤微生物數量和活性關系密切[51]。Zhou和 Wu[73]通過外源添加黃瓜自毒物質香豆酸至土壤中,導致根際土中細菌顯著減少,同時還造成病原菌大量繁殖增長,表明自毒物質顯著影響了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Guo等[74]對葡萄連作障礙的研究表明,外源添加葡萄連作自毒物質對羥基苯甲酸后改變了土壤細菌和真菌的群落結構和功能多樣性,同時對羥基苯甲酸也影響葡萄的根系分泌物及葡萄根系分泌物與根際微生物的互作,對羥基苯甲酸介導下微生物和根系分泌物的互作是影響對羥基苯甲酸化感自毒潛力表現的關鍵因素,且該互作也是影響葡萄連作障礙的主要原因。地黃須根自毒物質阿魏酸和對羥基苯甲酸一方面加劇了病原菌對地黃的致害過程,另一方面促進了真菌繁殖生長,進一步增強真菌對寄主的致害作用[71]。外源添加苯甲酸不僅使土壤微生物功能多樣性降低,而且促進了土壤中病原菌增殖并抑制了拮抗菌的生長。自毒物質對病原菌具有正趨向作用而對拮抗菌卻具有排斥作用,病原菌可以更好地利用作物連作累積的自毒物質,從而比拮抗菌更易定殖于作物根際,這可能是連作障礙造成土傳病害流行暴發的機理之一[75]。表明化感自毒物質是連作障礙產生的初始誘因,化感自毒物質通過誘導改變根際微生物區系、群落結構和多樣性,影響有益微生物與病原菌的互作關系而促進連作障礙發生。
2.4.3 連作自毒物質與作物生理生化和結構抗性的關系 黃瓜自毒物質肉桂酸使植株保護酶活性降低,根系活性氧自由基含量增加并加速了膜脂過氧化程度,從而刺激了病原菌使病菌更易侵入,導致發病率高,土傳病害嚴重發生[23]。蘆筍自毒物質損傷蘆筍根尖和表皮細胞,降低過氧化物酶活性,提高電解質外滲,從而增加了鐮刀菌的浸染機會[76]。草莓根系分泌物中酚酸物質使根系TTC還原活性降低、相對電導率增大、SOD酶活性降低及MDA生成量增多、葉片光合作用受抑制程度增加,進而加重草莓根系養分和水分外滲,根系抗病性下降,枯萎病嚴重發生[77]。對羥基苯甲酸處理使草莓體內對枯萎病菌“抑制型”氨基酸如天冬氨酸含量降低,但提高了“促進型”氨基酸種類和含量[78]。對羥基苯甲酸脅迫下,尖孢鐮刀菌菌絲在草莓根系中的侵染速率明顯加快,對根系表皮、皮層、中柱薄壁細胞及導管壁結構的破壞程度也明顯加重[77]。表明連作自毒物質通過影響寄主作物的生理生化過程和組織結構而影響寄主抗性,影響土傳病害的發生和發展。
3 展望
3.1 自毒作用與連作障礙
作物可通過不同途徑向環境中釋放化感自毒物質,加劇連作障礙的發生,但目前對根系分泌自毒物質的研究較多,缺乏對其他釋放途徑產生的自毒物質的研究。由于尚不清楚植株水浸液、殘茬腐解等途徑釋放的自毒物質與根系分泌的自毒物質種類含量是否一致,根系分泌的自毒物質能否涵蓋作物釋放的所有自毒物質尚不明確,同時這些自毒物質對作物的自毒效應也不清楚。因此,加大對其他釋放途徑產生的自毒物質的研究也必不可少。另外,土壤環境極其復雜,自毒物質在土壤中易受土壤微生物、土壤理化性狀,質地等因素的影響,而測定自毒物質在土壤中的增減也是研究其自毒效應的關鍵。
不同作物連作所產生的自毒物質種類不同,即使是同種作物在不同生育期和不同環境條件下連作產生的自毒物質種類和數量也有差異[79]。目前的研究一方面多集中在對作物某一個生育期收集到的自毒物質進行分析,缺少對作物整個生長階段中各個生育期收集到的自毒物質進行研究。另一方面多集中在對作物某一連作年限釋放的自毒物質進行研究,而缺少對連作年限連續性條件下自毒物質的研究,對于自毒物質在不同連作年限下對作物的自毒作用是否相同尚不明確。因此,對作物在不同連作年限、不同生育期通過不同途徑釋放的自毒物質有必要進行收集并研究其對作物的自毒作用。
3.2 根際微生物與連作障礙
土壤營養元素的循環受根際土壤微生物數量、多樣性、區系等變化的影響,進而影響作物的生長發育。對作物連作障礙的研究表明,連作作物根系分泌物改變了土壤微生物類群,通過控制有益微生物增殖,增加了根際有害微生物的定植,最終使土壤生物多樣性降低,加劇病原菌繁殖。因此根系分泌物的種類與病原菌增殖的關系等問題將是今后研究的新熱點。連作導致有益微生物減少,但究竟是哪些有益微生物的減少引起病原菌增殖,有關根系分泌物–病原菌–有益微生物的互作關系尚不清楚。近年發展起來的高通量測序技術,對深入研究連作對土壤微生物群落組成和功能變化是較好的技術手段,該技術能夠分析某些特定的菌群,如細菌、氨氧化細菌、真菌及一些植物病原菌 (鐮刀菌類、茄科勞爾氏菌) 的變化情況,測定的微生物種類和數量更加多樣、豐富,結果也會更加可靠[80]。因此,采用該測定技術可明確連作土壤中發生變化的關鍵微生物種群,對進一步探明連作障礙成因及尋找有效的調控措施尤為重要。
3.3 多因子協同作用共同導致連作障礙
在尋求連作障礙防治措施中,我們發現單純的土壤滅菌只能在短期內能控制某些病害的蔓延,并不能從根本上解決作物連作障礙問題,表明連作障礙的發生不僅僅是單一因素所導致的,而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目前多數研究仍停留在單因子水平上,缺乏對不同因子內在相互關系和本質的了解,未能深入揭示連作障礙發生的真正原因。如酚酸累積–微生物變化–土傳病害發生的關系,長期連作條件下,土壤中累積的酚酸使土壤微生物群落結構改變、病原真菌富集、微生物群落環境惡化,而惡化的微生物群落結構使土壤中的酚酸物質降解緩慢,造成酚酸物質積累,積累的酚酸不僅繼續改變微生物群落結構,而且會抑制作物生長,提高作物發病率,如此惡性循環,產生作物連作障礙[59]。但是,化感自毒物質組成差異對土壤微生物群落變化有何影響尚不清楚。且不同作物及不同土壤的連作障礙可能有不同原因與主次,今后的研究需綜合考慮各個因素間的相互制約關系,尋找關鍵的突破點。
[1] 蔡祖聰, 黃新琦. 土壤學不應忽視對作物土傳病原微生物的研究[J]. 土壤學報, 2016, 53(2): 305–310
[2] 蔡祖聰, 張金波, 黃新琦, 等. 強還原土壤滅菌防控作物土傳病的應用研究[J]. 土壤學報, 2015, 52(3): 469–475
[3] Louwsa F J, Rivard C L, Kubota C. Grafting fruiting vegetables to manage soilborne pathogens, foliar pathogens, arthropods and weeds[J]. Scientia Horticulturae, 2010, 127: 127–146
[4] Ratnadass A, Fernandes P, Avelino J, et al. Plant species diversity for sustainable management of crop pests and diseases in agroecosystems: A review[J]. Agronomy fo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2012, 32: 273–303
[5] 葉素芬. 黃瓜根系自毒物質對其根系病害的助長作用及其緩解機制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學, 2004
[6] 張曉玲, 潘振剛, 周曉鋒, 等. 自毒作用與連作障礙[J].土壤通報, 2007, 38(4): 781–784
[7] 張子龍, 王文全, 楊建忠, 等. 三七連作土壤對其種子萌發及幼苗生長的影響[J]. 土壤, 2010, 42(6): 1 009–1 014
[8] 郭紅偉. 連作對土壤性狀和辣椒生育、生理代謝的影響[D].南京: 南京農業大學, 2011
[9] 沈寶云, 劉星, 王蒂, 等. 甘肅省中部沿黃灌區連作對馬鈴薯植株生理生態特性的影響[J]. 中國生態農業學報, 2013, 21(6): 689–699
[10] 王艷芳, 潘鳳兵, 展星, 等. 連作蘋果土壤酚酸對平邑甜茶幼苗的影響[J]. 生態學報, 2015, 35(19): 6 566–6 573
[11] 于妍華. 西洋參連作障礙微生態機制及生防放線菌的抗病作用[D]. 陜西楊凌: 西北農林科技大學, 2011
[12] Wu Z J, Yang L, Wang R Y, et al. In vitro study of the growth, development and pathogenicity responses of Fusarium oxysporum to phthalic acid, an autotoxin from Lanzhou lily[J]. World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5, 31: 1 227–1 234
[13] 郝晶, 周寶利, 劉娜, 等. 嫁接茄子抗黃萎病特性與根際土壤微生物生物量和土壤酶的關系[J]. 沈陽農業大學學報, 2009, 40(2): 148–151
[14] 孫權, 陳茹, 宋乃平, 等. 寧南黃土丘陵區馬鈴薯連作土壤養分、酶活性和微生物區系的演變[J]. 水土保持學報, 2010, 24(6): 208–212
[15] 張樹生, 楊興明, 茆澤圣, 等. 連作土滅菌對黃瓜(Cucumis sativus)生長和土壤微生物系的影響[J].生態學報, 2007, 27(5): 1 809–1 817
[16] Hiddink G A, Termorshuizen A J, van Bruggen A H C. Mixed cropping and suppression of soilborne diseases// Lichtfouse E. Genetic engineering, biofertilisation, soil quality and organic farming, sustainable agriculture reviews[M]. Netherlands: Springer, 2010, 4: 119–146
[17] 董艷, 湯利, 鄭毅, 等. 施氮對間作蠶豆根際微生物多區系和枯萎病發生的影響[J]. 生態學報, 2010, 30(7): 1 797–1 805
[18] 董艷, 董坤, 湯利, 等. 小麥蠶豆間作對蠶豆根際微生物群落功能多樣性的影響及其與蠶豆枯萎病發生的關系[J]. 生態學報, 2013, 33(23): 7 445–7 454
[19] Zhou X G, Yu G B, Wu F Z. Responses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in the rhizosphere of cucumber (Cucumis sativus L.) to exogenously applied p-Hydroxybenzoic acid[J]. Journal of Chemical Ecology, 2012, 38: 975–983
[20] Li X G, Ding C F, Zhang T L, et al. Fungal pathogen accumulation at the expense of plant-beneficial fungi as a consequence of consecutive peanut mono culturing[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14, 72: 11–18
[21] Wu Z J, Xie Z K, Yang L, et al. Identification of autotoxins from root exudates of Lanzhou lily (Lilium davidii var. unicolor) [J]. Allelopathy Journal, 2015, 35: 35–48
[22] Ren L X, Shi M S, Xing M Y, et al. Intercropping with aerobic rice suppressed fusarium wilt in watermelon[J]. Soil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2008, 40: 834–844
[23] Ye S F, Zhou Y H, Sun Y, et al. Cinnamic acid causes oxidative stress in cucumber roots, and promotes incidence of Fusarium wilt[J]. Environmental and Experimental Botany, 2006, 56: 255–262
[24] Xu W H, Dan L, Wu F Z, et al. Root exudates of wheat are involved in suppression of Fusarium wilt in watermelon in watermelon-wheat companion cropp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2015, 141: 209–216
[25] 黃玉茜. 花生連作障礙的效應及其作用機理研究[D]. 沈陽: 沈陽農業大學, 2011
[26] 劉建國, 張偉, 李彥斌, 等. 新疆綠洲棉花長期連作對土壤理化性狀與土壤酶活性的影響[J]. 中國農業科學, 2009, 42(2): 725–733
[27] 劉莉, 趙安潔, 楊雁, 等. 三七不同間隔年限種植土壤的理化性狀比較分析[J]. 西南農業學報, 2013, 26(5): 1 946–1 952
[28] 孫雪婷, 龍光強, 張廣輝, 等. 基于三七連作障礙的土壤理化性狀及酶活性研究[J]. 生態環境學報, 2015, 24(3): 409–417
[29] 王興祥, 張桃林, 戴傳超. 連作花生土壤障礙原因及消除技術研究進展[J]. 土壤, 2010, 42(4): 505–512
[30] Berendsen R L, Pieterse C M J, Bakker P A H M. The rhizosphere microbiome and plant health[J]. Trends in Plant Science, 2012, 17: 478–486
[31] Bron P A, van Baarlen P, Kleerebezem M. Emerging molecular insights into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probiotics and the host intestinal mucosa[J]. Nature Reviews Microbiology, 2012, 10: 66–78
[32] Wang H B, Zhang Z X, Li H, et al. Characterization of metaproteomics in crop rhizospheric soil[J]. Journal of Proteome Research, 2011, 10(3): 932–940
[33] Wu L K, Wang H B, Zhang Z X, et al. Comparative metaproteomic analysis on consecutively Rehmannia glutinosa-monocultured rhizosphere soil[J]. PLoS One, 2011, 6(5): e20611
[34] 李孝剛, 張桃林, 王興祥. 花生連作土壤障礙機制研究進展[J]. 土壤, 2015, 47(2): 266–271
[35] Ying Y X, Ding W L, Zhou Y Q, et al. Influence of Panax ginseng continuous cropping on metabolic function of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J]. Chinese Herbal Medicines, 2012, 4: 329–334
[36] 吳鳳芝, 王學征. 設施黃瓜連作和輪作中土壤微生物群落多樣性的變化[J]. 中國農業科學, 2007, 40(10): 2 274–2 280
[37] 陳冬梅, 柯文輝, 陳蘭蘭, 等. 連作對白肋煙根際土壤細菌群落多樣性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 2010, 21(7): 1 751–1 758
[38] 鄒春嬌, 齊明芳, 馬建, 等. Biolog-ECO解析黃瓜連作營養基質中微生物群落結構多樣性特征[J]. 中國農業科學, 2016, 49(5): 942–951
[39] 胡國彬, 董坤, 董艷, 等. 間作緩解蠶豆連作障礙的根際微生態效應[J]. 生態學報, 2016, 36(4): 1 010–1 020
[40] 黃玉茜, 韓立思, 韓梅, 等. 花生連作對土壤酶活性的影響[J]. 中國油料作物學報, 2012, 34(1): 96–100
[41] 張恩平, 張文博, 張淑紅, 等. 苯甲酸和肉桂酸對番茄幼苗根部保護酶及膜質過氧化的影響[J]. 西北農業學報, 2010, 19(1): 186–190
[42] 孫垂華, 徐效華, 陳建軍, 等. 勝紅薊化感作用研究Ⅸ.主要化感物質在土壤中的轉化[J]. 生態學報, 2002, 22(8): 1 189–1 193
[43] 李紹文. 生態生物化學(二):高等植物之間的生化關系[J].生態學雜志, 1989, 8(1): 66–70
[44] 吳林坤, 林向民, 林文雄. 根系分泌物介導下植物–土壤–微生物互作關系研究進展與展望[J]. 植物生態學報, 2014, 38(3): 298–310
[45] 肖靖秀. 小麥間作蠶豆的根系分泌物特征及其對蠶豆枯萎病菌的響應研究[D]. 昆明: 云南農業大學, 2013
[46] 鄭倩, 李俊華, 危常州, 等. 不同抗性棉花品種根系分泌物及酚酸類物質對黃萎病菌的影響[J]. 棉花學報, 2012, 24(4): 363–369
[47] 李坤, 郭修武, 郭印山, 等. 葡萄根系腐解物的化感效應及酚酸類化感物質分離鑒定[J]. 果樹學報, 2011, 28(5): 776–781
[48] 趙先龍. 玉米秸稈腐解液化感效應及典型化感物質分離鑒定[D]. 哈爾濱: 東北農業大學, 2014
[49] 張秋菊, 張愛華, 孫晶波, 等. 植物體中萜類物質化感作用的研究進展[J]. 生態環境學報, 2012, 21(1): 187–193
[50] Huang L F, Song L X, Xia X J, et al. Plant-soil feedbacks and soil sickness: From mechanisms to application inagriculture[J]. Journal of Chemical Ecology, 2013, 39: 232–242
[51] Wu F Z, Wang X Z, Xue C Y. Effect of cinnamic acid on soil microbial characteristics in the cucumber rhizosphere[J]. European Journal of Soil Biology, 2009, 45: 356–362
[52] Bouhaouel I, Gfeller A, Fauconnier M L, et al. Allelopathic and autotoxicity effects of barley (Hordeum vulgare L. ssp. vulgare) root exudates[J]. BioControl, 2015, 60: 425–436
[53] 孔垂華, 胡飛. 植物化感相生相克作用及其應用[M]. 北京: 中國農業出版社, 2001: 30–42
[54] Hao Z P, Wang Q, Christie P, et al. Allelopathic potential of watermelon tissues and root exudates[J]. Scientia Horticulturae, 2007, 112: 315–320
[55] He C N, Gao W W, Yang J X. Identification of autotoxic compounds from fibrous roots of Panax quinquefolium L.[J]. Plant and Soil, 2009, 318: 63–72
[56] 王勇, 吳國良, 李登科. 核桃樹體內酚類物質含量的變化[J]. 果樹學報, 2003, 20(4): 325–327
[57] Yan J, Bi H H, Liu Y Z, et al. Phenolic Compounds from Merremia umbellata sub sp. orientalis and their allelopathic effects on arabidopsis seed germination[J]. Molecules, 2010, 15(11): 8 241–8 250
[58] 張新慧, 朗多勇, 陳靖, 等. 蒙古黃芪植株水浸液的自毒作用研究[J]. 中藥材, 2014, 37(2): 187–191
[59] 李培棟, 王興祥, 李奕林, 等. 連作花生土壤中酚酸類物質的檢測及其對花生的化感作用[J]. 生態學報, 2010, 30(8): 2 128–2 134
[60] 焦曉林, 畢曉寶, 高微微. p-香豆酸對西洋參的化感作用及生理機制[J]. 生態學報, 2015, 35(9): 3 006–3 013
[61] Xu Y, Wu Y G, Chen Y, et al. Autotoxicity in Pogostemon cablin and their allelochemicals[J]. Revista Brasileira de Farmacognosia, 2015, 25: 117–123
[62] van de Voorde T F, Ruijten M, van der Putten W H, et al. Can the negative plant–soil feedback of Jacobaea vulgaris be explained by autotoxicity[J]. Basic and Applied Ecology, 2012, 13: 533–541
[63] Wu H S, Raza W, Liu D Y, et al. Allelopathic impact of artificially applied coumarin on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niveum[J]. World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08, 24: 1 297–1 304
[64] Ye S F, Yu J Q, Peng Y H, et al. Incidence of Fusarium wilt in Cucumis sativus L. is promoted by cinnamic acid, an autotoxin in root exudates [J]. Plant and Soil, 2004, 263: 143–150
[65] 王茹華, 周寶利, 張啟發, 等. 茄子根系分泌物中香草醛和肉桂酸對黃萎菌的化感效應[J]. 生態學報, 2006, 26(9): 3 152–3 155
[66] 王倩, 李曉林. 苯甲酸和肉桂酸對西瓜幼苗生長及枯萎病發生的作用[J]. 中國農業大學學報, 2003, 8(1): 83–86
[67] 馬云華, 王秀峰, 魏珉, 等. 黃瓜連作土壤酚酸類物質積累對土壤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響[J]. 應用生態學報, 2005, 16(11): 2 149–2 153
[68] Tian G L, Bi Y M, Sun Z J, et al. Phenolic acids in the plow layer soil of strawberry fields and their effects on the occurrence of strawberry anthracnose[J]. European Journal of Plant Pathology, 2015, 143: 581–594
[69] 程瑩, 白壽發, 莊敬華, 等. 甜瓜殘茬腐解物對鐮孢枯萎病的助長作用[J]. 中國農學通報, 2011, 27(8): 217–221 [70] 楊瑞秀, 高增貴, 姚遠, 等. 甜瓜根系分泌物中酚酸物質對尖孢鐮孢菌的化感效應[J]. 應用生態學報, 2014, 25(8): 2 355–2 360
[71] 李振方. 自毒物質與病原真菌協同對連作地黃的致害作用研究[D]. 福州: 福建農林大學, 2011
[72] 齊永志. 根系化感物質與病原菌在草莓連作障礙中的協同作用研究[D]. 保定: 河北農業大學, 2008
[73] Zhou X G, Wu F Z. P- Coumaric acid influenced cucumber rhizosphere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 and the growth of Fusarium oxysporum f. sp. cucumerinum Owen[J]. PLoS ONE, 2012, 7: e48288
[74] Guo X W, Wang B, Li K, et al. Effect of 4-hydroxybenzoic acid on grape (Vitis vinifera L.) soil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and functional diversity[J]. Biotechnology & Biotechnological Equipment, 2015, 29(4): 637–645
[75] 劉艷霞, 李想, 蔡劉體, 等. 煙草根系分泌物酚酸類物質的鑒定及其對根際微生物的影響[J]. 植物營養與肥料學報, 2016, 22(2): 418–428
[76] Hartung A C, PutnamA R, StePhens C T. Inhibitory activity of asparagus root tissue and extracts on asparagus seedlings[J]. Journal of American Society for Horticultural Seienee, 1989, 114: 144–148
[77] 齊永志, 蘇媛, 王寧, 等. 對羥基苯甲酸脅迫下尖孢鐮刀菌侵染草莓根系的組織結構觀察[J]. 園藝學報, 2015, 42 (10): 1 909–1 918
[78] 馬燕會, 齊永志, 趙緒生, 等. 自毒物質脅迫下不同草莓品種枯萎病抗性變化的研究[J]. 河北農業大學學報, 2012, 35(2): 93–97
[79] 滕應, 任文杰, 李振高, 等. 花生連作障礙發生機理研究進展[J]. 土壤, 2015, 47(2): 259–265
[80] 薛超, 黃啟為, 凌寧, 等. 連作土壤微生物區系分析、調控及高通量研究方法[J]. 土壤學報, 2011, 48(3): 612–618
Advance in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HOU Hui1, DONG Kun2, YANG Zhixian3, DONG Yan1*, TANG Li1, ZHENG Yi1,4
(1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650201,China; 2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Yunna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Kunming650201,China; 3Yunnan University,Kunming650091,China; 4Southwest Forestry University,Kunming650224,China)
With the constant improvement of the intensive cultivation’s degree, continuous cropping results in decrease of crop production and quality as well as soil-borne diseases which seriously restrict modern agricultur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mechanism of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CCO) has been one of hot spots at home and abroad. In recent years,a lot of work have been done from many aspects on CCO. However, most efforts are focused on the effect of a single factor while few attentions are paid to the internal interactions and essence of the various factors, which hinder the deep reveal of the real reasons for the occurrence of CCO. The further understandings of the causes of CCO and the interact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are the basis to control the soil-borne diseases caused by soil-borne pathogens, to alleviate CCO and to realize the zero increase target of pesticide consumption by 2020 in China. This paper reviewed systematically the mechanisms of continuous cropping from the deterioration of soil physiochemical and biological properties, the decrease of plant physiological resistance, self-toxicity of continuous cropping,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arious factors. The further studies in this filed were also suggested to looking for the theory evidence of mitigation strategies in a safe, environmental and effective way.
Continuous cropping obstacle (CCO); Soil-borne diseases; Autotoxicity; Rhizosphere microorganisms
S154. 36
10.13758/j.cnki.tr.2016.06.002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31360507,31560586,31060277,31210103906)、國家“973”計劃項目(2011CB100405)、農業部公益性行業科研專項課題項目(201103003)和云南省科技計劃重點項目(2015FA022)資助。
* 通訊作者(dongyanyx@163.com)
侯慧(1992—),女,湖北襄陽人,碩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為作物連作障礙成因與調控。E- mail: 132738264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