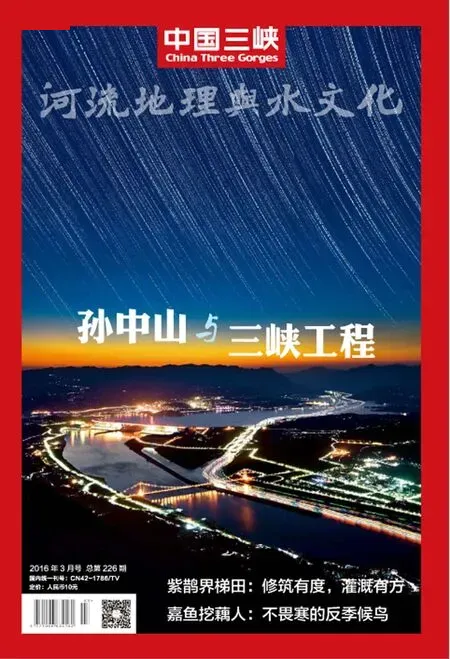夢止沅江
文/羅澤民 繪圖/李雨瀟 編輯/羅婧奇
?
夢止沅江
文/羅澤民繪圖/李雨瀟編輯/羅婧奇

一
對我來說,第一次在意識中把沅江和自己聯系在一起,是在四五歲的某一個端午節。
那一次外婆帶著我前往臨河的土墻上觀看附近鄉鎮組織的龍舟賽。假如我這二十多年的記憶沒有出錯的話,那應該是我親眼見過的唯一一場民間組織的龍舟賽——之后雖也見識過旅游項目、學校活動等龍舟賽的形式,但那些龍舟太過新鮮,像糊在年畫上的圖片,美則美矣,卻從來沒能給我帶來那種整條河兩岸都在歡呼的氣氛。河邊的人們純良又狡黠,會在比賽的時候以充滿男子漢氣概的吆喝聲鼓舞己方士氣、奚落對方船員。比賽還是看時間和速度,最后取得冠軍和落敗的隊伍,都得到了兩岸觀眾的喝彩。
雖說這是我關于沅江最早的記憶,然而外婆說從她第一次以背簍模式帶我出門,到可以牽著我走去看龍舟賽,我每次都會喊著要去看“大河”。山里人的方言這樣稱呼他們眼前的山水,他們可能并不知道它的學名叫沅江,對于生活在狹小山區的人來說,名詞并不會很豐富,當然,更不會跟遠在千里之外的那條黃色的中國母親河聯系起來。
“又出門呀?”“帶娃娃趕場去啊!”山地聚落的中心在渡口,所以外婆每逢鄉下集鎮趕集的日子,都會帶我出門,然后一路上去渡口,也就是臨江的集市。趕集的人絡繹不絕,并且互相都能說得出家長里短。外婆家住在山腳,從山中出來去往河岸的居民要經過我們家門口,我經常看到老爺爺老太太們晃悠悠地從我家門口走過,去渡口趕集。后來我常常想到《桃花源記》里的句子,想起在這個山村中“土地平曠,屋舍儼然”“阡陌交通,雞犬相聞”的生活,并一直認為這樣的場景稀松平常。怎么城里人少見多怪,還要熱衷于尋找隨處可見的烏托邦呢?
二
《水經注·卷三十七》中寫到了沅江:“又東北過臨沅縣南,臨沅縣與沅南縣分水。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竦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之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就是那么巧,那個渡口前就是夷望溪與沅江的交匯處。偶爾還能在當地的旅游地圖中發現這個小集鎮,二十年過去,那個集鎮的基本模式還是沒有變,從渡口上來就是一個十字路口,當地居民的吃穿用度,基本上就在這個十字路口完成了。往三條主街道方向走,便漸漸到了山路,農田村落盡現眼前,再往前走,便是南方常見的山地,青翠濃郁,霧氣升騰,竹海從遠方傳來風的氣息。
這就是我外婆家所在的千里沅江上的一個小渡口,小到不會在任何貨運港口的統計表中出現。這里的人說著西南官話,沿著沅江分布的是這個山城常德的偏遠鄉鎮。桃源,這個被認為是陶淵明筆下桃花源所在地的縣城,因為山路崎嶇,隱藏在這個行政縣上游的若干鄉鎮在早年都只能靠著河運,而隨著河流上中游水壩的修建、山中公路的延長等原因,河運也漸漸衰竭了。
小時候從縣城坐車去往外婆家的那段山路無疑是噩夢,將近兩個小時的行程,破爛的公共汽車,嘈雜而擁擠的人群,直到外婆家對面的渡口,我才緩過來。渡口前正是壯闊的沅江,年幼時覺得浩淼如想象中壯闊的大海,過河就可以在外婆家里開始暑假了,記憶鏈就是這樣神奇的聯系在一起。如果意識流真的可以追根溯源,那么我想起沅江,一定會想起此前若干個在山里逍遙自在度過的寒暑假。不用上補習班,山里好玩的事物太多,童年時代的藍天白云和風雨雷電都那么夢幻,不管從哪個角度爬山都能看到這條大河環抱著我的小鎮。童年或者少年時,誰不認為“念書-放假-念書-放假”的循環是永恒的呢?
三
到了中學時讀《邊城》,我固執地認為沈從文的世界我也經歷過,不然翠翠那一聲“砍腦殼死的”,我怎么那么熟悉呢?后來讀沈從文的散文集,原來他從沅江坐船下來真的能到桃源,也許幾十年前他還曾路過我外婆家所在的那個小渡口,還在那里停船買過煙草呢。
地理教材中的聚落曾分析過“山地聚落的趕集分布”,我第一時間想到的是那些商人們靠著河水的運載,在周圍的鄉鎮兜售那些外來的新鮮物,也難怪附近的集市永遠都是錯開日子,一到趕集的日子,渡口就停滿了客船,如果你想在上下幾個集市體驗民俗,那么可以乘著客船在之后幾日隨便往來,到特定的日子又能回到起點。如此循環往復、有跡可循的生活,給年幼時的我帶來了特別的情感,如同長年不變的假期和玩伴。
更有趣的還是外婆給我講的那些生活故事,比如她們正在山下的溪流洗衣服時,后山傳來趕山人們的吼叫,一頭野山羊就直接撞死在溪對岸。也曾見過這些滄桑的趕山人,他們帶著獵槍和獵犬,希望冬天能打一些野味。我想起漫天風雪的時候外公去趕山人家造訪,談到集市中有賣野味的商人,他擺擺頭,敲著煙斗說,那些都是假野味,給你看我今年打的,于是回家的時候外公偶爾會拎著一根羊腿。外公總給我說他們老朋友的情誼,比如某年修水壩的時候,外公吃不飽工地的饅頭,總是能得到一些人的照顧。
在很久之后,當我放棄回鄉村過暑假而做“更有意義的事”,我的童年終結在與沅江作別之時。
四
因為這條大河,我對中國的水系形成了一種執念,總希望人們在談河流與水文的時候,會提一下這條長江流域內并不太出名的長河,講講它的風土人情和自然地理。然而它不常被提起,我就開始默默地幻想這條碧波千里的河流。
酈道元的《水經注》中提到的夷望山,又叫水心寨。河邊的居民為這座河流中間的孤山造了無數的故事,比如說它是天上明月的倒影,是另一個月亮,是河中兩條龍斗法的法器所化,是東海在大陸的時空之門。而這些故事也許都是從上游流傳下來的,畢竟千年之前的武陵郡的傳說中,沅水上游高辛族的祖先和盤瓠生下了六男六女,連人與畜之間的界限都被模糊了,遠古的神話變幻著流傳了下來,無論是明月還是竹海,神獸還是玉帶,如酈道元所說,“風籟空傳,泉響不斷”,天下河川莫不如此,也許不同之處就在于它們的故事吧。
而《山海經》中僅僅提了一句“禱過之山,沅水出焉”,便能引發想象,想這條千里長的河流是如何從云貴高原的小溪間發源,飛鳥從林中穿過的時候掠過它的上空,也許鹿群還在源頭處喝過水,然后它慢慢流到山腳,帶著另外的小溪聚合成一條更大的小河,再艱難奔騰過群山萬壑,在一個又一個的渡口或城市旁逗留成河灣,最后形成了大河的模樣。
世界聞名的旅行寶典《孤獨星球》也別出心裁的在湖南省的旅游攻略中,策劃了一條水運走湘西的路線。至少現在的沅江中上游一直都有客船和航運,那種帶著斗篷的長船定期在這條河上的不同渡口行走。如果要重走湘西路,從這里開始便是一個好選擇。我當時默默做筆記,因為發現這條路線的起點竟然就在外婆家渡口的下一個鎮,曾想抽個暑假走一趟,走的遠一點,看看芙蓉鎮什么的,可每次都有事耽擱。高中畢業以后,我在這個小渡口生活的日子越來越少,想到每次來去匆匆,比起出游還是選擇留在外公外婆身邊更讓他們安心。
五
去年清明節,媽媽一定要我回去。家鄉習俗有個清明會,山村里一個大家族的親戚聚集在一起,熱熱鬧鬧地把清明節也變成了團聚的節日。只是因為現今青壯年大多在外,所以清明會都是一些老年人在過,滿座都是白發,熱鬧之中卻格外的蕭索。
吃到一半,媽媽眼眶紅了,明明看到一群阿公阿婆們吃喝得正開心,我很是疑惑。之后我跟媽媽在河邊散步,問她為什么哭,她欲言又止,又還是下定決心,告訴我外婆得了癌癥,她害怕會失去她。那個下午春風料峭,回憶爭前恐后地涌到了腦海里,我也想不出什么話安慰她,因為我也好像從來沒想過外婆有一天會離開我。
從小看《紅樓夢》,最喜歡的人物探春有“千里東風一夢遙”的讖語,我站在沅江邊上,想到這條奔騰了千年的大河,竟絲毫不會感受到我的悲傷、媽媽的悲傷和外婆的悲傷,它只是流淌著。我得把它跟我的回憶抓住,而過去的歲月如同看不到頭的迷夢,我無法再次經歷與這條河更密切的時光,也許這些都會隨著河運的徹底衰落而終結,但我唯一知道的是,我關于沅江的夢也許就到此為止了,它之后的明月疏風,竹海松濤,山澗清泉,都終永遠地離開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