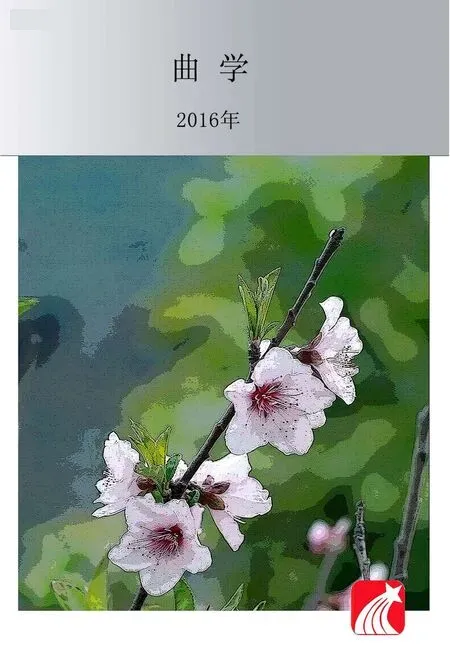挽歌流變考
解玉峰
《曲學》第四卷
挽歌流變考
解玉峰
引 言
挽歌作為送葬歌曲,在中國古代喪禮中使用極為普遍,因為挽歌不論對下層社會、還是對上層社會而言,都有其特殊的功用,故能歷數千年之久。漢代以后挽歌的儀式化、制度化,對挽歌詩的創作則有推動之功,并最終使得挽歌(詩)成為中國詩歌的重要組成部分。挽歌的普遍使用,最終導致職業性挽歌郎的出現,職業挽歌郎和業余唱家們,則為中國古代的歌唱藝術增添了新的藝術品類。故挽歌源流變遷的梳理,或有助于我們從一個側面理解數千年中古代中國在禮儀、風俗、文學、音樂等方面的文化傳統。
關于挽歌的研究,學術界過去主要集中于兩方面: 一是對魏晉南北朝時文人所作挽歌(詩)思想意蘊的解讀,二是關于挽歌產生年代或起源的考證。*前一類論文主要有盧葦菁《魏晉文人與挽歌》(《復旦學報》1985年第5期)、王宜媛《六朝文人挽歌詩的演變與定型》(《文學遺產》2000年第5期)、吳承學《漢魏六朝挽歌考論》(《文學評論》2002年第2期)、歐陽波《漢魏六朝挽歌研究》(華中師范大學2007年碩士學位論文)等;后一類論文主要有齊天舉《挽歌考》(《文史》第29輯)、丘述堯《〈挽歌考〉辨》(《文史》第43輯、第44輯)、何立慶《早期挽歌的源流》(《文史雜志》1999年第2期)等。由于前一類研究有相當多的成分為主觀闡釋,也難求共識,所謂“詩無達詁”,故本文無意卷入訴訟。后一類研究對挽歌研究的深入展開而言有著極重要的意義,是其他研究得以展開的根基和前提。但在筆者看來,挽歌作為民間葬禮中的一種儀式,其形諸文字的時代必遠遠落后于其實際存在,故今人只能對挽歌的產生年代做出概貌性推論,而不可能有精確性判斷,結論愈求精確,距離事實真相可能也愈遠。如果我們把更多的注意力轉向其在后來歷史中的變遷,從而在更廣闊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察考挽歌在歷代禮樂、風俗、文學、音樂等方面實際影響和作用,其意義或勝于某一歷史起點的推定。
過去關于挽歌研究的另一重要問題是“挽歌”概念的無限泛化。我們認為,挽歌應基本界定為送葬歌曲,即牽引靈柩前往墓地時所歌之曲,而古代或近代各種臨尸而歌(存世文獻中多稱之為“喪歌”或“哭喪歌”)都不宜歸為挽歌。正是因為對挽歌缺少基本的界定,致使有的研究者在挽歌產生年代問題上無限前移*如丘述堯先生《〈挽歌考〉辨》文(《文史》第44輯)即將挽歌上溯到原始社會,中華書局,1998年,第 219頁。,如此對挽歌各方面的論述也不能做到有的放矢*“喪歌”或“哭喪歌”的形態、功能各異,而挽歌大都是“一倡眾和”、“以齊眾力”(詳后),對中國古代葬禮及中國文學、音樂有實際意義的也正是此類“挽歌”。。
有鑒于此,本文試圖在挽歌為送葬之曲這一基本界定下,從禮樂制度、風俗時尚等方面考察挽歌的源流變遷,努力還原中國古代挽歌的生存圖景,進而考察其對中國文學、中國音樂的意義。疏陋之處,敬祈宏達之教正。
一、 挽歌的起源
關于挽歌的產生時代或起源,眾家結論不一,概括說來主要有起于先秦、起于漢初田衡、起于漢武帝等三說。涉及挽歌的產生時代或起源的文獻資料,主要有以下數條。
《左傳》哀公十一年(前484),吳伐齊,“將戰,公孫夏命其徒歌虞殯”。晉杜預(222— 284)注云:“虞殯,送葬歌曲,示必死。”孔穎達(574—648)疏曰:“杜云送葬歌曲,并不解虞殯之名。禮啟殯而葬,葬即下棺,反日中而虞。蓋以啟殯將虞之歌,謂之虞殯。歌者,樂也。喪者,哀也。送葬得有歌者,蓋挽引之人為歌聲以助哀。今之挽歌是也。”*(唐)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卷五十八,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1979年,第2166頁。
《莊子》“逸篇”有:“紼謳所生,必于斥苦。”晉司馬彪(?—306)注曰:“紼,引柩索也。斥,疏緩也。苦,用力也。引紼所以有謳歌者,為人有用力不齊,故促急之也。”*(南朝宋)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張驎酒后,挽歌甚凄苦”注,轉引自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第407頁。

東漢末經學家譙周(199— 270)《法訓》有:“有喪而歌者,或曰:‘彼為樂喪也,有不可乎?’譙子曰:‘《書》云:‘四海遏密八音。’何樂喪之有?’曰:‘今喪有挽歌者,何以哉?’譙子曰:‘周聞之: 蓋高帝召齊田橫,至于尸鄉亭,自刎奉首。從者挽至于宮,不敢哭而不勝哀,故為歌以寄哀音。彼則一時之為也。‘鄰有喪,舂不相’,引挽人銜枚,孰樂喪者邪?’”*(南朝宋) 劉義慶《世說新語》“任誕”篇劉孝標注,轉引自徐震堮《世說新語校箋》,中華書局,1984年,第407頁。
西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音樂第三”曰:“《薤露》、《蒿里》,并喪歌也,出田橫門人。橫自殺,門人傷之,為之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滅也,亦謂人死魂魄歸乎蒿里。故有二章,一章曰:‘薤上朝露何易晞,露晞明朝還復滋,人死一去何時歸!’其二曰:‘蒿里誰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踟躕!’至孝武時,李延年乃分為二曲,《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為挽歌。”*(晉)崔豹《古今注》卷中,遼寧教育出版社標點本,1998年,第8頁。
綜合以上諸種文獻看,筆者認為,挽歌的產生時代似以先秦說較勝,至于產生于西周、還是春秋戰國時代,則較難判定。周人重禮,“吉、兇、軍、賓、嘉”五禮中,喪葬之事甚被看重。厚葬在上層階級或富貴階層往往流行,棺槨則相當沉重,十數人或上百人執紼引柩乃屬常見。故《禮記·曲禮》有“助葬必執紼”。鄭玄注云:“紼,引車索。”*(清) 阮元《禮記正義》卷三,中華書局影印阮刻《十三經注疏》本,1979年,第1249頁。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同上注,第1298頁。在這樣的情況下,就有同聲協力的必要。《莊子》“紼謳所生,必于斥苦”,正是指出了挽歌用以齊眾力的功用。挽歌在先秦時,是否已施用于上流社會,《儀禮》、《禮記》等文獻未載,難于考實,但其施用于民間當無可疑。有些挽歌曲調在民間應非常流行,故公孫夏率兵伐齊時,命兵士唱挽歌,以示必死之心。宋玉《對楚王問》中說歌唱《蒿里》,“和者數千人”;歌唱《薤露》,“和者數百人”。但先秦時,挽歌歌辭可能隨用隨棄,不必為精心制作,而漢初田橫門人葬田橫時所歌《薤露》、《蒿里》二章,則情真辭切,故備受后世文人矚目,這應是后人將挽歌源起歸至田橫時的主要原因。
二、 挽歌的制度化
從文獻記載看,上流社會葬禮中用挽歌,至遲應始于漢武帝時代,所謂“《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按,宋玉《對楚王問》中說歌唱《蒿里》“和者數千人”,而歌唱《薤露》“和者數百人”,或可說明早在戰國時代挽歌已有雅俗貴賤之別,當時挽歌使用已有禮制因素,唯文獻闕如,我們暫且將挽歌的制度化歸于漢武帝時。。至此,挽歌的使用乃成為漢家制度。漢初百廢待興,漢家制度倉皇未備,至武帝時禮樂制度大興,故挽歌作為一種新型禮制進入喪禮,也在情理之中。當然,挽歌作為一種新禮,也不斷遭遇到守舊士人的反對。如東漢儒士刁雍作《行孝論》,訓誡子孫曰:“轜車止用白布為幔,不加畫飾,名為清素車。又去挽歌、方相,并盟器雜物。”*(北魏) 魏收《魏書》卷八十四《刁沖傳》,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1858頁。漢末經學家譙周也不贊成用挽歌,認為挽歌乃田橫門人“一時之為”*見前引《世說新語》“任誕”篇劉孝標注。。甚至直至西晉摰虞時,也仍有人認為挽歌“非經典所制,違禮設銜枚之義”。但摰虞認為,“漢魏故事,大喪及大臣之喪,執紼者挽歌。……挽歌因倡和而為摧愴之聲,銜枚所以全哀,此亦以感眾。雖非經典所載,是歷代故事”。*(唐) 房玄齡《晉書》卷二十《禮志中》引虞摯《挽歌議》,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626頁。故從西漢以后的文獻看,相關挽歌的文獻記載已非常豐富,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武帝后挽歌在日常社會中的制度化。
當挽歌被上層列入喪制之后,下層社會的挽歌與上層社會的挽歌開始有日漸顯著的差異,其差異應不限于所歌曲調的不同(所謂“《薤露》送王公貴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禮以別異”,不同身份等級的人,所用挽歌亦有異。《通典》“挽歌”條云:

按,唐代宗遺制中關于其喪禮(包括挽歌)的規定,固然反映了中唐時的情況,但必前有所本。《太平御覽》卷五百五十二引《晉公卿禮秩》有:“安平王葬,給挽歌六十人,諸公及開府給三十人。”*(宋) 李昉《太平御覽》卷第五百五十二禮儀部三十一,《四部叢刊》三編影宋本,第3333、1085、2580、2076頁。檢《晉書·司馬孚傳》,安平王司馬孚(180—272)之葬“皆依漢東平獻王蒼故事”。按,東平王劉蒼為劉秀之子,司馬孚即司馬懿之弟、晉武帝司馬炎之叔祖,二人皆帝室宗親,權勢傾蓋一時。《晉書·桓溫傳》說桓溫死,“一依太宰安平獻王、漢大將軍霍光故事”,“賜九旒鸞輅,黃屋左纛,輼輬車,挽歌二部,羽葆鼓吹,武賁班劍百人”。《晉書·謝安傳》說謝安死,“依大司馬桓溫故事”。如史家記述,霍光、劉蒼、司馬孚、桓溫、謝安等葬皆同一等級,據此我們可認為,霍光等葬可能皆應給挽歌六十人(所謂“挽歌二部”)。而次一等級的“諸公及開府”(“三品以上”)則給挽歌三十人(所謂“挽歌一部”)。如《宋書》卷五一《劉道規傳》:“及長沙太妃檀氏、臨川太妃曹氏后薨,祭皆給鸞輅九旒,黃屋左纛,輼輬車,挽歌一部,前后部羽葆、鼓吹,虎賁班劍百人。”*(梁) 沈約《宋書》卷五十一,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1475頁。這便是次一等級的情況。
從《唐六典》、《通典》、《唐會要》、《五代會要》、《通志》、《續通志》、《續通典》等文獻看,“挽歌”作為葬禮儀式的一部分在隋唐以后各代中皆有相應之規定,雖世有變革,但仍可見其一貫性特征,如清乾隆三十二年(1767)編成的《欽定續通志》卷一百十八“挽歌”條有:
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命翰林學士李昉等重定士庶喪葬制度,昉等奏準后唐長興二年詔,五品六品常參官喪,輿舁者二十人,挽歌八人,明器三十事,共置八床。七品常參官,舁者十六人。挽歌六人,明器二十事,置六床。六品以下京官及檢校試官等,舁者十二人,挽歌四人,明器十五事,置五床,并許設紗籠二。庶人舁者八人,明器十二事,置兩床,悉用香輿魂車從之。*(清) 嵇璜編《續通志》卷一百十八《禮略》,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353頁。
對照前《通典》所載,我們不難看出其大多仍循前朝故事。挽歌的這種制度化,為挽歌在上流社會的生存提供了較可靠的保障。數千年來,民間社會婚喪禮俗大多崇奢尚厚,上有所好,下必從之,更兼風俗傳統的慣性使然,挽歌在民間社會也一直綿延不絕,直至近代。從明清及近代各地方志看,民間葬禮用挽歌者仍很普遍。如乾隆二十八年(1763)刻本湖南《清泉縣志》有:
舁柩者或多至三十六人,下至十有六人,舁者作邪許聲,有詞唱相導,蓋古《薤露》、《蒿里》之遺。*《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中南卷),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991年,第547頁。
又如光緒十年(1884)刻本江蘇《六合縣志》亦云:
發引日,用僧樂、挽歌以導輀車,亦有陳列紙帛人物、祭章、亭幔及用方弼方相者。*《中國地方志民俗資料匯編》(華東卷),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第365頁。
自先秦以來,中國對周邊地區的朝鮮、越南、日本等風俗文化形成都有重大影響,唐宋以來,隨著航海等交通技術的發展,這種影響更為顯著,葬禮中用挽歌應很早即及傳至這些周邊國家。承韓國漢陽大學吳秀卿教授相告,直到今日,在韓國一些農村地區葬禮中仍有使用挽歌的。韓國學者李素羅《韓國喪歌中厄避邪歌和wu ya huol huol》文中也談到,在韓國挽歌多稱“行喪歌”。據李文介紹,韓國的喪歌有六種: 1. 行葬禮之前夜的歌, 2. 葬禮之日的早上,把棺材從房間往外抬時唱的“避邪歌”, 3. 發靷(祭供桌前的祭祀)和路祭中吟唱的“告祱”, 4. 把棺材運往墓地時唱的“行喪歌”, 5. 下葬時唱的“踏墓歌”, 6. 葬禮后,回家途中演唱的歌。以上的1和6都很少見,3是朗誦調,屬于全國性的多。2在過去曾廣泛流行,但現在知道的人已很少。*李素羅《韓國喪歌中厄避邪歌和wu ya huol huol》,《藝術探索》1997年第6期。
故從挽歌的變遷來看,漢家禮樂制度始備的漢武帝時代,的確是一個值得矚目的一個階段。若從挽歌的制度化而言,后世有挽歌起于武帝說并非不可思議。因為在這一階段,在易為文人矚目的上流社會,挽歌的儀式化、制度化色彩更加顯著。同時,挽歌的這種儀式化、制度化,也催發了文人挽(歌)詩的制作。
三、 挽歌詩的制作
如前所述,挽歌在民間喪禮中其使用雖可能很普遍,但其歌辭的制作一直不被重視,隨意為之,也隨用隨棄,故田橫門人為田橫制作的挽歌詩才能流行一時,為人矚目。但當挽歌走向制度化以后,情形便大不一樣了。既然送葬時例需有挽歌,請文人學士為亡者制作挽詩乃成為必然之趨勢。
從存世文獻看,兩漢時未見有文人寫作挽詩的記載。兩漢時文學尚未自覺,詩歌寫作尚未成為文人風尚,兩漢詩歌除少量樂府詩外,今存者甚少,故漢詩中未見挽詩似亦在情理之中。由此我們也可以推斷,兩漢文人寫作挽詩應未成為常例,即使偶有嘗試也屬率意為之,自家他人皆不珍視,故今日未見漢人挽詩流存。
值得注意的是魏晉時代。三國時曹操(155—220)有《薤露行》、《蒿里行》各一首,曹植(192—232)有《薤露行》一首。從詩的內容來看,我們不能說曹氏父子以《薤露》、《蒿里》為題的詩是專為送葬挽歌所作,但我們可以認為,《薤露》、《蒿里》二挽歌曲調當時非常流行,故曹氏父子如后世詞曲家一樣倚曲填詞,曹氏父子之詩在當時皆可倚曲而歌。魏人繆襲(186— 245)今存挽歌詩一首。晉人傅玄(217— 278)今存挽歌詩四首(其中三首似不完整),陸機(261—303)今存挽歌詩七首(其中三首不完整),張駿(306— 346)有《薤露行》一首,陶潛(365— 427)今存挽歌詩三首。魏晉時代流傳至今的挽歌詩外,除陶潛三首因為是為自家寫的挽詩,有明顯的個人化色彩,其他挽歌詩都看不出是專為某人寫作的。又,唐虞世南《北堂書鈔》引陸機挽歌詩時有“王侯挽歌辭”、“士庶挽歌辭”、“庶人挽歌辭”等三種標題。由此來看,魏晉文人已開始參與挽歌詩的寫作,但此時的挽歌詩大多是公用性質的,專為某人寫作挽詩似未成為主流。魏晉以后,文人專為某王公貴戚、親朋好友貢獻挽詩或受命、受他人之托寫作挽詩,則漸成一種傳統。
據逯欽立先生所編《先秦漢魏六朝南北朝詩》、《全隋詩》,南北朝文人所作挽詩今存者有宋顏延之(384— 456)《挽歌》一首,宋鮑照(415?— 470)《代挽歌》一首,宋江智淵(418— 463)《宣貴妃挽歌》一首,北魏溫子升(495— 547)《相國清河王挽歌》一首,北齊盧詢祖(生卒不詳)《趙郡王配鄭氏挽詞》、北齊祖珽(生卒不詳)《挽歌》、北齊盧思道(約531—582)《彭城王挽歌》、《樂平長公主挽歌》。單從數量上來說,南北朝時文人所作挽詩今存者并不算多,但南北朝時可能有相當多的挽歌詩未能被保存下來。如《南史》卷七十二《丘靈鞠傳》:“宋孝武殷貴妃亡,丘靈鞠獻挽歌三首,云:‘云橫廣階暗,霜深高殿寒。’帝擿句嗟賞。”*(唐) 李延壽《南史》卷七十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第1762頁。而丘靈鞠所獻三首挽歌今無一存。又,《隋書》卷五十七載北齊著名文人盧思道事云:“文宣帝崩,當朝文士各作挽歌十首,擇其善者而用之。魏收、陽休之、祖孝征等不過得三首,唯思道獨得八首,故時人稱為‘八米盧郎’。”*(北魏) 魏徵《隋書》卷五十七,中華書局標點本,1973年,第1397頁。不但魏收、陽休之、祖孝征等“當朝文士”所作挽歌詩今皆不存,即使盧思道大為時人稱頌的八首挽詩也無一存。前代挽歌詩之亡佚,于此可見一斑。
唐宋以來,文人為亡人奉獻挽歌詩的現象,似更普遍。唐蘇鶚《杜陽雜編》卷下載咸通九年(869)同昌公主喪事云:
(同昌)公主薨。上哀痛之,自制挽歌詞,令百官繼和。及庭祭日,百司與內官皆用金玉飾車輿服玩,以焚于韋氏之庭,家人爭取其灰,以擇金寶。*(唐) 蘇鶚《杜陽雜編》,遼寧教育出版社標點本,2000年,第24頁。
宋朱熹(1130—1200)《晦庵集》卷九《孝宗皇帝挽歌詞》前《序》云:
阜陵發引,詔許近臣進挽歌詞,熹恭惟盛德大業,不易形容,方將攄竭鄙思以效萬一,冥搜連日才得四語。*(宋) 朱熹《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九,《四部叢刊》影明嘉靖本,第119頁。
據任半塘先生統計,《全唐詩》中以“挽歌”、“挽詞”、“挽歌辭”為題者二百五十四首*任半塘《唐聲詩》,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424頁。。唐駱賓王、王維、岑參、杜甫、白居易、韓愈、李義山、劉禹錫、溫庭筠等,宋歐陽修、王安石、司馬光、蘇軾、黃庭堅、陳師道、陸游、朱熹等著名文人,皆有相當數量的挽歌詩。
如前所述,魏晉南北朝以來,文人之所以有挽歌詩的寫作,因為挽歌詩有其用: 這些挽歌詩很可能在送葬時即交付歌郎歌唱。如《新唐書》卷八十二《承天皇帝倓傳》,述大歷三年(768)肅宗子李倓遷葬事云:
(代宗)遣使迎喪彭原,既至城門,喪輴不動。帝謂(李)泌曰:“豈有恨邪?卿往祭之,以白朕意,且卿及知倓艱難定策者。”(李)泌為挽詞二解,追述(李)倓志,命挽士唱,(李)泌因進酹。輴乃行,觀者皆為垂泣。*(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八十二,中華書局標點本,1975年,第3619頁。
又,《新唐書》卷七十七載代宗皇后獨孤氏葬事云:
大歷十年薨,追號為皇后,上謚。帝悼思不已,故殯內殿,累年不外葬。……又詔群臣為挽辭,帝擇其尤悲者令歌之。*(宋) 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七七,第3497頁。
又,宋金盈之編《醉翁談錄》載: 唐藝妓顏令賓,歿前向相識之士大夫求挽詞:
尋卒,士夫持至數封。其母拆視之,皆哀挽之詞,擲之于地曰:“能救我朝夕耶?”其鄰有張□□因取挽歌數篇,教挽柩者唱之,聲甚悲愴。*(宋) 金盈之《醉翁談錄》卷八,遼寧教育出版社標點本,1998年,第36、37頁。
近些年來,在唐宋新出土文獻的整理和利用方面,有些研究者注意到唐宋時在墓志蓋上鐫刻的挽歌。*如陳忠凱、張婷《西安碑林新藏唐——宋墓志蓋上的挽歌》(《出土文獻研究》第3輯,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金程宇《稀見唐宋文獻叢考》之《新見唐五代出土文獻所載唐人詩歌輯校》(中華書局,2008)、胡可先《墓志新輯挽歌考論》(《浙江大學學報》2009年5期)。值得指出的,這些挽歌與《全唐詩》等傳世文獻所載挽歌有不同的特征: 一是其文字一般較為淺俗;二是普遍存在文字相互因襲的現象;三是其作者皆不可考,非出自當時有名望的文人;四是這些挽歌所歌詠的即墓主,均非顯達人士。這些特點恰恰反映了這些挽歌可能曾作為民間通用性的歌辭被歌郎演唱。凡此,皆可見當時文人所作挽歌詩交付歌郎歌唱之風尚。
正從上述意義而言,我們可以說,漢武帝以后挽歌的儀式化、制度化在客觀上推進了文人挽歌詩的制作。
四、 挽歌的娛樂化和職業化
在指出挽歌始終具有的實用性功能(“以齊眾力”)以及其在走向制度化以后擁有的“禮以別異”的功用之外,我們也應當指出,挽歌既然是一種歌唱,也自然有一定的藝術性、娛樂性,故自起產生之日起就可能用以娛樂,而不必一定用于送葬儀式中。從史料來看,至遲在漢末,挽歌用為娛樂的現象已很普遍。如東漢應劭(約153—196)《風俗通義》云:
靈帝時(168— 190),京師賓婚嘉會,皆作魁儡,酒酣之后,續以挽歌。魁儡,喪家之樂;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天戒若曰:“國家當急殄悴,諸貴樂皆死亡也。”自靈帝崩后,京師壞滅,戶有兼尸,蟲而相食者。魁儡、挽歌,斯之效乎?*王利器《風俗通義校注》,中華書局,1981年,第568、569頁。
又,《后漢書》卷六一《周舉傳》:
(永和)六年三月上巳日,(大將軍梁)商大會賓客,讌于洛水,(周)舉時稱疾不往。(梁) 商與親昵酣飲極歡,及酒闌倡罷,繼以《薤露》之歌,坐中聞者,皆為掩涕。太仆張種時亦在焉,會還,以事告(周)舉。(周)舉嘆曰:“此所謂哀樂失時,非其所也,殃將及乎!”(梁) 商至秋果薨。*(劉宋)范曄《后漢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65年,第2028頁。
又,《晉書》卷二十八《五行志》:
海西公時,庾晞四五年中喜為挽歌,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又宴會輒令倡妓作新安人歌舞離別之辭,其聲悲切。時人怪之,后亦果敗。*(唐) 房玄齡《晉書》卷二十八,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836頁。
又,《晉書》卷八十三《袁松傳》:
山松少有才名,博學有文章……舊歌有《行路難》曲,辭頗疏質,山松好之,乃文其辭句,婉其節制,每因酣醉縱歌之,聽者莫不流涕。初,羊曇善樂,桓伊能挽歌,及山松《行路難》繼之,時人謂之“三絕”。時張湛好于齋前種松柏,而山松每出游,好令左右作挽歌,人謂“湛屋下陳尸,山松道上行殯”。*(唐) 房玄齡《晉書》卷八十三,第2169頁。
又,《宋書》卷六十九《范曄傳》:
元嘉九年冬,彭城太妃薨,將葬,祖夕,僚故并集東府。曄弟廣淵,時為司徒祭酒,其日在直。曄與司徒左西屬王深宿廣淵許,夜中酣飲,開北墉聽挽歌為樂。義康大怒,左遷曄宣城太守。*(劉宋)沈約《宋書》卷六十九,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1819—1820頁。
正是因為挽歌的歌唱有一定的藝術性或技術性要求,挽歌郎必然要有一定的技術訓練才能稱職,并非如一般挽士一樣易于獲得*有研究挽歌的學者以為,挽歌郎常為官宦子弟或優秀人才,實是將挽郎與挽歌郎混而為一。前引《通典》“挽歌”條關于挽郎與挽歌郎的區分甚明白,此不贅述。。故挽歌郎的職業化可能很早即已發生。北魏楊炫之《洛陽伽藍記》卷四有云:
市北(有)慈孝、奉終二里,里內之人以賣棺槨為業,賃輀車為事。有挽歌孫巖,娶妻三年,不脫衣而臥。巖因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毛三尺,似野狐尾,巖懼而出之。*周祖謨《洛陽伽藍記校釋》,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第159、160頁。
又,唐白行簡《李娃傳》傳奇寫到世家子弟鄭生為挽歌郎歌唱時,有非常精彩的描繪:
又,唐李亢《獨異志》“李佐”條所載也多傳奇色彩:
李佐,山東名族,少時因安史之亂失其父。后佐進士擢第,有令名,官為京兆少尹,陰求其父,有識者告,后往迎之于鬻兇器家。歸而奉養,如是累月。一旦,父召佐謂曰:“汝孝行絕世,然吾三十年在此黨中。昨從汝來,未與流輩謝絕。汝可具大豬五頭、白醪數斛、蒜虀數甕、薄餅十拌,開設中堂,吾與群黨一酧申欵,則無恨矣!”佐恭承其教,數日乃具。父散召兩市善《薤歌》者百人至,初即列坐堂中,久乃雜謳。及暮,皆醉,眾扶佐父登榻,而《薤歌》一聲,凡百齊和。俄然相扶父出,不知所在。*(宋) 李昉等《太平廣記》卷二百六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影印《四庫全書》本,第670、671頁。

宋元以來,隨著城鎮商品經濟的發展和繁榮,社會各類職業劃分更趨細密和成熟,遠非前代可比,故挽歌郎作為一種特殊職業也應比此前更成熟。從《水滸傳》、《連城璧》等小說來看,“棺材出了門,討挽歌郎錢”(意謂為時已晚,自找晦氣),乃是宋元以來的民間諺語。《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卷二十一有:
(閻)婆惜冷笑道:“你這黑三倒乖,把我一似小孩兒般捉弄,我便先還了你招文袋這封書,歇三日卻問你討金子。正是‘棺材出了,討挽歌郎錢’,我這里一手交錢,一手交貨,你快把來,兩相交割。”*《李卓吾批評忠義水滸傳》,江蘇古籍出版社點校本,2000年,第227頁。
又如李漁《連城璧》申集:
殷四娘看見大勢已成,恐怕眾人到了一處,大家和好起來,說出兩相情愿的話。這個和事老人就不但無功,反有過了,“棺材出門之后,去討挽歌郎錢”,那里還得清楚,所以兩邊終日催促要想完姻,殷四娘故意作難,只是延捱推阻,直等那三主謝儀陸續收完了,方才與他成事。*清康熙寫刻本,第158頁。
諺語中的“挽歌郎”當然都是專事此業的。宋末元初人燕南芝庵《唱論》述及唱曲題目有云:
有曲情,鐵騎,故事,采蓮,擊壤,叩角,結席,添壽;有宮詞,禾詞,花詞,湯詞,酒詞,燈詞;有江景,雪景,夏景,冬景,秋景,春景;有凱歌,棹歌,漁歌,挽歌,楚歌,杵歌。*(元) 燕南芝庵《唱論》,《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一),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60頁。
按,燕南芝庵為宋末元初人,生平不詳,其所著《唱論》實為當時民間唱家集體智慧的結晶。《唱論》既將“挽歌”列為“唱曲題目”之一,亦可見挽歌對當時職業唱家的重要。吳敬梓(1701— 1754)《儒林外史》從很多方面反映了清中葉時的社會風習,小說第二十六回寫到鮑文卿葬事時,有云:“這里到了出月初八日,做了銘旌。吹手、亭彩、和尚、道士、歌郎,替鮑老爹出殯,一直出到南門外。”*(清) 吳敬梓《儒林外史》,人民文學出版社點校本,1962年,第315頁。這里的“歌郎”,顯然也是職業性質的。
漢末以來,挽歌被用為娛樂以及挽歌職業化發展,都說明挽歌不僅有實用性或制度性功用,而是一種有特殊風味色彩的歌唱藝術,故歷代才會有如此多知名或不知名的人們耽愛挽歌。《李娃傳》中挽歌唱的描繪令人神往,作為小說家言其中不免過多夸飾和渲染,但仍促使我們試圖對挽歌唱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探討。
五、 挽歌的歌唱:“文”與“樂”
挽歌唱首先是一種“相和歌”,即一人倡之、眾人和之。關于挽歌這種一倡眾和的歌唱形式,多種文獻可為佐證。如前引《風俗通義》云:“挽歌,執紼相偶和之者。”《晉書》說“自搖大鈴為唱,使左右齊和”。《李娃傳》說西肆挽歌人“擁鐸而進,翊衛數人”,《獨異志》寫道李佐父“薤歌一聲,凡百齊和”。宋郭茂倩(1041—1099)《樂府詩集》將挽歌詩歸為“相和歌辭”一類。朱熹(1130—1200)《朱子語類》論及《詩經》時說:“如《清廟》一倡三嘆者,人多理會不得。注下分明說:‘一人倡之,三人和之。’譬如今人挽歌之類。今人解者又須要胡說亂說。”*(宋) 朱熹《朱子語類》,中華書局點校本,1986年,第2065頁。
挽歌唱是一種“相和歌”,文獻俱在,無可疑議。作為“相和歌”,挽歌唱是一種究竟應當何處用“和聲”?歷代文人所作挽歌詩多為整齊的五、七言詩(中唐以前多為五言,中唐以后始見七言*筆者所見最早的七言挽詩為白居易《元相挽歌詞三首》。,但仍以五言為主流),這些挽歌詩在交諸歌郎演唱時是否會有改造?
上述問題對我們總體上理解挽歌詩甚為重要,可惜相關的文獻資料甚少,下面讓我們研讀以下幾條較珍貴的資料。宋魏慶之《詩人玉屑》卷十六“寒食詩”條引《王直方詩話》云:
(蘇)東坡云與郭生游寒溪,主簿吳亮置酒。郭生善作挽歌,酒酣發聲,坐為凄然。郭生言恨無佳詞,因改樂天寒食詩歌之,坐客有泣者。其詞曰:“鳥啼鵲噪昏喬木,清明寒食誰家哭。風吹曠野紙錢飛,古墓累累春草綠。棠梨花映白楊路,盡是死生離別處。冥寞重泉哭不聞,蕭蕭暮雨人歸去。”每句雜以散聲。*(宋) 魏慶之《詩人玉屑》,上海古籍出版社點校本,1978年,第343頁。
按,《王直方詩話》的作者王直方(1069—1109),算是蘇軾的后輩,其所述或有所本。其所謂每句后的“散聲”應即是“和聲”,不過此處唱挽歌唯郭生一人,故“和聲”也只能由其一人歌唱。
《綴白裘》為蘇州人陳德蒼于清乾隆二十八年至三十九年(1763—1774)陸續編成的著名的折子戲選本,內收源自戲文《幽閨記》的《請醫》一折,其中有庸醫一家四口唱《蒿里歌》一段表演,或有助于我們更好地理解挽歌的功用及歌唱形式(念白為蘇州方言):
(凈)是我里家主婆、小兒、兒媳哉,扛子棺材,我里家主婆說道:“喂,老個,我里又心好哉,唱介只《蒿里歌》,接接力罷。”我說道:“使得個!”我就第一個來哉,說道: (唱)“我做郎中命運低。蒿里又蒿里!”(白)我里家主婆來哉,說道: (唱)“你醫死個人兒,連累著妻。蒿里又蒿里!”(白)唔猜我里個強種拿個扛棒得來,對子地下一甩,說道: (唱)“唔醫殺子胖個,扛不動。蒿里又蒿里!”(白)我里兒媳婦好,孝順得極,走得來,對子我深深里介一福,說道:“公爹,(唱)從今只揀瘦人醫。蒿里又蒿里!”*(清) 陳德蒼編《綴白裘》第十二集,中華書局點校本,1955年,第228頁。
按,“請醫”一折所保存的《蒿里歌》,應當反映了下層民間挽歌的演唱,其歌辭有明顯隨心編造的特點,但其每句后合唱“和聲”的形式,應當是所有挽歌的共同形式。值得注意的明樂天大笑生輯笑話集《解慍編》所收與《請醫》顯然有淵源的一則笑話,《解慍編》卷三“揀瘦者醫”條有:
一庸醫不依本方,誤用藥餌,因而致死病者,病家責令醫人妻子唱挽歌,舁柩出殯。庸醫唱曰:“祖公三代做太醫。呵呵咳。”其妻曰:“丈夫做事連累妻。呵呵咳。”幼子曰:“無柰亡靈十分重。呵呵咳。”長子曰:“以后只揀瘦的醫。呵呵咳。”*(明) 樂天大笑生編《解慍編》,中國戲劇出版社點校本,1999年,第12頁。
今日昆曲之折子戲多是明中葉后因舞臺演出而不斷打磨加工而成,其最終定型基本上可認為在清乾隆中葉。《請醫》一折在原戲中本為極為簡短的過場戲,后來被藝人加工成可演出長度約三十分鐘左右的折子戲。故筆者認為,《綴白裘》所收《請醫》中歌唱《蒿里歌》一段表演當主要據類似《解慍編》所載嘲笑庸醫類的笑話加工而成。兩相比較,其不同主要是: 一、《解慍編》中唱辭為整齊的四句七言詩,《請醫》中唱辭長短不齊;二、 “和聲”部分,《解慍編》為“呵呵咳”,《請醫》為“蒿里又蒿里”。對于后者,較易解釋。從一般情況看,凡用“和聲”的歌曲,其“和聲”部分的音樂旋律一般有相對穩定的特征,“和聲”部分的主要意義也在“樂”,不在“文”,故“和聲”的“文”可用無實指意義的虛詞(“呵呵咳”或“邪許喲”)或者虛指的“蒿里又蒿里”,故郭生唱蘇軾改造的寒食詩,也應是每句后另加“蒿里又蒿里”一類的虛指辭。
挽歌郎歌唱時一般是嚴守原詩,還是在本辭基礎上有所增益?齊言之詩(五言詩或七言詩)是否一定要變為長短不齊的雜言才能歌唱?對這一問題,若單純依賴相關挽歌的文獻材料則無從回答,我們只能依照常例去推定。從樂府詩歌唱的一般情況看,樂人或唱家往往要對原辭進行一番改造的。《南齊書》卷十一《樂志》有:“侏儒導舞人自歌之。古辭俳歌八曲,此是前一篇二十二句,今侏儒所歌,摘取之也。”*(唐) 蕭子顯《南齊書》,中華書局標點本,1974年,第195頁。其實,樂人或唱家對原辭的改造并非僅限于“摘取”這一種形式,以下僅取二例以說明之。魏武帝曹操《苦寒行》為很著名的樂府詩,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卷三十三并載其原辭以及其被晉樂演奏時的歌辭,我們現在將其并列如下:
本辭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阪詰屈,車輪為之摧。
晉樂 北上太行山,艱哉何巍巍。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羊腸坂詰屈,車輪為之摧。一解
本辭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路啼。
晉樂 樹木何蕭瑟,北風聲正悲。何蕭瑟,北風聲正悲。熊羆對我蹲,虎豹夾道啼。二解
本辭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
晉樂 溪谷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少人民,雪落何霏霏。延頸長嘆息,遠行多所懷。三解
本辭 我心何怫郁,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
晉樂 我心何拂郁,思欲一東歸。何拂郁,思欲一東歸。水深橋梁絕,中道正徘徊。四解
本辭 迷惑失故路,薄暮無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
晉樂 迷惑失徑路,暝無所宿棲。失徑路,瞑無所宿棲。行行日已遠,人馬同時饑。五解
本辭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
晉樂 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擔囊行取薪,斧冰持作糜。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六解
兩相對照,我們可以看到,晉樂演奏曹操《苦寒行》時,對原詩改動極少(僅將“迷惑失故路”改為“迷惑失徑路”、“薄暮無宿棲”改為“暝無所宿棲”),但歌唱時卻大量使用疊唱(如疊用“太行山”、“艱哉何巍巍”等),使得原來純粹的五言詩中加入少數三言詩句,入樂后的歌辭篇幅明顯超過原辭。
又如魏眀帝曹叡的《歩出夏門行》,《宋書》卷二十一、《樂府詩集》卷三十七并載其在魏晉時演唱的歌辭:
步出夏門,東登首陽山。嗟哉夷叔,仲尼稱賢。君子退讓,小人爭先。惟斯二子,于今稱傳。林鐘受謝,節改時遷。日月不居,誰得久存。善哉殊復善,弦歌樂情。一解
商風夕起,悲彼秋蟬。變形易色,隨風東西。乃眷西顧,云霧相連。丹霞蔽日,采虹帶天。弱水潺潺,落葉翩翩。孤禽失群,悲鳴其間。善哉殊復善,悲鳴在其間。二解
朝游清泠,日暮嗟歸(“朝游”上為艷)。蹙迫日暮,烏鵲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卒逢風雨,樹折枝摧。雄來驚雌,雌獨愁棲。夜失群侶,悲鳴徘徊。芃芃荊棘,葛生綿綿。感彼風人,惆悵自憐。月盈則沖,華不再繁。古來之說,嗟哉一言。(“蹙迫”下為趨)
按,這段署名魏眀帝的歌辭,實際上除采用曹操《短歌行》“烏鵲南飛”數句外,又取曹丕《丹霞蔽日行》全篇(略易數字),將“丹霞蔽日”到“悲鳴其間”六句插到第二解,又以“月盈則沖”以下四句放在篇末。
余冠英先生曾一語中的地指出:“古樂府歌辭,許多是經過隔截拼湊的,方式并無一定,完全為合樂的方便。”*余冠英《樂府歌辭的拼湊與分割》,見余冠英《古代文學雜論》,中華書局,1987年,第157頁。我們認為,唐前挽歌詩的演唱與一般的樂府詩無根本差別,故唐前挽歌詩的演唱也應有很多文辭的隔截拼湊。沈(佺期)、宋(之問)之后,隨著文人律詩(包括挽歌詩)的成熟,挽歌在歌唱文人所作挽詩時,隨意隔截拼接文辭的現象應當明顯減少*古體詩本無嚴格的格律限制,近體詩則不然,隔截拼接文辭很容易導致不合律。,故唐宋以后也有可能存在按照原詩演唱(每句后加“和聲”)的,前引《詩人玉屑》郭生唱寒食詩即應是這種情況。
以上我們對挽歌唱的探討,主要就其“文”(辭)而言,其“樂”究竟如何?相關挽歌的音響資料,筆者僅見兩種: 一是前文提及的《請醫》中的《蒿里歌》,二是韓國新編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中的一段挽歌表演*新編歌劇《羅密歐與朱麗葉》,韓國首爾藝術團音樂劇2008年10月26日上演于南京文化藝術中心。。《請醫》一折,今日國內江蘇省昆劇院、浙江昆劇團等院團尚能演出*《異同曲集》第四集二十二卷下冊、《拜月亭全記曲譜》卷三及《幽閨記曲譜》下卷第一部分等皆載其樂譜,因上述樂譜皆用工尺譜,錄入不便,故本文未引錄。。
從共通點來看,這兩處的挽歌唱都是無板眼節奏的徒歌,這一點也可與傳世文獻相印證。如清佚名撰《異聞總錄》所載某農人為鬼唱挽歌事亦可說明:
方子張,家居秀州魏塘村,其田仆鄒大善刀鑷。嘗有人喚之云:“某家會客,須汝為歔。”鄒謝曰:“吾所能只唱挽歌爾,何所用?”曰:“主人正欲聞此曲,當厚相謝。”鄒固訝其異,然度不可拒,密攜鈴鐸,置懷袖以行。既至,去所居甚近,念常時無此人家,而屋又窄小,且哀挽非酒席間所宜聽,益疑焉。將鼓鐸而歌,坐上男女二十余人同詞言曰:“吾曹皆習熟其音調,無唐□人相混也。”乃徒歌數闋。皆擊節稱善,歡飲半酣。……審其處,榛棘蒙蓋,蓋一古冢耳。*(清) 佚名撰《異聞總録》卷四,清康熙振鷺堂據明商氏稗海本重編補刻本,第26頁。
從文獻記載來看,挽歌歌唱的伴奏樂器主要是“鐸”,即一種借撞擊而發音的鈴類樂器,許多文獻皆可說明此點。如唐姚思亷《梁書》卷五十《謝幾卿》傳有:“(謝幾卿)肆情誕縱,或乘露車歷游郊野。既醉,則執鐸挽歌,不屑物議。”*(唐) 姚思亷《梁書》卷五十,中華書局標點本,1973年,第708頁。唐蕭嵩《大唐開元禮》卷一百三十九《兇禮》“陳器用”有:“鐸者,以銅為之,所以節挽者。”又云:“鐸,每振,先搖之,搖訖三,振之。”*(唐) 蕭嵩《大唐開元禮》卷一百三十九,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648頁。伯2662號寫本《書儀》敘述柩車發引,有:“以帛兩匹屬轜車兩邊,以挽郎引之,持翣振鐸,唱《薤露》之歌。”*轉引自周一良《魏晉南北朝史論集續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1年,258頁。以鐸伴奏唱挽歌的例證甚多,不具引征。《史記》卷五十七《周勃世家》說周勃早年“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唐司馬貞《索隱》曰:“《左傳》歌虞殯,猶今挽歌類也。歌者,或有簫管。”*(漢) 司馬遷《史記》卷五十七,中華書局標點本,1959年,第2065頁。司馬貞以為挽歌唱伴以簫管,顯然有誤解。
不是用可以表現音樂旋律的管弦伴奏,而是以簡單的打擊樂器伴奏,也從另方面說明了挽歌唱為徒歌式的吟唱。
述及挽歌演唱,也許有讀者會有興趣想知道: 假如春秋戰國時代即已有挽歌唱,除文獻普遍載錄的《薤露》、《蒿里》兩曲調外,人們歌唱挽歌時是否還使用其他曲調?戰國時代的《薤露》、《蒿里》,是否會歷兩千年之久一直有相對穩定的唱腔或旋律被傳唱至后世?換言之,李延年時代的《蒿里》與折子戲《請醫》中的《蒿里》是否有繼承性?
上述問題,實際都可以歸結到這樣一個根本性問題: 挽歌唱是否有確定的調高、調式、節奏、節拍以及確定的旋律腔調或唱調?
對這一問題的回答,實際上觸及了中國韻文歌唱“文”與“樂”的相互關系問題。按照筆者目前對這一問題的認識,筆者認為,(20世紀前未受西洋音樂觀念影響的)中國式的歌唱,其首要目的是傳辭,故其“樂”從根本上來看是為“文”(文辭、文意)服務的,“文”為主,“樂”為從。中國式的歌唱主要是方言入唱(也有可能盡力用官話或者盡力向官話靠近的方言),方言的字讀語音語調對樂音旋律高下有根本性影響(今日各地民歌、地方戲猶然)。從“樂”的角度看,某一唱調一開始可能會有相對穩定的旋律腔調,歌者也可以借用這一相對穩定的旋律腔調去“套”唱文字形式相同或相近的“文”(辭),但由于方言(或者努力“打官腔”的方言)的局限,而方言語音又始終處于變遷之中,更兼古代中國長期缺少較準確可靠的記譜符號和技術,這樣即使產生了相對穩定的旋律唱調,這樣其穩定性也勢必有很大的時間和空間的局限性,人去樂亡的現象普遍存在。從這一意義上說,時間跨度數百年或上千年,《薤露》或《蒿里》能始終保存其原始的旋律腔調,哪怕是部分保存,都是幾乎不可能的。
故我們可以肯定地回答說: 雖然從文獻記載看,《薤露》和《蒿里》兩調的歌唱被歷代文獻廣泛載錄,但西漢李延年之歌《薤露》,其唱調肯定不同于西晉之袁山松,也肯定不同于北宋之郭生。歷代的挽歌郎可能曾經創造和使用了無數不同旋律腔調的挽歌,這些當然挽歌也有共同的特征——皆為“摧愴之聲”,可令聽者“歔欷掩泣”——故稱“挽歌”。
六、 挽歌的案頭化與挽聯
自先秦直至近代,挽歌演唱雖一直綿延不絕,但我們也應指出,挽歌(詩)也有日益文學化或案頭化的一面。魏晉以前,挽歌詩的寫作不為文人關注,但魏晉以后,與中國文人詩歌的日益成熟和精致同步,挽歌詩的文學水平也日漸提高。挽歌詩同其他類詩歌一樣,也成為文學品鑒的對象,成為文人學士才學修養的重要表現。而且有許多挽歌詩都是在王公貴人亡故后,文人學士們應旨同時奉獻的,這就使人們咀嚼辭藻、品評高下成為可能,也為文人們展現才藝提供了特殊機緣。北齊“八米盧郎”的佳話,已可見時人對盧思道才情的無比艷羨,后代亦然,如北宋陶岳《五代史補》載五代時石文德獻挽歌事,云:
石文德,連州人,形質矬陋,好學,尤攻詩。霸國時屢獻詩求用,文昭以其寢陋,未曾禮待文德,由是窮悴。有南宅王子者,素重士,延于門下。其后文昭知之,亦兼怒王宅,欲庭辱文德而逐之。居無何,秦國夫人彭氏薨,文昭傷悼,乃命有文學者各撰挽詞,文德乃獻十余篇。其一聯云:“月沉湘浦冷,花謝漢宮秋。”文昭覽之大驚,曰:“文德有此作用,吾但以寢陋而輕之,乃不如南宮小兒卻能知賢耶?”于是始召文德而愧謝之,未幾承制授水部員外郎。*(宋) 陶岳《五代史補》卷三,明虞山毛氏汲古閣刻本,第18頁。
又如歐陽修《六一詩話》載宋初名儒李昉(925— 996)為宋太祖趙匡胤(927— 976)進獻挽詞事云: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為首出。*(清) 何文煥編《歷代詩話》,中華書局點校本,1980年,第264頁。
由此可見,挽歌詩特殊的寫作背景,使得挽歌詩極易為人矚目,也促使文人學士為其文字用心雕琢,精益求精。像丘靈鞠、石文德輩因獻挽詩而獲升遷,名利雙收,自然也是令時人艷羨之事。
但事物總是相反相成,當文人們為挽歌詩精心雕琢、不斷提高挽歌詩的文學水平時,其“樂”(由于主要是由社會底層的職業歌郎承擔)則并未相應地不斷進步,“文”的藝術水平遠遠高過“樂”,這必然導致挽歌“文”、“樂”這一對組合關系中愈來愈偏向“文”,乃至最終“文”成為“挽歌”的全部,人們主要關心其文字如何,至于其是否最終被付諸歌唱則無關緊要。由于漢字特有的屬性以及中國文人對文字的情有獨鐘,中國文學在魏晉時代即已相當成熟、精致,故魏晉時挽歌“文”與“樂”這一對組合關系中偏向“文”實際上已經發生,愈至后來則愈為突出。五代以前,文人挽歌詩仍多稱“挽歌”或“挽歌詩”、“挽歌辭”,五代以后則多稱“挽詩”、“挽辭”或“挽章”,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文”的提升和“樂”(歌)的降低。五代以后,雖然文人挽歌詩的寫作仍在持續,但已主要是文學之事。
挽歌詩出于悲悼亡者之意,多“述其行誼”、“美其功伐”,故孝子賢孫或門生弟子將所得之挽詩搜集成冊以表其孝義,元明以來亦漸成風尚。元著名文人許有壬(1287—1364)《特進大宗師閑閑吳公挽詩序》云:
至正六年十月七日,特進上卿玄教大宗師閑閑吳公薨于大都崇真萬壽宮承慶堂。中朝士大夫駢呇走吊,莫不哀傷,哀傷之不足,又形諸歌辭,諸弟子裒為卷軸,征序其首,以倡嗣音,以廣其哀焉。*(元) 許有壬《至正集》卷三十五,清文淵閣四庫全書補配文津閣四庫全書本,第207頁。
又,明永樂時名臣楊榮(1371—1440)《待詔滕公挽詩序》云:
姑蘇滕公用衡,年幾七十,承召至京師,仕為翰林待詔,凡五年,無疾而終。朝之士大夫相與賦哀挽之詩,于今又十年,積為巨帙,公之婿凌浩求予言以為序。*(明) 楊榮《文敏集》卷十三,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第167頁。
對挽歌詩,從“擇其尤悲者,令挽士歌之”,到將其裒集成冊、以廣流傳,顯示了挽歌詩的又一變遷,也可以說是挽歌詩日益案頭化的必然結果。
挽歌詩日益案頭化的另一結果,便是挽聯的日益流行。自魏晉時代起,偶對精工的詩句即很受人青睞,挽歌詩亦然,故丘靈鞠挽歌詩句“云橫廣階闇,霜深高殿寒”,深得宋孝武帝賞識。五代以來,隨著對聯寫作之風的興起,挽聯寫作也應始于此后不久。今人多以北宋人蘇頌(字子容)(1020—1101)為韓絳(字康公)(1012—1088)所寫“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為現存最早的挽聯。梁紹壬(1792—?)《兩般秋雨盦隨筆》“挽聯”條云:
挽聯不知起于何時,古但有挽詞而已,即或有膾炙二句者,亦其項、腹聯耳。(葉夢得)《石林燕語》載:“韓康公得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人。后為相四遷皆在熙寧中。”蘇子容挽(辭)云:“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此則的是挽聯之體矣。*(清) 梁紹壬《兩般秋雨盦隨筆》卷六,清道光振綺堂刻本,第193頁。
梁紹壬有關挽聯起源的這段話,梁章鉅(1775—1849)《楹聯叢話》曾全文轉錄,梁氏于此未加評述,這或即是今人將挽聯歸于蘇頌的文獻依據。然筆者頗疑蘇頌所撰“三登慶歷三人第,四入熙寧四輔中”僅為其挽詩中之一聯,因此聯概述韓絳生平事跡,頗為精工,故為時人傳誦。但同為概述亡者生平事跡、功業,如前引李昉挽趙匡胤時所撰“奠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顯然亦為“挽聯之體”,且早蘇頌百余年。在筆者看來,今日若想對挽聯產生之年代做出確定判斷,是非常困難的。但無論如何,考慮到文人詩中“聯”的相對獨立性,由挽詩的“聯”進而變為“挽聯”,可謂順理成章之事。
五代以后,當挽歌詩已主要是一種案頭文字,而不一定交付歌郎演唱時,其作為文字的功用(“述其行誼”、“美其功伐”)實際上也可基本上由挽聯取代。*我們這里說“基本上”,主要是因為挽聯還不能完全取代挽詩,挽詩比之挽聯有更久長的歷史傳統,故挽詩的寫作比之挽聯更顯鄭重,同時由于挽詩有較長篇幅,可以有數章,故可包括比挽聯更豐富的內容。明清以來,對聯寫作更為風行,這種風氣必然對挽聯寫作有更大的推動。同時,由于挽聯常可懸掛于靈堂(近世或用殯儀館)供參加喪事者的觀瞻,故在整個喪事活動中挽聯比之挽詩更易為人矚目。凡此種種,使得挽聯的地位,隨著歷史時間的推移,愈來愈有與挽詩并駕齊驅之勢,甚至最終超越挽詩。這就使得現代的人們,大多知挽聯而不知有挽詩,知挽詩而不知挽詩之用、挽詩之變。
小 結
兩千多年來,發生在挽歌中的變遷甚多,這些變遷可從以下幾方面稍加概括:
從民間文化和主流文化的關系而言,挽歌本為流行于民間社會的一種有具體實用功能的儀式,漢武帝以后開始為主流社會所接納和吸收,最終成為上層社會禮儀制度的一部分,挽歌也成為個人身份等級的標志之一。這一點恰反映了數千年中國傳統禮樂文化強大的吸收力和同化力。
從風俗時尚來看,挽歌初起時即作為送終之禮而用于喪事,有其特殊的使用情境和功用,唯“兇”事才用挽歌,但漢末以來即用于“賓婚嘉會”,成為人們娛樂游戲之一種,許多任誕之士更癡迷于挽歌,置流俗非議于不顧。挽歌的職業化也大概發生在此時,降至后來,挽歌歌唱乃成為職業唱家們才情修養的一部分,職業唱家們所作“摧愴之聲”,當然是有意為之,不必出于真情實感。
從文學與音樂的關系來看,挽歌的文學化歷程也印證了中國各類韻文演進的基本規律: 其初始階段,“文”與“樂”彼此依存,“樂”的地位相對突出,“樂”在客觀效果上推動了“文”的制作,但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文”(學)的日益提高,“樂”的地位則相對日漸降低,乃至無足輕重,導致“文”最終脫離“樂”,案頭化的文字幾成為全部。故“挽歌”一變為“挽歌詩(辭)”,再變為“挽詞”、“挽詩”、“挽章”和“挽聯”。從現象上看,古人留給今人難以盡數的挽(歌)詩、挽聯,而其樂則幾無一存。
2016年,123— 14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