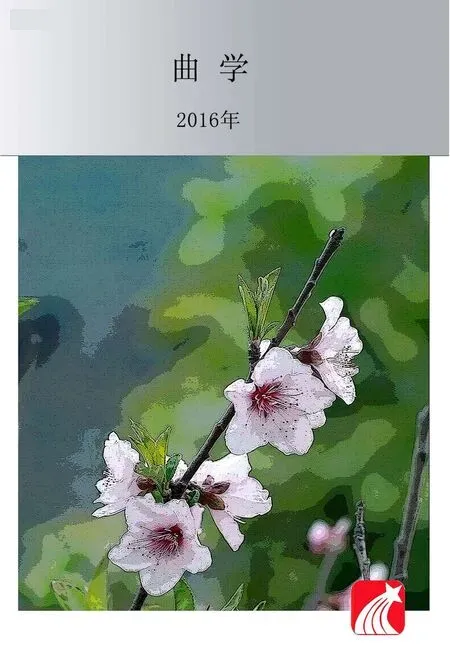考據學語境下的清中期戲曲理論
石 芳
《曲學》第四卷
考據學語境下的清中期戲曲理論
石 芳
考據為中國古代傳統治學方法,約萌芽于先秦,其法始用于治經,后用于治史,推而及其他學術門類。清代考據學為經學在清代的表現形態: 明中后期明理學演變所呈現出的弊端引起部分學人重視,他們開始強調博學求是;明末清初,異族入主中原,江山易代,學界痛定思痛,將“亡天下”歸因于宋明儒者拋棄元典,束書不學而空談性理,故主返經復古,務經世致用之學,以求救國之道。這股學術思潮,在經歷順康之世后,救亡圖存之用淡化,治學方法與學風則為學者繼承發揚,發展至乾嘉兩朝,氣象蔚然,領學術風潮近百年,其后余緒,至民國猶存。由于講求博證求真、質樸求實、不務空言,主要運用考據方法治學,清時學人即有認為考據學為清學特色及主流學術思潮者,又或以樸學稱之。
清中期戲曲理論指乾嘉兩朝(1736—1820)之戲曲理論,這一時期是清代考據學之鼎盛時期,同時也是清代戲曲最為繁盛輝煌的時期,樸學思潮深入滲透學界,諸多經史學家、音韻學家等亦投身于戲曲創作與戲曲理論建構,因此最為典型地呈現出清代學術思潮對曲論演變的影響和戲曲理論的時代變化。
考據學所注重的實地考察、親身體驗、邏輯論證、比較歸納的學術方法,廣征博引、懷疑批判、闕疑存異等學術規范與精神,在清中期曲論著述中得到更為普遍的體現,同時它所帶來的更深層次的曲論研究傾向、內容與著述體例的變化,也較之清前期更為鮮明地顯現出來——如果說明清之交的曲論尚多繼承明人之處演變到清中期,曲論更直觀地彰顯出時代的差異,同時也為清后期考據學語境下傳統戲曲理論的深化及總結做好了鋪墊。當然,由于戲曲與曲學地位所限,清中期曲論著述中,考據學治學方法的運用與學術規范的依循相較于經學著述,仍呈薄弱之勢,也時常不能做到以曲學為本而致于繁冗雜亂,逸出曲學本體研究之外,這種現象直至清后期梁廷枏、姚燮等著作的出現才得以改變。
經學思想的更替也引發了曲論三種變化,簡而言之,即以經為本,以史說法,以禮為度,它們萌芽于清前期,而在清中期形成主流。
其一,清代曲論家順應考據學返經復古的趨勢,認為戲曲是融六經于一體的藝術樣式,傾向于以六經之道為基礎闡發戲曲創作理論、表演理論等,強調經學對戲曲的統攝作用,由此強化了曲學與其他學術門類之關聯。清前期毛先舒即以經學為主導將音韻學、詩學、史學與曲論研究相貫通。至清中期,這種研究趨勢也促進了戲曲相關理論研究,清代曲論家強調六經與戲曲關系的論述主要見于這一時期,焦循更將其易學思想貫徹于曲學研究當中;由于向被視為“絕學”的音韻學、樂學在乾嘉時期進一步得到充足重視,戲曲音律研究成果也格外突出,徐大椿《樂府傳聲》、沈乘麐《韻學驪珠》、方成培《香研居詞麈》與《燕樂考原》即其代表。
其二,清初詩壇傷明史難存,倡“詩史”之論,曲壇亦興起“曲史”之風,要求以曲補史、寫史,發揮歷史教育功能,并出現典范之作《桃花扇》,歷史題材劇作之虛實關系處理問題、本事考證逐漸引起曲論界注意。至清中期,一方面“以曲為史”的創作傾向進一步推動了戲曲創作中的崇實傾向,還有部分投身于戲曲創作的考據學家,如董榕、桂馥、許鴻磐、孔廣林等,甚而以曲為經,將治學習慣延入戲曲創作之中,在凡例、序跋、附錄中進行戲曲本事、源流的考辨梳理,甚或戲曲語言也融入經史學問,進一步導致文人戲曲作品案頭化。另一方面,戲曲本事考證引起更為普遍的學術興趣,不獨諸多文人筆記時有涉及,曲論著作亦日益重視,并由此涉及歷史題材劇作之虛實關系處理問題。
其三,清初思想家反明學之弊,既不贊成“情”“欲”的過度張揚,也不贊成以“天理”為“禮”,過度束縛人的情感欲望需求。他們重張禮學以針對“理學”之弊,趨向于“以禮節情”而求協調,認為理想的道德規范應該達人之情、遂人之欲,并且能進行合理節制,這一理路為其后學者繼續拓展,清中期凌廷堪提出“以禮代理”之說,得到焦循贊同。由此,針對實現戲曲社會教育功能的主張也發生變化——即明代理學家主以“理”教之,心學家主以“情”導之,清代樸學家則主以“禮”范之。自清初鄒式金、李漁始,便有“言情”與“風教”兼美之主張。伴隨著學術批判深入和考據學的發展,清中期曲論家進一步重釋“情”字,以求得“情”與“禮義”之兼容,蔣士銓、李調元對“情”與“禮”關系的辨析,焦循“人己之情通”的主張,都具有代表性。
另外,清代考據學思潮也使得乾嘉時期戲曲理論呈現出兩種典型時代傾向,一是清前期務實致用思想在乾嘉時期雖有所淡化,但在曲論著述中繼續發揚。部分學人致力于使個人的理論研究切實服務于戲曲創作與舞臺演出需要,例如沈乘麐、徐大椿、李調元、焦循、凌廷堪之曲論著作,都體現出立足現實,務求實際以致用的特征。二是清初學人以復古返經方式求學術解放,而追本溯源,曲論家亦以元曲為宗,崇古思想在清中期曲論領域演化為較為明顯的復古崇元意識,凌廷堪、焦循為其中代表,至清后期,則轉變為推崇康乾時期。
由乾嘉時期代表性曲論著述,可以更明確地了解考據學語境下,曲論著作由考據方法的引入而引起的文體、內容與研究方法的變化。在共同的時代特性下,曲論家之戲曲思想和曲論觀點也各有特征,顯現出考據學語境下曲論的較為復雜變化。
一、 音韻學成果與《韻學驪珠》《樂府傳聲》
沈乘麐的《韻學驪珠》與徐大椿的《樂府傳聲》均誕生于乾嘉時期,前者主要為歌者演唱和指導南北曲創作而作,后者專為指導歌者演唱而著。二者的部分內容,呈現出清代音韻學空前發展語境下戲曲音律著作的變化,徐大椿之《樂府傳聲》更頗有借歌唱之法推導古樂,以助樂學研究之用的意圖。
(一) 沈乘麐與其《韻學驪珠》
元代周德清作《中原音韻》規范北曲用韻;南曲興起并流行后,魏良輔改革昆山腔,以《中原音韻》為南北曲應當遵從的用韻規范;其后以沈璟為代表的吳江派亦認同此論。但是,明初官方修訂的《洪武正韻》沒有為明代作家廣泛采用,大量曲家仍以《中原音韻》為用韻參考,明后期以王驥德為代表的曲論家指出曲有南北之分,用韻亦應有所區分,加之《中原音韻》有諸多不合于南曲用韻的疑難之處,明代起即有曲學家重新撰寫韻書以適應實際創作需求,如沈寵綏之《度曲須知》和范善溱之《中州全韻》。入清后,毛先舒曾撰《南曲正韻》(擴略刊行于《韻學通指》),這些著作各有創見,但仍然未能徹底解決南北曲用韻問題。至清中期,沈乘麐《韻學驪珠》、王鵕《中州音韻輯要》、周昂《增訂中州全韻》先后立足于《中州全韻》,參考《中原音韻》與《洪武正韻》,試圖解決這一難題,其中又以沈書最早且最為切用。
三部曲韻書是南北曲發展與學術思潮演進到一定階段情況下之產物。乾嘉時期是清代音韻學研究的鼎盛時期,名家輩出,如江永、戴震、段玉裁、孔廣森、王念孫等,不勝枚舉。其因在于清代考據學者認為小學研究與經學關系莫大,繼清初顧炎武“讀九經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清) 顧炎武《答李子德書》,見《亭林詩文集》,上海涵芬樓影印清康熙刊本,卷四,第6頁。的主張之后,清中期學者更進一步視小學為求索經學本義之根本途徑。段玉裁認為:“治經莫重于得義,得義莫切于得音。”*(清) 段玉裁《〈廣雅疏證〉序》,見王念孫《廣雅疏證》,清嘉慶王氏家刻本,卷首。王念孫之語更為人熟知:“訓詁聲音明而小學明,小學明而經學明。”*(清) 王念孫《〈說文解字注〉序》,見段玉裁《說文解字注》,經韻樓刻本,卷首。三部曲韻著作即誕生于音韻訓詁之學格外發達的時期,作者均具備深厚的韻學功底。與為經學研究服務之音韻學家不同的是,三者研究目的均系服務于曲學,看重的是現實南北語音而非古音。雖然韻學中曲韻研究不受重視,但相較于其他曲學著作則稍勝一籌,曲韻著作也往往有正統音韻學著作所不及者,如毛先舒從沈寵綏《度曲須知》悟“收音六條”之說,李光地編纂《音韻闡微》,又從毛、沈二人曲韻著作中得到啟發。
沈乘麐歷五十年,七易其稿,終成《韻學驪珠》一書。此書自問世后,便為度曲家奉為圭臬,并成為昆曲界唱念所遵奉的經典。周昂稱:“夫以舉世絕不留心之事,而費五十年之功為之,與章道常《音韻集》致力略相似。”*(清) 周昂《〈韻學驪珠〉序》,見沈乘麐《韻學驪珠》,中華書局,2006年,第47頁。可見其用心不下于正統音韻學家。
從《韻學驪珠》之體例與內容來看,除沈乘麐所列舉諸書外,它可能還參考了當時最新的音韻學研究成果,即清前期李光地、王蘭生奉旨編纂的官方韻書《音韻闡微》。《音韻闡微》的獨特之處包括編纂體例的革新和反切之法的改良,《韻學驪珠》也恰有此優點且又更進一步,通過二者之比較更好地理解《韻學驪珠》之進步與貢獻。
《音韻闡微》體例的獨到之處在于韻書結構安排,它將此前韻書依據等韻原理劃分小韻的方法進一步明朗、系統化。其以韻部為經,字母為緯,每韻部下按照“四呼”(開、齊、合、撮)分為四類,每類據三十六字母劃分不同聲母字,三十六字母又進一步分為四等。每韻部下小韻的劃分兼顧每字之聲母、韻母、聲調,清晰明了,但歸類仍稍顯繁瑣。《韻學驪珠》更為簡潔一些,它以七音*七音源于五音,五音指宮、商、角、徵、羽,對應喉、齒、牙、舌、唇五個聲母發音部位,后等韻學家又增半舌音、半齒音為變宮、變徵,三十六字母統于七音。劃分小韻,即按聲母類別劃分韻部,入聲單分為八個韻部,每韻部下分平、上、去三聲,平、去分陰陽,上聲陰陽注于字下;*入聲八個聲部無平、上、去之分,僅分陰陽,余同其他二十一韻部。三聲下以七音統字,七音下復按清濁與呼法細分,從字尾之類別進一步區分;除入聲單列外,南北音有別之字于字下另注,簡潔且便于比較。《音韻闡微》以三十六字母分四等、四呼以統字,已經使韻書的小韻劃分清晰明朗且系統化,但《韻學驪珠》以七音代替三十六母,而以陰陽、清濁、呼法進一步細分,以邏輯層次代替類別之間的并列,更為清楚簡潔;而其經緯配合,又考慮到了唱念之需求,兼顧字頭、字腹、字尾,直觀呈現了各字念法,便于南北曲創作和演唱之需。沈乘麐以等韻理論統籌小韻,體例編排精微細致,層次分明,而發音、收音之法的直觀呈現也考慮到了曲韻書的實用性,體現了乾嘉學術求實、務實之精神。
《韻學驪珠》的反切之法較之《音韻闡微》也更為靈活通變。反切法雖有許多優越性,卻一直存在兩個障礙:“一是拼讀的窒礙,一是用字的麻煩。”*林序達《反切概說》,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頁。歷代音韻學家試圖通過規范反切用字來改良反切之法,至明代呂坤《交泰韻》和清初潘耒《類音》,都力圖使反切二字連讀可得被切之字音,要求反切上字必須與被切字聲母、清濁相應,反切下字盡量選用零聲母字,反切用字盡量減少并統一,這樣主張并無問題,但二人的嚴格執行,造成了好用生僻字的新問題,使反切實際上失去了注音功能。清代致力于改良反切的音韻學家較多,如樸隱子《詩詞通韻》中附《反切訂譜》,王鵕《〈中州音韻輯要〉凡例》中反切之法的闡述。其中,清前期《音韻闡微》受滿文十二字頭啟發,彰明了與呂、潘相類的主張,提倡“合聲”之法:“蓋翻切之上一字定母,下一字定韻。今于上一字擇其能生本音者,下一字擇其能收本韻者,緩讀之為二字,急讀之即成一音。”*(清) 李光地、王蘭生等撰《音韻闡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40冊,第 9頁。即要求反切上字呼法與被切字一致且不帶輔音韻尾(此即李光地所要求的歌、麻、支、微、齊、魚、虞七部),下字則選零聲母字,且《音韻闡微》不用生僻字。然而由于漢字注音的局限,即使李光地、王蘭生極力改良,也無法以上述規則注所有漢字,故以借用、協用、今用等法彌補,羅常培稱:“拿合乎原則的百分之一二·五和百分之六六·七以上的例外對峙,怎么能希望它行得通呢!”*羅常培《王蘭生與〈音韻闡微〉》,見《羅常培語言學論文集》,商務印書館,2004年,第404頁。
《韻學驪珠》最大限度地發揚了“合聲”法之妙,沈乘麐盡量選用固定、簡單的反切用字,嚴格要求反切上字的清濁、陰陽、呼法,盡量保持聲調與被切字的一致或相近,盡量選用不帶輔音韻尾的字,即使偶然例外,也選擇反切上字韻尾與下字聲母發音部位相近之字,以求上下字連讀和諧,如“朗,冷沆切”;反切下字的選用較反切上字更為統一、固定,且嚴格要求與被切字聲調、韻母相同。《音韻闡微》用零聲母字,即“影、喻”二母字,故而出現韻母不夠而借韻的局限,《韻學驪珠》反切下字絕大部分選用“影喻”二母字,次而選用與“影、喻”二母同屬喉音的“曉、匣”二母字,再次之,選用牙音“見、溪、群、疑”諸母(此部分相對而言極少),以求上下字連讀之和諧,相比較其他聲母的發音位置,沈乘麐考慮到了在缺乏“影、喻”二母情況下,喉音、牙音作為介音,與上字連讀能夠產生相對更為良好的拼讀效果。因此,就實際拼讀而言,《韻學驪珠》在拼讀效果不受影響的情況,其反切有“合聲”和近于“合聲”的效果,也能更準確地呈現被切字讀音,自然也就更適宜于戲曲創作與演唱之需。劉禧延十分贊賞沈乘麐反切之精:
近太倉沈苑賓《韻學驪珠》以《中州全韻》為底本,參以《中原音韻》、《洪武正韻》,其切音又加明顯(按,指潘耒《類音》反切而言有進步),總之上音用同呼字,下音用本韻影喻二母字,相摩而合成一音,呼之者固讀二字之音,聽之者止覺為一字之音。*(清) 劉禧延《中州切音譜贅論》,任中敏編《新曲苑》(六),中華書局,1940年,第56頁。
晚清劉禧延注意到《韻學驪珠》反切之精,和周昂一樣都認為沈乘麐反切之法較潘耒稍高一籌。
《韻學驪珠》是對此前與當時音韻學的繼承與進一步開拓,有著正統音韻學著作所不能及者;其以治經學之精力明聲音之道,非為“通經”而系“通曲”,更屬難能可貴。這部精妙切用的曲韻理論著作自問世后被曲界奉為圭臬,顯示出其價值與意義。
(二) 徐大椿與其《樂府傳聲》
《樂府傳聲》約成于乾隆甲子年(1744),徐大椿幼時棄時文而事經學,博學多能,醫術與醫學著作出色,兼擅天文、水利、地理、武藝等致用之學,秉持了清初以來考據學者崇尚博學、注重實地調查研究、關注現實的學術精神,故能注意到現實戲曲演唱的弊端,并在實踐中嘗試以等韻學知識規范演唱技巧,進一步概括為系統化的聲樂理論,指導演唱藝術。
作為乾嘉學者,徐大椿以經學為指導的學術思維,使《樂府傳聲》這一聲樂理論著作有鮮明的探求古樂、輔翼經學的動機。他表明:“樂之亡,先王之教失也。我謂欲求樂之本者,先從人聲始。”*(清) 徐大椿《樂府傳聲》,《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58頁。是以他以人聲為樂之本,以唱曲之道為延續古樂之途徑:
又數十年來,學士大夫全不究心,將來不知何所底止。嗟夫!樂之道久已喪失,猶存一線于唱曲之中,而又日即消亡,余用憫焉,爰作傳聲法若干篇,借北曲以立論,從其近也;而南曲之口法,亦不外是焉。古人作樂,皆以人聲為本,《書》曰:“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人聲不可辨,雖律呂何以和之?故人聲存而樂之本自不沒于天下。*(清) 徐大椿《〈樂府傳聲〉序》,《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中國戲劇出版社,1959年,第153頁。
清前期學者為研究樂學,已重視人聲之作用。顧炎武《日知錄》指出:“言詩者,大率以聲音為末藝,不知古人入學自六藝始,孔子以游藝為學之成。后人之學好高,以此為瞽師、樂工之事,遂使三代之音不存于西京。西京之音不存于六代;而聲音之學,遂為當今之絕藝。”*(清) 顧炎武著,周蘇平、陳國慶點注《日知錄》,甘肅民族出版社,1997年,第239頁。以聲音為樂之本而提升聲音之學的地位。毛奇齡《竟山樂錄》云:“先臣嘗曰:‘樂未嘗亡也。樂者,人聲也,天下幾有人聲而亡之理?自漢后論樂,不解求之聲,而紛綸錯出,人各為說,而樂遂以亡。’”*(清) 毛奇齡《竟山樂錄》,中華書局,1985年,第2頁。闡述人聲和樂學的關聯,從人聲不會消亡的特征強調以人聲探求古樂的合理性。雍正初期成書的官方音韻學著作《音韻闡微》也注重人聲與樂的關系:“天地有自然之聲,人聲有自然之節,古之圣人得其節之自然者而為之依永和聲,至于八音諧而神人和,胥是道也。”*(清) 李光地、王蘭生等《音韻闡微》,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第240冊,第1頁。在考據學之發端期,由小學而通經的思維已使學者們注意由音韻之學考求古樂之道的重要意義,較好地將聲音之道與樂學融會貫通的是清中期徐大椿的戲曲演唱理論著作,他不單借樂的社會功能強調其演唱理論的價值與意義,更具體地將“樂”分為七個部分,表明了人聲作為樂的構成要素的意義,進一步運用了等韻學理論構筑其演唱理論。
《樂府傳聲》口法部分吸收了清前期潘耒的音韻學研究成果,將其貫入戲曲演唱理論。元代燕南芝庵著有《唱論》,其演唱理論多通過描述曲情、音色風格等論述演唱技巧;至魏良輔《曲律》,則指出:
五音以四聲為主,四聲不得其宜,則五音廢矣。平上去入,逐一考究,務得中正。如或茍且舛誤,聲調自乖,雖具繞梁,終不足取。其或上聲扭做平聲,去聲混作入聲,交付不明,皆做腔賣弄之故,知者辨之。*(明) 魏良輔《曲律》,載傅惜華編《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人民音樂出版社,1957年,第27頁。
已簡單提及等韻學之五音、四聲與戲曲演唱之關系,明代王驥德《曲律》也曾以等韻學概念述演唱理論,如《論閉口字》、《論腔調》部分內容。明確提出韻學之理與演唱之理相通者有沈寵綏《度曲須知》:
予嘗考字于頭腹尾音,乃恍然知與切字之理相通也。蓋切法,即唱法也……守此唱法,便是切法,而精于切字,即妙于審音,勿謂曲理不與字學相關也。*(明) 沈寵綏《度曲須知》,載傅惜華編《古典戲曲聲樂論著叢編》,第86、87頁。
沈寵綏論韻學的切入點為反切與唱法,故而《度曲須知》論演唱技法,也著重從“收音”“反切”與“字頭、字腹、字尾”三個方面詳細闡述,清初音韻學家毛先舒的“收音六條”之說即受沈氏“收音”之論啟發。徐大椿《樂府傳聲》演唱方法的理論來源系潘耒之《類音》。徐大椿自述云:
余之留心詞曲也,當弱冠從意庭先生游,先生適校潘稼堂先生所著《類音》,其書集天下有字無字之音,皆以反切出之,分晰精微,不爽毫發。余頗有會心,四呼五音之理,日往來于心。每聽優人所唱之音,皆模糊不能辨識,心竊疑之。乾隆七年,先慈目眊,無以為娛,延老優衛天衢者至家,買二童子,教之唱曲,以博母歡,所唱即世俗戲曲也,盡有音而無字。余誨之曰:“曷不遵四呼五音而出之乎?”衛曰:“此不可入管弦也。”余曰:“我試唱而若吹之,果協調乎?”吹之甚協。衛大服,遂以其法教童子,音高節朗,迥非凡響,乃伸其說,著《樂府傳聲》。*(清) 徐書城纂修《吳江徐氏宗譜》,清乾隆五十七年稻香樓刻本,卷三,第55頁。
意庭先生即徐大椿之師周振業,康熙間與潘其炳校其父潘耒之《類音》,而潘徐兩家亦數代交好,故徐大椿熟悉潘耒韻學著作。他試圖打通兩種學問,以四呼五音之法點撥伶人演唱技法。他已朦朧意識到人體作為發音器官的作用,視其為“履中蹈和之具”,《樂府傳聲》之《出聲口訣》與《聲各有形》,從口腔之構造闡述吐字發聲必須尊重五音四呼原則的原因,然后從五音、四呼擴及鼻音、閉口音,闡述唱念之道。
潘耒為顧炎武弟子,亦精音韻之學,其《類音》最大的特色是提出了“四呼”概念。等韻學中呼法分類此前并未統一,鄧文彬指出:“他(潘耒)是等韻學史上第一個把‘四呼’的概念、類型、范圍和特點描繪清楚的人,對后世有很大影響,后世基本上沿用了他的說法。”*鄧文彬《中國語言學史》,北京交通大學出版社,2006年,第121、122頁。《類音》指明四呼和四呼之要云:
何謂四呼?曰: 開口也,齊齒也,合口也,撮口也,凡有一字,即具此四呼。
音之由中達外,在牙腭間則為開口,歷舌端則為齊齒,畜于頤中則為合口,聚于唇端則為撮口。*(清) 潘耒《類音》卷一,清康熙遂初堂刻本,第26頁。
《樂府傳聲》則云:
開、齊、撮、合,謂之四呼。此讀字之口法也。開口謂之開,其用力在喉;齊齒謂之齊,其用力在齒;撮口謂之撮,其用力在唇;合口謂之合,其用力在滿口……今人雖能知音之正,而呼之不清者,皆開、齊、撮、合之法不習故也。*(清) 徐大椿《樂府傳聲》,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第161、162頁。
顯然,徐大椿在接受潘耒四呼之論基礎上,領悟四呼發音之技巧,闡述演唱吐字之要,以求歌者唱念準確,確實發前人所未發。
徐大椿還辯證接受了潘耒的五音之論。潘耒所述五音與傳統韻學家所論五音并不相同,《類音·聲音元本論下》不滿古代韻學家牙、舌、唇、齒、喉的五音之說,認為五音有天然次序,由喉、舌、腭、齒、唇依次而出。實際上,古人所云“牙”指靠近喉嚨的大牙,牙音實為舌根音,隨著語言的發展,牙、齒統稱牙齒,潘耒誤以為牙音“僅抵腭也”,還改三十六字母為五十字母,五音各統十母。王力《〈類音〉研究》已指出潘耒之誤,認為其改法比不上古人高明。徐大椿《五音》一篇則云:
喉、舌、齒、牙、唇,謂之五音。此審字之法也。聲出于喉為喉,出于舌為舌,出于齒為齒,出于牙為牙,出于唇為唇,其詳見《等韻》、《切韻》等書。最深為喉音,稍出為舌音,再出在兩旁牝齒間為齒音,再出在前牝齒間為牙音,再出在唇上為唇音。*(清) 徐大椿《樂府傳聲》,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第161頁。
他釋齒音為舌根音,認為牙音發于前牡齒間,五者發音自有其天然秩序,次第而出。這樣的闡釋與重新排序,都表明對潘耒五音之論的認同。
除四呼、五音外,徐大椿的陰陽之論也受到潘耒啟發,潘耒認為:“物莫不有陰陽,其在音也,重則為陰,輕則為陽;一陰一陽,常相對偶。”“陰陽之必相對……有一音出焉,既得其陰,必得其陽。”*(清) 潘耒《類音》卷一,清康熙遂初堂刻本,第4、5頁。徐大椿《四聲各有陰陽》明確指出:
字之分陰陽,從古知之……惟《中原音韻》,將每韻分出,最為詳盡;但只平聲有陰陽,而余三聲皆不分陰陽,不知以三聲本無分乎?抑難分乎?抑可以不分乎?或又以為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此更悖理之極者。蓋四聲之陰陽,皆從平聲起,平聲一出,則四呼皆來,一貫到底,不容勉強,亦不可移易,豈有平聲有陰陽,而三聲無陰陽者,亦豈有平去入有陰陽,而上聲獨無陰陽者。*(清) 徐大椿《〈樂府傳聲〉序》,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七),第163、164頁。
與《樂府傳聲》前后問世的《韻學驪珠》,也不約而同地在韻類編排上明四聲陰陽之別,其后周昂的《增訂中州全韻》、清末王德暉和徐沅澂之《顧誤錄》,也都延續此見。顯然,音韻學和昆曲演唱藝術的發展,促使曲韻學與戲曲演唱論進一步精細化。
徐大椿借由等韻學理論闡述唱曲之道,以有功于樂學研究,實為戲曲演唱理論做出了貢獻,并利于指導演唱實踐。他對潘耒音韻學成就與謬誤的繼承,也牽涉到后世相關研究,清末民初吳梅《中國戲曲概論·度曲》和王季烈《螾廬曲談·論口法》,便受到直接影響。
二、 經學家李調元與曲話的歷史嬗變
李調元生逢乾嘉鼎盛之際,其學嗜博,著述以經學為主,而又廣及音韻訓詁、史學金石、天文地理、詩文戲曲,幾乎無學不涉,然其雖博通群籍,展乾嘉之風,但專精之藝,則非所能,難稱乾嘉名家。至于曲學,有曲論專著《雨村曲話》、《雨村劇話》(以下簡稱“二話”)。作為乾嘉經學家,其學術思想和以考據治學的方式卻也同樣貫徹曲學著作,二話雖也有博涉而難專精之特征,卻系諸作之中,最為學界重視且稱道者。
(一) “曲話”文體的定義與“二話”之考據特點
李調元以“曲話”“劇話”區分其兩部戲曲理論著作,但廣義而言,“二話”均屬于曲話范疇。楊劍明《曲話文體考論》總結“二話”特征:
實現著述主體通過戲劇事象的考核和例證的歸納,在為藝術史提供可信材料的同時,作出一定的科學結論或形成界說戲劇事象本質的概念。是為戲劇學在近代形成完整學理邏輯的最早發端。*楊劍明《曲話文體考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242頁。
此論對“二話”經由考據方法確立曲話的文體定義給予了高度評價,在考據學最為發達的乾嘉之際,李調元主動,且有意識地以考據研究小道末技之戲曲,將其運用于曲話之限定,不僅清晰地確立了曲話之定義,且構筑曲話體例的新嘗試,開辟了其后戲劇學著作的探索方向。
《雨村曲話》在引《涵虛曲論》中論元代各曲家作品風格后所下按語云:
曲話惟此最先。自王弇州《曲藻》以前,未有論及者。今各家曲雖多失傳,存此尤有考其萬一。*(清) 李調元《雨村曲話》,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10頁。
依據朱權品評之語的議論屬性,李調元將《涵虛曲論》判斷為《曲話》之發端,同時又在乾嘉考據學注重文獻思想指引下,認為其有“考其萬一”的保存文獻功能,自覺歸納與限定了曲話的文體屬性。
李調元之前的曲學家已經有意識地按照曲話的議論與記錄屬性勾勒曲話輪廓,然這類曲話性質的著述內容,許多附于筆記小說,或合并于詩話、詞話作品之中;系統的、獨立單行的專著,如徐渭《南詞敘錄》、呂天成《曲品》、祁彪佳《遠山堂曲品》等,也都還未冠以“曲話”之名。清初張大復《寒山堂曲話》提出“曲話”之名,但附于《寒山堂曲譜》中,條目大半襲自凌濛初,未能對“曲話”定義表現出更多的探索,因此,李調元《雨村曲話》之出現具有典型意義。
“話”實為一種十分自由,且包容性極強的文體,曲話的產生源于對詩話、詞話類文體的模仿。章學誠考定“詩話”云:
詩話之源,本于鐘嶸《詩品》。然考之經傳,如云:“為此詩者,其知道乎?”又云:“未之思也,何遠之有?”此論詩而及事也。又如“吉甫作誦,穆如清風”,“其詩孔碩,其風肆好”,此論詩而及辭也。事有是非,辭有工拙,觸類旁通,啟發實多。江河始于濫觴,后世詩話家言,雖曰本于鐘嶸,要其流別滋繁,不可一端盡矣。*(清) 章學誠撰、李春伶校點《文史通義》,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43頁。
“話”這一體裁可以由本體而及各種相關文獻考辨、軼聞時事記載、議論批評等,明人更側重于“辭有工拙”,清人更側重于“事有是非”。李調元有《雨村詩話》《雨村詞話》《雨村曲話》《雨村劇話》《雨村賦話》,顯然有意以“話”創作一個完整的批評系列來品評詩、詞、曲、劇、賦。因此,李調元限定曲話定義的第一步,即從文學體裁之區別,確立“曲話”文體的獨立意義;第二步,作為經學家的李調元尋根究源,追溯“曲”、“劇”二字之本義,由考證而認為“曲”系與詩詞一脈相承的、與樂相配之韻文,“劇”為始于優伶表演的有道德教化功能的演劇活動,注意到作為場上之曲的戲曲是一種群體性的藝術活動。這種以訓詁明字義之本區分著作內容的劃分標準,與明代祁彪佳依據體裁區分“曲”與“劇”全然不同。
徐大椿認為“樂”的構成有七種要素,將其分屬為文士大夫、樂工、演唱者三者之事,李調元的認識有異曲同工之處,《雨村曲話》多就“文士大夫”而論,《雨村劇話》則廣及戲曲活動其他人員,如樂工、歌者、觀眾等,他們均認識到文人士大夫之參與只是戲曲活動的一部分。李調元特重花部、主張花雅并存,《雨村劇話》卷上末八條,均為各種地方聲腔的記載與考證文字,他認為:
《詩》有正風、變風,史有正史、霸史,吾以為曲之有“弋陽”、“梆子”,即曲中之“變曲”、“霸曲”也。*(清) 李調元《雨村劇話》,《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47頁。
以地方聲腔入“劇”、關注戲曲演劇活動之動機正源于此,即在經學觀念指導下充分重視民間戲曲活動之價值與意義。當然,李調元追溯根源,區分文學本體與演劇本體的做法,除乾嘉時期治學方式的自然運用外,也反映出清代戲曲演變的影響——即花雅相爭,案頭創作與舞臺演出日漸分離的戲曲現象促使了李調元“曲”“劇”分離觀念的形成。
李調元繼之進一步限定曲話之著述體例,比較科學地條理出“二話”的編排序列。作為乾嘉時期經學家,李調元選擇匯輯札記體條目的曲話文體,是因為它切合考據學治學特征。札記體以靈活便捷的著述方式契合了考據學學術需求,適合微觀研究,能隨時隨地記錄考據學家所思所得,便于學術積累與學術更新,最終呈現學者之學術品性與學術分量,是清代學人極為青睞的著述方式,清代諸多經典考據學著作即學術札記。自李調元之后,焦循、梁廷枏、姚燮、楊恩壽也紛紛選擇了曲話文體。片斷化的札記條目的輯錄匯編,決定了“話”之體例編排難以擺脫零散、系統性不足的特征。李調元的“二話”卻以史為序,以類相從,通過分類歸納與排序形成了較為清晰的邏輯序列,這是一種有益的嘗試,較之其后焦循曲話著作更為清晰,也開辟了梁廷枏、楊恩壽之改良路向。
除“曲話”之文體確認,李調元用考據方法治曲,為曲話注入了新的特色,由原先元明曲話側重于品評議論的特性轉而重視記錄與考辨,明確顯現出清代曲論著作的轉型特征。當然,嗜博而不講求專精,大量征引與剿襲,也使得李調元“二話”呈現出一些弊端,較好地顯現李調元考據學功底和獨立學術思考的是《雨村劇話》。
李調元納本事考證入“曲話”范疇,他承認戲曲有“謬悠”之特征,其考證與胡應麟相似,即學術目的在于考證歷史文獻與故事內容之聯系與區別,故李調元并不就二者異同多作批評,褒貶暗含于結論之中,秉持了乾嘉考據學實事求是、客觀公正的治學原則。其考據顯示出作者歷史文獻與戲曲涉獵之廣博,如:
《呂蒙正破窯》劇,《避暑錄》:“文穆為父所逐,衣食不給。龍門寺僧識其貴人,延至寺中,鑿山巖為龕居之,凡九年。后諸子即石龕為祠堂。”按: 元關漢卿、王實甫俱撰《蒙正風雪破窯記》,貢性之有《風雪破窯圖詩》。破窯,當即石龕。又據《宋史》,與蒙正共淪躓者,母劉氏也,今傳奇乃謂蒙正妻。又飯后鐘事,見《北夢瑣言》,乃段文昌事——《摭言》傳為王播事,今以移屬呂文穆,乃自元人馬致遠始。又《彩樓》劇饐瓜事,見邵伯溫《聞見錄》。*(清) 李調元《雨村劇話》,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58頁。
此雖部分參考了翟灝《通俗編》,但能將傳奇對史事的改編挪用一一指明,如數家珍,也彰顯出李調元博學多識的考據功底,更表明對戲曲文獻之熟悉。需要指出的是,考據家具體而微、注重細節的治學習慣也給《雨村劇話》帶來一定的問題,且一定程度上帶有以歷史為本位的傾向,務求史實真實而糾纏于細枝末節,以致失之繁瑣,于戲曲藝術本體研究意義并不太大。如考蘇秦與《金印記》條云:“秦行第三,故云季子,俗乃謂行二,與史傳注文不合。”*同上,第49頁。
《雨村曲話》內容更近于傳統“曲話”,剿襲處較多,考據水平略呈弱勢。如李調元考《西廂記》作者,張人和《〈西廂〉曲論辯誤》指出:“李調元、梁廷枏以《曲藻》為據認定王實甫作于‘碧云天’止,不僅不符合王世貞原意,而且也是沒有根據的。”*張人和《〈西廂〉曲論辯誤》,載張月中主編《元曲通融》(下冊),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1870頁。李調元曲解王世貞之語,梁廷枏《藤花亭曲話》之論轉引自《雨村曲話》,受其誤導。又如:
作曲最忌出情理之外。王舜耕所撰《西樓記》,于撮合不來時,拖出一須長公,殺無罪之妾以劫人之妾為友妻,結構至此,可謂自墮苦海。舜耕,高郵人。*(清) 李調元《雨村曲話》,見《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20頁。
實系剿襲金兆燕《〈旗亭記〉凡例》,又誤解、誤信《藝苑卮言》,錯將王世貞所言《西樓樂府》當成《西樓記》,混淆了王舜耕與王磐籍貫。攘人之美、曲解文獻、輕率征引,均非考據學所主張。
作為經學家,李調元將考據方法引入曲話,多有開拓,且為曲論著述帶來諸多新的特征。正如四庫館臣評價楊慎學術:“漁獵既富,根柢終深,故疎舛雖多,而精華亦復不少。”*(清) 永瑢、紀昀主編,周仁等整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海南出版社,1999年,第621頁。這一評價也適用于李調元。然乾嘉學術鼎盛之際,正是考據學治學原則陸續規范之際,這些與乾嘉學者所倡導的學術原則背道而馳的舉動,也無疑削弱了兩部曲論專著之價值,曲論著述中考據方法的施用尚待進一步深入與規范。
(二) 融匯諸家,鑄為新論
李調元擅長融合他說,鑄為新論。作為乾嘉時期的考據學者,這種對前說的更改化用,呈現出其作為乾嘉時期學者和精通戲曲的曲論家充滿時代色彩的理論認識。
《〈雨村曲話〉序》承明代張琦《情癡寤言》之語而予以補充,這種補充反映出兩個時代學人截然不同的曲論主張。張琦原文為:
古之亂天下者,必起于情種先壞,而慘刻不衷之禍興。使人而有情,則士愛其緣,女守其介,而天下治矣。*(明) 張琦《衡曲麈譚》,見俞為民、孫蓉蓉編《歷代曲話匯編》(明代編)第三集,黃山書社,2006年,第 348頁。
主心學之張琦,其論強調了“情”的巨大力量,然李調元則添加了數語:“夫曲之為道也,達乎情而止乎禮義者也。”“知其則而止乎禮義,而風醇俗美。”“不知其則,而放乎禮義,而風不淳,俗不美。”*(清) 李調元《雨村曲話》,《中國古典戲曲論著集成》(八),第5頁。“達情”之論,出于皖派戴震,李調元一面肯定“達乎情”之意義,一面要求自我約束以“止乎禮義”,強調戲曲之社會教育功能。
明人以“情”與“理”相對立,然李調元認為情、理實相統一,此由其詩學思想相貫通。李調元認為“詩”是人品、性情的統一,《雨村詩話》云:
詩以人品為第一,蔡京書法,荊公文章,直不可寓目,所謂惡其人者,惡及儲胥也。*(清) 李調元著,詹杭倫、沈時蓉校正《雨村詩話校正》,巴蜀書社,2006年,第24頁。
蓋詩道性情,(李杜)二公各就其性情而出,非有偏也。使太白多作五七律,于杜亦何多讓。*同上,第13頁。
李調元主張先立身,后為文,為人當與文學創作相統一,如此則人品、性情、文章都統于道德規范之下,“情”與“理”自無矛盾可言。是以,李調元《〈雨村曲話〉序》所言之“性情”實以道德為范,表明對戲曲道德教化功能的高度重視。故此,盡管《燕子箋》藝術性較高,李調元卻予以否定;盡管《五倫記》、《香囊記》受到晚明曲論家批評,李調元卻予以肯定。在他看來,若有裨風化,即使“俗”“鄙陋”的戲曲也有其價值;《雨村曲話》引《譚曲雜札》論《琵琶記》語,卻盡刪其中批評詞句,轉而認為《琵琶記》勝于《拜月亭》,言情、詞美、有裨風教,當為南曲之首。
《〈雨村曲話〉序》著重闡發李調元“達乎情而止乎禮義”的曲論主張,《〈雨村劇話〉序》則代表清中期學人對戲曲與歷史關系的辯證思考。自“古今一戲場”后,李調元糅合程大衡《〈綴白裘〉合集序》與時元亮《〈綴白裘〉九集序》,至“書不多不足以考古”,始為李調元之補充。李調元從二序中條理出三者共同的認識: 一、 歷史如戲;二、 將歷史故事搬上戲曲舞臺,可以發揮同樣的教化功能;三、 戲曲題材來源于歷史、人生。自清前期始,曲與史之關系便為學人與曲家所關注,李調元與程、時二人的闡述是清代曲論家對曲與歷史關系認識的一個較為全面的總結。
李調元所增語句更能表明其作為乾嘉時期經學家所關注的重點。一,李調元嗜博好奇,博覽群籍,兼嗜戲曲,這使他能夠發現歷史文獻與戲曲故事之淵源,即戲曲藝術來源于歷史與現實生活卻不盡相同,身處崇尚博學、求知尚實的乾嘉學術風氣中,他認為博覽群籍,探索歷史與戲曲故事之關系,也是學術之一端;二,本著考據學者實事求是的學術精神和推行儒家倫理道德理想的目的,他認為一方面要注重歷史事實與戲曲故事之聯系,通過探尋戲曲故事之本源使受眾信任戲曲故事的真實性,從而更好地發揮二者的道德教化功能;另一方面,也要明確辨析歷史事實與戲曲故事之區別,以免受眾混淆二者,從而形成錯誤的歷史認識。《雨村劇話》內容與學術風格正是其學術主張的實現,這一補充使其觀點更顯全面、理性。
李調元身兼考據學家與曲論家雙重身份,博覽群書,他將考據法延入曲話論著,規范其文體定義,拓展其研究方法,闡發個人學術思想與主張,在諸多層面顯現出開創性特征和個人特色,這種學術上的貫通,使“二話”成為李調元諸多著作中最為人稱道者,其文體選擇、體例編排與具體觀點深刻影響了清后期曲家。
三、 凌廷堪: 禮樂思想主導下的曲論探索
凌廷堪為翁方綱門生,他私淑戴震,又與黃文旸、焦循、阮元、李斗等揚州派學人交好,在學術思想上多有交流,被視為皖派重鎮與揚州學派中堅,友人江藩視其為顧炎武、胡渭之后的接班人。
諸學之中,凌廷堪最精禮學、樂學,且義理、考據、辭章之學俱通,兼擅駢文與詩、詞、曲。乾隆四十四年(1779),伊齡阿奉旨在揚州設詞曲局刪改、查找違礙詞曲,凌廷堪擔任分校。其與戲曲理論相關者主要存于《燕樂考原》、《論曲絕句三十二首》、《與程時齋論曲書》、《〈一斛珠〉傳奇序》中。
凌廷堪既有強烈的復古崇經學術思想,又極富考據學家之懷疑與批判精神,其為學積極探索,不迷信權威而一秉實事求是之宗旨,不僅批評宋明理學之弊,也能認識到清代學術發展的危機,對當時學界的種種弊端大膽提出了批評。這種學術思想與學術精神既用于曲學研究,便能就曲壇現象與曲論疏失提出了諸多批判與建設性意見。
(一) 《燕樂考原》之戲曲音律研究特征
《燕樂考原》系凌廷堪之樂學研究著作,以與《禮經釋例》相配,完整地表述其以禮樂經世的學術思想。凌廷堪學術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即“以禮代理”,這是對理學的一大否定,他舍抽象的理而言可具體施用之“禮”,希望通過其禮學研究成果,使人倫日用有制可依,有禮可循,從而讓儒家倫理道德規范能夠得到切實實踐。江藩《〈校禮堂文集〉序》云:
(凌廷堪)釋禮之暇,謂樂由中出,禮自外作,合情飾貌,相須為用者,乃辨六律五音,明四旦七調,著《燕樂考原》,絕無師承,解由妙悟。*(清)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清嘉慶十八年張其錦刻本,卷首。
凌廷堪主攻禮學之余而重視樂學,是為了完整地實踐其以禮樂經世的學術理想,故認為“此書(《燕樂考原》)及《禮經釋例》尚為有關系之作,非雜文詩詞可比”*(清) 凌廷堪《與阮伯元侍郎書》,《燕樂考原》卷六,絲埜堂藏板,第39頁。。
在復古崇經的趨勢下,樂學雖為絕學,然既屬六經之學,清人不僅將樂之功能寄托于今樂,也著意探索樂學,自清初便有毛奇齡《竟山樂錄》,后又有李塨《學樂錄》、江永《律呂新論》、胡彥升《樂律表微》等,它們或多或少涉及曲律。燕樂之宮調,流傳至清,已經很少有人了解,世人疑為失傳。凌廷堪為使樂學研究成果切近人倫日用,選擇了研究燕樂作為貫通古樂、今樂之切入點,使其學既有助于探索古樂面貌,又能施于今樂以得其用。由于少所參考,凌廷堪“稽之于典籍,證之以器數”*(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序》,《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2頁。,搜集了大量文獻史料,以排比文獻、添加按語的方式辨疑析難,歸納總結,又從客觀實踐角度,與樂之器數相互參驗,實際驗證(即調查法),試圖闡明古今樂學理論正誤,廓清人們對燕樂模糊不清的認識,清后期重要的樂學著作——陳澧之《聲律通考》,即源于《燕樂考原》的啟發與影響。因此,《燕樂考原》考據學史上的重要著作,其間對戲曲宮調和曲源的探索,也是清代戲曲音律研究中極為重要的內容。
1. 《燕樂考原》之前的戲曲音律研究
元代燕南芝庵《唱論》認為:“大凡聲音,各應于律呂,分于六宮十一調,共計十七宮調。仙呂調唱,清新綿邈;南呂宮唱,感嘆悲傷……”他認為十七宮調各有聲情,此說被曲家廣泛認可。周德清《中原音韻》則云:“自軒轅制律一十七宮調,今之所傳者一十有二。”據此將樂府三百三十五章分屬于十二宮調下。明初朱權《太和正音譜》將五音宮、商、角、徵、羽附于五行之說,完全吸收了燕南芝庵和周德清的宮調理論,也同樣認為宮調為黃帝所制。
明代蔣孝《舊編南九宮譜》開以九宮、十三調對南曲曲調進行分類之先河,將九宮、十三調分立,其后明沈璟之《增訂南九宮曲譜》、鈕少雅、徐于室均循此道,但卻都認為聲音之道渺茫難知,沒有闡述劃分的樂理依據。王驥德不滿明代曲律研究,認為周德清習而不察,沈璟語焉不詳,考歷代樂書而認為古樂八十四調在流傳過程中因為繁瑣而陸續省略亡佚,終得十七宮調,之后演變為十三調,王驥德對八十四調亡佚過程的考辨較其他戲曲音律學家要更為清晰,同時,他認為十三調之名源于“盡去宮聲而不用”,仍將宮、調分立。
清代曲家與學人對明代曲律研究總體狀況感到不滿,陸續起而矯之。明清之交,張大復《寒山堂曲譜》認為隋代音樂家萬寶常據龜茲傳入琵琶之七調,“附會于五音、二變、十二律,旋相為宮,得八十四調,而不用二變及徵調,僅有四十八調”*(明) 張彝宣《寒山堂新定九宮十三攝南曲譜》,續修四庫全書第1750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 635頁。,歷五代、宋、金,又僅余十三調。據此,他批評了蔣孝、沈璟將九宮十三調分立的做法。
其后王正祥《新定十二律京腔譜》不滿以河圖洛書等易理天文之說附會于樂理的做法,也不滿意明人南曲宮調襲北曲訛謬的現象,盡廢宮調而不用,返諸古樂而用五音十二律之說,以五音配五行,十二律分屬其間,根據其聲情歸于四季,而十二律呂又分律呂陰陽,配十二月。
乾隆時恭親王等編纂了《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他們據《宋史·樂志》明燕樂二十八調之略,但對燕樂二十八調與南北曲宮調關系中的疑難之處并未深入考證,轉據廖道南所云之五星、五行之理,認為樂有本于天地自然不可易者,將南北曲所存燕樂二十三調根據聲情分屬于十二月,這是對古樂十二律配十二月的一種模仿。
清中期方成培《香研居詞麈》認同宋仁宗《樂髓新經》之說,考其十二均八十四調圖,又謂宋燕樂于七聲中只取宮、商、羽、閏,各生七調而得燕樂二十八調,至南北曲則部分已殘缺失傳。他分析了南曲曲譜產生謬誤的原因,指出宮亦是調,認為恭親王等人所編《新定九宮大成南北詞宮譜》以二十三調配十二月,所配均有差謬,屬不明律呂之過。
可見,清代曲家與學人在復古返經、實事求是的學術思想指引下,反對明代戲曲音律學家不求甚解的撰述態度,摒棄了樂學研究中的神秘因素,追本溯源,試圖依據古代音樂文獻和古法,恢復古樂之面貌與法則以規范戲曲音律。至凌廷堪則集大成,他通過大量文獻的梳理排比做了精深的全面總結,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認為《燕樂考原》的研究方法為后人開辟新路,與陳澧《聲律通考》為清代“最能明樂學條貫者”*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天津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397頁。然王季烈《螾廬曲談》則言:“如毛西河、凌次仲諸家,意在溝通古今樂律而武斷曲解,使樂理愈晦。”。其宮調說之要點大略為:
自鄭譯演蘇祗婆琵琶為八十四調,而附會于五聲二變十二律,為此欺人之學,其實繁復而不可用。若蔡季通去二變而為六十調,殆又為鄭譯所愚焉。后之學者,奉為鴻寶,沿及近世,遂置燕樂二十八調于不問。……琵琶四弦,故燕樂四均,一均七調,故二十八調。*(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序》,《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1頁。
其名八十四調者,實只二十八調。七角一均及三高調、七羽之正平調,宋人已不用;七羽一均,元人已不用,所存者惟六宮十一調,共為十七宮調。自明至今之俗樂,又只用燕樂之七商一均。*(清) 張其錦《〈燕樂考原〉跋》,載凌廷堪《燕樂考原》,卷末。
在這一基本認識的輪廓中,凌廷堪考辨了“宮調之源”“南北曲之源”“宮調之辨不在起調畢曲”“字譜即五聲二變”“聲不可配律”等戲曲音律相關問題。
2. 《燕樂考原》之學術傾向
凌廷堪之學術精神與學術思想也在《燕樂考原》中顯露無遺,選擇“燕樂”為打通古樂、今樂之門便顯現出其復古思想,其他學術傾向具體表現為: 學求致用的學術精神、反對樂學研究中的迷信和神秘色彩、對明代戲曲音律研究空疏淺陋之批判。
揚州學派時期的學人已經重新重視清初學人之經世致用思想。凌廷堪研究燕樂,目的在于施用,不滿前人樂學研究之繁復和止于理論的研究傾向。其所主張的“致用”包括兩個層次。首先,主張音樂理論研究能夠用于現實的音樂實踐,因此,能否致用成為衡量音樂理論著作的一個重要標準,他不僅指責八十四調為欺人之學,繁復而不可施用,遂導致失傳,還批評了清代樂學理論與實踐相脫節的現狀:
竊謂世儒有志古樂,不能以燕樂考之,往往累黍截竹,自矜籌策,雖言之成理,及施諸用,幾如海上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序》,《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2頁。
進一步而言,凌廷堪私淑戴震,同樣認為小學僅是通經致用的途徑,而非學問的最終目的,這一批判與他批判清中期部分漢學家沉迷并止步于音韻訓詁之學而忽視經世之道相一致。他所主張的致用,指在以樂學理論指導樂之實踐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樂的政教功能:
案: 房庶此論見《宋史·樂志》……此論古樂與今樂,獨平易條鬯如此,不獨講燕樂者當知之,即講雅樂者亦當知之,故與馬氏之說并載于篇焉。*(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38、39頁。
對凌廷堪而言,歸根結底,音樂理論研究運用于實踐的最終目的,是發揚樂的觀風化俗功能,唯其如此,方能與其禮學研究相呼應,使禮明樂張,共同發揮經世之用。
由于樂學之難解,后人研究樂學,常常以易學之理、歷算推演來闡述樂理,或者偽托古人,使樂學更具神秘色彩,如江永這樣的考據名家,亦借易學解說樂學理論,其《律呂新論》第一篇即為“五聲之體本于河圖”。然凌廷堪本著實事求是的學術態度,主張以科學的方法考辨分析樂理,盡棄神秘、虛妄之說。以陰陽易數闡釋樂學的研究方式,清前期毛奇齡《竟山樂錄》便認為可以廢除,王正祥也如此主張,這種現象正反映了考據學實事求是的學術主張下樂學研究之新變。凌廷堪批評以歷算、陰陽易象入樂學者未得其法,徒為樂學研究增添困惑:
自宋以來,實學日荒,世儒又高談小學之六書九數,窮年考證說文,推測勾股,于此等不暇深究,或徑以算數代之,故用心雖勞,而其著書終無入門處也。至于前人之書,多不知而作,于其所未解者,往往故為疑陣,良由未洞悉其源流,不得不旁及陰陽易象,以惑世而自欺,故讀其書亦無入門處也。*(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7、8頁。
從《聲律通考》來看,凌廷堪的這一主張也為陳澧接受。他還反對為增加論說權威性,不知其理而妄托古人的做法,批評周德清不知十七宮調由來而妄稱為軒轅所制,這實際上也就批評了采用周論的朱權:
考十七宮調,北宋乾興以來,教坊所用之宮調也,乃以為軒轅所制,何鹵莽也!周氏在當時號為知音者,所言尚謬悠如此,況其下者乎。*(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28頁。
凌廷堪希望排除戲曲音律研究中的主觀神秘因素,否定抽象的理論推演,以將考辨與論述專注于樂理本身。
不滿明學之空疏淺陋是清代考據學興起的原因之一,自清初起,便陸續有諸多學者對明學進行了尖銳的批評。明代戲曲發達,宮調之說卻隱晦、混亂,著意于樂學的清代學者凌廷堪認為音律研究混亂錯訛也是明人空疏不學的表現,他考察文獻以明各調之曲時干脆摒棄明人之譜不錄。除此外,《燕樂考原》不乏批判明代樂學之語,如:
明人制譜,不知九宮十三調為何物,漫云某曲在九宮,某曲在十三調。近方氏《物理小識》,又于七調之外妄立十三調之名,皆不得其解而臆說也。*(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卷一,絲埜堂藏板,第30頁。
明人不學,合其數而計之,乃誤以為九宮,至于近世,著書度曲,以臆妄增者,皆不可為典要也。*(清) 凌廷堪《燕樂考原》卷六,絲埜堂藏板,第6頁。
至《明人九宮十三調說第十一》一篇,于明代以沈璟為代表的音律學家之學說進行了整體性批判,也部分廓清了明人曲律研究的混亂現象。
然而從《燕樂考原》全書來看,凌廷堪對古今樂學家幾乎無一滿意,自鄭譯、蔡季通一直批判至同時代的胡彥升,不過,其考斷也有失之武斷、過分自信之嫌。清后期陳澧的《聲律通考》于凌廷堪《燕樂考原》之失多有糾正并闡明其致誤之由,如:
凌次仲不察,乃詆其六十調為鄭譯所愚,蓋凌氏未考《周禮》三大祭之樂及《隋志》蘇夔之說耳。*(清) 陳澧《聲律通考》,清咸豐十年陳氏刻本,卷一,第9頁。
凌廷堪治學的過度自信與疏漏,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其學術研究結果的客觀性,是為《燕樂考原》之失。
(二) 《論曲絕句三十二首》的崇元復古傾向
凌廷堪《論曲絕句三十二首》見于《校禮堂詩集》卷二,這一組論曲詩與其他論曲組詩相區別者在于其層次嚴明,可稱為一部微縮戲曲史,而收于《校禮堂文集》中的《與程時齋論曲詩》,內容與主旨與這組詩篇大體相似,可稱為注解與補充。
《論曲絕句三十二首》分五個部分簡述了戲曲演變歷史。第一部分(1—3)集中追溯了戲曲之源頭,第二部分(4—15)論述元代雜劇史,第三部分(16— 22)論述明代戲曲史,第四部分(23—31)論述元明曲學,明南北曲之異同,第五部分(32)為總結。組詩以歷史為序,結構體制已具備后世戲曲史的大致雛形。凌廷堪選取了最具代表性的戲曲作家、作品和曲事進行記載、考辨、點評,完成了對元明戲曲史簡明而精要的勾勒與評價,這種精到的選擇彰顯出凌廷堪在大量閱讀戲曲文獻之后對元明清三代戲曲發展史與戲曲作品的深入了解。作為考據學家,凌廷堪的治學之方式也影響到了《論曲絕句三十二首》的撰述方式與內容。《論曲絕句三十二首》十分注重究根究底,考辨源頭,辨析作品、曲事之間的內在關聯。比如考證戲曲之源頭,更分別論述雜劇、傳奇之始;認為王實甫《西廂記》本于董解元;認為湯顯祖《牡丹亭》部分情節參考了《青衫淚》和《金錢記》;考辨《中原音韻》中的錯誤和韻學失誤等等。為了補充考辨,凌廷堪習慣在相關詩作之后添加注語,以考據完善其觀點,這就使其論曲詩在闡述戲曲觀點的同時還具有文獻參考價值。
作為乾嘉時期代表性的考據學家,凌廷堪在《論曲絕句三十二首》中所闡述的戲曲理論與其學術思想、學術主張亦相貫通——《論曲絕句三十二首》從各部分內容之比例上即直觀體現了凌廷堪強烈的崇元復古意識。
組詩之篇幅以第二部分元雜劇史所占比例最大,作者對元代作家、作品不吝贊美之詞,如“文到元和詩到杜,月明孤雁《漢宮秋》”,“安得櫻桃樊素口,來歌一曲《梅香》”,“紅牙按到《梧桐雨》,可是王家遜白家”;述明代戲曲史部分,則多批評之語與失落之語,如“事必求真文必麗,誤將剪彩當春花”,“一自青藤開別派,更誰樂府繼誠齋”,曲學部分則無論語言還是音韻,均以元代為典范,如“拈出進之金作句,風前抖擻黑精神”,“一卷《中原》韻最明,入聲元自隸三聲”。最后,《論曲絕句三十二首》對明清戲曲近四百年的發展史做了一個失望的總結:“下里紛紛競品題,陽阿激楚付泥犁。元人妙處誰傳得?只有曉人洪稗畦。”*(清) 凌廷堪《校禮堂詩集》卷二,清道光六年張其錦刻本,第9—12頁。
凌廷堪曲論中的崇元復古觀念與其經學思想一致。清代考據學發端于學界的自我反思,他們將儒學的衰落歸結于宋明理學,一開始便以復古返經為旗幟針對宋明理學,倡導回歸儒家經典,尋求真正的儒家精義,以發揮經世宰物致用,凌廷堪遠繼清初顧炎武、胡渭之學術精神,近承戴震之學術思想,他反理學最鮮明的主張即“以禮代理”,希望通過探索與恢復儒家禮制以規范人倫日用。凌廷堪倡導以樂學與禮學呼應,格外重視作為俗樂的戲曲之道德教育功能,在凌廷堪看來,元曲在戲曲中之地位,有如六經在經學中之地位。但是,與乾嘉經學演變狀況相類,戲曲演變之現狀同樣并不符合凌廷堪的期待,一方面戲曲創作日益趨于案頭化,傳奇、雜劇發展呈衰落之勢,一方面花部戲曲則蔚然興起。凌廷堪在《與程時齋論曲詩》中道:
前明一代僅存餼羊者,周憲王、陳秋碧及吾家初成數公耳。若臨川南曲,佳者蓋寡,《驚夢》《尋夢》等折,競成躍冶之金;惟北曲豪放疏宕,及科諢立局,尚有元人意度。此外以盲語盲,遞相祖述,至宜興吳石渠出,創為小乘,而嘉興李漁效之,江河日下,遂至破壞決裂,不可救藥矣。四百年來,中流砥柱,其稗畦之《長生殿》乎!*(清)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清嘉慶十八年張其錦刻本,第6頁。
他認為戲曲之演變每況愈下,元曲之佳處日漸湮沒不傳,明代傳奇、雜劇不如元曲,清代戲曲整體又遠不如明代。反思雜劇輝煌難再、昆曲處境尷尬的戲曲演變態勢,他認為這根源于元曲之法日漸不傳,提出以復古為途徑的戲曲改革理想:“有豪杰之士興,取元人而法之,復古亦易為力。”*(清) 凌廷堪《校禮堂文集》卷二十二,清嘉慶十八年張其錦刻本,第5頁。提倡效法元代作家,以恢復雜劇、傳奇創作之盛況。
凌廷堪所言元人妙處主要包括兩點,一指元曲謬悠之特征,二指元曲音律與語言兼美,這同時也代表了凌廷堪的曲論主張。
凌廷堪指出:“元人雜劇事實多與史傳乖迕,明其為戲也。后人不知,妄生穿鑿,陋矣。”*(清) 凌廷堪《校禮堂詩集》,清道光六年張其錦刻本,第10頁。他認為元代雜劇之所以與史傳相異,是要表明其為虛構的故事而并非真實的歷史,以避免受眾將歷史與戲曲相混淆,這是其體例所致而不能視為缺陷,后世之人執意地將戲曲與歷史相比較,違背了元人制曲本意。在清代考據學學術思潮影響下,諸多經史學家與曲論家都格外注重戲曲與歷史關系的考辨,但凌廷堪認為虛構的是戲曲藝術之本質,對以歷史真實要求戲曲、以考證入曲的傾向提出了批評:
是真是戲妄參詳,撼樹蚍蜉不自量。信否東都包待制,金牌智斬魯齋郎。(元人關目,往往有極無理可笑者,蓋其體例如此,近之作者乃以無隙可指為貴,于是彌縫愈工,去之愈遠。)
弇州碧管傳鳴鳳,少白烏絲述浣紗。事必求真文必麗,誤將剪彩當春花。*同上。
凌廷堪十分清楚戲曲傳播的力量:“至今委巷談三國,都自元人曲子來。”*同上。然與考據學家們憂心這一現象的態度相反,他將考證戲曲與歷史關系者視為撼樹蚍蜉,指出他們的考辨并不可能改變普通觀眾對戲曲真實的接受。他批評明代王世貞為代表的駢儷派作家“事必求真”的創作傾向是將假花當作真花要求;批評清代戲曲家“以無隙可指為貴”的創作傾向只會離元曲之真意越來越遠。這些針對曲壇不良創作傾向的批評十分可貴,但是在側重戲曲藝術虛構特征的同時,全然否定戲曲本事考辨之學術意義,甚而進一步否定明清戲曲,亦有偏頗之處。
凌廷堪以元曲語言風格為標準衡量明清二代戲曲之語言,認為戲曲語言應當講求本色當行,他肯定康進之《李逵負荊》之語言刻畫出了李逵的形象,反對駢儷濃艷的語言風格。也反對以學問入曲的時代陋習。但是,他認為的本色當行不是李漁的“一味作俳優語”:
仄語纖詞院本中,惡科鄙諢亦何窮。石渠尚是文人筆,不解俳優李笠翁。*(清) 凌廷堪《校禮堂詩集》,清道光六年張其錦刻本,第11頁。
凌廷堪以“事必求真文必麗”批評王世貞等人戲曲,反對藻麗的戲曲語言,也反對以學問入曲的時代陋習,但其組詩也夸贊了吳炳戲曲語言尚有文人氣,而李漁戲曲語言則有俳優習氣。
由此聯系凌廷堪列舉文人作家作品的舉動,可知盡管主張“以禮代理”的凌廷堪關注人倫日用,但在花部崛起的情況下,仍然堅持由文人主導戲曲演變方向,以復古崇元為振興戲曲之途,不夠重視新的生命力旺盛的戲曲力量,這就使凌廷堪不滿現狀卻又無法提出真正有效的措施。
凌廷堪對元雜劇之“佳處”把握精準,但他忽視戲曲發展的歷史趨勢,一味以元雜劇為標準要求明清二代戲曲,則陷入是古非今的誤區,以至于對明清戲曲史認識較為偏頗。相較于同時代曲論家李調元、焦循對當代戲曲現象與特征的敏銳觀察和對其價值的認可,凌廷堪之戲曲理論無疑為復古思潮制約而有所局限,他的觀點也與清后期推崇本朝戲曲的曲論家全然不同。
凌廷堪以考據學家治正學之方法與嚴肅的學術態度治曲,囊其入“樂”而重視治此學之意義,曲論著述也就因之全面承載了其學術思想與學術觀點,他的學術批判精神使他能夠切中時弊,把握戲曲發展與曲論研究中的不足,具有典型的時代特征,無論是就正統學術還是古代曲學而言,都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
四、 焦循: 考據學家曲論研究之典范
焦循是清代考據學大家,也是揚州學派代表人物,被目為乾嘉碩儒、通儒,其學博大通達,著述宏富,不勝枚舉。
考據學大體有吳、皖、揚州三派,揚州最為晚出而試圖突破乾嘉學術之瓶頸,博采眾長,匯通各家,于皖派戴震之學多所繼承與發展,以通達著稱。在焦循看來:
蓋古學未興,道在存其學,古學大興,道在求其通。前之弊患乎不學,后之弊患乎不思。證之以實而運之于虛,庶幾學經之道也。*(清) 焦循《雕菰集》(四),中華書局,1985年,第215頁。
焦循推崇戴震之學,認為宋明學術的弊端在于思而不學,乾嘉考據學又陷入學而不思的泥淖,故認為:
經學者,以經文為主,以百家子史、天文術算、陰陽五行、六書七音等為之輔,匯而通之,析而辨之,求其訓故,核其制度,明其道義,得圣賢立言之指,以正立身經世之法。以己之性靈,合諸古圣之性靈,并貫通于千百家著書立言者之性靈,以精汲精,非天下之至精,孰克以與此?不能得其精,竊其皮毛,敷為藻麗,則詞章詩賦之學也。*(清) 焦循《雕菰集》(四),第213頁。
焦循崇尚的博學,是主張以經學為主,其他諸學為輔,貫通諸學而得圣賢之意,明立身與經世之法。這一主張看重一切學問與經學之關聯,但又注重個人思想意志之主導性以通于古圣賢。焦循留心曲學,便與這種以考據為方法,博綜百家而獲得個人認識的學術旨趣有關,當然,這也同樣不可避免地以曲學為經學之輔了。
焦循曲學著作有《曲考》(已佚)、《劇說》、《花部農譚》、《易余曲錄》。作為清代考據學的代表性人物,焦循的曲學研究具有典型意義,考據學的治學之法、學術特征和學術思想在其曲學研究中充分體現,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在指出焦循曲學研究特點之后高度評價了其曲學研究之意義:
焦循考據中的戲劇學,精彩處不勝枚舉。從這種意義上來看,《花部農譚》和《劇說》都是戲劇考據學的杰出代表作。焦循對挖掘材料的用功,在材料排比中自然作出新的見解,以大量歷史事實來證明自己對戲劇的認識,由此而建立自己的戲劇理論與戲劇史觀,這種優秀的科學的考據精神與方法,影響了近一個世紀的戲曲研究,以后在王國維的戲曲研究中得到發揚與進一步的改善。*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466、467頁。
這一評價客觀揭示了焦循曲學研究的考據特色,而焦循學術思想與其戲曲理論的關系也值得進一步探究。
(一) 考據中的戲劇學
焦循現存的三部曲論著作均為札記體曲話,它們積累了大量的戲曲文獻史料和研究心得,呈現出焦循識見之浩博,而其閱讀傾向與輯錄內容以及其間散金碎玉的個人論說部分,也呈現了焦循的學術思想與戲曲理論之特點。
焦循的戲曲考據較同時代李調元、凌廷堪更為規范、精到,也較好地將乾嘉學者治學之法施用于曲學。
《劇說》于卷前列引用書目一百六十六種,類似的做法,前有孔尚任《桃花扇考據》,以作考證劇本內容真實性之需,焦循之目錄一則以備查證的功能,一則依循了“不攘人之美”的學術規范。經過明末及清代學人之努力,這已經成為考據學通行的學術規范,《劇說》所征引內容均注明出處,簡則列作者或書名。雖仍存不足,但較之存在此類問題的李調元、凌廷堪,顯然更符合乾嘉學者之治學規范。
焦循戲曲考據之精,如《劇說》開卷之首考演劇之源頭:
《樂記》云:“新樂進府退府,奸聲以濫,溺而不止,及優侏儒,獶雜子女,不知父子,樂終不可以語,不可以道古。”注云:“獶,獼猴也,言舞者如獼猴戲也,亂男女之尊卑。‘獶’,或為‘優’。”疏云:“《漢書》: 檀長卿為獼猴舞,是狀如獼猴。”《左傳·襄公二十八年》:“慶氏以其甲環公宮。陳氏、鮑氏之圉人為優。慶氏之馬善驚,士皆釋甲束馬而飲酒,且觀優,至于魚里。”《正義》云:“優者,戲名也。”史游《急就篇》云:“倡優俳笑。”是優俳一物而二名。今之散樂,戲為可笑之語而令人笑是也。《史記·滑稽列傳》:“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余,像孫叔敖,楚王及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又:“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于大道。”然則優之為技也,善肖人之形容,動人之歡笑,與今無異耳。*(清) 焦循《劇說》,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廣陵書社,2008年,第1頁。
此考證理路即戴震所言“求之古經而遺文垂絕,今古懸隔也,然后求之于訓詁。訓故明則古經明,古經明則賢人圣人之理義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清) 戴震《題惠定宇先生授經圖》,見張岱年主編《戴震全書》(六),黃山書社,1995年,第505頁。焦循征引了經學經典中的《禮記·樂記》與《春秋》三傳之《左傳》的原文、后人疏注,以探尋“優”在經學中之原義,然后列舉兩篇典型文獻,一側重動人歡笑,一側重肖人之形容,二者排比羅列,歸納出“優”之特征,循“訓詁明則古經明”之道而以己意貫穿,不僅考明倡優表演之特征,也表明戲曲演劇記錄最早出于經學經典,強調了戲曲表演與經學之關系。文獻的選擇和排比、邏輯與歸納最能體現考據學家之學術功底與見識,此條以清晰的層次和邏輯推理得出精要的結論,使《劇說》開卷便扣住演劇藝術之要素——“優伶”,這就有別于明清以來諸多曲論家以戲曲作家為主體而從戲曲文學本體追溯戲曲源頭的做法,也表明焦循的戲曲審美偏好及其對戲曲藝術演變趨向的準確把握: 清代花部發展以來,戲曲舞臺漸由文人主導讓位于藝人主導。是以《劇說》卷一以優伶為中心,考戲曲演劇本體之相關內容,卷六以優人演劇之逸聞軼事結篇。另外,焦循“訓詁明則‘曲’學明”的考源方式更對王國維產生了較大影響,其《宋元戲曲史》開篇亦以巫、尸、優之訓詁而從演員的角度探演劇藝術之源。
焦循治學注重調查觀察法的一面在三部著作中也充分體現,此法清人稱為目驗、親歷。考據學者之著作,雖多成于書齋,然自顧炎武踏遍山川而為地理學著作之始,目驗、親歷驗證便成為清代考據學者證明個人觀點的一種重要手段,胡渭、惠棟、戴震、王念孫等諸多考據學名家,均秉持懷疑與實事求是之精神而重視這一方法,他們通過觀察古代遺物與現實生活,將觀察結論運用于名物訓詁、天文地理之學,焦循學術著述中不乏調查觀察之法的運用,此亦見于曲學研究,如考《祝英臺死嫁梁山伯》本事的條目:
《錄鬼簿》載白仁甫所作劇目有《祝英臺死嫁梁山伯》,宋人詞名亦有《祝英臺近》。《錢唐遺事》云:“林鎮屬河間府,有梁山伯、祝英臺墓。”乾隆乙卯,余在山左,學使阮公修《山左金石志》,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臺墓碣文》,為明人刻石。丙辰客越,至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臺墓。載于志書者詳其事,云:“梁山伯、祝英臺墓,在鄞西十里接待寺后,舊稱‘義婦冢’。”……乃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為“祝英臺墳”。余入城必經此。或曰:“此隋煬帝墓,謬為英臺也。”*(清) 焦循《劇說》,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廣陵書社,2008年,第30、31頁。
雖未形成最終結論,但三種親歷、目驗史料的記錄,卻顯示出焦循有意考索這一戲曲故事本事真偽的意圖。另如其分析昆腔劇《雙珠記》、《西樓記》雷殛情節的設置不如花部《清風亭》合理,此后言:
余憶幼時隨先子觀村劇,前一日演《雙珠·天打》,觀者視之漠然。明日演《清風亭》,其始無不切齒,既而無不大快。鐃鼓既歇,相視肅然,罔有戲色;歸而稱說,浹旬未已。彼謂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見也。*(清) 焦循《花部農譚》,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78頁。
根據親見之兩種雷殛情節所引起的不同觀演效果,焦循得出了其重要的理論認識:“彼謂花部不及昆腔者,鄙夫之見也。”親歷、目驗的考據方法,不僅使焦循能夠將實地見聞與文獻記載相參照,亦使其能夠敏銳地把握戲曲演變的歷史趨向而更為重視花部。他通過親身體驗感受到戲曲演出所產生的強大力量,故而其考據關注戲曲表演藝術,關注花部戲曲,以期更好地實現經學之道在戲曲中的傳達。
焦循考據之精當,在三部曲論著作中不勝枚舉,與乾嘉時代其他曲論家,尤其是與其研究理路相近的李調元相比,焦循以更為深厚的考據學功力,將考據方法充分運用曲學研究,而又貫以個人之學術思想,形成了個人曲學研究的鮮明特色,也獲得了顯著成績。當然,誠如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所言:
焦循考據常有的那種事無巨細均作煩瑣考證、材料淹沒觀點、寫作不顧邏輯條理的弱點,則在王國維那里有所克服。因此說,王國維后來戲曲研究的巨大成功,得力于焦循處甚多。*葉長海《中國戲劇學史稿》,中國戲劇出版社,2005年,第467頁。
這樣的弊端一由于考據的癖好,一由于札記體的著述體例之局限。焦循治曲,時附以疏證而確定所記材料的真實性,或考史實而兼訓詁,或引他書而兼校注,重于微觀研究,以文獻積累為先,并不太重視宏觀構架與邏輯編排,著述之初即無嚴密體系之構想,亦無固定形式之限制。《里堂道聽錄序》云:
余生質極鈍,然每得一書,無論其著名與否,必詳閱首尾,心有所契,則手錄之。余交游素少,然每有以著作教我者,無論經史子集以至小說詞曲,必詳讀至再至三,心有所契,則手錄之。歷二三十年,盈二尺許矣。*(清) 焦循《雕菰集》(四),第257頁。
三部曲話皆如此著錄而得,也就很難更好地規劃體例,規范著錄范圍與內容,較之李調元“二話”,焦循之曲話更明顯地呈現出札記體瑣碎、零散、片斷化之局限。同樣,李調元規范曲話體例編排的治學路數,也未為焦循拓深,而是直到梁廷枏時期才進一步改良的。
(二) 焦循之學術思想與戲曲理論
經學之中,焦循尤精易學。易學為焦循家傳之學,焦循幼年即好易學,研究易學近三十年,有《易學三書》,其學術研究整體上深受個人易學思想主導,如其重要著作《孟子正義》。他在《與朱椒堂兵部書》中闡述治《易》所得云:
《易》之道,大抵教人改過,即以寡天下之過。改過全在變通,能變通即能行權,所謂使民宜之,使民不倦。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圣人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全于此一以貫之。則《易》所以名“易”也。《論語》、《孟子》,已質言之。*同上,第201頁。
“通”與“道德”是焦循易學研究極為注重的兩點,焦循著述中經常可見“通變”“通達”“旁通”一類主張,這種靈活變通的學術思想,使其治學相對較少受到學術思維慣性的制約,在他看來:“通核者,主以全經,貫以百氏,協其文辭,揆以道理,人之所蔽,獨得其間,可以別其是非,化拘滯,相授以意,各慊其衷。”*(清) 焦循《雕菰集》(二),第109頁。焦循也因此以突出的學術成就彰顯了揚州學派學術博綜匯通之特征。
焦循視易學為“教人改過”之學,重視以易學理論闡述儒家倫理道德思想,其《易圖略·卷六·原卦第一》考諸家于易學宗旨的論說后,認為伏羲創八卦是為了明天倫,定人道:
以知識未開之民,圖畫八卦以示之,而民即開悟,遂各遵用嫁娶,以別男女而知父子,非質而明能之乎?故在后世觀所畫之卦,陰陽、奇偶而已。而在人道未定之先,不知有夫婦者;知有夫婦,不知有父子者;知有父子,人倫王道自此而生。非圣神廣大,何以能此!*(清) 焦循《易圖略》,焦循撰、李一忻點校《易學三書》(下冊),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94頁。
牟宗三視焦循易學為“道德哲學之易學”,陳居淵認為“焦循易學的思想內容,始終沒有能跳出象數派以卦象和數字推導出社會制度與倫理道德的有關原則”*陳居淵《焦循儒學思想與易學研究》,齊魯書社,2000年,第270頁。。由于戲曲演劇藝術最為切近人倫日用,焦循三部曲論著作也受到這一思想的影響。他認為,戲曲能夠充分發揮儒家倫理道德說的經世之用,如云:“宮大用《范張雞黍》第一折,乃一篇經史道德大論,抵多少宋人語錄。”*(清) 焦循《劇說》,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16頁。即使理學在清代受到考據學家諸多批判,焦循此論依然頗為驚人。
概而言之,焦循的易學思想對其戲曲理論的影響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抑昆崇花、崇元而不陋今的戲曲觀;“以己之情、度人之情”的戲曲言情論;載道為重、娛樂為輔的戲曲功能觀;靈活變通的戲曲虛實論。
1. 抑昆崇花、崇元而不陋今的戲曲觀
李調元已重視花部戲曲,焦循則進一步提出獨好花部的觀點,并否定了明代傳奇。焦循認為花部代替昆曲是戲曲演變規律的必然,在傳揚儒家倫理道德思想方面較傳奇有著無可比擬的優越性:
梨園共尚吳音。“花部”者,其曲文俚質,共稱為“亂彈”者也,乃余獨好之。蓋吳音繁縟,其曲雖極諧于律,而聽者使未睹本文,無不茫然不知所謂。其《琵琶》、《殺狗》、《邯鄲夢》、《一捧雪》十數本外,多男女猥褻,如《西樓》、《紅梨》之類,殊無足觀。花部原本于元劇,其事多忠、孝、節、義,足以動人;其詞直質,雖婦孺亦能解;其音慷慨,血氣為之動蕩。郭外各村,于二、八月間,遞相演唱,農叟、漁父,聚以為歡,由來久矣。自西蜀魏三兒倡為淫哇鄙謔之詞,市井中如樊八、郝天秀之輩,轉相效法,染及鄉隅。近年漸反于舊。余特喜之,每攜老婦、幼孫,乘駕小舟,沿湖觀閱。*(清) 焦循《花部農譚》,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73頁。
作為考據學家的焦循,從戲曲的構成要素上比較昆山腔與花部優缺點,指出花部之藝術特征使其更容易為普通百姓所接受。更值得注意的是,焦循認為昆山腔之劇本多描寫男女之情,花部故事多本于元劇,承載了忠孝節義的道德理想,故《花部農譚》中,其對司馬師扮相的感慨、對《清風亭》雷殛效果的議論、對《賽琵琶》情節的喜愛,都透露出其重視花部戲曲社會教育功能的傾向。
整個明代數百種傳奇作品,焦循所看重者唯《琵琶記》、《殺狗記》等十數種有功于教化者,幾乎全面否定明代戲曲成就。焦循十分厭惡描寫男女之情的作品:“其男女贈答,夸淫斗麗,余所深惡,特絕之。”*(清) 焦循《雕菰集》(四),第257頁。因此,他雖鐘愛元劇,卻唯獨不喜《西廂記》,三部論著中所收錄的《西廂記》相關文獻,均為負面材料,直言:“蓋《西廂》男女猥褻,為大雅所不欲觀。”*(清) 焦循《花部農譚》,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80頁。其《西廂記》相關考證,認定王實甫本《西廂記》語言因襲董解元、情節設置不合理,無勸懲意義,一反通達寬容的學術觀念。焦循的“一代有一代之所勝”說,則以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時文為序,將時文視為明代文學藝術成就之代表,完全否定了明代小說、戲曲的歷史性成就——與他一樣持“日新”文藝發展觀的清初學者毛先舒,卻贊同“今之真詩在南曲”*(清) 毛先舒《〈麗農詞〉序》,見《潠書》,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齊魯書社,1997年,集部210冊,第622頁。之語,可見,焦循抑雅揚花和一代有一代之所勝的文藝發展觀雖然具有其歷史進步性,卻也反映了其在以儒家倫理道德為主導的文藝觀影響下的認識偏差。
焦循以元曲為元代文學藝術之代表,上述序言透露出,其所以推崇元曲,原因在于認為元曲多寫忠孝節義之事,有利于教化百姓。三書中關于元雜劇語言之本色、當行,戲曲本事、演出體制等的諸多考辨,也都顯示出對元雜劇的推崇與高度評價,他甚而認為八股文亦當以元曲之格為法。
焦循同其友人凌廷堪一樣,都由復古返經之學術思想影響而高度認同元曲,鄙視明代戲曲成就,其區別則在于凌廷堪最終全面否定了明清戲曲成就,焦循則更進一步把目光投向了花部,在充分認識到花部戲曲的優點之后,他將戲曲發展之希望和儒家倫理道德思想之傳揚寄托在花部戲曲上。
2. “以己之情,度人之情”的戲曲言情論
焦循對“情”與倫理道德關系的認識也頗具代表性。《易通釋》云:
以血氣心知之性,為喜怒哀樂之情,則有欲。欲本乎性,則“欲立立人,欲達達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有以“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類”猶“似”也。以己之情,度人之情,人己之情通。而人欲不窮,天理不滅,所為善矣。*(清) 焦循《易通釋》,焦循撰、李一忻點校《易學三書》(上冊),九州出版社,2003年,第119頁。
焦循認同孟子的“人性本善”觀念,因此他認為以己之情,度人之情可以獲得道德平衡的理想狀態,即由變通、轉化之觀念,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理解、體貼,以此達到“人己之情通”的效果,最終使儒家倫理道德主張得到落實。《使無訟解》中進一步闡釋了強調“人己之情通”的最終目的:
格物者,旁通情也。情與情相通,則自不爭,所以使無訟者,在此而已……情通于家則家齊,情通于國則國治,情通于天下則天下歸仁,而天下平。*(清) 焦循《雕菰集》(三),第138頁。
焦循所主張的“情”以善為本,具有濃厚的倫理道德意味,他認為戲曲中此類故事,證明其觀點正確可行,可以借戲曲貼近人倫日用的特點更好地實踐自己由易學研究而獲得的經世之法,這與明代曲論家“曲以言情”所指之“情”全然不同,亦與李調元所主張之“達乎情止乎禮義”的觀點有所區別。
焦循最喜歡的花部戲曲為《賽琵琶》,其中又最愛《女審》一節,述秦香蓮主審陳世美,怒數陳世美之罪,而陳有悔色。焦循認為這出戲能將之前積壓的情緒一泄而盡,又特地指出:
觀此劇者,須于其極可惡處,看他原有悔心。名優演此,不難摹其薄情,全在摹其追悔……*(清) 焦循《花部農譚》,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80頁。
《女審》一節,男女主角今夕地位對調,提供了情與情通之基礎,而“追悔”則能表現陳世美在與當時秦香蓮相似處境下認識到自己錯誤,這一具體情感流露恰恰體現了焦循由“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推導出的“人己之情通”的認識,從而達到教育的目的。
值得注意的是,焦循在《劇說》中還透露過創作戲曲的意圖,并詳細講述了引發其創作欲望的三個故事。故事其一即后世京劇《鎖麟囊》之本事;其二述富翁陳國瑞委其子尋覓墓地,其子與王生以低價騙買張翁產業,陳國瑞得知后宴請張翁,執意補足差價,張翁則信守合同拒收錢財,二人互相謙讓;其三述佃戶李慶低價謀得司大田產并羞辱司大,司大欲夜焚其家,聞其妻產子轉念,歸而致富后,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李慶怨憤,夜焚司家,司妻亦因產子得免,司大悟而以德報怨,與李家解怨交好。焦循將這三個故事匯編于同一條目,并且欲親自改寫為戲曲劇本,是因為三個故事的共同特征是主人公都具有善良的本質,且都能設身處地為對方著想。因此,這三個故事是焦循“以己之情,度人之情”經世理論的最佳詮釋,焦循認為可以借戲曲的傳播特點,發揮這三個故事的教育功能,切實有益于導民化俗。
3. 載道為重、娛樂為輔的戲曲功能觀
焦循于戲曲功能的認識較為全面、客觀,他雖然與諸多清代曲論家一樣重視戲曲的道德教化功能,但也充分肯定戲曲的娛樂功能,將其視為戲曲本質。在《劇說》之始,焦循考“優”一詞,已然指出戲曲之娛人功能從古到今都沒有發生變化。根據其易學思想,焦循將詞曲與正學視為一陰一陽之道,他認為:
學者多謂詞不可學,以其妨詩、古文,尤非說經所宜,余謂非也。人稟陰陽之氣以生者也,性情中必有柔委之氣寓之,有時感發,每不可遏,有詞曲一途分洩之,則使清勁之氣,長流存于詩、古文。且經學須深思冥會,或至抑塞沈困,機不可轉,詩詞足以移其情,而轉豁其樞機,則有益于經學不淺。文武之道,一張一弛。古人一室潛修,不廢弦歌。其旨深微,非得陰陽之理,未云與知也。*(清) 焦循《雕菰集》(三),第153、154頁。
焦循將經學與詞曲之關系視為一張一弛之道,以詞曲之學為經學研究之余的調劑。清代乾嘉時期揚州戲曲活動頻繁,焦循研學之余,經常踏出書齋觀看花部戲劇演出。他的三部論曲之作的產生,均與這種“一張一弛”“一陰一陽”的學術觀有關。其著《劇說》云:
嘉慶乙丑,養病家居,經史苦不能讀,因取前帙,參以舊聞,凡論宮調、音律者不錄,名之以“劇說”云。*(清) 焦循《劇說》,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頁。
其著《花部農譚》云:
天既炎暑,田事余閑,群坐柳陰豆棚之下,侈譚故事,多不出花部所演,余因略為解說,莫不鼓掌解頤。有村夫子者筆之于冊,用以示余。余曰:“此農譚耳,不足以辱大雅之目。”為芟之,存數則云爾。*(清) 焦循《花部農譚》,同上,第173頁。
著《劇說》是因為病中難治經史之學,故而治曲以為調劑;著《花部農譚》是因為其解說能夠娛樂村民。因此他不僅將看戲視為與經學相輔的娛樂,更將研治曲學作為經學之輔翼。當然,從其“一張一弛”的描述中,也可以認識到,焦循亦終視戲曲為小道。
焦循一方面認為戲曲承載經學之道,主張發揮戲曲經世之用,一方面也沒有忽視戲曲之娛樂功能,他對戲曲功能的完整認識是以道德教化為主,以娛情相輔,正如其評價周元公《謨觴閣破愁》四劇:“事可解頤,詞頗醒世。”*(清) 焦循《劇說》,同上,第144頁。這是焦循娛樂與教化功能并重觀念的簡練表達。
4. 靈活變通的戲曲虛實論
凌廷堪和焦循對戲曲敘事虛實關系的認識都顯示出揚州學派學主通達的觀念。凌廷堪極為關注戲曲“謬悠”的藝術特征,焦循則更關注戲曲虛實關系處理方式與戲曲教化功能的統一。他并不像諸多曲論家一樣糾纏于戲曲應否崇實或務虛,而是在認可戲曲具有“謬悠”特征的基礎上,強調合理處理以更好地發揮戲曲的道德教育功能。
焦循虛實論的核心是:“忠、孝、節、烈之跡,則宜以信傳之。”強調傳奇的虛構不能與倫理道德的宣揚背離。此論緣于《雌木蘭》之考辨:
而所傳木蘭之烈,則未嘗適人者;傳奇雖多謬悠.然古忠、孝、節、烈之跡,則宜以信傳之。因文長有“王郎成親”之科白,而詳之于此。*(清) 焦循《劇說》,見焦循著、韋明鏵點校《焦循論曲三種》,第142頁。
焦循認為木蘭并未嫁人,寫其成親有損木蘭“烈”的形象。其考《長命縷》云:
江東勝樂道人作《長命縷》傳奇,演單符郎與邢春娘重逢故事,本宋王明清《摭青雜說》。但春娘已落倡家作妓,而傳奇則有《懷貞》等出,此亦勸善維持風俗之一端,固不必其事之實耳。*同上,第144頁。
認為這樣的虛構有益于風化,可以接受。因此,焦循的戲曲創作“虛實論”,以是否有利于道德教化作為判斷標準,他如批評《量江記》污蔑后主,肯定馮夢龍的傳奇改編有利于傳播忠孝節義思想,都本于此。
《花部農譚》中,焦循考楊業之死,認為史書記載中楊業所言“奸臣”實指潘美而非王侁,撰史者為了維護潘美的形象,運用了春秋筆法隱晦地表達了潘美之失,故贊揚花部《兩狼山》劇直接歸罪于美的做法,認為這一寫法“與史筆相表里”,即認為戲曲還可以揭史家諱筆,還歷史真相,有褒貶分明,獎善罰惡之能,這同樣是肯定戲曲教育功能的做法。
與此對應,焦循肯定花部戲曲《鐵邱墳》模仿《八義記》的做法。焦循本人反對抄襲或者承襲,但他卻指出,表面上《鐵邱墳》拙劣地抄襲了《八義記》,徐勣與薛家非親非故,以己子替薛子的情節設置并不合理,但《鐵邱墳》將歷史上徐敬業討武氏的真實事件,移之于戲曲中的薛交,是通過戲曲對徐勣進行了批判與懲罰,實為妙筆——因為焦循不喜歡徐勣,認為他不可能有忠義之后。贊同《兩狼山》補史之筆,認可《鐵邱墳》虛構之妙,表面看似矛盾,實則表明,在焦循看來,虛實處理得宜,戲曲可以更好地發揮歷史獎善罰惡的教育功能。
焦循在肯定戲曲謬悠特征的基礎上提出了戲曲虛實關系的處理原則,避免了尚實或尚虛的兩極化,具有靈活通變的特征。作為想要改變考據學派沉迷訓詁治學傾向、強調儒學經世致用特征的學者,他對倫家倫理道德理想的強調建立在對戲曲藝術本體特征的認可之上,也無可厚非。
乾嘉時代是清代考據學與戲曲發展的巔峰時期,揚州是戲曲演出活動最為繁盛之地,焦循則系乾嘉時期為考據學注入新的學術活力的揚州學派之典范,因此焦循的戲曲觀和曲學研究在這一特定的歷史語境和學術環境中,極具典型意義。和在此之前的曲論家相比,焦循在通達的學術觀念影響下,戲曲觀亦極為通達,懂得靈活變通而不拘泥執一;而其復以深厚的學識和治學功力研究戲曲,發揚考據方法之長,使它在曲學研究中大放異彩,形成了諸多超越前人的理論認識;而最難能可貴的是,清代許多學者在研治曲學、關注戲曲的道德教化功能時,往往忽視了戲曲之藝術特征,焦循卻能致力于二者的和諧統一。正因為如此,他的治曲之道才對后世戲曲研究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考據學思潮的興起所帶來的學術思想更替與治學方式的變化,為傳統戲曲理論研究開辟了一條新路。清前期雖有毛奇齡、毛先舒等學人導夫先路,然終以延續晚明理路為主;清中期曲論家則在表演理論、音律理論、創作理論、戲曲史論等從多個方面以典型的學術品格和時代特征區辨于明代曲論,其代表性曲論家之理論觀點與其著作之內容與特征,清晰地展現了這一新路所帶來的諸多變化與益處,而其中所顯現出的經學束縛與研究弊病也從更深層面地顯現出傳統戲曲理論發展之局限與障礙,此亦不可忽視。
2016年,219— 255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