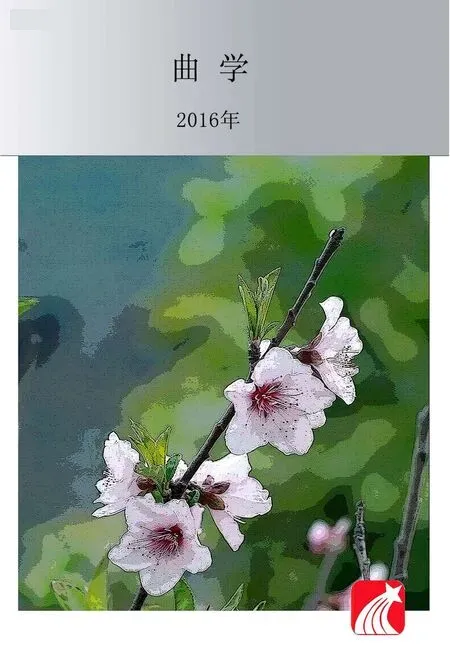韓國知識人與中國詩詞曲的發展
〔韓〕 金學主
《曲學》第四卷
韓國知識人與中國詩詞曲的發展
〔韓〕 金學主
一、 緒 言
古時候,韓國很長的期間在中華文化圈里面生活,兩國人民過得差不多同一個國家同一種人民一樣。他們學習中國的文化倫理政治思想及文學等各方面,要過中國一樣的文化生活。但是從某一段時期開始,兩國之間的關系發生變化,漸次成為互相不大了解,互相關懷不多的國家。結果,到現在兩國關系反而變得疏遠,形成互相輕視對方的情形。這是非常重大的問題。我想這一個責任在韓國方面。韓國人的如此現象,什么時候開始?其原因在什么地方?這一問題如何解決?我們都應該探究,努力使兩國關系回復圓滿。請諸位多多指教!
中國已有幾千年的歷史,所產很多的典籍,都是用漢字寫的,統治階層皆學其先祖傳給他們的書,以其書的內容為社會規范,又為生活倫理。古時韓國統治階級看了那么宏大的中國書籍,當然要學其漢字要讀其書,學其治理自己社會的方法。古代中國文化里面最重要的是文學,又其文學以詩為中心發展。所以韓國人要學要讀的中國書里面,自然有關詩的多。不但要讀中國詩,又自己也要用漢字作詩。結果他們讀中國詩的趣向,與用漢字作詩的態度,都與他們對中國和中國文化的態度漸成有關。韓國用漢字寫的中國詩叫漢詩,散文則叫漢文。
中韓兩國關系的變化與韓國人對待漢詩的態度也有很深的關聯。韓國知識人特別尊重漢詩,所以讀漢詩作漢詩的人不少。但是中國詩詞曲發展變化的時候,韓國知識人隨著學習詩詞曲的態度不同,又對待中國文化的態度也都有不同。于此要討究韓國人對中國詩詞曲了解得如何?學習得如何?其中發生的問題是什么?有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法?
二、 韓國人如何學習中國詩詞曲?
新羅百濟高句麗三國時代(B.C.57—A.D.668)之前,韓國沒有自己的文字,但其統治階級已常用漢字漢文。當時在中國,詩的古體近體皆形成,發展迅速。故三國的一部分人學其詩,自己也作兩三篇作品,可說是漢詩的學習時期。新羅(668—935)與唐聯合統一三國以后,兩國關系特別好,新羅王派遣一批士人到唐游學,培養了自國的學者。如崔致遠(857—?),他十二歲時到唐游學,十七歲應科舉,及第為進士,在唐一面做官一面與文人交流,頗有盛名。二十八歲時(885),他以唐朝使節的身份回新羅。次年他向新羅國王獻上自己的文集二十八卷,里面有詩集。他在唐及回國之后,作了不少詩。他以外,樸仁范崔匡裕崔承佑等,游唐回國作漢詩的人不少。但留下自己作的詩集的人一個都沒有。
到高麗時代(918—1392),漢詩的學習發展得很多。作漢詩的人也增多,作詩的水平也比以前大大提高。北宋(960—1127)時代,高麗非常尊重北宋的學術文化,始終要向北宋學習,兩國互相關系很好。本來高麗人學的是唐詩,但與北宋往來而后不少人尊重宋詩,形成所謂宋詩派,特別喜歡蘇軾的人多。李奎報(1168—1241)在他的《答全履之論文書》里說:“方今為詩者,尤嗜讀東坡之文。故每歲榜出之后,人人以為今年又三十東坡出矣。”但是金(1115—1234)元(1206—1368)侵占統治中原以后,學術文化上高麗人輕視女真族與蒙古族,蔑視他們的詩文,由此兩國關系也變壞。高麗人蔑視元人的詩,不再向他們學習,只作自己的詩,沒受什么影響。但在高麗作漢詩的人仍然多,又留下自己所作漢詩集的人也增多。
朝鮮(1392—1910)時代,世宗(1419—1450在位)雖創作自己的新文字“正音”,即是現在的韓國文字,但朝鮮知識人仍然常用漢字漢文。所以朝鮮知識人里面作漢詩的人也大增。看張志淵編《大東詩選》十二卷,朝鮮以前的作品全部收錄于第一卷,其余十一卷收錄的都是朝鮮時代詩人作品,可知朝鮮作漢詩如何盛行。朝鮮時代的明(1368—1644)為漢人王朝,兩國關系圓滿,但明代詩人皆始終從事復古,唯追蹤唐宋詩,自己作詩沒有特征,不能給朝鮮人的漢詩特別的影響。到清(1616—1911)代,朝鮮人輕視女真族,不要向他們學詩,也沒給什么影響。再加上學術方面朝鮮時代唯尊朱子學,而朱子學不大尊重詩文之創作,偶爾作詩也唯尊道論,朱子學以外的思想不接受,他們雖作漢詩,其發展不能不受限制。
韓國人對詞了解得不多。他們雖然用漢字漢文,但對漢字的聲調不大了解,對文章里聲調的諧和問題更難知覺,故散文的駢儷文也不能了解,又詩律的真意也很難把握。所以詞律詞牌及詞的音樂更難知道,結果學詞作詞的人很少。新羅時代到唐游學的皆是晩唐時期,作詞的人一個都沒有。到高麗時代,重視北宋詩文,但沒人學宋詞,實際上是不能學習的。很多次到元去逗留的李齊賢(1287—1367)作很多篇詞,但他可說是例外。那么多可作漢詩的人里面雖偶有作詞的人,然所作的不過兩三篇而已。朝鮮時代也是一樣。他們可能都不以詞為正統的中國詩歌。
《高麗史》樂志里面載高麗王朝所用樂舞,有雅樂唐樂俗樂之三種。朝鮮成宗二十四年(1493)所刊《樂學軌范》卷三載高麗史樂志唐樂呈才圖說,卷四載時用唐樂呈才圖說,可知唐樂從高麗到朝鮮在宮廷繼續演出。雖稱唐樂,所載歌辭大都以宋詞為主,即是從北宋進來的,其中有歐陽修、柳永、蘇軾等的作品。詞進到高麗來,始終在宮廷里演唱,所以高麗知識人皆以詞為歌謠之一種,高麗與朝鮮的文人更難知道詞的文學性。
北宋以后金元侵占中原,繼以為曲的時代。至此,中國傳統文化漸變為與以前不一樣的方向發展。到那個時代,中國周邊的異民族都開始覺醒各自的民族意識。例如金元也都創作自己的新文字,要對抗中國的漢字漢文。
先看金國,他們的太祖阿骨打天輔三年(1119),令臣作女真大字,其后熙宗又作女真小字*參見《金史》卷二、卷四。。自世宗大定四年(1164),用女真文字翻譯中國的經書,大定十一年用女真文字開始實行科舉,登用人材。于大定十三年,中央設立女真國子學,諸路設置女真府學,努力克服漢字的文化。
在蒙古,初期開始用回紇文字相似的字,而到元世祖忽必烈,聘請國師八思巴創造蒙古新字,至元六年(1269)頒布天下。首都設立蒙古翰林院蒙古國子監和蒙古國子學,地方設置蒙古教授蒙古提舉學校官等,努力擴張蒙古字的教育與使用。至元八年(1271)京師設立蒙古國子學,至元六年在各路的蒙古字學,用蒙古文字翻譯《通鑒節要》,作為學校教學生的教科書*參見《元史》卷二〇二、卷八七、卷八一。。
金元都向漢族強調自己低俗的文化,漢人衣食住各方面都開始發生變化。但他們無法克服漢字的威力,反而他們自己被同化為中華民族了。可是他們給中國傳統文化很大的刺戟,叫它變化。老百姓所唱歌謠也有了變化,隨著這音樂的變化發展來的是曲。明代王驥德的《曲律》卷四《雜論》說:
元時北虜韃韃所用樂器,如箏蓁琵琶胡琴渾不似之類,其所彈之曲亦與漢人不同。
曲與以前的音樂,曲調不同,節奏也不同,伴奏樂器也都不同,是完全不同性格的歌曲。士大夫學了新的樂曲,用漢語寫其歌辭,成了新的詩歌,就是曲。曲與詞的形式雖然相似,音律是完全不相同的。
本來曲的歌詞也多用女真語或蒙古語,其內容既卑俗又低質的多。元時漢族讀書人根據民間流行歌謠的形式,利用他的文章能力寫出的新詩就是曲,但其中的胡氣俗味不能完全去掉。曲的音樂是女真或者蒙古的歌曲,伴奏樂器也是都用他們的,演唱與演出方法也有很大的變化。
中國到了“曲的時代”,高麗朝鮮人以金元為戎狄之國,蔑視其文化為胡狄的,不予尊重,曲的曲律音樂等對韓國人皆陌生,不能親近,不可了解。并且曲不但有小令,又有套曲與戲曲,曲以戲曲更為盛行,但韓國人對套曲戲曲尤不知,偶而聽其音樂也不喜歡。雖然漢族的明朝繼承元王朝,明自己亦不能恢復北宋以前的文化傳統,他們亦隨金元作曲唱曲。后來到清代,曲的文化發展得更活潑,更為大眾化。韓國人與曲離開得更遠,更不知套曲與戲曲。而套曲戲曲與小說戲劇密切有關,所以中國小說戲曲的真正性格與價值韓國人也不能了解。
如此韓國人忽視金元的曲文化,中國文化不能再影響韓國。古時韓國知識人皆學漢詩,努力作詩。在朝鮮,不知詩,不能及第科舉,不能任官職,不能認為知識人。可是學詞很難,很難了解。從詞開始,韓國人離開中國。到曲則以為是完全低俗的胡狄文化所產,更難了解,又無興趣,沒人照料。韓國知識人對戲曲更不知,對元雜劇沒有關心,對明傳奇也可說不知道,對清代各種地方戲及京戲則完全看不起,并將其輕視為低俗的戲劇,視其音樂與演出等也皆低劣。
因此到曲的時代,兩國忽變為文化性格完全不同的,互相不能了解的異質的國家。再說韓國人對曲的時代的中國文化,不但沒有關心,又蔑視不顧,隨著又失去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關心,兩國關系變為越來越疏遠。如此韓國人對中國曲的文化失去興趣,可說是很大的問題。這是現代韓中文化交流及兩國關系上的一大問題,這問題我們以后必須解決。
實際上更大的問題是在韓國人自己。現在韓國人全然不覺察這一重大事實,韓國人應該警醒。
三、 “曲的文化”與韓國人的問題
2007年4月初旬,我在韓國報紙上讀了放中國新作影片《梅蘭芳》的記事,那影片是名導演陳凱歌所編的。我非常喜悅,過幾天要去看那影片,可是韓國觀眾的反應不好,早已退回去不放映了。梅蘭芳是中國京劇名旦,他不但在中國出名,而且是歐美各國也都知道的世界性名優。他幾次到歐美與日本各地公演京劇,受到了熱烈歡迎。他在中國的公共地位與名聲也很大。惟韓國人不知梅蘭芳是什么人。韓國人又不知京劇是怎么樣的戲劇,偶而聽了其音樂也不喜歡,對其優人的衣服化妝也都不喜歡。我想韓國人如此,不能接近中國,不能親近中國人,不可了解中國文化的。
韓國人惟尊重中國士大夫文化,對其庶民文化沒有關心。可是在中國到近代,人民大眾的力量長大了。清末葉太平天國之亂以后到中華民國時代,西洋帝國主義列強隨便侵入中國,那時中國正如沒有主人的國家一樣。可是列強不能侵占中國的一片領土,反而中國吸收西藏、回紇等周邊民族,發展為更大的國家。我以為是由于下面庶民的力量。
我想韓國知識人對中國老百姓生活與民間文化太疏忽。詩的時代中國完全在士大夫階層的統治之下,特別用漢字寫的詩是他們的專有物,似與下層人民沒點關系。其實士大夫們的詩其根源也都在老百姓。西周時代的《詩經》國風,都是記錄各地的民歌而成的。東周時代的《楚辭》,也來自南蠻楚地的巫歌。西漢樂府東漢五七言古體詩,也都從民歌變化發展的。南北朝時代開始發展的近體詩,也都是受民歌與佛教音樂影響而形成的。后世的詞與曲,民歌與庶民文化的影響尤為明顯。所以雖然研究資料缺少,我們研究詩時代的文學或文化,也應該多努力討究有關老百姓的東西,才可得真正的實象。
如前已說,曲里面又有散曲與戲曲。散曲以很短的小令為基本,而又有連幾篇小令而成的大曲套數。套數的目的在詠唱更復雜的情節,是本來在民間唱故事為主的講唱形式的曲藝。戲曲是援用幾個腳色,演出一種故事的戲劇。曲的時代,元雜劇、明傳奇、清花部戲等大戲為中心,曲繼續發展。曲到后世,詩歌性漸變為不大重要,而其戲曲性發展的更大。這是因于其庶民性之增多,而韓國人疏忽又輕視此曲的庶民性,不照顧又不知道曲的文化,結果韓國人與中國漸離漸遠,變成日益不了解中國與中國人。
更大的問題在韓國人本身上面。古時在韓國民間演戲曲雜戲的人,都是其社會里面地位最低的賤民“常人”,特別朝鮮時代受朱子學的影響,非常賤視這類“常人”,連他們所演的各種演戲也不大重視。結果演戲曲雜戲的優人漸次減少,到現代完全消失了。以前在民間流行的戲曲俗講歌舞雜技等韓國的傳統演藝,到現在都沒傳下來,完全丟失,唯政府的保護下殘存其中的一部分。
又一個問題是,韓國統治階級學漢字常用以后,朝鮮初期雖創自己的文字,依然以漢文為標準文章,寫漢文漢詩才可謂知識人,可為統治階級。不知漢字則為文盲,所以老百姓大部分是文盲,自己的文字沒有用。可是韓國人的漢字知識有限,對那么多的漢字的形音義各方面知道的都不夠,使用上有不少問題。到現代這樣情形改變多多,可是在韓國社會,漢字的威力仍然很大,對他們為文化發展上的一種障礙。
四、 結 語
韓國人對中國文學的時候,從來惟知士大夫的詩文化,只學習漢詩漢文。但是我們知道對詞文化曲文化應該多注其意,才能使對中國的了解增多。到現代,庶民性或者大眾性日益增多的中國曲文化,應該更尊重多學習,才可以正確地了解中國與中國人民,可以與中國親近。韓國人不可誤解曲特別戲曲為胡族的或低質的,它們實是真正中國的曲文化,應當努力學習,多多了解。
日本人對中國曲文化的了解和接受態度與我們不同。例如1956年梅蘭芳63歲時,53天里訪問日本全國12個城市公演京劇,那時日本人的反應非常熱烈。雖為老男人扮演淑女美人,日本人對梅蘭芳與京劇的反應是狂熱的。*據吉川幸次郎《閑情の賦》梅蘭芳その他。我們也應如日本人一樣,努力學習中國演藝,又一塊兒欣賞。
我們不了解中國曲的文化,則不能接近中國。曲是與我國接鄰的,我們應該親近的,大國全體人民喜歡的演藝。我們應該覺醒,簡單而重大的一件事,不知曲則與中國、與中國人也很難接近。
2016年,323— 3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