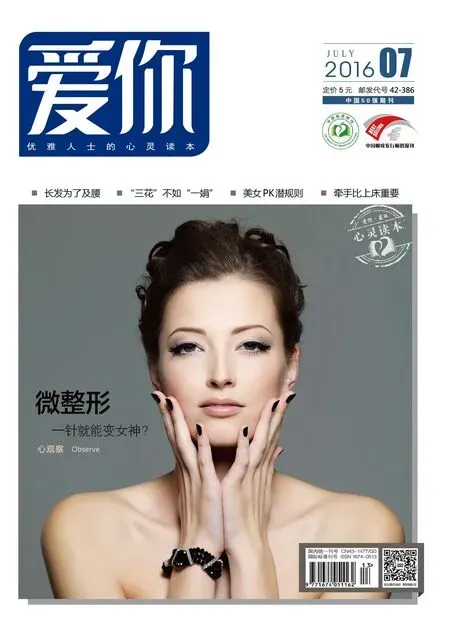決戰(zhàn)于美國(guó)法庭
◎ [美]李昌鈺
決戰(zhàn)于美國(guó)法庭
◎ [美]李昌鈺

在中國(guó),法庭科學(xué)家一般作為專家證人出庭作證,他們既不屬于控方,也不屬于辯方,地位超然;但是在美國(guó)法庭上,法庭科學(xué)家只能選擇支持控方或者辯方,可以說(shuō)美國(guó)法庭將“聽(tīng)取雙方當(dāng)事人陳述”這一原則發(fā)揮到了極致。
在法庭上,控方與辯方的交鋒決定著案件的結(jié)果,他們不得不使出渾身解數(shù)以求得陪審團(tuán)的信任。作為專家證人,我得時(shí)刻準(zhǔn)備接受律師的質(zhì)詢,法庭常處于劍拔弩張的氛圍中。
作為一位華裔法庭科學(xué)家,英語(yǔ)能力幾乎成為對(duì)方攻擊我的萬(wàn)能武器。早期,我在一次擔(dān)任控方專家證人的時(shí)候,辯護(hù)律師問(wèn)我:“李博士,您說(shuō)您來(lái)自中國(guó)臺(tái)灣,對(duì)嗎?”我很自豪地回答:“是的。”這位律師立即說(shuō)道:“難怪我剛才聽(tīng)不懂你說(shuō)的英文。”律師見(jiàn)我的證詞無(wú)懈可擊,試圖誘導(dǎo)陪審團(tuán)關(guān)注我的英語(yǔ)水平。我轉(zhuǎn)過(guò)頭去問(wèn)坐在旁邊的陪審員們:“請(qǐng)問(wèn)你們聽(tīng)懂我剛才說(shuō)的話了嗎?”陪審員們紛紛點(diǎn)頭。這時(shí),我回過(guò)頭來(lái)對(duì)律師說(shuō):“這里只有你聽(tīng)不懂我說(shuō)的英文,看來(lái)是你的問(wèn)題。”
在美國(guó)法庭上,控辯雙方的激烈對(duì)抗體現(xiàn)在每個(gè)環(huán)節(jié)中,他們不僅窮盡科學(xué)和法律知識(shí)來(lái)攻擊專家證人的證言,還會(huì)運(yùn)用一些語(yǔ)言陷阱來(lái)誘導(dǎo)專家證人。盡管有時(shí)候明知他們是故意刁難,但在法庭上做無(wú)謂的口舌之爭(zhēng)顯然不是明智之舉,法官和陪審團(tuán)也可能因此懷疑你的專業(yè)能力。如何在緊張的氛圍里幽默、機(jī)智地回避爭(zhēng)議并反擊對(duì)方,很考驗(yàn)每一位審判參與者。
前幾天,我作為控方專家證人出庭做證。那個(gè)案件已經(jīng)過(guò)去十幾年了,但我清楚地記得檢驗(yàn)每一項(xiàng)物證的過(guò)程。辯護(hù)律師沒(méi)能從我的證詞里找到漏洞,于是話鋒一轉(zhuǎn):“李博士,2002年檢察長(zhǎng)帶著刑警到你的辦公室拜訪,你還記得當(dāng)時(shí)有哪些來(lái)訪者?”我回答說(shuō):“我大概記得那個(gè)檢察長(zhǎng)叫肯特,那位刑警叫安德森。”律師說(shuō):“有一個(gè)金頭發(fā)的美女刑警,你還記得嗎?”那次拜訪已過(guò)去十幾年,我對(duì)這個(gè)金發(fā)美女完全沒(méi)有印象。律師對(duì)我說(shuō)的話公開(kāi)表示懷疑,認(rèn)為我不應(yīng)該忘記,試圖以我的記憶力存在問(wèn)題來(lái)攻擊我證詞的可信度。
我沒(méi)有與他爭(zhēng)論,而是微笑著說(shuō):“對(duì)我來(lái)說(shuō),美國(guó)姑娘看起來(lái)都很像,你們不也常說(shuō)我們亞洲人看起來(lái)很像嗎?”聽(tīng)到這里,幾個(gè)陪審員都笑著表示贊同,律師自知再糾結(jié)這個(gè)問(wèn)題已經(jīng)不是明智之舉。
美國(guó)社會(huì)推崇幽默文化,美國(guó)法庭就是美國(guó)社會(huì)的縮影。
(摘自《挑戰(zhàn)不可能:李昌鈺的鑒識(shí)人生》中信出版社圖/王建峰)來(lái)的。因?yàn)榘b紙上的條形碼只要從讀碼鏡上一過(guò),收款機(jī)就會(huì)打出這個(gè)商品的名稱和價(jià)錢(qián)。這張十分普通的購(gòu)物清單拿回家可以派上很大的用場(chǎng),日本家庭主婦是這樣介紹的:“我把購(gòu)物清單貼在冰箱上,每次用完了肉呀﹑菜呀,我都會(huì)用筆劃掉。比如今天用了洋白菜,我就會(huì)在購(gòu)物清單上的‘洋白菜’上劃一道黑線,表示洋白菜已經(jīng)用完了;魚(yú)用完了,我就會(huì)在‘魚(yú)’上劃一道黑線。”
“這樣做有什么好處呢?”我問(wèn)。
她笑道:“能減少打開(kāi)冰箱門(mén)的次數(shù),省電呀!”
聽(tīng)了日本家庭主婦的話,我實(shí)在佩服她們的絕頂智慧。其實(shí)還有很多類似這樣的例子,光是我能記住的就差不多有上百條。如果把這些日本主婦的智慧歸攏到一起編一本實(shí)用書(shū)籍,說(shuō)不定能在中國(guó)暢銷一把。(摘自《狂走日本》上海文化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