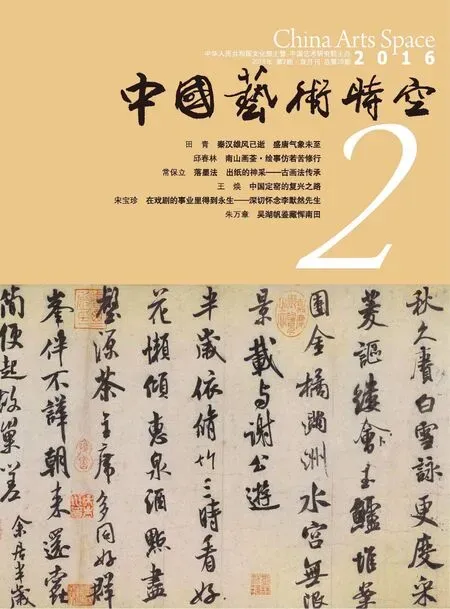南山畫荃·繪事仿若修行
中國藝術研究院 邱春林
南山畫荃·繪事仿若修行
中國藝術研究院 邱春林
繪畫如佛說法,縱口極談,因果歷歷在目,既超然意表,又不越人情物理。從事美術史論研究之學者往往悟得多,證得少,也就是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古代名丹表家都 屬于有悟有證之人,理論與實踐雙修,才能做到真正覺悟,技藝上也能有一日千里的進步。優秀的文學藝術家能在創作時暫時超越現實人格的束縛,如同“脫胎換骨”,淋淋離盡致地觀照和表現自己的理想人格。
利家 行家 證悟
今天是史上少有的藝術泛濫的時代,或者說泛藝術化生存作為一種生活方式十分流行的時代。其主要原因一是西方藝術觀念之快速變革令藝術無邊無界,這無疑拆毀了藝術的門檻;二是文化產業化將藝術推向資本市場和工業復制,平庸藝術因此大行其道。
古之繪畫是衣冠貴胄、逸人高士之少數人事業,他們依仁游藝,既重人品,又重才情,境界話題常談常新,易形成社會共識。當藝術隊伍過于龐大時,有境界的藝術畢竟不能占多大比重。加上丹青鏈接名利,筆墨混于塵埃,身心不自由局限了藝術的發展。黑格爾說,一種藝術門類愈受物質的束縛,精神活動的自由程度愈少,就愈低級;反之,一種藝術門類愈不受物質的束縛,愈顯出精神活動的自由,就愈高級。

嶗山仰口
古人畫畫一非易事、二非小事,所以古人恒思傳諸千古百年。如此,用意構思必深沉古厚,繪必神妙,材必講究,工必細謹。今天畫家為社會一大職業,畫畫是畫家的生業,也是社會化產業。所以畫家容易求悅庸人耳目,遍地皆畫,漸巧漸薄,畫道日卑之大勢很難逆轉。

前赤壁賦之一

前赤壁賦之二

初夏

潭深流靜

晨江放排
明人品藻畫家,以行家和利家分別之,如何良俊《四友齋畫論》以戴文進為行家第一,吳小仙、杜若狂、周東村其次;利家則推沈石田為第一,唐六如、文衡山、陳白陽其次。行家、利家之說首先有在朝在野身份之別,行家多以繪畫為職業者,如宣宗朝院畫代表人物之一戴文進,利家多指在野畫家,自然這種區分有它的不合理性,繪畫乃心靈事業,外在的社會身份并不能說明一切。更深層的區分卻也是最模糊的區分在于“畫品”的差異,畫家里頭的行家多丹青能手,即技藝高超的畫工,中規中矩,傳承性較好,畫品也因此多歸入能品。而利家之名來源于佛教用語“利根”一詞,楊炫之《洛陽伽藍記》載:“摩羅聰慧利根,學窮釋氏。”利根人即是有智者本性之人,也就是通常我們理解的天賦高、悟性好之人。高濂 《燕閑清賞箋》中又稱“隸家”,意思與利家等同。明人論書畫、演劇、詩文等特重利根人,何良俊以為沈石田的畫立意高遠,筆墨既出入宋元,又天機自現,非行家做能及,所以推沈石田為畫家中難得的利家子。高濂以為利家須有所謂士氣,有士氣者,能“用神氣生動為法,不求物趣,以得天趣為高。”
高濂要在行家與利家之間劃出一道無涇渭分明的界限。其實,描和寫、工與拙、物趣與天趣之間原本就是相輔相成的,行家與利家也是可以統一的,行家也能熟能生巧、不拘繩墨;利家天資再高也須有行家的功夫淬煉過程。所以,對于一個喜愛藝術的人而言,主觀分出誰是行家誰是利家其實不打緊,養成判定行畫與藝術的鑒別力才最緊要。
“公安派”文學反對“前后七子”“文必秦漢,詩必盛唐”的復古主張,首重性靈。袁宏道所謂的性靈既有李贄“童心說”的主張,也包含對自然情欲的肯定,珍玉與泥沙俱下。李日華論繪事也重性靈,以為“繪事以微茫慘澹為妙境,非性靈廓徹者,未易證入”(《竹嬾論畫》)。繪畫如佛說法,縱口極談,因果歷歷在目,既超然意表,又不越人情物理。明人論畫從心入手,靜心、洗心、空心,都為打開靈竅,使性靈灑落自現,這條路子是對的。繪事是唯心的,出自心靈,歸于心靈,因而繪事仿若修行,可視作修行法門之一。
繪事即修行,修行有手段,讀書是方便法門之一。讀書多即見古今事變多,胸襟自然開闊,不執己見,不拘小我小情。只有胸次寥廓,山川之雄奇清幽才能入得性靈,起到涵養人格的作用。
明人張風認為,繪事有悟有證,“悟得十分,茍能證得三分,便是快事!”(《大風論畫》)在佛教用語中,證與悟是一不是二,證即參悟,證即得道,它既是過程,也是結果。在繪事中,悟是認識;證是驗證、證實,是實踐。從事美術史論研究之學者往往悟得多,證得少,也就是未具此手,先具此眼。古代名丹青家都屬于有悟有證之人,理論與實踐雙修,才能做到真正覺悟,技藝上也能又一日千里的進步。
方薰云:“古人筆下五繁簡,對之穆然,思之悠然神往者,畫靜也。”(《山靜居筆記》)惲南田云:“意貴乎遠,不靜不遠;境貴乎深,不曲不深。”(《南田畫跋》)畫主靜,繪畫意義上的靜不是排斥聲音,有時恰恰要由視覺產生通感,達到如聞其聲、如臨其境的效果。關于靜,中國人有層次豐富的感覺,自然寂然無聲是靜,云出林梢、泉流石上也是靜;男人沉著冷靜是靜,婦女恬淡嫻靜也是靜;儒者清和文雅是靜,道士精神守一也是靜;靜還通“凈”,環境干凈、內心清凈都是靜的境界。于畫中藝術形象而言,靜是自然生機或理想人格的純粹表現;于畫之主體畫家而言,靜是一種修養、風度。蘇東坡詩云:“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送參寥詩》)心定才能知曉微動,心空才能容納萬千。程灝詩云:“萬物靜觀皆自得,四時佳興與人同。”(《偶成》)靜觀,有益于起興,文學和藝術往往要籍興會才能淋漓盡致。
史上人物品鑒,品高者如黃庭堅贊周敦頤有代表性:“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豫章集·濂溪詩序》)一個人內心越光明潔凈,不為名役,不為物誘,人格越主靜。如《紅樓夢》第一回:“雖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繩床,其晨夕風露,階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懷筆墨者。”但人有多面性,知人論世不能只看表象。金庸《笑傲江湖》的角色劉正風說:“曲大哥雖是魔教中人,但自他琴音之中,我深知他性行高潔,大有光風霽月的襟懷。”類似這種在一個人身上現實人格與理想人格分裂的例子比比皆是,但優秀的文學藝術家能在創作時暫時超越現實人格的束縛,如同“脫胎換骨”,淋漓盡致地觀照(如程灝所云靜觀)和表現自己的理想人格。至于能否獲得這種創造的自由,努力清凈本心是必行的功課,修行是唯一的途徑。
沈宗騫《芥舟學畫編》細分“雅”有五種:“古淡天真,不著一點色相者,高雅也;布局有法,行筆有本,變化之至,而不離乎矩鑊者,典雅也;平原疏木,遠岫寒沙,隱隱遙岑,盈盈秋水,筆墨無多,愈玩之而愈無窮者,雋雅也;深恬靜氣靜,令人頓消其躁妄之氣者,和雅也。”這種分類法其實不統一,似乎每類都有不同的著力點,其中高雅是針對藝術形象說的。色相原為佛家語,指萬物的形貌。《心經》云:“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白居易《感芍藥花寄正一丈人》詩:“開時不解比色相,落后始知如幻身。”繪畫離不開對事物形貌的描摹,當然,現當代一些先鋒藝術往往要有意去打散、重組事物的形貌,甚至回避對形貌的描摹或出現任何有指向性的暗示。不管怎樣努力,總有色、線等物質痕跡,這依然是色相。依沈宗騫的說法,要達到高雅,須“不著色相”,不著即不執著,無掛礙,以古淡天真來對治拘泥于形貌而產生的匠氣、脂粉氣。不著有心態上的不著,也有筆墨上的不著,中國畫不追求過于迫近現實,而是強調以“暢神”為主,目的是使觀者產生與現實色相之間的“審美間離”。

陳珂 《初雪》 69×69cm 2012
專 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