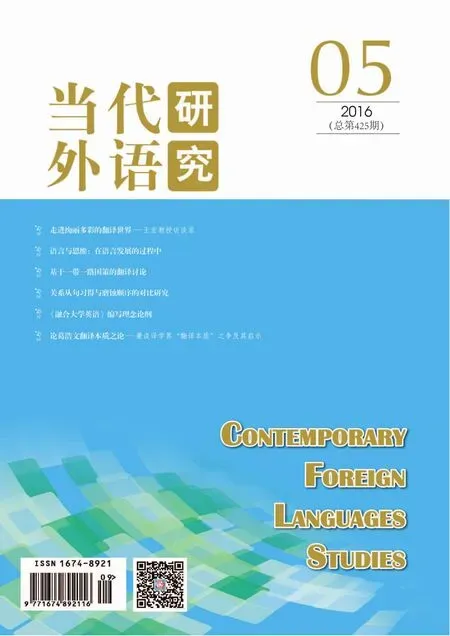語言與思維: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
主持/整理 范 莉
(北京林業大學,北京,100083)
?
語言與思維:在語言發展的過程中
主持/整理范莉
(北京林業大學,北京,100083)
引言(范莉)
Chomsky(2000:50-51)曾用了個形象的比喻:“說‘語言不是天賦的’就如說我的孫女、巖石和兔子之間毫無區別。若是如此,將巖石、兔子和我的孫女帶入一個英語的環境,他們也都會說英語。”縱使日日耳濡目染語言,巖石、兔子為什么無法造化成人類?當人的大腦與語言在廣袤無垠的時間與空間中邂逅時,到底發生了什么?語言在使用者身上的成長過程、存在狀態會引領我們破解關于語言與心智的許多謎語。
語言理論與語言習得的結合是語言科學發展的歷史必然。回眸歷史,約1900~1960年間語言學舞臺上的主角是結構主義,語言理論與語言習得研究之間町畦分明。在20世紀初至40年代,有些語言學家(Ronjat 1913; Leopold 1939/1949)主要以筆記方式記錄了兒童語音與詞匯發展的個案;40年代至60年代,結構主義語言學與行為主義心理學試圖運用對比分析等方法來研究語言學習。20世紀60年代是語言理論開始逐漸影響語言習得研究發展速度與軌跡的標志性時期。語言學發展日趨呈現出跨學科的特點,理論研究打破了單純從語言內部來內省的研究模式,觀察視角提升到了語言與心智互動的層面,尋求理論假設的心理現實性成了理論研究的終極目標。在這一時期,相繼萌芽和成長的生成語法、功能語法與認知語法逐漸從眾多學說中脫穎而出,成為語言學理論的“排頭兵”。這三個理論模式都清楚地闡述了各自的語言觀與語言習得觀,努力構建本體理論與習得理論互動的模式。
以Chomsky(1957,1965,1972,1975,1981,1986,1995,2000,2002,2004)為領袖的生成語法摒棄行為主義的“白板說”,認為語言是天賦的;人類大腦先天就具有特有的語言獲得機制(language acquisition device,LAD),它是語言的最初狀態,與普遍語法是等同的(Chomsky 2000:54);獲得和運用語言的能力是人類所特有的,有些深層的、限制性的原則深植于人的大腦之中,它們決定人類語言的性質(Chomsky 1972:102);語言的獲得與人的智力、語言環境無關(Chomsky 1972:79)。
Chomsky的理論假設與語言習得研究結合的經典體現是在一語習得研究中。兒童是如何習得語言?Chomsky認為要回答這個問題只需描寫普遍語法及其原則是怎樣與兒童的語言經歷相互作用而產生語言的(Chomsky 1986:3)。語言的獲得是一種潛意識的活動,即使沒有特意地去教授,兒童最終仍能成功掌握語言(Chomsky 1965:200-201)。“天賦論”的主要立證基礎是“刺激貧乏說”(poverty of stimulus),即在語言輸入不完美、缺乏反面證據的情況下,兒童作為抽象規則的使用者,亦能快、易、準地掌握母語。與Chomsky的觀點相同或相近的有Crain、Steedman、Thornton、Wexler等(Crain & Steedman 1985;Crain & Thornton 1998;Crain & Wexler 1999)。在Chomsky和Pinker(1984,1989)的思想基礎上,又出現了兩個重要假設即“可學性假設”(learnability hypothesis)和“連續性假設”(continuity hypothesis)。
Greenberg(1963)、Gass(1979)、Keenan和Comrie(1977)等的早期研究喚起了二語習得研究人員對普遍語法的興趣,而這主要體現在抽象的句法習得研究中。自20世紀80年代就開始涌現大量結合Chomsky的句法思想,特別是原則和參數理論,所做的習得成果,如Cook(1985)、Felix(1985)、Flynn(1987)、Liceras(1986)、Van Buren和Sharwood Smith(1985)、White(1990)。證實與證偽普遍語法的可及性是相關研究的重要著力點,也是產生顯著分歧的爭論點,例如Dulay和Burt(1974)、Ritchie(1978)、Krashen(1981)、Flynn(1987)和White(1990)的研究支持普遍語法在成人的二語習得過程中的作用;Bley-Vroman等(1988)證明了成人二語學習者具有某種形式、但不完整的普遍語法知識;Clahsen和Muysken(1986)、Schachter(1988)、Clahsen(1990)、Johnson和Newport(1989)的研究則反映出普遍語法對二語習得的影響不大。
基于社會功能語言學觀點,Halliday(2004/1975)認為,語言是一種社會語言符號,是聲音、形式、意義三者共同組成的一個多符號體系;語言習得是對語言功能的逐步獲得。Halliday(2004/1975:30)指出,“天賦論”是從成人語言出發,將兒童語言與成人語言對比得出結論,未充分重視兒童自己的語言系統。在建立形式與功能間的對應時,Halliday(2004/1975: 28-59)認為兒童對成人語言系統所表達的功能的獲得是一個漸進的過程。在初始階段只能以一個言語片段表達一種功能。就兒童語言與成人語言的關聯,在Halliday(2004/1975: 28-59)看來,一方面,兒童在最初階段使用的“語言”與成人的語言是沒有關聯的,兒童經歷了從自創語言到掌握并使用成人語言的過程;另一方面,在社會功能上,兒童的“語言”又與成人語言存在連續性,是一種功能意義上的連續性。概括起來說,語言習得在語言系統上是不連續的,而在語音和語義上是連續的。
功能語法對語言習得研究的推動力主要表現在二語習得的研究中,描述二語學習者的語言使用能力,揭示他們如何實現形式與功能間的映射。其次,理論探索與習得研究的結合也體現在系統觀與功能觀的精髓在教學方法中的運用與發揚,實現Halliday提出的具有特殊用途英語的教學,形成交際教學法、情景語言學等。這是功能語法對語言習得與語言教學最深刻和最典型的影響。
認知語法提出,語言不是一個自主的認知系統;語法是概念化的過程;語言知識產生于語言運用(Croft & Cruse 2004:1-3)。語言知識由語言表層形式的抽象而得,所有語法結構都是顯性的,不存在深層結構(Langacker 1987:46-47)。語言知識隨著語言使用者的經驗和使用而不斷增長。Tomasello是運用認知語法的視角研究兒童語言習得的領軍人物之一。Tomasello(2003:7)認為,以Chomsky的普遍語法為基礎來解釋兒童語言習得的過程是有問題的。語言知識不應該等同于一個形式語法的知識;即使兒童最后能進行抽象的語言歸納,但在語言發展的最初階段他們是根本不、或僅是在有些情況下才進行抽象的歸納。認知語言學家早期嘗試從“天賦論”的支撐論據來推倒它,如兒童語法與成人語法的差異(Tomasello 2000a; Cameron-Faulkner等 2003),生成語法對兒童語言創造力的過高估量(Pizzuto & Caselli 1992,1994; Burns & Soja 2000; Conwell & Demuth 2007)。同時,他們努力證明語言習得是基于語言運用的(Tomasello 2000a,2000b,2003);語言發展中使用的是人類共有的認知與社會認知過程(Tomasello 2000a,2000b; Dabrowska & Lieven 2005; Ramscar & Yarlett 2007),語言能力最終是一種文化能力(Tomasello 2000a; Ramscar & Yarlett 2007);構式(construction)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Tomasello 2000a,2000b,2003)。
在認知語法的框架下對二語習得的研究也逐步發展,有影響的研究課題主要有:一語與二語系統的關聯(Bybee 2008; Hudson 2008; O’Grady 2008)、輸入頻率對習得的影響(Bybee 2008)、構式對二語習得的積極作用(MacWhinney 2008)。
從語言習得來看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多種理論與假說,時而仿佛在看一個萬花筒。不過,深刻的思考、創新的研究,應該讓萬花筒變成顯微鏡。
1.語言與思維:在語言使用中,孰先孰后?
劉慶雙:語言一般落后于思維。沒有思維做基礎的語言,只是單純的符號。很多的時候是先有思想后有語言的表達,而且思想不成熟,就急于表達則語言一定是亂七八糟的。我個人總是語言跟不上思維,很多的時候基本能想明白,找到合適的措辭還需要花很長的時間,當然在這個過程中也有讓思維更加完整的處理過程。
范莉:在語言還未發生之前,兒童是會思考的,所以應是思維先于(人類)語言的發生。
張生祥:思維先行,語言是迫不得已的選擇,趕不上思維的速度,是思維的產品或衍生物。
甄鳳超:部分贊同劉慶雙老師的。對于范莉老師觀點,一旦習得語言,情況就不大一樣了。
范莉:兒童一旦習得語言,思維與語言應該具有相互促進性。
張生祥:為什么會討論語言與思維的關系呢?怎么不是語言和思考?
劉慶雙:思考主要是指思維的過程,思維的意思更寬一些吧?互相促進不等于語言與思維同步。在我看來,語言促進思維主要在于語言的整理作用:它可以幫助一個人理清頭腦中的關系,但無法彌補經驗、知識或邏輯上的不足。語言還有一個明顯的不足,就是很多人認為一個人能用語言能描述某個東西時就代表著自己理解了或明白了,但是,如果沒有具體的體驗、感受、操作,于那語言就是一個空殼。在科研上,常常看到有人講得條條是道,但具體操作中什么都弄不明白。
張生祥:思考是起點,思維是過程。要討論語言,必須先從思考開始,對世界進行一個全面或局部的了解,掌握情況后,再思維,用特定的或個性的方式剖析世界,尤其是文本世界。語言是世界文本的構成方式和物理表現形式。
余渭深:語言可以使經驗明晰化。語言可以激活涉身的模擬。人的經驗是模糊的,只有語言的介入,經驗才被anchored。并對周頻老師的問題“anchor這個詞是個隱喻,能否詳述其認知機制?”做出回答,被語言錨住的經驗可以隨時被提取,語言不等于世界,語言是錨,世界是帆。船是很大的。語言只是思維的部分,人的經驗很豐富,但只有部分經驗被語言錨入。
劉慶雙:但代替不了經驗。一個人經驗不足的話,語言更有害——使思維變成了一個沒有內容的符號系統。沒有經驗支撐起的邏輯是沒有意義的。
喬曉妹:語言不應該是思維的唯一方式。視覺思維一直是存在的,不少作家也都說過靈感來臨的時候,他們的思維往往依靠的不是語言,而是一幅幅mental image。
苗興偉:贊成語言不是思維的唯一方式或工具的觀點,人類在沒有語言的時候已經開始思維了。對緊急情況的本能反應是不是涉及思維?這種情況下也是不需要語言的。
劉慶雙:每個人的人腦里裝的東西總量不同,類型有別,組織結構也不同,雖然總的來說,通過語言是可以與其他人交流的,但是這種交流一定是無法完全達意的,還有太多無法用語言交流的東西。之所以能交流就是人社會化的作用,就是強制地協調人與人之間的可交流的基本前提,人們要遵守共同的語義、表達規則等等。如果一個人沒有社會化的過程,例如自閉癥,這些人有的思想可能非常發達,例如他們有很好的音樂或繪畫才能,但是他們無法與其他人交流。所以,人的社會化過程,是消除個性化思維的過程,讓本來有創造性或差異化的頭腦和語言與其他人有了共通之處,至少在某些方面讓人表面上看起來相同了。
2.語言與思維:在語言習得中,孰先孰后?
范莉:如果我們假設,在語言初始階段“思維先于語言”的話,現在把視線放到發展的維度,之后它們之間的關系又是怎樣的呢?
馮奇:語言和思維的發展幾乎是同步的。
吳建平:(討論在圖像中兩名兒童不使用語言進行有效的交流)這兩名兒童不使用語言,卻能進行較為復雜的思維,互相配合默契。兒童這種無語言就可以交流,發生在特定情境下。促使、推動語言發展的驅動力在于人類常常需要脫離情境的語言交流,也就是抽象的交流。例如,學校教育的知識傳授、會議發言交流、學術交流。思維確實不光受語言影響,更多地受經驗和社會文化影響。
范莉:在兒童語言習得過程中,語言初始階段,兒童的思維也是處于雛形狀態的。語言與思維的兩個幼苗一起成長。但是,二語習得中,學習者的認知能力是達到一定程度的,不是白板狀地進入語言發展。相對兒童語言習得,學習者習得二語時策略性更強,這是建立在一定認知基礎上的,而且也同時要求一定的認知資源。
張生祥:兒童獲取的是直觀的經驗,是局部的,還沒開始思考,等經驗積累好了,試錯到位了,就開始思考了,為什么會犯錯?等弄清楚錯的原因,就開始抽絲剝繭,進入思維過程里了。
杜世洪:記得Leslie的實驗觀察,她發現18個月大的兒童能夠完整地完成假裝游戲,如拿根香蕉當電話筒假裝打電話,但相比之下,這個年齡段的兒童語言表達不太完整。這說明,幼兒完成假裝游戲所需的思考比她的語言復雜得多。對Leslie的觀察,我們能找到反駁的實驗證據不?
劉慶雙:這代表兒童思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關聯能力。
馮奇:語言能力的發展和思維能力的發現速度因人而異。今天參加本科生答辯,語言能力和思維能力不是相同的。此觀點也得到劉慶雙老師的贊同。許多情況下思維能力受經驗影響。
劉慶雙:關于馮奇老師的觀點,我認為語言發展的速度驚人是因為思維已經為此做好了前提準備。喬氏所說的普遍語法,我認為是人的思維和邏輯的主要規則,不是語言的內容,如果硬把這些說成是語言的內容,只是思維在語言層面上的一種體現。喬氏硬把思維的規則說成是語法的,于是大家都認為語言就是思維。
喬曉妹:語言是人類的本能,不需要學習。這是Chomsky的觀點。
余渭深:語言只起經驗的定位作用,每次有詞語出現我們只提取與語境相關的經驗。而不是經驗的全部。我想語言不是人類的本質,可能是人的某種認知能力。這種能力不僅處理語言,可能還處理更多關于意義的問題。因為語言不等于意義,意義更宏大。
許德金:語言習得能力是先天的,與思維能力同步發展,不過個體上會有差異;社會和周邊環境會影響個體的后天語言習得能力及思維能力,結果可能是:不同的個體后天的語言習得能力與思維能力受社會環境的影響,可能在某一時段失衡或不平衡發展。(1)人的習得能力是先天的,天賦的,也是后期發展的基礎,很難說后期就會如語言學家那樣分層學習。當然,無論語言還是思維能力都要經歷一個后天發展的過程,也是可以培養的,這就是社會和群體的作用。我的意思是:兒童在習得時是無意識的,有父母遺傳的先天基因,因而他看似無意識的發音其實是有語言符號的意義的。語法也是人類后天規劃或描述出來的。(2)對苗興偉老師的問題“從功能語言學的角度很容易理解兒童是如何發現用語言來才做世界的”做出回答,認為后期發展到一段階段,開始認識這個世界時就可以有意識地學習了。
苗興偉:兒童經歷一個proto-language階段,這時的語言系統是聲音與意義的簡單對應關系,隨著智力和語言能力的發展,兒童才發展出三層級的語言系統,即意義和聲音之間有詞匯語法,意義是通過詞匯語法系統體現的,詞匯語法系統是通過音位系統體現的。我覺得不是所有的語法知識。首先是一種意識,然后才是發展的問題。如果意義和聲音對應,兒童能夠發出的聲音(包括其組合,就像狗的叫聲)是有限的,那么所表達的意義也是有限的。只有通過詞匯語法系統,才能表達出無限多的意義。
余渭深:對泛化的幫助,慢慢固定到特有幫助,這就像找到了錨,把船固定了。當然船上可以加樓層,涂新色。
馮奇:我的觀點是,語言的發展和思維的發展因人而異。有些人善于抽象思維,有些人善于具象思維。這樣的人在從業方面也就有了分化。走上學術道路的人傾向于思維的發展,而從事推銷的人則發展了語言能力。
劉慶雙:雙語者有兩種思維可能的基礎:一種是兩種思維相對獨立,另一種是兩種思維相互融合。理科生的頭腦大都是以邏輯和客觀世界為基礎的。關于范莉老師的問題即“思維在外語學習中發揮什么樣的作用呢?”,思維是為表層語言轉變為語義提供了基本框架。說到思維,我覺得語言中的“所指之類的詞語”,如果沒有經驗和思維做基礎,則根本無法描述我們自認為已經明白的這些東西。
喬曉妹:二語詞匯結構里有個著名的triangle模型認為雙語使用者能夠使用兩種語言,但是這兩種語言共用的是一個概念系統。
馮奇:sense和reference哪個更難確定?有時很難說。因為語境可以讓意義具體化,有時也可以語境賦義。
余渭深:本來想用錨來表示語言,船來表示經驗,但問題是經驗是不可見的,語言是可見的。所以比喻有問題。
范莉:請喬老師也談談詞匯學習中的“隱蔽啟動范式”,我們在外語詞匯學習的時候,最初是學sense,還是什么?
喬曉妹:我之所以提這個問題是因為它反映的是無意識加工,這個跟周老師前面提到的語言的加工、信息提取有關系,它比較有趣的是因為無意識加工的存在是否反映了思維之獨立于語言而存在?
馮奇:隱喻的習得是在sense基礎上發展起來的。經驗是第二個理據,基于對事物相似性的認識。但需要有語境和reference支持。
許德金:無意識加工的存在恰恰反映了思維無法獨立于語言而存在。隱喻的存在同樣應考慮人類先天的遺傳和基因情況。隱喻的習得也具有先天性和明顯的遺傳性。
周頻:當上升到語言層面時,就已經是有意識的思維了。但人類大量的思維是無意識的,這卻被我們忽略了。現在說的很多證據都來自內省、直覺,可靠性不夠。
吳建平:對劉慶雙老師的觀點表示贊同。這就像紅樓夢里,林妹妹與焦大沒有共同語言一樣。從小成長的環境不同,長大后自然不會有共同語言。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理解萬歲”的重要原因。
范莉:接著周老師的觀點發問:外語學習中,思維是有意識的,還是無意識的?或者,兩者都有?如果隱喻的實現是以范疇之間的關聯為前提的,是不是這種關聯是基于人類認知的共性呢?
吳建平:外語學習中的思維是有意識的。這與平時人的思維不一樣。之所以說外語學習中的思維是有意識的,原因在于這種思維無論開始是出自強迫或是興趣,學習者的思維是集中的,而且遵循著外語學習的規則,例如語法規則等。
劉慶雙:人的思想的成長,不完全是邏輯的過程。有太多的東西是無厘頭的。(1)對馮奇老師的觀點“基礎就是相似性”,表示不同的背景或頭腦對相似性的理解有很大的差異。或者說每個人對相似性的激活能力有明顯的不同。下意識學得的東西,就會下意識地運用,有意識地學習后可能更不好用。這是心理學上說的。有的腦袋就是機械得要命——“嚴謹”而“邏輯”。大腦的可塑性是智力的一部分。總體來說,大腦機械的人,走路的姿勢也僵硬。另外他的語音語調也都是硬邦邦的。這種關聯性應該是因為大腦的很多處理能力是可通用到所有方面的。思維就是一種行為,而且思維的這種行為,可以投射到可見的行為上。(2)對范莉老師的問題即“在思維發展在外語習得中的狀態:靜止、發展?”做出回答,心理學家認為,運動,特別是精細運動,可促進思維。在外語學習中,如果一個人的思維可塑性強,外語就可能有深遠的發展。
馮奇:我教兒子的第一個詞是燈,后來兒子把deng的所指泛化了,把星星也理解為燈。說明兒童在語言習得中有推理的過程。基礎就是相似性。思維外化表達為行為方式。
周頻:外語學習也需要建立大腦的神經突觸聯結。但年齡越大,大腦的可塑性就不如小的時候,而且有關鍵期的問題。再說語言學習不僅有詞匯語法,還有語用能力等,這是一個系統,需要在真實的語境下無意識地習得。
喬曉妹:其實我說的無意識不是說學習是無意識的,而是語言加工是否能做到無意識,這是鑒別語言能力的一個可能指標。其實語言的無意識加工反映的是語言使用的一種自動化程度(automaticity),并不能說與思維分離。
范莉:對馮奇老師的觀點表示贊同,認為先習得cover term,然后逐步在習得過程中,就語義及語法在精細度(delicacy)上逐漸加深。
3.語言與思維:在外語教學中,孰重孰輕?
馮奇:我們有必要把語言能力的發展和思維能力的發展區分開來是因為這兩種能力的發展是不均勻的。否則我們評價學生演講和作文為什么提出語言和邏輯兩套評價方案?
余渭深:從四、六級作文看,低分作文,用大量漢語思維的表達,但沒有英語語言,只有詞匯;中等作文英語對了套話,沒有了思維,抑制了思維;高分作文有了思維和語言。不知道這是發展過程,還是天生決定的。
許德金:語言習得的同時,思維能力肯定也是在發展的。思維的分類同樣是為研究的目的,為對應而對應,與思維的發展實際會有很大差距。
劉慶雙:我教過很多不同年齡段的人的英語,有的人早期學得非常好,后來不行了,原因就是思維不可塑。對思維類型進行分類非常有好處,有利于第二語言學習的思維,還上升不到很多不同類型的智商上來,只能是某些方面,例如基本概念和邏輯。
范莉:但為什么學外語的學生越來越顯得“笨”呢?
劉慶雙:有些人的英語學得很好,一定是有思維基礎的,但是只能學好外語,還真的做不了別的事情。高考能達650 分以上沒幾個學外語專業的。關于越學越笨我總結一下:我的觀點是:(1)總體來說,英語人才的能力與高考的分數相適合,既沒變笨,也沒變聰明;(2)外語人才的笨與不笨,與他的學習方式,相關學科學習或跨學科學習和自主提升有關;(3)只會學外語而且不會學其他學科的人,在哪個學科都學不好。
許德金:這個觀點不敢茍同:人后來如果專注于語言習得而忽視了其他,其他的思維當然就退化了。同理,如果個體過于關注一個方面,其他的方面自然會受影響。
吳建平:學外語的學生為什么會顯得笨?主要原因在于,純語言專業的學生,其學習范圍和知識面窄,而且基本激發不了創造力。天長日久,創造力愈發沒有了。缺乏激發和培養創造力的思維!
余渭深:因為目前外語教學中思維缺席。沒有發展思維所致。外語教學太注重技能訓練了,本來好端端的一篇文章被肢解成碎片了。美其名曰訓練技能。講了技能,但忘了文章的意義。
周頻:按照Howard Gardner多元智能理論,聰不聰明沒有統一標準,每個人的智能優勢不同罷了。
劉慶雙:學習對象和內容只是語言的話,就不會有辦法批思想。批判就得有靶子。外語課上沒有內容,用什么當靶子?討論一定得有話題和可討論的點,這就是靶子。我認為外語課上的批判太簡單了,遠遠低于學生智商的水平,他們覺得無趣兒,加上語言能力不足以表達自己,這樣的活動幾乎等于無任何意義。學生能讀懂,再用英語來表達自己嚴謹或清晰的觀點,這在現在的學生課堂上是不可能的。
尤澤順:關鍵是師生都不注重內容,只注意語言形式。語言形式好教好學,內容不好把握,不好分析。學生對知識性的東西沒有正確認識,他們只關心今天認識了幾個單詞。
甄鳳超:我們學習的外語文章經過精心選擇,文章中有觀點,有思想。對同一個話題,我們選擇多個角度、多個論點的文章。再者,我不認為詞匯教學就是低級的,它同樣可以訓練我們學生的思維。
祝平:我覺得外語課(即便是語言課)也可以有內容。關鍵是關注點是什么,怎么上?比如綜合英語和高級英語(以前的精讀)都有內容可以挖掘的,不能只作為學習語言的材料。
余渭深:由于學生外語能力低,特別是表達能力低,所以在外語教學中壓低內容只講一些早已知道的百科知識,壓抑了學生的思維認知能力,美其名曰訓練語言,結果沒了思維,這就是現狀。
范莉:各位專家都認可:語言教學必須要注重學生的思維培養。但是,具體在語言教學中,如何執行?而且,如老師們所提到的,學習成果的評估方式顯然是個決定因素。
吳詩玉:用圖片進行詞匯教學,和用詞典教學,效果差別顯著。
甄鳳超:我們應該進行有效教學。能否掌握一門世界通用語言就關乎生存。
李葆重:詞匯、語法教學都可以做到有趣、有內容!
余渭深:思維是跟生存相關的,沒有生存攸關的思維只是訓練。外語課堂的討論很多都很幼稚,不是成年人該討論的東西,所以很難訓練思維。外語學習的動機很重要,是個人生存的方式。
毛浩然:我們的討論基礎是否應該更接近現實一點,其實至少我身邊的老師們上課大多數不是這么上的,不會上成沒有內容或低水平無信息的。我也聽過幾百節的課,似乎前面提及的現狀離我有點遠,讓我不寒而栗,感覺生活除了眼前的茍且,還有遠方的茍且和茍且,中國的外語教育完全毀于一旦了。我上聽力課,比如TED學術演講,每次我都會讓大一大二的學生回答四個問題:(1) What is the research question?(2) What are the conclusions?(3) How did he/she reach the conclusions?(4) Is there any unconvincing evidence in his/her presentation?
現在我的大二學生回答出來的答案,已經不會遜于研一學生了。
祝平:無論是綜合英語和高級英語,我都是做篇章分析的。主題是什么,怎么表達主題的,各部分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如何,怎樣為主體表達服務。你自己的觀點是什么?我想這些都可以算作對critical thinking的培養。對于簡單幼稚化的內容我就讓學生挑課文的毛病,準許他們胡亂說。
廖正剛:在討論中,可以促進文本的理解。
范莉:由于語言問題,我們選入的材料有時在思想內容上比較簡單,所以在觸發學生思考時很難做到 i+1的功效。要培養篇章能力、邏輯能力、分析能力,教材則是關鍵。
許德金:批判性思維能力與語言訓練我覺得是風馬牛不相及,可以談論如何在語言習得中或語言能力培養中訓練批判性思維能力的問題。語言訓練是語言習得的一部分。批判性思維無處不在:數學、語文、物理等所有學科都有批判性思維的能力培養。
劉慶雙:批判性思維,一定要引起學生的思考。我看我們的英語課堂遠遠沒有做到判斷思維,只是做做樣子。對范莉老師的問題 “例如詞匯教學,聽力教學,如何促發學生去思考”,做出回應:(1)要給學生一些辯論的口語與交流能力;(2)要有基本的邏輯語言能力;(3)要對問題有分析,要提出自己的觀點。老師要找到學生關注的話題,要有課下的準備。用我的話說:唱歌跑調的老師,還想教出好學生,不太容易。
范莉:批判性思維是可單獨操練,但精力與時間的比重如何分配?例如,外語專業的學生,怎么辦?教師是舵手,理念很重要。教材是風帆,質量很重要。
許德金:批判性思維能力可通過單獨訓練加以提高,在此基礎之上,配以豐富的語言可以使思想充分展示。我的感受,作為一名大學老師,自己對批判思維模式的概念有時會模糊,尤其是課本材料不合適時,不知道如何鍛煉他們的批判性思維。所以鍛煉好學生的批判性思維的前提是老師要有一個好的批判性思維,這樣才能在授課時引導學生,贊同大家的說法。但是誰來關注老師批判思維能力呢?語言習得中培養批判性思維能力關鍵是要有合適的材料,好的老師的引導,好的議題。許多課程,包括各位老師說的綜合英語、聽力等幾乎所有的課程都可以至少部分培養學生的批判性思維能力。學生愿不愿意也在于老師引導。
祝平:我們經常抱怨教材沒有內容,不好進行批判性思維訓練。其實,任何一本教材都難以滿足所有人。我個人覺得,教材內容的確很重要,但誰上、怎么上才是最關鍵的。這涉及教師本人的teaching beliefs,也進而影響到課堂設計。
余渭深:教師能讀出作者的思維很重要。外語教學中重語言輕思維,也是這種實用主義的結果。
周頻:訓練批判性思維的教學是蘇格拉底式的,膜拜老師的教學方式是孔子式的。兩種完全不同的教學傳統所致。孔子很少讓學生去質疑他,他在上面傳道授業,下面的學生聽他講,回去好好復習領會。由此可見,古希臘的蘇格拉底是因追求和堅持真理而被司法錯誤審判獻出了自己的生命,是一個名副其實的殉道者,其追求真理的過程與方式是通過自由、開放、平等的對話過程來體現,從來不以獨斷語錄的方式呈現真理,這些開放的思想體系,供后人研究與借鑒之用。使得2000多年來,不斷讓后人超越前人。而孔子是獨斷話語,培育的是專斷思維與專制話語霸權者。有人說,蘇格拉底是永無終止的追問,孔子則是提供結論卻沒有思辨的過程。前者激發學生,后者固化學生。還有人說,蘇格拉底只是學生們通向更高思維歷程的“助產士”,其身后有柏拉圖(繼而有亞里士多德)青出于藍;而孔子的后學們卻永遠都活在孔“至圣”的籠罩之下。后人只是在孔子的話里尋章摘句,找出那么一鱗半爪就說他鼓勵批判,其實要看他整個教育理念是否是成系統地提倡批判性思維,否則只是斷章取義。
毛浩然:我個人覺得,討論雖然是發散性的,不過如果既能把脈,還能開藥,而且最終還能治病,是不是會更好一些。都說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是科研最最基礎的三部曲,可遺憾的是,就是這么基礎的邏輯,個別學者比學生還差得遠。我們要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但不要見到什么人都踩上去。不然可能東施效顰,邯鄲學步。提出問題沒到位,解決問題又不堪,就玩完了。我覺得沒必要把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這個基礎邏輯內部對立起來,能做的,先做到。不能做的,其實高大上的,也不排斥,關鍵是要真的能提出像蘇格拉底等高人那樣的有價值甚至能推動人類思維的問題。
4.語言與思維:在隱喻認知中,如何共進?(從隱喻能力研究看隱喻思維與語言習得的關系)
王立非:首先回顧一下應用認知語言學的發展:認知語言學研究成果引起了應用語言學領域學者的關注,原因之一在于認知語言學以認知科學和認知心理學為基礎,從人類認知的角度研究語言,試圖揭示人類在理解與交際中的相關機制。認知語言學強調認知在語言理解和現實之間的中介作用,強調主體在認知過程中的能動作用。越來越多的研究者開始關注如何將認知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應用于第二語言習得研究或外語教育,“應用認知語言學”這門新興學科(Boers & Lindstromberg 2006;Pütz 2007)隨之出現。
在應用認知語言學領域,多數研究都圍繞隱喻展開,隱喻成為認知語言學和第二語言習得兩門學科的接口。隱喻可以說是實現“現實-認知-語言”三者之間關系的重要手段和方式,是人們對現實世界進行范疇化、概念化以及思維過程中的一種工具和結果(王寅 2007:406)。隱喻作為認知語言學、二語習得、心理語言學等多種理論相互作用的窗口,是人類認識自我、語言和世界之間關系的平臺。學習者隱喻能力研究已成為應用認知語言學研究的焦點之一。隱喻能力是通過隱喻思維過程反映出來的跨域認識事物的能力,隱喻思維具有體驗性。
我們認為隱喻能力的本質是“認知主體在不同認知對象之間建立語義關聯的能力”(袁鳳識等 2012),語義關聯指的是隱喻意義。從能否建立語義關聯的角度來說,隱喻能力是一種技能;從語義關聯的內容來說,隱喻意義是一種思想。這種技能是通過隱喻思維過程表現出來,這種思想是隱喻思維的結果。
隱喻與認知、思維、語義密切聯系。“認知的最簡單的定義是知識的習得和使用,它是一個內在的心理過程,這涉及諸如感知覺、型式識別、視覺表象、注意、記憶、知識結構、語言、思維、決策、解決問題等等心理表征在內心里的操作。”(桂詩春 1991) 該概念強調了認知的心理過程,而這種過程與語義密切聯系。“所謂的認知包含兩個過程,一個是思維過程,即人們能動地認識世界;一個是世界通過大腦對我們思維的反映。”(胡壯麟 1997) “認知是客體通過主觀經驗和社會實踐作用于人腦而形成的能動反映,而語義就是認知結果通過語言單位在人腦的反映,被語言群體公認后而成為語義事實都是人腦的反映……人除了直接反映客觀事物的外部特征的直接反映外,更有通過語言和思維反映事物內在的本質和規律的概括反映。”(王德春 2009) 該概念強調了語義的來源在于人腦通過語言對認知結果的反映。人類依靠自身在與周圍世界的互動過程中所形成的互動體驗,慢慢掌握了周圍物質世界的基本特點和規律,然后通過大腦各種功能實現了對這些特點和規律的思維表征,進而通過語言加深對世界的認知。
袁鳳識等(2012)、許保芳等(2014)、袁鳳識(2014)等的相關研究中,在對語言、文化、隱喻例句的結構、成人被試等因素進行一定的控制之后,發現被試在五項調查任務所表現出來的差異性與語言水平并無關聯關系。這說明隱喻能力與語言能力之間并不是一直呈線性增長的邏輯關系,擁有語言能力并不一定意味著擁有隱喻能力。我們重視語言能力的同時,還應重視隱喻能力,隱喻能力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從語言能力中剝離出來,剝離出來的隱喻能力的差異性主要由認知因素和體驗差異性造成的。
認知主體要依賴于自身認知體驗來建構隱喻語義關聯,而認知體驗的核心內容則是普通概念化能力(general conceptualizing capacity)。Johnson(1996)對Lakoff的概念隱喻觀進行歸納,指出Lakoff強調傳統概念隱喻存在于我們的日常語言中,是概念系統的一部分,隱喻通過日常語言表達得以實現,但它從根本上說是一個概念過程(conceptual process)。Lakoff假設認為雖然概念系統可能具有跨語言和跨文化的差異性,但人們的普通概念化能力具有普遍性。既然隱喻是植根于兩種文化共有的人類經驗之中,那么二語學習者就能運用其普通概念化能力來建構隱喻意義。這種普通概念化能力可能就是Cummins(1984)所說的相互依賴于一語和二語的“共有能力”(common underlying proficiency)的一部分。這種普通概念化能力的含義就是人們根據自身體驗對周圍萬物進行認知并最終形成概念的能力。概念反映事物的一般和本質特征,概念是體驗的一部分。Johnson(1996)認為如果這種概念化能力在隱喻理解中起著根本作用且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們就不能期望二語水平會對二語隱喻解釋概念水平或復雜性水平有著非常重要的限制作用。反過來說,如果語言所體現出來的概念系統不具有普遍性,那么我們就可能期望語言或文化背景會對隱喻解釋的內容產生影響。
我們認為,人們在與周圍世界的互動過程中,逐步形成了這種普通概念化能力,這種能力的實質就是人們對事物的認知具有一定共性,個體體驗在隱喻思維過程中起著關鍵作用。身體的認知體驗行動不僅形成了語言與思維的復雜系統,而且其主觀感覺經驗為思維和語言提供了主要基礎(程珊、胡開寶 2008)。
不同文化和語言背景的人們由于有著基本相同的生活體驗,所以擁有相同的概念化能力,從而能夠理解和學會彼此的語言。在隱喻理解和產出過程中,認知主體根據自身體驗,充分發揮這種普通概念化能力,依靠自身在對事物概念化過程中形成的對事物基本屬性的認識,充分發揮聯想,在不同語義范疇的認知對象之間構建起一定語義關聯,最終實現隱喻意義的解讀或根據需要構建新的語義聯系。這種普通概念化能力決定了不同文化人們擁有基本相同的隱喻能力。因此袁鳳識等(2012)研究結果支持Johnson(1996)的觀點,二語水平不會對隱喻解釋的概念水平或復雜性水平起著非常重要的限制性作用。
不同語言水平、不同文化的人們由于對我們周圍世界認識的共同性決定他們在概念范疇方面認知共性。施光和辛斌(2007)指出,人們的思維在感性、認知、社會和語言心理方面具有廣泛的共同之處,這是因為客觀世界的相似性決定了感性認識的共同性,因而導致思維(即概念構成)的共同性;換言之,大自然的結構特點制約著人的基本思維方式,使其在基本概念范疇方面有共同之處。人類具有大致相同的認知體系,它適合各個時代的不同民族和不同語言,因為從整體上說,人類面對相同的客觀世界;具有相同的思維工具——大腦和各種感知器官,生理機制是相同的;具有相同的認知能力;同樣能夠使用語言(張煉強 2007)。因此,不同文化的人們對一般詞語所指的客觀事物的屬性有相同的聯想,所建立的語義聯系也基本相同。
人與周圍世界的互動體驗在隱喻理解中起著關鍵作用,因為互動體驗是表象、概念、語言、隱喻產生的源泉。隱喻能力的構建要依賴普通概念化能力,這種能力的構建過程可能具有如下規律:人類首先通過身體感覺感知事物的個別屬性,各種個體屬性作為整體反映在大腦之中形成知覺。經過感知后的客觀事物屬性或情景在大腦中再現的完整形象就是表象或意象。主體在表象的基礎上通過綜合、歸納、分析、聯想等方式進行的活動就是形象思維。形象思維過程中由于語言沒有介入,所以語義尚未真正產生。在形象思維的基礎上,人能夠將自己與外界互動體驗過程中形成的常規性樣式進行一定的圖式化,對表象或意象進行概括與抽象,形成一定意象圖式。在意象圖式基礎上進一步形成認知模型和范疇,從而進一步形成概念,并通過語言固定下來。“當人在大腦中用語言把表象概念化,用詞語從眾多形象中概括、抽象出一類事物共同的本質特征時,人就有了理性認知,有了邏輯思維,就擺脫具體經驗。上升到理性認識。這時,詞語所概括的意義經過約定俗成、社會公認,就成為使用語言集體的全民財富,客觀地存在于社會,存在于群體思維之中。”(王德春 2009)這個過程正反映人類普通概念化能力的形成過程。
語言產生后進一步增強了人類的認知能力,人類利用語言進一步感知世界、積累知識和交流思想。各種感知和經驗本身不能直接幫助人們實現對事物的理性認識。人類能夠利用大腦的功能,在概念和表象的基礎上進行思維,進一步實現對客觀事物和現象的認知。“思維是人在語言的基礎上產生的理性認知及其過程,是從經驗抽象出來的對客觀事物的間接的、概括的反映,是單憑感覺和經驗無法得到的對客體的本質和發展規律的理性認識。”(王德春2009)隱喻思維與聯想也密切聯系,隱喻思維能夠在表象或概念的基礎上通過一個事物能夠想到另一個事物,是一種高級的認知活動。由于新事物層出不窮,語言中的概念有限,人類就必須借助已知的概念來理解和表征未知領域,這樣就通過隱喻思維、聯想和概念隱喻化,實現各種新創意義的表征,并主要通過語言隱喻表達出來,因此隱喻的創新是隱喻思維的結晶。通過隱喻思維,我們實現了加深了對概念所代表的客體的各種屬性的認識,從而在大腦中建立各種事物之間聯系的網絡。
Fauconnier和Turner(1998)的概念整合理論正是基于對新創意義產生原因的思考而誕生的理論。創新隱喻的產生離不開人類原有的生活體驗和對一般概念的理解,否則就達不到交際目的。因此,我們在創造隱喻用法時,一般需要考慮事物或概念的一般突顯屬性特征,從而易于被接受和推廣。在我們遇到一個創新隱喻時,我們在表象和概念基礎上對其進行隱喻思維,反思表象所代表事物的一般突顯屬性或概念的含義,利用普通概念化能力,在源域和目標域之間建立相應的語義關聯,從而理解隱喻意義。人類認知主體這種在不同認知對象之間建構起一定的隱喻意義的能力就是隱喻能力。因此,隱喻意義來源于我們與周圍世界的互動體驗,我們也需要依賴這種互動體驗來理解和使用隱喻,普通概念化能力在中間起著橋梁作用。
隱喻能力與語言能力之間并不是一直呈現線性增長的邏輯關系,在對語言能力的要求達到一定的閾值之后,認知主體更主要依賴認知體驗來理解和產出隱喻。我們認為,由于不同語言水平的人們擁有基本相同的認知體驗和普通概念化能力,因此其隱喻能力具有共性。另外,隱喻能力和語言能力對認知能力的依賴程度并不相同。隱喻能力主要依賴認知體驗,而對于語言能力則需要多種認知能力協作完成。
石毓智(2007)對此進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語言能力合成說”。該假說認為,人類認知是一個層級系統,語言能力不是一個獨立模塊,也不是處于認知系統最基層,語言能力既不是天生的,也不是獨立于其他認知能力,是組成其他認知能力的基礎,它主要由以下七種更基本的認知能力協同合作的結果:(l)符號表征能力;(2)對量的認知能力;(3)概括、分類能力;(4)記憶、預見能力;(5)聯想、推理能力;(6)聲音、形狀的辨別能力;(7)空間、時間的辨認能力。由此可見,語言能力所依賴的認知能力類型與隱喻能力所依賴的認知類型有著較大的差異性,從而可能影響了隱喻能力與語言能力的關系。
總之,第二語言習得中最大的困難之一可能在于母語與二語在概念上的差異性,二語學習者要充分利用概念化能力實現對二語的概念流利性,特別是要實現如母語中的概念一樣流利,才能從根本上提高二語習得效果和二語使用能力。
參與微論壇討論的專家學者(以姓氏筆畫為序)
王立非,博士(后),對外經貿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應用語言學、語料庫語言學、商務英語。
尤澤順,博士(后),福建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政治話語分析、跨文化交際、語言與文化。
毛浩然,博士,華僑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話語修辭和二語習得。
馮奇,博士,上海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應用語言學、語言對比與翻譯。
喬曉妹,博士,上海財經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詞匯認知與識別、詞匯習得、句子加工、第二語言加工和英語教學法。劉慶雙,醫學博士、英語碩士,軍需大學英語教授(退休)。主要研究方向為認知語言學、計算語言學、語言與人工智能。
許德金,博士,對外經貿大學英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英美文學文化、文化資本與跨文化。
杜世洪,博士,西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哲學。
李葆重,人民教育出版社編輯。
吳詩玉,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二語習得。
吳建平,博士,廈門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雙語詞典與翻譯研究、語義與語用研究、語料庫研究。
余渭深,重慶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語言學、應用語言學、外語教學與測試。
張生祥,博士,浙江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跨文化交際、翻譯傳播學理論。
苗興偉,博士,北京師范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功能語言學、語用學、語篇分析、文體學和語言教學研究。
周頻,博士(后),上海海事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認知神經語言學、語言哲學、語言科學研究方法論。
祝平,博士,蘇州科技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20世紀及當代英美文學文化、文學翻譯、英語課程與教學論。
甄鳳超〗,博士,上海交通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語料庫語言學、學習者語言研究。
廖正剛,博士,吉林大學公共外語教育學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認知語言學和語義學。
“引言”部分)
Bley-Vroman,R.W.,S.Felix & G.L.Ioup.1988.The accessibility of universal grammar in adult language learning [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4):1-32.
Burns,T.& N.Soja.2000.Children’s acquisition of NP-type nouns: Evidence from semantic constraints on productivity [J].Language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15:45-85.
Bybee,J.2008.Usage-based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In P.Robinson & N.C.Ellis (eds.).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New York/London:Routledge.216-236.
Cameron-Faulkner,T.,E.Lieven & M.Tomasello.2003.A construction-based analysis of child directed speech [J].Cognitive Science 27:843-873.
Chomsky,N.1957.Syntactic Structures [M].The Hague:Mouton.
Chomsky,N.1965.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Cambridge,Mass:MIT Press.
Chomsky,N.1972.Language and Mind (enlarged edn.) [M].New York: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Chomsky,N.1975.Reflections on Language [M].New York:Pantheon Books.
Chomsky,N.1981.Lectures on Government and Binding [M].Dordrecht:Foris.
Chomsky,N.1986.Knowledge of Language:Its Nature,Origin,and Use [M].New York:Praeger.
Chomsky,N.1995.The Minimalist Program [M].Massachusetts:The MIT Press.
Chomsky,N.2000.The Architecture of Language (edited by N.Mukherji,B.N.Patnaik & R.K.Agnihotri) [M].New 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N.2002.On Nature and Language (edited by A.Belletti & L.Rizzi.)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homsky,N.2004.The Generative Enterprise Revisited [M].Berlin:Mouton de Gruyter.
Clahsen,H.& P.Muysken.1986.The availability of universal grammar to adult and child learners:A study of the acquisition of German word order [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2):98-119.
Clahsen,H.1990.The comparative study of first and second language development [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135-153.Conwell,E.& K.Demuth.2007.Early syntactic productivity:Evidence from dative shift [J].Cognition 103:163-179.
Cook,V.J.1985.Chomsky’s universal grammar 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J].Applied Linguistics (6):2-18.
Crain,S.& K.Wexler.1999.Methodology in the stud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A modular approach [A].In W.C.Ritchie & T.K.Bhatia (eds.).Handbook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C].San Diego:Academic Press.
Crain,S.& M.Steedman.1985.On not being led up the garden path:The use of context by the psychological parser [A].In D.Dowty,L.Karttunen & A.Zwicky (eds.).Natural Language Parsing:Psychological,Computational and Theoretical Perspectives [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320-358.
Crain,S.& R.Thornton.1998.Investigations in Universal Grammar:A Guide to Research on the Acquisition of Syntax and Semantics [M].Cambridge:MIT Press.
Croft,W.& D.A.Cruse.2004.Cognitive Linguistics [M].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abrowska,E.& E.Lieven.2005.Towards a lexically specific grammar of children’s question constructions [J].Cognitive Linguistics 16:437-474.
Dulay,H.& M.Burt.1974.Natural sequences in chil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J].Language Learning 24:37-53.
Felix,S.1985.More evidence on competing cognitive systems [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47-72.
Flynn,S.1987.A Parameter-Setting Model of L2 Acquisition:Experimental Studies in Anaphora [M].Dordrecht:Reidel.
Gass,S.1979.Language transfer and universal grammatical relations [J].Language Learning 29:327-344.
Greenberg,J.1963.Some universals of grammar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the order of meaningful elements [A].In J.Greenberg (ed.).Universals of Language [C].Cambridge:MIT Press.73-113.
Halliday,M.A.K.2004/1975.Learning how to mean [A].In J.Webster (ed.).The Language of Early Childhood [C].London: Continuum.28-59.
Hudson,R.2008.Word Grammar,Cognitive Linguistics,and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 [A].In P.Robinson & N.C.Ellis (eds.).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New York/London:Routledge.89-113.
Johnson,L.& E.Newport.1989.Critical period effect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The influence of maturational state on the acquisition of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J].Cognitive Psychology 21:60-99.Keenan,E.& B.Comrie.1977.Noun phrase accessibility and universal grammar [J].Linguistic Inquiry (8):63-99.
Krashen,S.1981.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Oxford:Pergamon Press.
Langacker,R.W.1987.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1: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opold,W.1939/1949.Speech Development of a Bilingual Child [M].Evanst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Liceras,J.1986.Linguistic Theory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Tubingen:Gunter Narr Verlag.
MacWhinney,B.2008.A unified model [A].In P.Robinson & N.C.Ellis (eds.).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New York/London:Routledge.341-371.
O’Grady,W.2008.Language without grammar [A].In P.Robinson & N.C.Ellis (eds.).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C].New York/London:Routledge.139-167.Pinker,S.1984.Language Learnability and Language Development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Pinker,S.1989.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M].Cambridge:MIT Press.Pizzuto,E.& C.Caselli.1992.The acquisition of Italian morphology [J].Journal of Child Language 19:491-557.
Pizzuto,E.& C.Caselli.1994.The acquisition of Italian verb morphology in a cross-linguistic perspective [A].In Y.Levy (ed.).Other Children,Other Languages [C].Hillsdale:Erlbaum.137-188.
Ramscar,M.& D.Yarlett.2007.Linguistic Self-correction in the absence of feedback:A new approach to the logical problem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J].Cognitive Science 31:927-960.
Ritchie,W.1978.The right roof constraint in an adult-acquired language [A].In W.Ritchie (ed.).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Issues and Implications [C].New York:Academic Press.33-63.
Ronjat,J.1913.Le developpement du langage observe chez un enfan bilingue [M].Paris:Librarie ancienne H.Champion.
Schachter,J.1988.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its relationship to Universal Grammar [J].Applied Linguistics (9):219-235.
Tomasello,M.2000a.Do young children have adult syntactic competence? [J].Cognition 74:209-253.
Tomasello,M.2000b.The item-based nature of children’s early syntactic development [J].Trends in Cognitive Science (4):156-163.
Tomasello,M.2003.Constructing a Language.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Van Buren,P.& M.Sharwood Smith.1985.The acquisition of prepositions stranding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and parametric variation [J].Second Language Research (1):18-46.
White,L.1990.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universal grammar [J].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12):121-133.
參考文獻(第4部分)
Boers,F.& S.Lindstromberg.2006.Cognitive linguistics applications in second language instruction: rationale,proposals,and evaluation [A].In G.Kristiansen,M.Achard,R.Dirven & F.J.Ruiz de Mendoza Ibánez (eds.).Cognitive Linguistics: Current Applications and Future Perspectives [C].Berlin/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Cummins,J.1984.Bilingualism and Special education: Issues in Assessment and Pedagogy [M].San Diego: College-Hill Press.
Fauconnier,G.& M.Turner.1998.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J].Cognitive Science 22(2): 133-187.
Johnson,J.M.1996.Metaphor interpretations by second language learners: Children and adults [J].Canadian Modern Language Review 53:219-41.
Pütz,M.2007.Cognitive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A].In V.Evans & M.Green (eds.).Cognitive Linguistics: An Introduction [C].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139-1159.
程珊、胡開寶.2008.心智與語言體驗性研究的新發展——《體驗與認知科學》評析[J].外語教學與研究(6):470-472.
桂詩春.1991.認知和語言[J].外語教學與研究(3):3-9.胡壯麟.1997.語言· 認知 ·隱喻[J].現代外語(4):50-57.
施光、辛斌.2007.語言· 思維 ·認知——再論沃爾夫假說[J].四川外語學院學報(1):102-106.
石毓智.2007.語言能力合成說的認知心理學證據[J].語言研究(3):59-68。
王德春.2009.論語義與認知[J].外語電化教學(3):3-7.
王寅.2007.認知語言學[M].上海: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
許保芳、于巧麗、袁鳳識.2014.隱喻能力與語言能力關系的理據分析[J].外語研究(1):47-50.
袁鳳識.2014.英語專業大學生概念隱喻歸納能力研究[J].外語教學(5):35-39.
袁鳳識、許保芳、王立非.2012.再論隱喻能力的定義[J].外語教學(5):1-7.
張煉強.2007.語言和言語活動的認知思維理據[J].首都師范大學學報(2):99-114.
(責任編輯管新潮)
范莉,香港中文大學博士后、北京語言大學博士,北京林業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形式語言學、語言習得。電子郵箱:fansong_ cn@yaho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