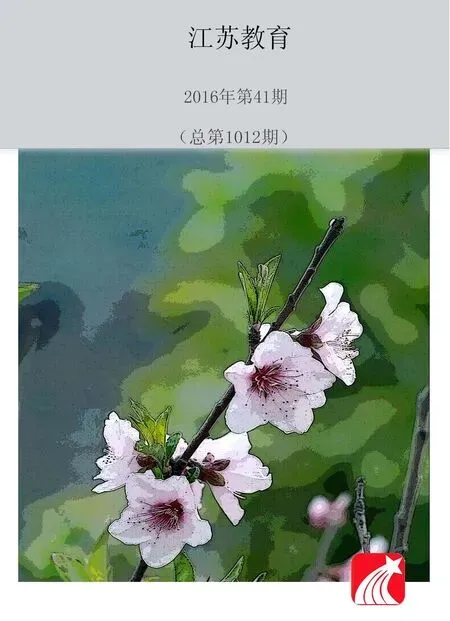順應“童性”:尋繹習作教學的幸福路徑
陳嬿竹
順應“童性”:尋繹習作教學的幸福路徑
陳嬿竹
寫作是兒童生命的一種存在方式。習作教學應基于兒童對“體驗”“自由”“開放”的習作的向往,順“性”而教,通過“有意思的場景體驗”“有意識的自由表達”“有意義的開放評價”,引導兒童在前期運作、中期創(chuàng)作、后期制作三個階段中逐步建立習作的“自我”“自信”“自尊”,從而穩(wěn)步提升習作的幸福感。
習作;童性;幸福感
習作是孕育童年幸福感的絕佳“母體”,提升兒童習作的幸福感應是每一位語文教育工作者的道德堅守和行為自覺。教師應“平視”兒童,用心傾聽他們發(fā)自內(nèi)心的“童聲”,順其“天性”,匠心獨運地引導其主動投入習作實踐,逐步建立“自我”“自信”“自尊”,穩(wěn)步提升習作的幸福感,在生命的綻放中涵養(yǎng)母語情懷,豐盈精神世界。
一、基于“有意思的場景體驗”,引導兒童內(nèi)化行知,于前期運作中發(fā)覺“有我”的語用情感
1.激發(fā)“鏡頭語言”,用本真的感性體驗為習作儲蓄素材因子。
兒童每天經(jīng)歷的生活場景充滿著變數(shù),這些自然演變的生活場景本身就是寫作的“富礦”,教師應啟發(fā)學生從中捕捉屬于自己的“鏡頭語言”,用“隨記”的形式及時“留影”,使之成為習作中最精彩的“特寫”。
一次大風天氣下的跑操使學生深有感觸,為之談論不休。筆者及時利用放學前的十分鐘,讓學生記錄下剛才的“鏡頭語言”,內(nèi)容盡管有些零散,但很精彩:“伴隨著節(jié)奏感十足的哨聲,大伙兒在風中一片凌亂!”“我們的隊伍被瞬間經(jīng)過的一陣狂風沖散了,大家三五成群,相互攙扶,就像是一批剛過完草地的小紅軍。”……由于這些應運而生的現(xiàn)實“鏡頭”是童眼所見、童耳所聞、童心所想的原創(chuàng)素材,所以,它們源源不斷地奔騰而來,待其聚沙成塔之后,便會以噴薄之勢驅(qū)動兒童一吐為快,從而獲取最初的習作樂趣,這正是兒童習作表情達意最主要的動力。
2.掘發(fā)“經(jīng)典語言”,用美妙的知性體驗為習作培育文學因子。
兒童時常被表達時的詞不達意所困擾,其原因在于語言內(nèi)存的匱乏,這就需要他們從大量有益的閱讀中獲取知識,其中,書面的閱讀尤其重要。面對海量的閱讀文本,教師要引導兒童學會選擇、學會閱讀、學會提取、學會運用。
蘇教版三下《廬山的云霧》一文遍布精彩詞句,教師可以啟發(fā)學生采擷自己最喜愛的文字,編輯成短小精悍的散文詩:“那籠罩山谷的/是戴在山頂上的白色絨帽/那纏繞半山的/是系在山腰間的條條玉帶/那彌漫山谷的/是茫茫的大海/那遮擋山峰的/是巨大的天幕……千種姿態(tài)/萬般風情/是大自然的又一部杰作……”富于變化的事物極易引起兒童的注意,進而使他們自發(fā)地趨近和模仿。學生就地取材,任“性”捕捉經(jīng)典語言中令他們印象最深的文字,在調(diào)詞遣句的游戲中獲得審美體驗,使其對文本語言的審美能力實現(xiàn)突破與增值。這樣情趣共振的言語實踐是兒童習作積聚 “顏值”最重要的助力。
3.引發(fā)“鏈梢語言”,用生態(tài)的理性體驗為習作滋潤文路因子。
兒童占有語言的最終目的是借助言語表達自我,這種“表達”應是連貫而非斷點式的,應是整體而非局部化的。因此,教師要引導其理化存儲,建立主題化的“思維鏈”,在聚零為整的過程中,提升對表現(xiàn)認知及表達情感的整體觀照能力。
趣味化和挑戰(zhàn)性是令兒童萌生幸福感的核心要素。可以嘗試引導學生將自己日常學習和生活中的原生素材、印象文字、瞬時靈感等以類似于思維導圖的形式,按“歸整→梳理→串聯(lián)→豐富→管理”的程序建立個性化資源庫。有的學生以“成長樹”的形式建立了以“愛”為主題的資源庫,“樹”上四根粗壯的“枝”分別代表:朋友之愛、師長之愛、親人之愛、社會之愛,生活中的代表人物便是它們各自分生出的“叉”,再不斷繁殖出典型事件的“梢”、生出細節(jié)之“葉”……這種自由調(diào)配、圖文并茂的鏈式追逐既可用于分類積累、索引素材,也可用于疏通思路、謀篇布局,集聚主題性、序列性、層級性、生長性和趣味性,是兒童習作選材布局最需要的推力。
二、基于“有意識的自由表達”,輔助兒童活化意趣,于中期創(chuàng)作中啟動“本我”的讀寫實踐
1.引導自主“仿生”,在遷移摹創(chuàng)中創(chuàng)生屬于“我”的表達圖式。
“仿生”意即基于仿作之上的創(chuàng)生。調(diào)查中發(fā)現(xiàn),學生在向往自由表達的同時,依然希望多一份適時出現(xiàn)的輔助力量,尤其是詩歌、游記之類的習作。教師可以借助經(jīng)典作品的閱讀,在兒童與之相遇時,開辟時空,催發(fā)言語的創(chuàng)生。
教學蘇教版四下《只揀兒童多處行》時,筆者嘗試采集文中語言,以詩歌的形式出示:“兒童是小天使/成千盈百地從大魔術(shù)匣子里飛涌而出/兒童是春光/噴發(fā)著太陽的香氣息/舒展出新鮮美麗的四肢……”再設問:“在你心中,兒童是什么樣的?”由此引發(fā)了學生意趣勃發(fā)的創(chuàng)想:“兒童是一顆小小的種子/從埋進土壤的那一刻/便開始為生根、發(fā)芽做準備”“兒童是一捧清澈的水/以純潔的心/折射出多彩的情”……在言語活動中,兒童“先天的言語潛能得以實現(xiàn),這是內(nèi)部言語與外部言語的聯(lián)結(jié)過程”[1]。筆者以冰心溢于字里行間的對兒童的喜愛觸發(fā)了每一個兒童“愛的哲學”,用童詩開啟了學生“愛的歷程”,引導其在“仿生”中實現(xiàn)創(chuàng)作范式的自主轉(zhuǎn)化。
2.鼓勵自在“變式”,在創(chuàng)意表達中釀造屬于“我”的新鮮語言。
“變式”意即變通語用形式。教材中的名家名篇亦常采用“變式”增強表達效果,如冰心在《只揀兒童多處行》中所寫的“散發(fā)著太陽的香氣息”,孫友田在《月光啟蒙》中所描繪的“飄滿了芳香的音韻”等。教師應鼓勵兒童大膽嘗試,綻放言語個性。
一位學生這樣描寫她的“活寶”妹妹:“妹妹盯著我手中的阿爾卑斯棒棒糖,咽了一下口水,糯糯地說:‘姐姐,我舔一下就還給你,保證不騙人!'”妹妹“糯糯”的娃娃音令人自然聯(lián)想到甜軟細膩,還帶著些許黏性的味道,這種感覺性語言生動至極。另一位學生在描寫父母表情變化時嘗試了形象化的移植:“聽著錄音機里放出的爭執(zhí)聲,爸爸的面容漸漸‘陰轉(zhuǎn)多云',媽媽的眉毛也從‘八點二十'變成了‘九點一刻'。”令人叫絕!兒童的思維空間廣袤得令人吃驚,甚至擁有成人無法獲知的言語異能,他們不拘一格的表達最純凈、最新鮮、最彌足珍貴。習作教學要“減少對學生寫作的束縛,鼓勵自由表達和有創(chuàng)意的表達”[2],在“變式”中促成創(chuàng)作個性的自在變化。
3.支持自由“織夢”,在虛實相間中飛舞屬于“我”的律動思維。
“織夢”意即用文字編織夢想中的景象。弗洛伊德認為,從每一個人的夢中,都可以找到夢者所愛的自我,且都表現(xiàn)著自我的愿望。兒童學習語言的最初目的是表達自我,因而想象類作文是他們的最愛,所以師者應適時拋設“支點”,助其生長夢境。
在一次古文經(jīng)典誦讀活動中,筆者以一首五言:“渡水復渡水,看花還看花。春風江上路,不覺到君家。”引渡出一個個炫彩的童夢:“一個華麗的踮腳起步,雨珠輕盈地從高空跌落。旋轉(zhuǎn),左右,并腳,踏步,換位……”這是童趣觸發(fā)的夢;“遠處,天如水,水映山,山似畫,畫成花,陣陣春風拂面,細膩如母親的雙手,耳邊回蕩著唱晚的漁歌……”這是童韻生發(fā)的夢……一旦順應兒童想象力的自由發(fā)展,諦聽童夢的心律和足音,便可聆聽到石破天驚的童真宣言,領(lǐng)略到兒童文化別樣的風情。“夢”是兒童獨特的生長方式,習作教學應給予兒童放飛夢想的舞臺,令其在“織夢”中獲得心智的成長。
三、基于“有意義的開放評價”,協(xié)同兒童外化情志,于后期制作中發(fā)展“知我”的交流場域
1.開啟“第一讀者”的能動空間,在“回看”和“取舍”間體驗習作的悅納感。
管建剛老師說,學生的“寫作熱情來自真誠的回應”[3]。兒童習作的第一讀者應是作者本人,教師要發(fā)動其“首讀者”的身份回看文本,在忠于“本真之我”的叩問、修繕中產(chǎn)生最初的審美認同。
兒童自主修改作文的熱情來源于對作品開放的期待。當學生得知作文不再只是“填格、交差、下發(fā)、訂正”這幾個循環(huán)進行的規(guī)定動作,而是可以公開、推介、評鑒,甚而可以晉級、追評、建檔時,他們會自覺主動地以“作者”的身份投入創(chuàng)作中,并在“作品”問世之前,反復斟酌,對比取舍,揣摩修繕,以求盡善盡美,管建剛老師謂之“作品意識”。開放作品更利于作者以讀者的身份,于方寸之外進行理性審視,在“自我”和“前我”的博弈中獲得新的審美體驗。因而,兒童的“創(chuàng)作→返讀→自改”是一個不斷發(fā)現(xiàn)“本真之我”的過程。
2.開發(fā)“顯性讀者”的互動空間,在“點贊”和“捉蟲”間生發(fā)習作的振奮感。
“語言是一個媒介,一個載體,‘理解'是發(fā)生在文本之內(nèi)的語言事件,它完全是一種人與人的交流。”[4]教師要順應兒童喜歡游戲式交往的天性,借助富于變化的互動形式,助其精神振奮地投入到言語認知活動中去。
筆者曾嘗試在教室墻面上開辟出一塊習作交流區(qū),并在每篇交流的習作旁設置“點贊區(qū)”和“捉蟲區(qū)”,以供學生進行分類批注并署名。周末,作者參考同伴批注,自主進行二次習作,再次展示。由此,評比出“星級評價師”和“星級作文”。維果斯基的“最近發(fā)展區(qū)”理論告訴我們,“應關(guān)注兒童已有水平及所具潛能,引導其更進一步”[5]。同齡人更了解習作者的學習狀態(tài)和發(fā)展水平,這種“伙伴協(xié)同、異質(zhì)交流”的互動,生成的是兒童與兒童之間的“最近理解”,而成人的習作評價則應后置進行。因而,兒童的“開放→吸納→復創(chuàng)”是一個不斷理解“本真之我”的過程。
3.開放“隱性讀者”的聯(lián)動空間,在“發(fā)表”和“比較”間延展習作的成就感。
兒童熱愛幻想,一切神秘的事物都會引發(fā)他們的關(guān)注和探究。如何延續(xù)他們在習作中產(chǎn)生的愉悅和振奮感,并逐步放大,形成恒久的習作幸福感呢?筆者以為,最佳路徑是將其精心修改的作品即時“發(fā)表”,尤其是面向未知的讀者群。
對于學生的優(yōu)秀習作,筆者曾嘗試借助三類媒介予以發(fā)表:各級相關(guān)報刊、校園網(wǎng)專欄、個人博客。其中,博客平臺因用稿率高、互動性強而最受學生關(guān)注。馬斯洛的需求層次理論告訴我們,自我實現(xiàn)是人最高層次的需求。當一個學生看到自己的文字和名字以電子文本的形式出現(xiàn)在互聯(lián)網(wǎng)上時,那份激動、滿足和成就感會銘刻在心,成為永恒的記憶。未知的世界最為高深莫測,隱性的讀者群和不斷生長的交互信息加速了兒童潛能的內(nèi)驅(qū)式噴發(fā),寫作成為他們表達自我、建立自信的一方樂土。此外,兒童在橫向群比和縱向自比中,深化了對世界對自我的認識。因而,兒童的“發(fā)布→關(guān)注→化用”是一個不斷豐盈“本真之我”的過程。
馬克思·范梅南說:“面對兒童就是面對可能性。”理解兒童的可能性,理解兒童心中的需要、眼中的生活、筆下的世界,追隨兒童的本真性情,這便是順應“童性”的真義。教師的姿態(tài)是一種自然的融入和自覺的守望,以幫助兒童成為“兒童”,在生活中學會發(fā)現(xiàn),在習作中釋放發(fā)現(xiàn),在交往中拓展發(fā)現(xiàn),在對生活的向往和對理想的追求中發(fā)覺自我、發(fā)動自我、發(fā)展自我,過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幸福生活。
[1]李海林.言語教學論[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44.
[2]中華人民共和國教育部.義務教育語文課程標準: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2:23.
[3]管建剛.我的作文教學主張[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12.
[4]竇可陽.接受美學與象思維:接受美學“中國化”[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76-77.
[5]魯?shù)婪颉ぶx弗.兒童心理學[M].王莉,譯.北京:電子工業(yè)出版社,2010:189.
注:本文獲2015年江蘇省“教海探航”征文競賽二等獎,有刪改。
G623.24
A
1005-6009(2016)36-0027-03
陳嬿竹,江蘇省連云港市建國路小學(江蘇連云港,222002),一級教師,全國德育科研先進工作者,連云港市優(yōu)秀教育園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