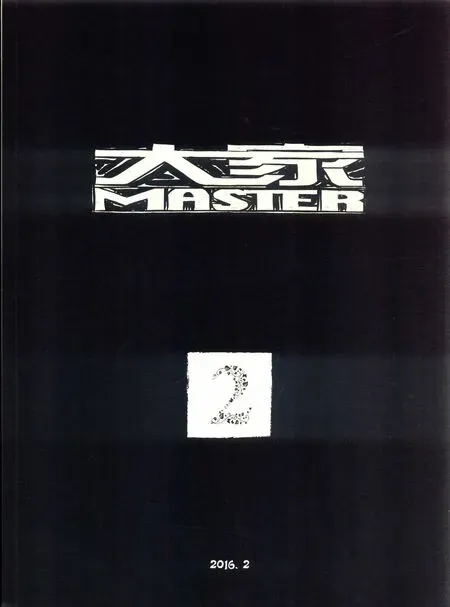三塊銀元
∥郝煒華
?
三塊銀元
∥郝煒華

郝煒華,1970年代生人,山東省簽約作家。主要從事中短篇小說創作,在《北京文學》《清明》《山花》等期刊發表中短篇小說100萬字,出版中短篇小說集《向南向北》。作品多次入選年度選本。
1
士兵嘁嘁喳喳從房后經過時,紀來福正在磨辣椒醬。泡好的黃豆、綠豆、胡蘿卜塊、芝麻、紅辣椒擱進磨眼里,石磨轉動,粉紅色的辣椒醬從磨盤里擠出來,辣乎乎的氣息彌漫在角角落落。紀來福用木勺子將辣椒醬刮進瓷盆,已經刮了半瓷盆。這是膠東人家喜歡的吃食,擱鍋里蒸熟了,又辣又香又好看,買都買不到。
聽到屋后嘁嘁喳喳的聲音,紀來福慌忙用布子將瓷盆蓋起來。村東邊的山頭駐扎著偽軍,偽軍和他們的老婆隔三差五從山上下來,捉雞逮狗,摘果挖菜,什么好吃弄什么。紀來福家門口種著一棵梨樹,梨樹下種著一株葡萄,葡萄蔓爬到了梨樹上,結著青煦煦的葡萄籽。等到八月十五,葡萄籽成熟,變得又肥又紫,摘下來,放進瓷盤里供養月亮娘娘再合適不過。
紀來福怕鄰家的孩子摘了葡萄籽,怕雞、狗、貓、鳥糟蹋了葡萄籽,打發七歲的兒子在梨樹下守著。兒子倒是盡心,站在梨樹下,眼睛不眨一下,午飯都是他媽送到梨樹下面,就著青翠翠的葡萄葉子、梨樹葉子一口一口吃進肚里。鄰家孩子、雞、狗、貓、鳥但凡靠近,兒子就扯開嗓子大喊一聲,連人帶家畜帶鳥類,一溜煙地跑個一干二凈。這日下午,一個偽軍的老婆來到梨樹下面,那個女人懷了孕,肚子里像塞了一個面盆,鼓鼓囊囊的。她手里拿著一截向日葵稈,站在梨樹下面打那些葡萄籽。一棍子一棍子打下去,青煦煦的葡萄籽落了一地。偽軍老婆撿了一把裝進口袋,又撿了一把捧在手里,轉身一扭一扭地走了,落在地上的葡萄籽被她踩得稀爛。紀來福的兒子在梨樹下站著,既不敢說話,又不敢喊,更不敢哭,等到女人走遠,眼淚才稀里嘩啦地流下來。兒子去找紀來福,紀來福正在井臺旁邊提水,水是給偽軍提的。東邊的山上沒有水井,偽軍命令村里的青、壯男子每天給他們擔水,洗菜、做飯、洗衣服、洗臉和洗澡。兒子找到他時,紀來福正將一桶清亮亮、甜兮兮的井水提上來。聽完兒子的話,他“呸”的一聲往水桶里吐了一口唾沫。唾沫很快融解進井水里。紀來福說:“那些娘們會打人,不管她就對了。”
說完,嘩的一聲將水桶里的水倒掉了,還用另一只桶里的水涮了涮水桶。
紀來福趴在窗戶上往外瞧。窗外是條小河道。沒有雨的時候,河道里布滿泥巴和碎石子,人在河道里走來走去。有雨的時候,山上的雨水淌下來,順著河道流到村西的小河,女人在河道里洗衣服,孩子在河水里嬉戲,大人蹲在河邊抽煙。有時,有銀色的小魚在河水里游來游去。
昨夜剛剛落雨,河道里充滿清亮亮的雨水,那些士兵踩著雨水走在河道里,雨水將他們的鞋子與褲子都弄濕了。士兵的衣服也是濕的,烏黑油亮的頭盔上還掛著雨珠。紀來福側臉看天,灰色的云彩后面露出太陽的金邊。這幫士兵是從遠地方來的,那個地方剛剛落雨。
紀來福聽到院門被人啪啪拍響,他慌忙將盛著辣椒醬瓷盆塞進炕洞,抓了一把柴草堵住洞口。囑咐老婆、兒子、女兒別出聲,才去開院門。
門開處,挨挨擠擠的士兵站在門口,一直排到胡同的盡頭還拐了一個彎。一個軍官模樣的男人站在前頭,跟紀來福說話。男人的是中國人,說話的腔調卻非常奇怪,紀來福一句聽不懂。看著紀來福迷惑不解的樣子,男人朝身后大聲喊一聲。一個黑臉、矮胖的男人擠過來,站在紀來福面前,說:“我們晚上住在你家。”
男人說的是本地口音,跟紀來福村里的口音略有不同。這種細微差別只有本地人才能聽出來。男子說的是離紀來福村子二十里路,離白河縣城五里路的徐家鎮的口音。
紀來福老婆的娘家就是徐家鎮的,紀來福熟悉這種口音,忍不住多看了男人兩眼。
士兵全部住進西院。屋子裝不下,士兵從屋里轉移到院子。院子里的泥地太潮濕,昨夜剛剛落了雨,今天一天又沒有太陽,泥土一按就能按出水漬來。還是那個黑臉、矮胖的男人走過來,問麥秸垛在什么地方。所有的麥秸垛都在村前的場院里。剛剛曬干的麥秸黃澄澄的,凝結著土地與麥粒的芳香。紀來福的老婆說:“俺家沒有……”“嘩啦”一聲是槍上栓的聲音。紀來福急忙說:“有、有,我就帶你去。”
幾名士兵跟在紀來福身后,穿過胡同,拐了彎,順著濕漉漉的泥巴路來到場院。場院里堆著十幾個麥秸垛,都是村里人家的。紀來福將士兵帶到自家的麥秸垛前面。士兵圍著麥秸垛轉了一圈,扒掉濕了的麥秸開始往外抱麥秸。一抱,一抱,又一抱黃澄澄、干爽爽的麥秸被抱走了。汗水從紀來福的后腦勺、脊梁骨冒了出來。粘糊糊、涼颼颼的,弄得紀來福渾身上下冷得不行。
遠遠的,紀來福看到老婆從村子里走出來。她站在場院邊上,手搭涼棚向這邊張望。望著望著一個跟頭栽到地上。士兵們往來了幾個來回,不再過來。紀來福將散落在場院上的麥秸堆到垛上。厚墩墩的一個垛子消失了四分之三。
紀來福走到場院邊上,掐老婆的人中。老婆晃晃悠悠地醒過來。看看麥秸垛,看看紀來福,說:“你怎么不領他們扒別人家的草垛。”
“咱們不能做那樣的事。”紀來福說,“咱們不能做那樣的事。”
2
紀來福到紀有德家時,紀有德正坐在炕上,用手捂著左耳朵。
紀有德的左耳朵豁了兩個小洞,如果把紀有德的門牙取下來,正好可以塞進兩個小洞。
從前,紀有德聽過十指連心這句話,現在,他感覺耳朵垂子也連著心。從凌晨時分到現在,耳朵垂子紅腫,發炎,冒黃水,火辣辣的,一跳一跳地疼。在炕上平躺著不行,側躺著不行,趴著也不行,紀有德索性坐起來,用手捂著耳朵,盯著房前的芋頭花發呆。
已是黃昏時分,太陽在西邊的山頭露出半個面孔,暈黃的陽光斜照在芋頭花葉子上,給寬大碧綠的葉子鑲上一道金邊。芋頭花跟芭蕉模樣相似,枝干碧綠,葉子寬大,每一片葉子都可以當成草帽戴在頭上。只是芋頭花長得比芭蕉高大,紀有德家的這株已經越過墻頭,葉子和紅色、白色、黃色的花蓬蓬勃勃地伸展到院子外頭。
紀來福進門的時候,先在芋頭花下站了一會,扯起一片葉子晃蕩了晃蕩,幾顆水珠從葉子上掉下來,落到紀來福的頭頂。紀來福一縮脖子,一聳肩,搖搖頭,看上去很冷的樣子。
雨是昨夜下的,為何,現在葉子上還窩著水珠?紀來福進屋,在炕前的凳子上坐下,不說話,紀有德也不說話。
紀有德是天快亮時回到村子的。他從紀來福屋后頭的河道走過,嘩啦啦的淌水聲驚醒了紀來福。其實,紀來福剛剛睡下不到一個小時,半夜時分響起的槍聲,將他的睡眠嚇到九霄云外,天亮時分才戰戰兢兢地回到他的身上。紀來福沒敢推開窗戶,趴在窗縫上,看到紀有德一手捂著左耳朵,一手拎著一個黑色包裹,渾身水淋淋地往家走。紀有德在煙臺做事,是村里少有的見過世面的人,每次回村都是儀表堂堂、氣勢軒昂。這次,卻如同吃了敗仗的殘兵一樣。
芋頭花葉子吞噬掉了最后一抹陽光,夜色一層一層漫上來,眼看著到了點燈時節,紀來福咽了一口唾沫,嘴張張,卻沒吐出一個字。
紀有德回頭瞅了紀來福一眼。他與紀來福是沒出五服的親戚。紀來福對他向來尊敬,紀有德也挺喜歡他。紀有德說:“來兵了。”
紀來福點點頭,依舊不說話。
紀有德又說:“什么事?”
紀來福這才開口,仿佛千斤秤砣掛在嘴上,口開得艱難,話說得也艱難。紀來福說:“兵爺爺要三塊銀元,我哪有三塊銀元,叔……”
紀有德似乎一直在等紀來福這句話。他的臉上露出輕松和歡喜的表情。他的手從左耳朵上放下來,似乎左耳朵不疼了。他下炕,打開柜子,拿出那個黑色包裹,手伸進包裹里摸來摸去,拿出來時,手心里臥著三個圓溜溜的銀元。紀有德將銀元遞給紀來福,銀元上還保留著熱乎乎的溫度。
紀來福的眼睛盯著銀元,擔心一眨眼,銀元就會不翼而飛。他很少見到銀元,最近一次見它還是結婚時,丈母娘塞了一塊銀元作為嫁妝叫老婆帶了過來。紀有德五指并攏,將銀元緊緊攥在手里。他側過臉,叫紀有德看臉頰,“叔,他們打我。你看,臉上的大手印子還在。”
黑夜籠罩著屋子的角角落落,不知為什么,紀有德的老婆沒有端來油燈。隱隱約約的白光從院子里透進來,并不能夠看到臉上的大手印子。
紀有德咳嗽了兩聲,手又捂到左耳朵上,愁苦的表情重新堆積到臉上,剛才的輕松和歡喜仿佛人臨死前的回光返照。他說:“侄媳婦是徐家鎮人?”
“是。”
“聽說那個鎮子死人了沒有?”
兵荒馬亂,死人的事情經常發生,就連他們的小村子都經常死人。有掉進水井里的,有溺死在西河里的,有走著走著路突然撲到地上沒了氣息的。所有的死都應該和兵有關。可是沒有人敢和兵追究。
紀來福想起昨天半夜時分的槍聲。那個時候,天還沒有落雨。槍聲劈里啪啦,像過年時放的鞭炮,又像燒干透了的豆秸。天亮后,他到西院察看,屋里炕上的被子、褥子還在,地上鋪的柴草還在,院子里鋪滿水漬,水漬淹沒了腳印子,水漬里沒有紫紅色的血跡。倒是院西邊的土墻,掉了半塊土坯。
沒有死人的跡象。
紀來福說:“徐家鎮是個大鎮,五六個村莊,你侄媳婦的家在鎮東北的河邊。這是你知道的。她村里沒聽說死人。”
“不是因為侄媳婦,也不會聽出徐家鎮的口音。”紀有德嗞嗞吸著涼氣,仿佛耳朵疼得受不了了。他說:“銀元不用還了。”
“哪能呀,叔。借的錢一定要還。再說,你掙錢也不容易。”
兵們橫七豎八地躺了一院子,見到紀來福進院,眼皮都不抬一下。他們嘁嘁喳喳說話,說的全是紀來福聽不懂的方言。院子的東墻架著兩口鐵鍋,一口鍋里盛著煮熟的米飯,灰色的米粒夾雜著黃色的稻糠和黑色的、褐色的小石子。另一口鍋里燉著爛乎乎的蔬菜,已經看不出菜的品種。
順著院子邊,紀來福進了屋子。那個軍官坐在炕上,面前擺著一張方桌,方桌上放著一盤炒雞蛋、一盤炒茄子、一碗粉紅色的辣椒醬。暈黃的燈光閃閃爍爍,將軍官的背影映滿整個墻壁。
軍官似乎嫌辣椒醬不夠辣,拿起碗,澆了半碗辣椒醬在米飯上面。
紀來福伸開手,把一直攥得緊緊的三塊銀元放到方桌上,銀元依舊熱乎乎的,泛著瓷實的白光。紀來福恭恭敬敬地說:“長官,銀元。”
礦石云英巖化明顯,石英、云母、長石約占礦物總量的96%以上,其他礦物含量少。為全面、準確地確定礦石中礦物的種類,我們按礦物特性,采用重選和浮選手段進行富集,使少量、微量礦物在X射線衍射分析中能夠顯示出來。經過系統工作查明礦石中的主要礦物成分為石英、長石和云母,其他礦物為螢石、輝鉬礦、黃鐵礦、錫石、鈣鈦礦等(表2),根據上述礦物性質和含量不同進行了分類統計,結果見表3。
軍官敲敲桌子,呱啦呱啦說了一通方言,紀來福一句聽不懂。看到紀來福迷惑不解的樣子,軍官扯起嗓子喊了一聲,又是那個黑臉、矮胖的男人過來。軍官呱啦呱跟他說著什么。黑臉、矮胖的男人出去又進來,懷里抱著一幅卷軸,打開,是一幅水墨畫,右上角四個字——“古城春色”。男人說:“長官送你幅畫。”軍官用手比劃著,呱啦呱啦說話。男人說:“你家兒子七八歲了吧?等他結婚時,把這畫掛到婚房里。”
3
士兵的呼嚕聲、磨牙聲、說夢話聲、放屁聲、搓腳丫聲將空氣弄得如同海水一般,波濤起伏,躁動不安。
紀來福與老婆一個坐在炕東頭,一個坐在炕西頭,倆人沒敢點燈。紀來福“吧嗒吧嗒”抽煙,屋子里只有明明暗暗的一點煙火的紅光。老婆趴窗戶上向外瞧瞧,半夜了,天反倒晴了,一彎細細的下弦月伴著滿天的星光。
老婆回過頭,摸摸兒子的腳丫,將它塞進了被窩里。
紀來福小聲問:“你們那,徐家鎮,昨夜里死人了沒有?”
“徐家鎮那么大。”老婆的聲音也低低的,倆人不像聊天,倒像密謀,“我哪知道死沒死人?到處鬧兵災,興許天天死人。”
“就是死了人。”老婆爬過來,頭湊到紀來福臉前,頭發弄得紀來福的臉癢癢的。老婆說:“也不可能這么快知道。除非死的是我家親戚或是我們村里的人。”
第二天,天沒有亮透,院子里的士兵就起身,洗臉、整理服裝,吃飯,嘁嘁喳喳地說話。院子里亂哄哄、鬧哄哄的。紀來福一家不敢出門,躲在屋子里透過窗縫、門縫往外瞧,就見那個黑臉、矮胖的男人穿過院子,來到他們房屋門口。沒聽見推門聲,男子已經站在炕前。
男子說:“大嫂是徐家鎮人?”
紀來福老婆知道男子在跟她說話,看看紀來福,嘴唇哆嗦著,沒敢應聲。
“我也是徐家鎮人。”男子手伸進懷里,摸出一個黑色小包,他說出一個村莊的名字,“大嫂幫我打聽一個人,如果這個人還在,就把這個包交給他。”
晨光一下子瀉進屋內,照亮了紀來福與老婆臉上的白色。那是內心驚恐帶來的顏色。
紀來福的眼前浮現出一張瘦長的臉,那張臉每次出現在他面前,都會擠出一絲令人心酸的笑容。
關于這些士兵的去向,村里人眾說紛紜。有人說他們一路向東,翻過數座山,穿過數條小路,去了煙臺。煙臺有浩瀚無邊的大海,他們在那里坐船,去往可以通過海到達的任何地方,比如日本、朝鮮,比如大連、上海、福建,再比如臺灣。有人說他們沒有去煙臺,而是去了白河縣城。這些彎彎曲曲的土路同樣可以到達白河縣城,解放戰爭已經到了最后關頭,國民黨的部隊加強了白河縣城的駐守力量。
村里人議論紛紛的時候,紀有德拿著那幅水墨和那個黑色小包仔細看。黑色小包里裝著一塊巴掌大的石頭,灰白色的石身上綻放著數朵白色的菊花。紀有德說:“水墨畫的是湖南的鳳凰古城,這碧綠的,如同綢緞一樣的水名叫沱江。江邊的竹樓名叫吊腳樓。這塊石頭也有名稱,叫做天青菊花石。這幫兵來自湖南……”
“不是的、不是的。”紀來福的老婆說,“拿石頭的那個兵是徐家鎮人。”
聽到“徐家鎮”三個字,紀有德立刻變了臉色。他將手捂到耳朵上。他的耳朵紅腫得厲害,如同半只切開的紅辣椒。兩個小洞淌出了黏稠的膿水。
紀來福與老婆將院子里的麥秸重新搬到場院里。塌了的麥秸垛又鼓鼓囊囊地堆在場院里了。紀來福俯下身,臉幾乎要趴在地上。他的手伸進麥秸垛,摸呀摸,拽出一把黃澄澄的、干爽的麥秸,臉上露出滿足和歡喜的笑容。
半夜時分,紀來福被輕輕的敲窗聲驚醒。自從家里住過偽軍后,他的睡眠總像在水面上產卵的蜻蜓,輕輕一點,便離開水面。紀來福趴在窗戶縫上,暗淡的月光下,看到窗外的人影。這個男人三天前的晚上來過他家。紀來福打開窗戶,男人一下子跳了進來,腳上粘的泥巴蹭到了窗戶欞上。
紀來福的老婆陪著男人說話。紀來福打開院門,出了村子來到場院。寂靜的場院上堆著一個一個又一個麥秸麥。這些被太陽曬得熱烘烘的麥秸垛,此刻都靜悄悄的,默不作聲地看著紀來福。
紀來福家的麥秸垛在場院的西北角。三天前的半夜時分,他來到麥秸垛旁邊,趴到地上,在麥秸垛的下面掏了一個洞。昨天晚上,那幫湖南來的兵扒掉了四分之三的麥秸垛,再往下扒那么一點,就會發現紀來福在洞里藏的東西。如果那樣,紀來福、紀來福的老婆,他們的兒子、閨女會一齊丟了性命。
紀來福來到麥秸垛旁邊,趴到地上,一把一把地扯麥秸,黃澄澄的麥秸鋪在他的屁股后面像鋪了一塊金黃色的地毯。很快,紀來福摸到了他藏在麥秸垛里的東西,沒有了麥秸嚴嚴實實的阻擋,他輕而易舉地將那件東西拿了出來。
紀來福將掏出來的麥秸重新塞回去,抱著那件東西站起了身。他聽到場院里面一陣窸窸窣窣的聲音,側耳細聽,卻又沒有了任何聲音。彎彎的下弦月似乎比剛才亮了幾分,星星的眼睛也眨巴得越發頻繁。風細細地吹過來,麥秸垛的影子一齊晃動起來。
紀來福的老婆還在陪男人說話,兩人聲音很低,像輕風掠過河面,又像微風拂過花瓣。紀來福的老婆說: “我叫他藏在別人家的草垛里。他說:咱們不能做那樣的事,藏別人家草垛就等于害了人家。”
紀來福將懷里的東西遞給男人,拉著老婆出了屋,并且閉了屋門。一會兒工夫,屋門打開。一個穿著軍裝的英俊男子站在他們面前。
“跟你打聽個事。”紀來福老婆說,“徐家鎮死沒死人?”
“我沒去徐家鎮。不過,前天凌晨,在鶴山旁邊的官道上,我看到了一個死人。”
鶴山是靠近徐家鎮的一座山峰。山下的官道可以通向徐家鎮,可以通向白河縣城,再往東,可以通向煙臺。
4
紀來福要陪老婆回娘家,他們想跟娘家借三塊銀元,他們也不知道娘家有沒有三塊銀元,但是問了總比不問好。
紀有德捂著耳朵站在他家門口,一條腿支在門框上,說:“三塊銀元不用還了,給了當兵的,又不是用來過日子。”
“這個更要還。如果不給銀元,他們會要了我的命。那不是過日子的錢,那是救命的錢。”
紀有德瞅著他們,一臉愁苦的表情。他的耳朵紅腫得更加厲害,耳朵垂子灰白,像紙片燃燒后的灰燼,似乎一碰,耳朵垂子就會掉下來。
回娘家必須經過鶴山,鶴山不高,但是山體龐大,延綿數十里,山峰郁郁蔥蔥,密密麻麻地種著松樹、柏樹、水杉,還有蘋果和梨樹,山里有時藏著偽軍、國民黨兵,有時埋伏著八路軍。清清靜靜的日子會突然響起“噼噼啪啪”的槍聲。夜深人靜的時候,時常有飛機在山頂盤旋,“轟隆轟隆”往下扔炸彈。弄得人們成晚上地睡不著覺。
轉過一條小河,拐一個彎,上一道坡,再下一道坡,眼前的路曲折而又幽暗起來,一邊是綠樹覆蓋的鶴山山體,樹木過于濃郁了,葉子綠得發黑,冷風“唰啦啦”吹過來,渾身的汗一下子消止了。路的另一邊是十幾米高的懸崖,崖上布著亂石,亂石縫里長著一蓬又一蓬野草,崖底是狹長的深溝,溝里淌著墨綠色的水。這塊地界有個嚇人的名字——“閻王鼻子”,時常發生攔路搶劫的事情,每年都要死五六個人。
紀來福與老婆低頭走路,想快快通過這塊危險的路段。不承想,前方突然傳來一聲長呼:“回家嘍、回家嘍!”
紀來福與老婆一下子停住腳步,倆人你瞅我一眼,我瞅一眼,鬧不清長呼的是人還是鬼。紀來福的老婆撇撇嘴,眼里淚花閃閃,馬上要哭出來。紀來福扯起老婆的手,壯著膽子往前走,轉了一個彎,一個穿著黑衣服、頭發花白、腰都要彎到地上的老婦人出現在他們眼前。老女人手里拿著一件深藍色的衣服,一步一步艱難地挪動腳步,一聲一聲地長呼:“回家嘍、回家嘍!”聲音蒼老而又凄厲,聽得人的汗毛都要立起來。
老婦人是來招魂的。家里人死在外頭的,都要用這種方式將他的魂招回去,如此,死去的人才能重新投胎轉世。
紀來福的老婆捂住嘴,眼里的星星淚花變成了疑惑與驚懼。紀來福緊緊咬著下嘴唇,臉上的肌肉因為過于緊張一下一下地跳動。他們都聽出來了,老婦人是徐家鎮的人。
紀來福走到老婦人身邊,問:“大娘,你這是給誰招魂?”
“兒呀、兒呀,俺家的兒。前天晚上死這里了。可憐呀,俺家的兒啊!被人用石頭砸碎了腦袋……”
紀來福與老婆相互瞅了一眼,紀來福臉上的肌肉跳得更加厲害,他的老婆都要暈倒了。
紀來福拿出一個黑色小包,是黑臉、矮胖的男人留下的那個小包。包里放著那塊天青菊花石。紀來福將小包捧在手心,像捧著一座沉甸甸的大山。他說出那個村莊的名字,黑臉矮胖的男人告訴他的那個村莊名字。他害怕或者盼望老婦人回應。可是老婦人沒有回應,不知是沒有聽見,還是不想搭理紀來福。她拖著那件深藍色的衣服,一聲一聲喚著,一步一步向前走去。
紀來福的岳母、兩個小姨子正在家里包水餃。院子里坐滿了士兵。這些士兵不同于住在紀來福家里的士兵,他們的軍帽上有顆紅紅的五角星。士兵們一個挨著一個安靜地坐在院子里,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休息。
“今晚,他們去解放白河縣城。”紀來福的岳母說,“都是些孩子呢。得叫他們吃得飽飽的上戰場。”
韭菜豬肉餡水餃。韭菜是新割下來的,綠油油的,像水頭很足的碧玉。豬才四個月大,一頭豬通常半年出欄,但是為了叫士兵吃得好,紀來福的岳父毫不猶豫地宰了這頭豬。家里時不常地來偽軍,他們鉆進豬圈搜八路、打開碗櫥搜八路、打開衣柜搜八路,這頭豬能夠長到四個月實屬不易。
紀來福加入包水餃的行列。他雖然是男人,但是會揉面和搟水餃皮,一根搟面杖捏在手里像一支揮灑自如的槍,水餃皮雪片子般“啪啪”甩到案板上。紀來福的老婆、岳母、兩個小姨子,十指翻飛,胖嘟嘟的、小元寶似的水餃在蓋簾上快速排開。

《柏濤塔》何興攝影2014年
紀來福的老婆突然碰了碰紀來福的胳膊,嘴向院子里努努。紀來福抬眼向院子里望,不用老婆仔細指點,他就知道老婆要叫他看什么。一個臉頰瘦長的士兵坐在門樓下面。
紀來福心跳得厲害,他的老婆又是要暈倒的樣子。紀來福一把扶住她,白色的面粉全都沾到她的衣服上。紀來福說:“像,真像。”
老婆點點頭。
紀來福說:“多包點肉。單獨煮。肉多的水餃專給他吃。”
紀來福的老婆包了三十多個差不多全是肉的水餃,單獨擱在一個蓋簾上。水餃煮好了,一碗一碗端出來,紀來福將肉多的那碗遞到臉頰瘦長的士兵手中,同時將那個黑色小包放在他的腳旁。
5
天亮時分,槍聲、大炮聲、飛機的轟鳴聲全部消止了。天空藍得出奇,云彩白得出奇。很多人站在村口,袖著手向白河縣城的方向張望。很多人急火火地往縣城跑,說戰爭結束了,要去撿好東西。下午時分,各種各樣的消息傳回村子,有的說,白河縣城的城樓插著紅旗。有的說,有人看到一條被炮火熏黑的馬腿扛起來就跑,跑到半路,才發現那是條人腿,嚇得一下子扔掉了。
紀來福不敢去白河縣城,這幾天他的腦子里裝了太多的東西,這些東西弄得他有些迷迷糊糊的。先是家里住了偽軍,后來來了穿著軍裝的解放軍,后來來了說話叫人聽不懂的國民黨兵,再后來就是昨天白天在岳母家的院子里吃水餃的士兵。他們的模樣,他們的影像重疊在他的腦海里,紛紛揚揚,揚揚紛紛,就像鋪天蓋地的大雪,將他大腦里的溝溝壑壑全都淹沒了。
晚上,紀來福岳母家來了幾名士兵,是昨天在院子里吃水餃的士兵。他們仿佛被火燎了一把,又黑又焦又干,又憔悴又疲倦。別的兵呢、別的兵呢……這幾個兵捂住嘴嗚嗚咽咽地哭了起來。
紀來福將那個黑色小包拿出來。臉頰瘦長的士兵沒有將小包拿走。小包在院子里是很醒目的,那么多那么多的士兵從它旁邊經過,沒有人將它拿走。
紀來福將小包捧在手心,舉過頭頂,陽光亮燦燦地照在上面,給小包鑲了一道耀眼的銀邊。
紀來福的岳母家也沒有三塊銀元。他們給紀來福出了個主意,用糧食抵銀元。這倒是個好主意。紀來福回家后,將想法講給紀來福聽,紀來福捂住耳朵,不說行也不說不行,一張臉鐵青。
第二年春天,天還有點冷,紀來福家里來了兩個人。不,應該說是三個人。第一個人手里牽著一個小女孩。那人說話帶徐家鎮口音,一進門,就將紀來福與他老婆嚇了一跳。紀來福與老婆一齊問出聲:“你沒死?”
“差點死了。”那人說,“晚上睡著覺就聽到槍聲大作。當官的喊:不好了,解放軍來了!我爬起身,什么都不管,翻過院墻就跑了。還好,一路跑回了家。娶了媳婦,可惜媳婦不會生養,就抱養了這個孩子。”
紀來福的老婆抱起小女孩。這個臉頰瘦長的男人是曾經住到她家里的偽軍。因為都是徐家鎮人,她給他洗過衣服、縫過扣子、補過補丁,還煮了兩次雞蛋給他吃。
男人第一次吃雞蛋時,偷偷拿了一塊銀元給紀來福老婆看。第二次吃雞蛋時,一塊銀元就變成了三塊。他說:“大嫂,等我回家,用這錢娶個媳婦,生個孩子,成個完整的人家。”
紀來福老婆的臉窩在小女孩的脖子后面,笑得如同綻放的花,說:“沒死就好、沒死就好。”
另一個人是下午來的,穿著綠色的軍裝,手里提著一只紙盒子。紙盒子打開,一群毛茸茸、黃澄澄的小雞仔暴露在陽光下面。紀來福的兒子與女兒“哇”地大叫一聲,倆人去數小雞仔,都是上過學的,會數數,一下子就數清了。十一只小雞仔。
穿軍裝的男人向紀來福與他老婆敬了個標準的軍禮,說:“謝謝你們,你們為革命做出了貢獻。”
紀來福還記得那個晚上,穿軍裝的男人輕輕敲響他家的后窗。紀來福剛打開窗戶,男人就跳了進來。他穿著一身跟偽軍和國民黨兵不同的軍裝,軍帽的中間嵌了一顆紅色的五角星。紀來福小聲說:“西院住著偽軍,你怎么敢來?”
男人說:“不是因為住著偽軍,我也不會來。大叔,我知道你們是個革命家庭,你的大妹是村婦救會會長,二妹負責往墻上刷標語、搞宣傳。因為偽軍鬧得厲害,她們一個躲進了山里,一個嫁給了小時訂下的娃娃親。”
男人說的都是實情。紀來福手指豎在嘴邊,說:“你不穿軍裝,我也相信你。”
男人問了住在西院的偽軍情況——多少人?什么時候出門?什么時候回來?晚上都做什么?問完之后,躲到灶屋的角落,出來時,換了一身灰色衣服。男人將手里的包裹遞給紀來福,說,這是他的軍裝,他要到另外的地方偵察,麻煩紀來福將軍裝藏起來。
這是一件可能叫一家人丟掉性命的事情,沒有人會貿然接下這個包裹,況且西院里還住著偽軍。可是紀來福接下了包裹,他與老婆想了半天,感覺將包裹藏在場院的草垛里最保險。紀來福的老婆動員紀來福將包裹藏進別人家的草垛。紀來福一口拒絕:“咱們不能做害人的事情。”
穿軍裝的男人走后第二天晚上,西院響起槍聲,臉頰瘦長的男人翻過院墻跑掉了,然后說話叫人聽不懂的國民黨兵就來了,然后……
紀來福將最后一擔糧食挑到了紀有德家。紀有德的左耳朵沒有保全,耳朵垂子爛掉了。他的精神仿佛也垮掉了,不再到煙臺做事,日日在村口的高墻下閑坐。村里人也不像以前那樣尊敬他,背地里喊他“爛耳朵”。
紀來福將家里來人的事情告訴紀有德。紀有德的臉木木的,沒有一點表情。
紀來福的老婆找了一些廢紙,漚爛了,和上泥巴做了一個“紙洋缸”。缸底鋪上厚厚的麥秸,十一只小雞仔養在缸里面。怕小雞凍著了,她將“紙洋缸”放在了炕頭上。
紀來福的兒子、女兒趴在炕頭上看小雞,小雞嘰嘰喳喳的,就像小孩在說話。紀來福的兒子挪挪屁股,說:“炕頭太熱了,把小雞燙壞了怎么辦?”
他們將“紙洋缸”拖到了炕尾,可是又擔心炕尾太涼,凍壞了小雞仔。
紀來福的女兒說:“哥哥、哥哥,你摸摸涼不涼,別凍壞了小雞。”
紀來福的兒子將手伸進“紙洋缸”里,他的手伸進了麥秸的下面,他要摸麥秸下面的溫度,那里的溫度才是真實的溫度。
紀來福兒子的手碰到一個圓圓的、溫溫的、硬硬的東西。圓圓、溫溫、硬硬的東西?他的手摸來摸去,總共摸到三個那種東西。
紀來福兒子的手拿出來,三塊熱乎乎、泛著白光的銀元靜靜地臥在他的手心里。
責任編輯:馬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