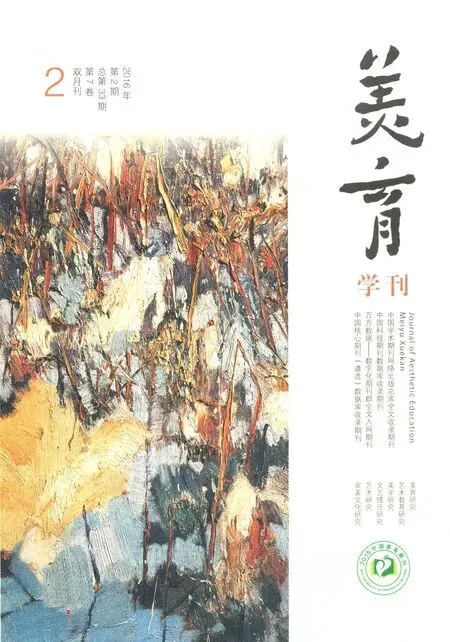杜威的藝術即經驗論
徐 岱
(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8)
?
杜威的藝術即經驗論
徐岱
(浙江大學 傳媒與國際文化學院,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在傳統美學史家眼里,作為實用主義哲學家的杜威很難稱得上是一位名副其實的美學家。但事實上,杜威以一部厚重的著作向我們全面地論述了他的美學思想。除此之外,他的美學思想滲透于他關于教育、倫理、政治等一系列著作里。在此意義上,杜威的實用主義美學不僅自成一體,而且也很有創新精神,值得我們認真對待。與其說他的美學是另一種“藝術哲學”,不如講是一種“生活詩學”。它不僅僅局限于藝術家的創造性活動,同樣涉及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從這個方面講,杜威的美學思想尤其值得我們關注,因為這是一種以人性的培養和人格的塑造為中心的、具有開放性的“大美學”。
關鍵詞:杜威;實用主義;藝術經驗論;大美學
一、實用主義思想家的美學
雖然按傳統的觀念看,美國實用主義哲學家杜威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美學家,但他于1934年出版的《藝術即經驗》,使他在20世紀美學史上占據了一個引人注目的位置。為了能充分地認識他的美學思想,我們首先要嘗試解決兩個問題:什么是實用主義?什么是杜威的實用主義美學?
在詞源上,實用主義(Pragmatism)是從希臘詞πραγμα派生出來的,意思即是行為、行動。它是產生于19世紀70年代的一種現代哲學派別,是誕生于美國本土的最具影響力的哲學思潮,甚至一度被視為美國的半官方哲學。對美國社會的法律、政治、教育、社會、宗教和藝術的研究產生了很大的影響。這一哲學思潮的早期代表主要有三位學者,分別為:皮爾士、詹姆斯、杜威。雖然美國著名學者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在1898年的一篇題為《哲學概念與實際結果》的文章中,是第一個在正式出版物里使用“實用主義”這個詞的人,但他把發明這個詞和它所代表的哲學原則,歸功于查爾斯·皮爾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因為于1871—1874年間在哈佛大學進行活動的“形而上學俱樂部”,被認為是美國第一個孕育實用主義思想的組織。俱樂部的主持人是后來被認為是實用主義創始人的皮爾士。在參加這個俱樂部的討論時,皮爾士寫了《信仰的整合》與《如何使我們的觀念清晰》兩篇文章。如今這兩篇文章被認為是實用主義誕生的標志。
威廉·詹姆斯在實用主義運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雖然他本人更傾向于使用“實踐主義”(Practicalism),但由于實用主義一詞更為流行,他也接受了這個事實。詹姆斯是美國心理學會的創始人之一,1875年建立了美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他的成名作《心理學原理》概括了整個19世紀的心理學,被翻譯為法文、德文、意大利文、俄文等廣為傳播,在國際學界產生了巨大影響。作為一名實用主義哲學的積極推廣者,詹姆斯撰寫了《實用主義》一書,為實用主義思想的崛起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這本書讓人們對實用主義擁有一個基本認識具有重要作用。根據詹姆斯的解釋,實用主義其實并不是完全新鮮的事物,西方思想的奠基者蘇格拉底就是它的源頭。因為實用主義代表一種在哲學上人們非常熟悉的態度,即經驗主義。它不同于一般的理論,僅僅只是一種方法。[1]29這個方法也沒有什么讓人驚詫之處,只不過是強調并不注重于去看最先的事物、原則、范疇和假定是必需的東西,而是去看最后的事物、收獲、效果和事實。在這個意義上,實用主義是一種以經驗為本的實驗哲學而非由概念出發的理論哲學。在實用主義者看來,“理論成為我們可以依賴的工具,而不是謎語的答案”[1]30-31。
威廉·詹姆斯認為實用主義是理性主義的對立面。就像理性主義只有在抽象的概念面前才覺得舒服,實用主義離開了經驗事實就覺得不舒服。兩者的根本差異體現于對“實在”的認識方面:就理性主義而言,實在一直就是現成的和完全的;從實用主義立場講,實在則是不斷創造的,其一部分面貌尚待未來才產生。誠然,詹姆斯關于實用主義的理解還帶有他本人的特色。比如他認為,實用主義和非實用主義的爭執大半是系于究竟應該怎樣理解真理這一點。而區別只在于:實用主義者所說的真理,只限于指觀念而言;理性主義這樣的非實用主義者所說的真理,一般都是指客體而言。[1]37,158這與我國學者馮友蘭的看法相符。他在總結實用主義的主要特色時寫道:“實用主義的特點在于它的真理論。它的真理論實際是一種不可知論。它認為,認識來源于經驗,人們所能認識的,只限于經驗。至于經驗的背后還有什么東西,那是不可知的,也不必問這個問題。這個問題是沒有意義的。因為無論怎么說,人們總是不能走出經驗范圍之外而有什么認識。要解決這個問題,還得靠經驗。所謂真理,無非就是對于經驗的一種解釋,對于復雜的經驗解釋得通。如果解釋得通,它就是真理,是對于我們有用的。有用就是真理。所謂客觀的真理是沒有的。”[2]需要補充的是,實用主義的真理觀意味著一種“效果論”。換句話說,“任何一種陳述,它的真理就在于它的效果,特別是好的效果”[1]188。
實用主義思想的第二代學者主要有:唐納德·戴維森(Donald Davidson,1917—2003)、理查德·羅蒂(Richard Rorty,1931—2007)、希拉里·普特南(Hilary Whitehall Putnam,1926—)、理查德·伯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1944—)。但無論是第一代還是第二代,實用主義哲學陣營中最重要的人物非杜威莫屬。只有杜威的思想,最充分和強烈地體現了實用主義哲學的精髓,尤其是對于實用主義美學而言。用美國學者舒斯特曼的話講,“實用主義美學肇始于約翰·杜威,而且也差不多在他那里終結”[3]10。這也就是為什么每當人們談到作為一種哲學思想的實用主義時,有意無意地都會想到杜威的原因。從這個意義上講,關于實用主義的兩大問題,最終都聚焦于杜威身上。這也是威廉·詹姆斯甚至曾把實用主義稱之為“杜威主義”的原因。杜威的思想決定了實用主義思想的高度和在20世紀哲學界的位置。有研究者指出,如果深入認識了杜威思想的那種“深刻的簡單”性,那么我們將有充足的理由“把杜威與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一道,視為20世紀真正重要的思想家之一”[4]320。我認為這個評價十分恰當。為此,我們對實用主義以及實用主義美學的討論,有必要集中于對杜威思想的理解上。如果說皮爾士創立了實用主義的方法,威廉·詹姆斯建立了實用主義的真理觀,那么杜威則建造了實用主義理論大廈。
約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誕生在一個中產階級的雜貨商家庭。位于新英格蘭(New England)的維蒙特(Vermont)州的貝林頓(Burlington),那里的人民崇尚自由,篤信民主制度。他于1879年畢業于維蒙特大學,爾后進入霍普金斯大學研究院師從皮爾士,1884年獲博士學位,此后相繼在密執安大學、芝加哥大學、哥倫比亞大學任教。五四運動前后他曾來中國講學,曾經先后在北京、南京、杭州、上海、廣州等地講學,促進了實用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主要著作有《哲學之改造》《民主與教育》《自由與文化》《教育哲學》《追求確定性》《評價理論》《經驗和自然》《經驗和教育》《人類的問題》《藝術即經驗》。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與皮爾士和詹姆斯既相關又有區別。皮爾士的實用主義思想的主旨體現在這一觀點中:“思維的唯一職能在于確立信念”,認識的任務不是反映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而是認識行動的效果,從而為行動提供一種堅強的信念。作為皮爾士在霍布金斯大學的學生,杜威贊同皮爾士的實用主義只是一種方法而并非一種教條的見解。實用主義者所講的方法是指進行哲學思考的特殊方式,它并不拘泥于亞里士多德的主語-謂語的邏輯形式,而是試圖改變思維方式,為思維活動建立一種新的邏輯框架。這種思維方式不是就概念本身而論概念,而是探究它會產生什么效果。但杜威更多的是沿著詹姆斯所改變的,從功利主義的“效果至上”的原則出發的道路發展,按照這一立場,傳統哲學中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論爭都被認為是無意義的形而上學之爭。大寫的真理被小寫的真理所取代。
比如詹姆斯提出,人的認識并無“先存的原型”。真理不是客觀事物的“摹本”,只是經驗與經驗之間的一種關系。一個觀念是不是真理,也不是看它是否符合客觀實際,而是看它是否具有效用。這樣,有用與無用便成為他劃分真理和謬誤的標準。換言之,“有用便是真理”,這就是詹姆斯關于真理的根本觀點。杜威主張,真理只是我們完成任務的一種思想工具,所以他的實用主義傾向于“工具主義”(instrumentalism)。這種“工具主義真理觀”和詹姆斯的觀點實質上是一致的。他也認為觀念、概念、理論等的真理性并不在于它們是否符合客觀實際,而在于它們是否能有效地充當人們行為的工具。又比如詹姆斯明確提出了“真理即是善”的命題,認為只要一個觀念對人的生活有益,它就是“真”的,而且只要它是有益的,它就是善的。杜威也認為真理、道德都不反映現實生活的事實和規律,而是人根據自己的愿望、志向、信仰的發明和創造。道德和真理一樣,只具有實用的意義,只是人應付環境的工具。這是一種以行為的實際效用為善惡標準,把道德看作是應付環境的工具的道德理論。實用主義者認為,道德就是“道德生活”“道德行為”,不存在超越具體的道德實踐的抽象的道德教條。因而他們把“道德境遇”作為分析道德的中心環節。他們指出在人的日常生活中,只有當人處在疑難的境地,并需要在各種價值不同的決定中選擇時,才會出現道德境遇,產生道德問題。道德理論只能從每個具體的道德境遇中產生出來,而且任何道德理論也只是行為的計劃和假設,是個人應付具體情境的臨時措施。
傳統哲學把認知的主體、經驗者同被認知的對象、經驗分開,把精神和物質當作兩個不同領域的東西。但詹姆斯和杜威從實用主義立場出發,試圖利用“經驗”這個曾被不同學派做過不同解釋的概念來超越傳統哲學的主客觀對立的二元論。在他們的實用主義視野里,“經驗”既不是主觀的,也不是客觀的,而是超越物質和精神的對立的“純粹經驗”或“原始經驗”;物質和精神都是對原始經驗進行反省分析的產物,主體和對象、經驗和自然都是統一的經驗整體中兩個不同的方面,它們不能脫離經驗而獨立存在。所以有研究者指出,只有充分“理解‘經驗’一詞的意義,可以得到通往杜威哲學的西北航道,不能理解這一點,就難免會遇難”。[4]67杜威強調經驗的能動性,他認為人適應環境的活動不同于動物消極被動地適應自然,因為人有情感、意志和智慧,他按照自己的意志利用環境,使環境發生有利于人生的變化,以滿足自己的需要。因此,人同環境交互作用所形成的經驗,不是單純的記憶性的知識,而是活動的、實驗的,是由現在伸向未來的過程,是利用過去的經驗,變更現有的東西,建設未來的更好的經驗。對一般的實用主義者來說,對象客體是意志從經驗中切割出來的片斷,經驗和認識的主體也不過是在經驗中支配經驗活動的意志、目的、興趣和情緒等等而已。這就把人的意志作用絕對化,陷入了主觀唯心主義和唯意志論。
按照杜威的看法,“經驗”這個詞具有曖昧性。它的通常含義是指零散的、非整體的,不構成對經驗事實的完整認識。但除此之外還存在著“一個經驗”。它是一個單一、動態、完整的有機整體。這兩種經驗的差異就像孤立、零散、碎片化的“事件”,和具有相對整體性的“故事”的區別。詹姆斯曾指出,事物并非只是提供我們一些經驗的碎片,它還講述一個故事。作為有生命的活動,我們探究具有故事結構的事物,它結束于矛盾沖突的解決,而非客觀的符合一致。[5]78真正有意義的經驗就是類似“一個故事”的“一個經驗”,它并不是可以割裂的,而是彼此相關的,不僅與產生經驗的情境相關,而且經驗自身就是一個綿延不絕的發展歷程。經驗在發生的先后順序上是相關的,不僅是相關,而且是繼續不斷地成長。這種經驗的涵義,乃是因為杜威認為個體是存在于環境之中,是對環境加以作為(Doing);而環境對于個體所加之作為,定會有所反應,此種反應杜威稱之為“施為”(Undergoing)。人類在改造環境或者主動地適應環境時,如筑堤開渠。但與此同時,人類不僅對環境有所作為,同時環境對人類亦提供了可耕之田,或增加了收獲等,這就是環境對吾人的一種施為。此種作為與施為之間的交互活動,就是吾人經驗產生的來源。經驗不只是縱橫相關、綿延發展的,而且經驗自身是有機性的。經驗是具有擴張性、生長性、相關性與預測性的。我們對“水”的經驗是隨著我們在實踐中接觸水的各種情境而不同。水的概念是從與水的各種交互行動中得知,這些交互行動有的是直接參與其中,有的是直接獲得,這說明了經驗的變動性。
導致杜威的實用主義與眾不同之處在于,它的視野開闊,抱負也更大。從本質上說,杜威的實用主義哲學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思想方法,而是“一種關于社會重建的哲學,實用主義哲學把關注點從哲學家和其他知識分子的問題,轉移到了普羅大眾的問題上”。[6]137一切都是為了建立一個更好的社會。這也是與一般的哲學家熱衷于思想體系的建構不同,杜威的研究中十分重視教育的原因。他有兩句名言:“教育即生活”和“學校即社會”。為了實現這個目的,杜威首先選擇從哲學的改造入手。眾所周知,自柏拉圖以來,西方思想呈現出二元論的傳統形態。柏拉圖認為,可見的物質世界與不可見的理念世界形成了本體論的對立,這個對立進而引發了認識論上的二元論,即不同的知識類型的對立。自此以后,我們在亞里士多德那里發現了形式與質料的二元論,在奧古斯丁那里發現了上帝之城與人類之城的二元論,在笛卡爾那里發現了心靈與肉體的對立,在康德那里則發現了現象界與物自體的二元論。在這種種二元論中,哲學家們殫精竭慮地滿足于進行各種邏輯游戲,而無瑕關注真正有意義的問題。用杜威的話講:“當哲學不再成為處理哲學家們的工具,而是成為一種由哲學家們所醞釀的、處理人的問題的方法時,哲學就使自身得到了復原。”[7]33由于傳統中的不同哲學流派在經驗論上體現出一致性(都是根據“感覺”來定義“經驗”),所以改造哲學的努力便必須從改造經驗論開始,而“探究”的理論在哲學改造的過程中處于關鍵地位。[7]57,73為了理解經驗主義的意義,我們需要理解何為經驗。
二、對本體論美學的實踐論改造
經驗是什么?按照傳統的理解,經驗是一種感官知覺,當我們擁有一種經驗時,意味著人們通過自身的感官來感覺對象。在這個意義上,感官經驗是表象性的,它并不能反映我們與世界的直接聯系,而只是擔當了“中介者”的角色。再進一步講,承認經驗作為一種表象性,就必須區分表象與被表象的對象。這就是傳統的二元論哲學的生成基礎。比如,外在的蘋果是物理性的,而內在的蘋果的表象則是精神性的。但問題在于這種內在的表象是靠不住的,否則我們就不會有產生錯覺的問題。由此而產生出一個奇怪的邏輯悖論:經驗的不可靠性使我們無法通過經驗來證實,在思維之外存在著能夠在思維之內產生觀念的對象,盡管正是這種對象在發生學意義上生成了經驗。這就是休謨的懷疑主義的根源。如何解決這個“內部感覺世界”與“外部對象世界”的二元論?讓我們重新開始。何為經驗?我們再次注視著那只蘋果,將手伸向它并抓住它放入嘴中咬一口。所有這些操作的顯著之處在于它們并不是表現在一系列不相關的各自為政的感覺意識,而是表現出一種連續的行動。雖然從邏輯上講,這里存在著“看”“聞”“嘗”的階段性系列,但在實踐中呈現出的卻是一個視覺、嗅覺、味覺最終在吃蘋果這個單一的行動中得以相互協調的活動。這就意味著經驗首先并非如人們想象的只是一種孤立的感覺,而是一種彼此互動的事件。因此杜威下了這樣一個定義:“經驗就是同時進行的行為和經歷的統一體。”[7]53
由此可見,杜威對傳統經驗論的改造方法的核心,是將達爾文的學說運用到哲學中。在達爾文看來,歸根到底,是過程而不是不變性構成了實在的基本特征。這個過程體現為生命體與其生存環境相互作用的活動,在這個過程中,認識主體并不是一個旁觀者而是一個參與者。所以,生命體的概念成為杜威改造工作的根本所在。[7]63因此,杜威將他的學說稱之為“實驗性的認知理論”。在這種理論中,認識論所關心的不是“知識”而是“認知”。所謂認知,也就是對問題情境的“探究”過程,它是生命體對有問題的情境的回應能力。如果說傳統的整體化認識論強調對世界的整體性把握,那么實驗性的認知活動則堅持這樣一種立場:進步總是零零碎碎的。它只能零賣,不能批發。通過對人類行為的強調,杜威順理成章地取消了傳統的二元論思想。這里的關鍵在于不要孤立地看待人類活動。杜威提出:“人作為一個自然的生物,他和動物一樣地生活著,有飲食、斗爭、恐懼和繁殖。當他生活著的時候,在他的行動中有些行動產生了理解而有些事物發生了意義。”這種活動“尋求著和創造著一個人們可以在里面安全生活的世界。”[8]299這樣對哲學而言,并不需要糾纏于主觀與客觀、精神與物質等的二元論的問題,而是重建本體論的基礎。在杜威看來,“只有當我們取消了本質和存在之間的分離情況的時候;只有當我們把本質當作是要在具體經驗對象中借行動來體現的可能性的時候”,我們才能更好地認識經驗的實質。[8]309
所以在杜威這里,“經驗”的涵義呈現出一種開放性,他把生物學的涵義也摻入其中。從生物與環境的交互行動中提示我們:經驗應該是多元性的,即產生經驗的情境、內容、關系都來自于實際的生活,是個人經驗生活的一個單元。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方能理解杜威的實用主義本質上是一種工具哲學。所謂“工具就是用來當作達到后果的手段”。[9]120根據這種學說,經驗是工具性的,就是強調經驗自身并不就是價值所在。經驗之所以可貴,在于它能夠替我們解決具體生活中的那些實際問題,從而提升人類的生活質量。唯其如此,從達爾文學說中提取出來的“過程”(Process)也是杜威哲學上的一個重要概念。從生物的演變來看,個體總是處在一個發展的歷程中,過程是發展的各個階段之延續性的結合。由于不同的環境而有不同的交互活動,經驗在這種過程中得到發展。從工具論的視野看,傳統上對知識的“旁觀論”(The Spectator Theory of Knowledge)的說法是無法成立的。按照這種理論,我們能夠獲取知識在于知識本身完全是客觀性的外界存在物,這意味著知識可以脫離認知者,似乎能夠置身于認知者之外,而知識本身是絕對地客觀存在著。這種說法完全忽視了知識與認知者之間產生的相互作為。在杜威看來,“經驗方法的全部意義與重要性,就是在于要從事物本身出發來研究它們,以求發現當事物被經驗時所揭露出來的是什么。經驗材料所具有的這些特性與太陽和電子的特性一樣真實。它們是被發現出來的,被經驗到的,而不是利用某種邏輯把戲推究出來的。”[9]4
在杜威看來,把審美藝術經驗與日常生活經驗分離開來的做法完全是人為的、不合理的。他的“藝術即經驗”也意味著“經驗即藝術”。在《經驗與自然》一書中,杜威已明確提出這個觀點,以此來解釋古代希臘藝術。他認為“我們從其含蓄的意義方面來講,把經驗當作是藝術,而把藝術當作是不斷地導向所完成和所享受的意義的自然的過程和自然的材料”。因而,“在經驗的事實上,使得人們知覺到好的乃是藝術,那些互相溝通的藝術和作為社會溝通的擴大延續的文藝。”[9]274從杜威對經驗的這種闡釋中我們能夠發現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杜威的實用主義別具一格之處在于,它本質上具有一種走向“藝術哲學”的傾向。正如一位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樣:“杜威之方法的核心,在于將倫理學理解為幫助人們更豐富地生活,更敏于事情,以及更加充滿情趣地介入生活的藝術。”[5]138因此,就像康德哲學使現代哲學發生了一場哥白尼革命。有研究者提出,杜威的實用主義思想是“一次使倫理學以想象力為軸心的哥白尼轉折”[5]103。這個觀點是否妥當或許可以商榷,但由此使我們再次意識到經驗之于杜威哲學的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因為杜威美學理論的核心在于這一主張,即“藝術最直接最完滿地表明,作為經驗的經驗是存在的”[5]162。從這個意義上說,杜威的實用主義在本質上就通往藝術哲學。
杜威明確地指出,哲學的重大缺點就是有一種武斷的“理智主義”(intellectualism),就是指這樣一種學說,它認為一切經驗過程都是認識的一種方式,而一切題材、一切自然,在原則上就要被縮減和轉化,一直到最后把它界說成為等同于科學本身精煉的對象所呈現出來的特征的東西。[9]16為了避免落入這種陷阱,杜威十分重視經驗中的情感因素。他強調,確實不錯,我們的行為可能被情感性的偏見所歪曲,但是同樣確實的是,我們的行為也將為情感之缺乏所歪曲。對于杜威來說,如果我們要理解藝術,那就必須根據作為經驗的藝術的整體來看,不能忽視情感的重要性。用杜威的話說,“沒有情感,也許會有工藝,但不會有藝術。”[10]75眾所周知,在《藝術即經驗》這部書里,杜威向讀者提供了對于美學基本問題的深入分析,它涉及諸如藝術的表達、藝術的形式、題材與藝術作品本身的聯系、藝術品之間的聯系等等。從這個方面看,我們完全可以說,由于杜威把美學納入他的經驗觀點的中心,所以這些問題暗示了他的整個哲學。有研究者指出,杜威所取得的最深刻的洞見在于把他的美學理論的含義聯系到民主生活之目標的廣大觀點,聯系到文明的哲學。[11]這話并不過分。
研究者通常認為,杜威的學術生涯的早期和晚期,藝術與審美經驗在杜威的經驗分析時都扮演了極為重要的角色,唯獨他的中期相對顯得有些撲朔迷離。原因在于那個時期杜威所做工作的中心在于解決“生活即藝術”這個觀點。但這個觀點的含義既不是像后現代主義那樣,徹底消解藝術與生活的差異,甚至把拉屎拉尿當作“行為藝術”,也不是像唯美主義那樣舉著“為藝術而生活”的旗幟,反而把生活與藝術隔離開來。杜威的意思是批判“藝術的博物館化”,提醒我們不要以為只有那些能夠進入博物館,或者說就存在于博物館中的東西才是藝術品。在杜威看來,“歐洲的絕大部分博物館都是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興起的紀念館。”[10]7為此他強調藝術世界與日常生活的緊密聯系。生活與藝術的這種關聯通過“意義”的中介實現。就像詹姆斯重視“真理”,杜威的思想十分重視“意義”。杜威承認意義是普遍的也是客觀的,是獨立于心理景象、感覺印象以外的。但這并不表明意義是脫離人的存在而存在的、一個沒有時間性的精靈鬼怪,或者脫離具體事情的一種無聲無色的邏輯潛在物。[9]123再進一步,“藝術即經驗”的含義也意味著強調藝術的基本形態就在于它是意義的呈現者。
杜威認為,“大概沒有人在說藝術作品沒有意義時,是想說它們不存在任何意義。這些人似乎只是要將外在的意義,即存在于藝術作品本身之外的意義排斥出去而已。”[10]90當杜威提出“生活即藝術”而“藝術即經驗”時,他不僅是充分意識到了生活世界中所存在的一種“感性化”現象,同時也看到了我們擁有把握這種意義的手段:直覺。強調感性的意義在于,“感性的性質是意義的負載者。但是它不像是車負載貨物,而是像母親懷著孩子,孩子是她自身有機體的一部分。”[10]129意義之所以為“意義”,就在于它是能夠被我們通過“直覺”而直接感知的。所以“直接意義”這個概念是一種重復性的表達。意義就意味著超越概念的直接性。杜威主張:每個具體的、實際上所完成的心理上的結果都是直覺。“直覺標志著理性與感覺、普遍與特殊之間最后的綜合”[4]40。直覺意味著憑部分逐漸掌握整體,所以它是我們把握詩性意義的最佳手段。杜威認為,準確說來,想象的最高形式是對事物隱含意義的洞然于心,這種意義是記憶或感知不可見的東西,也不能靠思考過程反思獲得。可以把它定義為“直接感知意義”(direct perception of meaning)——就是感官形式中理想的價值,或者說是感官形式自動的發現,這種發現最有意味、最理想,因此也最能反映智力,同時也最吸引情感。[4]41
誠如美國學者亞歷山大·托馬斯所指出的,這些論述足以表明一點:“杜威對于意義的討論是他經驗形而上學與美學理論之間至為重要的連接。”[4]211當然,杜威這些論述的目的所在,乃是指望通過藝術來闡明“經驗”的意義,對于杜威來說,藝術作品是對于意義完滿的可能性富有意味的探索。這種探索通往他獨創的“一個經驗”。杜威特別強調,“這一個經驗是整體,其中帶著自身個性化的性質以及自我滿足。”[4]233意義存在于“一個經驗”中,通過“直接感知”的直覺而被我們獲得。所以直覺就是經驗成為有意識的運作和非認知維度。這就是說,直覺發揮功能是為了實現經驗的個體性,個體性也是對經驗整體性、整合或自我歸屬的感知。因而從某種意義上講,經驗、意義、直覺這三個概念是緊密聯系在一起的,它們共同構成并體現了杜威的“生活即藝術”的主張。“藝術即經驗”的意思,也可以說藝術無非是人類的生存中追求人類存在中具體體現的意義與價值。用托馬斯的話說:“生活的藝術就是杜威倫理學、民主哲學、教育理論背后的目的地所在。藝術地對待生活就是運用想象與反思探索當下的多種可能性。”[4]311杜威關于經驗與直覺的關系的討論之所以令人深思,是因為事實上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既存在著“非解釋的語言理解”,也存在著“非語言的有意義的經驗”。唯其如此,杜威旨在“恢復審美經驗同生命的正常過程之間的連續性”才擁有真實的基礎。它同時也反映了杜威的實用主義美學的一個重要特征:身體自然主義。[3]20
三、作為一種生活經驗的審美活動
杜威的經驗是,“經驗是透過皮膚的交往”[5]134。他的意思是,人類總是肌膚相親地生活與思維著,我們存在于他人中間,并且通過他人而存在。因此杜威強烈要求:無論冒多大的風險,藝術還是應該撤去它那神圣的分隔而進入日常生活領域,在這里藝術可以作為建構性的改革的指導、范式和推動,而不僅僅是對現實的一個外來的裝飾或一個令人向往的想象上的改變。舉一個最明白的例子,陶淵明《飲酒·其五》:“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首詩完全是對詩人日常生活中的一個情景的白描,語句如行云流水十分自然。但它能被詩人提取出來成為一首膾炙人口的詩篇,完全在于詩人憑直覺意識到了在這種日常生活里有著非同一般的作為“一個經驗”的深刻意義。當我們品味這首詩時,你完全可以說這是詩人真實生活的某個瞬間的記錄,從字面上看甚至毫無“詩意”可言,但它卻能深深地打動我們,讓我們產生一種共鳴。千百年過去了,它還是顯得如此新鮮。這讓人尋味杜威的這番話:“經驗并不是屬于某一個人所有的,它是屬于自然的。”[9]148自然人或者說人的自然性就是身體的在場,它是審美直覺得以實現的前提。
所以說“一個經驗可以為許多人所共享”[4]234。在這個意義上,實用主義美學繼承了尼采的有關思想,屬于一種“身體美學”(somaesthetics)。按照美國當代學者舒斯特曼的意見,身體美學可以暫時定義為:對一個人的身體經驗和作用的批判的、改善的研究。[3]354這個定義的平庸性是顯而易見的,但舒斯特曼的這個見解值得一提:對“實踐的身體美學”的強調。換句話說,身體美學具有的一種實踐性意味著“做”而不是“說”。由此可見,身體美學的實用主義特征就在于,它不屬于“專業主義”的理論空談,而是對生活世界里具體事物的感同身受。身體美學的提出是對以身體為基礎的綜合性的“感受力”(perceptiveness)的強調,因此,身體美學并非如舒斯特曼所說的,是對人的身體之美本身的關注(盡管這種關注在古代希臘和羅馬以及亞洲國家都有豐富多彩的案例),而是通過身體(不是大腦)對美的存在的領悟和接受。美國學者費什米爾提出:“如果通過杜威接近哲學,而不是繞開他的話,那就標志著大多數傳統認識論、形而上學、美學和倫理學問題的終結。與此同時,則促進了在人的認知、經驗、藝術與道德生活這些問題上哲學的介入。”[5]40這話的意思是指杜威哲學具有一種繼往開來的革命性。這樣的評價很高,但恰如其分。這就是杜威能夠與維特根斯坦和海德格爾一起并列為20世紀三大哲學家的原因。
具體回到我們所討論的身體美學上來,理解這個概念涉及對“美的存在”的認識。杜威指出,當我們說人類存在或生活在自然界中時,對“在”這個關鍵詞的準確理解極為重要。杜威的意思,它不是像“大理石裝在箱子中”,或“零錢‘在’口袋里,或油漆‘在’罐子中”那樣的,而是像“植物在陽光和土壤中”這類的例子。在這個語境中,“在”的含義不再是簡單的地理位置所在,而是意味著一種相互作用。[6]76我們強調美的存在之“在”具有同樣的意思。它體現了一種意義和價值,這種價值意味著美雖然有一種“有用”性,但這種有用性與諸如飲食起居的日常生活的“實用”性不能相提并論。這是因為“美”并非是一種具體的東西,而是具有物質性的客體在我們的精神世界里引起的一種反應。所以說,美是相對于具有美感意識的審美的人而言的一種價值。根據杜威的觀點,被認知的對象和具有價值的對象之間的關系,乃是現實與可能之間的關系。所謂“現實”包括既有的條件。所謂“可能”是指一種現在尚不存在,但可因現實條件的應用而使其存在的目的或后果。因此,“‘可能’就其對任何既有的情境而言,乃是尋求這個情境的一種理想,從操作論的定義(用行動去說明思維)的立場出發,理想和可能是意義相同的兩個觀念。”[8]302美的存在既意味著一種“可能”性,同時也意味著一種理想的境界。作為一種經驗的藝術作品正因為體現了這種價值而得到我們的珍惜。
盡管“藝術何為”的困惑一直糾纏著試圖認真對待藝術的人們,“為詩一辯”自古以來就是藝術哲學的基本職責,但事實上這些都屬于沒有必要的事。用杜威的話說,凡是不可避免的東西,就無須去證明其存在。這適用于絕大多數勞而無功的美學理論。在杜威看來,只要人繼續是一個人,就總是要有關于價值的觀念、判斷和信仰的。如果有人企圖一般地去證明其價值的存在,這是最笨不過的事了。因為“價值總是繼續存在著的”。就像正義是值得尊重的,但“這并不依靠我們能夠證明有一個正義的實有事先存在著。”[8]307對藝術呈現一種價值的這種強調,有助于我們破除對藝術品的盲目崇拜。因為就像杜威所說:“一件藝術作品,不管多么古老而經典,都只有生活在某種個性化的經驗之中時,才在實際上而不僅僅潛在地是藝術作品。”[10]118以上這些闡述,都體現了實用主義從事物本身出發,在具體語境中進行思考的特點。從實用主義的視野來看,歷來被奉為神圣的藝術,是人能夠有意識地,從而在意義層面上恢復作為活的生物的標志的感覺、需要、沖動以及行動間聯合的活的、具體的證明。由于經驗是有機體在一個物的世界中斗爭與成就的實現,它是藝術的萌芽。甚至在最初步的形式中,它也包含著作為審美經驗的令人愉快的知覺的允諾。[10]19,26這是日常生活與藝術作品之間并不存在隔離帶的前提。
如前所述,實用主義并不排斥日常生活經驗,而是對它們十分重視。這就開辟了一個新的理論視野,有助于我們發現在別的理論中難以意識到的東西。比如按照通常的慣例,人們對“以文載道”的作品頗有批評,認為這有損于一部作品的藝術價值。但杜威卻別開生面地指出,在絕大多數情況下,對藝術品中說教和經濟與政治上的宣傳在審美上的拒絕,會建立在過分重視某種價值而犧牲其他價值的分析之上。這些作品除了對那些處在同樣片面狂熱的狀態中的人以外,在其他人身上所出現的不是提神而是厭倦。[10]200不得不承認,杜威的這個似乎與“常理”相悖的見解是十分深刻的。又比如杜威提出,美的藝術總是人類與其環境的一種相互作用的經驗的產物。他以建筑為例指出:“絕大多數的廠房建筑之丑陋與普通銀行建筑之令人厭惡,盡管它取決于技術與物質方面的結構缺陷,同時也反映了一種對人的價值的扭曲,而這種扭曲又結合進了與建筑相關的經驗。”[10]257這就是說,藝術作品中審美價值的體現歸根到底是對人性的反映。再比如杜威指出,“‘無利害性’并不表示無興趣性。”他認為,“在審美對象中,強烈的感性性質占據著主導地位,這本身從心理學上說,就證明了欲望的存在。”[10]284這個見解對康德的形式論美學觀提出了很有根據的挑戰。還比如杜威寫道:“沒有人在看到小孩子游戲意圖時,不意識到游戲性與其嚴肅性完全的融合。”因而他強調,喜劇之外的藝術作品也常常具有消遣性,“但是這些事實并非根據消遣來定義藝術的理由。”[10]310-311
我們該怎樣理解和評價以杜威為代表的“實用主義美學”的意義?杜威在《藝術即經驗》的開頭部分就指出,許多關于藝術的理論已經存在了。要說明提出另一種關于審美的哲學的理由,就必須發現一個新的研究方法。[10]10,310杜威以身作則做到了這一點。他的實用主義通過對“作為意義的經驗”的強調構成了實用主義美學的核心。用杜威的話說:“除非一種藝術哲學使我們知道藝術相對于其他經驗形式的功能,除非它說明為什么這種功能實現得如此不充分,除非它表示功能能夠充分實現的條件,一種藝術哲學就是無效的。”[10]11,310在他看來,準確和深入地理解藝術須從理解日常生活中的“經驗”著手,這樣有助于我們實現這個目標。用他的話說:“一種從美的藝術與普通經驗間已發現性質的聯系出發的關于美的藝術的觀念,將能夠顯示有助于一般人類活動向具有藝術價值的事物的正常發展的因素與動力。”[10]10,310杜威以一部厚重的著作向我們全面地論述了他的這個觀點。除此之外,他的美學思想滲透于他關于教育、倫理、政治等一系列著作里。在我看來,杜威的實用主義美學不僅自成一體,而且也很有創新精神,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但與其說他的美學是另一種“藝術哲學”,不如講是一種“生活詩學”。它不僅僅局限于藝術家的創造性活動,同樣涉及整個人類文明的發展。在這個意義上,這是一種以人性的培養和人格的塑造為中心的、具有開放性的“大美學”。
參考文獻:
[1] 威廉·詹姆斯.實用主義[M].陳羽綸,孫瑞禾,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1.
[2] 馮友蘭.三松堂自序[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2.
[3] 理查德·舒斯特曼.實用主義美學[M].彭鋒,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2.
[4] 亞力山大·托馬斯.杜威的藝術、經驗與自然理論[M].谷紅巖,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2010.
[5] 斯蒂文·費什米爾.杜威與道德想象力[M].徐鵬,馬如俊,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6] 詹姆斯·坎貝爾.理解杜威[M].楊柳新,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
[7] 羅伯特·塔利斯.杜威[M].彭國華,譯.北京:中華書局,2002.
[8] 約翰·杜威.確定性的尋求[M].傅統先,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9] 約翰·杜威.經驗與自然[M].傅統先,譯.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
[10] 約翰·杜威.藝術即經驗[M].高建平,譯.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11] 拉里·希克曼.閱讀杜威[M].徐陶,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34.
(責任編輯:紫嫣)
Experience is Dewey′s Art
XU Dai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International Culture,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In the eyes of the historians of traditional aesthetics, John Dewey the pragmatist philosopher is not a veritable aesthete. But in fact, he elaborated his aesthetic ideas in a voluminous work. Besides, his aesthetic ideas also permeate his writings on education, ethics, politics and etc.In this sense, his pragmatic aesthetics not only merits the name of aesthetics, but is also very innovative and worthy of serious consideration. Rather than a "philosophy of art", it is a kind of poetics on life". Not confined to the artists′creative activities, it also treats of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civilization. This makes it paramount for us to heed Dewey’s aesthetic thought because it is an open-ended "mega-aesthetics" with a view to fostering humanity and shaping personality.
Key words:Dewey; pragmatism; theory of art as experience; mega-aesthetics
中圖分類號:B83-0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2095-0012(2016)02-0001-08
作者簡介:徐岱(1957—),男,山東文登人,浙江大學文科資深教授、人文學部主任、博士生導師,主要從事美學理論與藝術哲學、跨文化批評、中國現當代小說等研究。
收稿日期:2015-10-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