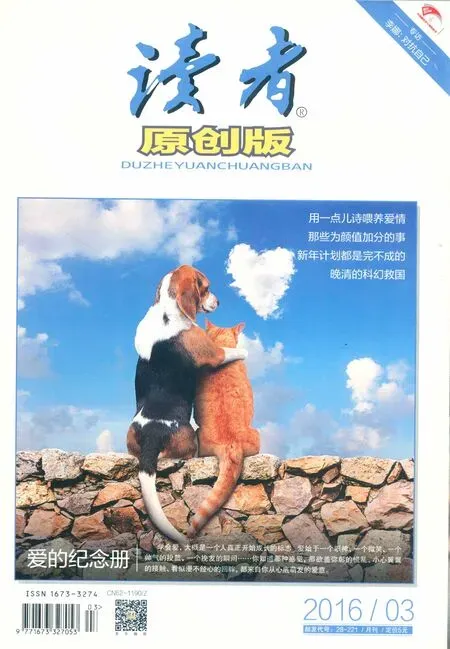一顆橙子
文_涼 炘
?
一顆橙子
文_涼炘

那個女孩,唇上有痣。剛洗完頭發,就披著風干。
她踮起腳尖,捋一把香椿芽,估計要炒雞蛋吃,或是烘干泡成茶。她經過院里養的鴿子群,咕咕的叫聲逗得她笑。賀蘭山的長風拂過銀川平原,剛好將天空吹出一些湛藍,這讓她欣喜,微微閉眼,仔細呼吸。她的脖頸上,有晨露似的汗珠,讓人有吮吸的念頭。
她從上至下,從左至右地掃視這藍天,于是看到了趴在墻頭上的我……
我左腳挫傷性骨折,打了石膏,母親坐在床頭諷刺我:“你小時候爬樹不是挺在行?現在爬個墻還能摔下來。”這是我高中時代全部記憶的起點。
她叫杜秋莼。
“莼菜,多年生水生宿根草本。葉子呈橢圓形,深綠色,浮生在水面或潛在水中。開暗紅色小花。”
時隔多年,第一次查了這種植物,恍惚之間覺得,它像極了她。
“莼菜”深綠的葉色,約等于她性格中的沉穩。高中時代,她做了三年的學習委員,像每一部糖水味兒泛濫的青春小說里寫的那樣,她抱著一沓厚重的作業本,走過窗外的走廊,陽光充當著畫匠,給她的長發描上金邊。男生們想盯著她猛看,但礙于面子,只匆匆掃過一眼,一眼就心潮澎湃,不能自已。
我作弊了——竊取了作家情書的撰寫方式,在她那里贏得了較高的分數,從一堆情書中脫穎而出,獲得了她的回信。現在想來,作弊的自慚隱隱可見,從這顆浸滿油鹽的心中生出芽來。
在《愛你就像愛生命》中,王小波的每一封信,開頭都寫著“你好呀,李銀河”,于是我把“你好呀,杜秋莼”放在了信的開頭。
后來她告訴我,收到那么多亂七八糟的信,很多以“美女”“莼莼”“阿莼”為開頭,都讓她深覺肉麻,無法閱讀。唯獨我的信開門見山,直呼名字,讓她倍感真誠。
但和她戀愛與不戀愛,沒有實質性區別。我曾為此懊惱不已,并痛斥她過于低下的戀愛熱情。白天在一個班上,沒有約會的空間;夜里兩個人的手機都被父母管制,更覺煎熬,從她簡短的“晚安”里,我看不見愛意深濃的影子。
我想吻她,想擁抱她,想牽著她的手游蕩街頭。我感受到身體中許多欲望正在組建,像一支軍隊,槍支火炮都已備好,唯獨找不到進攻的方向。
許多年過去,才知道她的愛意,恰如“開暗紅色小花”。她曾若無其事地從第一排座位走到我的座位邊上,剝開一顆橙子,送到我手邊。她曾與我打賭,說從《必背古詩詞合集》中隨便挑一頁來背誦,背不出就抽皮條或者刮鼻子。
我自然是輸了,《桃花源記》死活背不出來。她拉開我的袖子,二指并起,狠狠抽下來,留下一寸殷紅。
年輕、狂躁的我,又怎能理解一個內斂的女子內心的巨大熱情?像地下的暗河,洶涌無聲,靜謐奔騰。
我們的高考分數差異巨大,她去了沈陽,我去了武漢。一千多公里,“地大物博”在我心里首次淪為貶義詞。
十多年過去,我失去了她全部的聯系方式。我所記得的一切,就那樣隨風而起,又隨風散落。
昨天買香蕉時,水果店老板說,加顆橙子剛好10塊錢,我說行。
此時此刻,寂靜的寫字臺上,我將橙子剝開,清香撲面而來。仔細想想,她刻我的時候,我也磨了她。這符合宇宙的規則。她不可能毫不費力就讓我迷惘,我也不會平白無故讓她心傷。彼此的付出顯而易見,年輕的日子,就擺在那兒。
纖手破新橙,酸甜盡難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