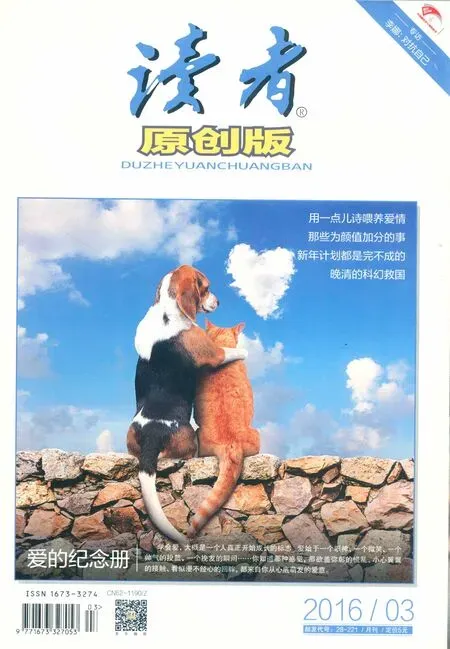晚清的科幻救國
文_hayashi
?
晚清的科幻救國
文_hayashi

劉慈欣的《三體》大熱之后,國內讀者的科幻熱情一下子被激發了起來。其實百年前,晚清的讀者們就有了第一次與西方科幻接觸的機會。在那個時候,科幻既不是用于消遣的飯后讀物,也不是哲學或社會學的研究文本,而是被視為救國救民的良方之一。
觀西人小說,大有助于學問也
1903年,美國的工人階級已經能從報刊亭的廉價讀物中讀到一種叫作“科學幻想故事”的東西了。自1896年一本只刊登虛構故事的雜志《大商船》問世以來,閱讀這些故事的成本就越來越低。而閱讀這些故事的目的,也越來越往娛樂的方向發展,城市的低薪工人們在百無聊賴的夜里,靠著書中的各種虛構故事,暫時逃離繁忙又平淡的日常生活。
也是在1903年,晚清學者孫寶瑄在他的《忘山廬日記》里表達了自己對西方小說的看法:“觀科學小說,可以通種種格物原理;觀包探小說,可以覘西國人情土俗及其居心之險詐詭變,有非我國所能及者……觀西人小說,大有助于學問也。”文中的科學小說即科幻小說,包探小說即推理小說。按照孫寶瑄的說法,閱讀這些小說的目的在于了解西方人,增長學問。
在洋槍大炮的猛攻之下,清廷終于發起“洋務運動”來學習西方技術。但技術歸技術,所謂中體西用,思想終歸還是老祖宗的好。學西方人的技術,也是為了“制夷”。但有些人怎么也接受不了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還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就在這時,法國小說家儒勒·凡爾納的科幻小說進入了晚清文人們的視野。出于“亡國滅種”的憂患意識,文人們都敏銳地感覺到,閱讀這些科幻小說是引起民眾對西方科學技術的注意,甚至產生好感的好機會。尤其是凡爾納帶有些許科學享樂主義的想象,既能在無形間增長民眾的科學知識,又能借凡爾納筆下的美好景象給予民眾精神動力,可謂一舉兩得。
當時比較重要的兩位科幻小說譯者,都是我們非常熟悉的人物:一位是“維新骨干”梁啟超,一位是“新文化運動主將”魯迅。
梁啟超的“豪杰譯”
梁啟超或許確是一名類型小說的愛好者,又或者對類型小說救國抱有極大的信心——他以翻譯者的身份引進了眾多國外的推理和科幻小說。他以“飲冰子”的筆名于1902年翻譯了法國作家佛琳·瑪麗安的《世界末日記》。次年,他又在逃亡期間抽空和羅普一道完成了凡爾納《兩年假期》的翻譯。梁啟超翻譯的《兩年假期》,譯本定名為“十五小豪杰”。書名的改動有藝術方面的考慮,也有廣告的作用——書本的譯名既要讓人迅速清楚書本內容的定位,又能勾起讀者的購買欲。梁啟超的這一改動,讓《十五小豪杰》馬上受到青少年讀者的歡迎。
但梁啟超的翻譯改造遠遠不限于此,除了書名之外,他還按照中國人熟悉的章回體對全書做了重新編排。到這一步,我們還可以說梁啟超只是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微調,但接下來,他刪去了大量關于科學原理和知識的部分,直接敘述由這些科技帶來的美好未來和奇妙體驗,導致譯本比凡爾納的原書薄得多。
其中最根本的原因,可能是文科生梁啟超自己也不知道那些理工科段落講的到底是什么,與其勉強翻譯,不如干脆整段刪去,不然一旦出現技術失誤,就相當危險。再者,他梁啟超都不懂的東西,就不要指望平頭百姓能懂了,所以這些內容沒有市場需求,譯出來還徒增閱讀負擔,不如不譯。反正其目的是告訴民眾“維新變法是天堂,科學技術是橋梁”,這點是做到位了的。
這種以受眾和自己的條件為出發點,簡譯甚至不譯原文的做法,后來被稱作“豪杰譯”,這個名稱就來自梁啟超翻譯的《十五小豪杰》。“豪杰譯”缺乏對原著的忠誠度,受到了后世不少學者的詬病,但其實這里面也有一些客觀原因。晚清的科幻翻譯固然有通過原著直接譯介的篇目,然而根據當時中國學者的語言習得情況,從日文轉手翻譯的更多。從日文翻譯就意味著晚清文人手上的資料已經是二手甚至三手的,和原文已有差別,再加上當時西方科幻小說的翻譯隊伍整體水平不高,日本文人又因為文化阻隔而存在理解上的差錯,這些錯誤在無形中也就被放大了不少。
魯迅的《月界旅行》
在凡爾納小說《從地球到月球》的開篇,英譯版還很準確地翻譯成“在南北戰爭期間,一個嶄新且影響力巨大的俱樂部出現在馬里蘭州的城市巴爾的摩”,但到了日譯版那里,譯者井上勤就犯了兩個錯誤,他把英譯版的“War of Rebellion”誤譯成獨立戰爭,又把巴爾的摩誤寫成馬里蘭州的首府。于是,到了中文譯者魯迅這里,原始材料就已經有硬傷了,對于當時對美國情況不熟,又只學了一年日語的魯迅來說,識別出這些錯誤顯然是不可能的。于是,魯迅保留了這些錯誤,在此基礎上,他又加入了一些自己的“私貨”。
魯迅在這個簡簡單單的句子里加入了大量的描述性內容,比如“學習過世界歷史的人都知道有一個叫做美利堅的國度”,“即使孩子都知道美利堅的獨立戰爭是一件多么轟動的事情”,“巴爾的摩是一個車水馬龍、摩肩接踵的著名都市”,“當你看到俱樂部前飄揚的美利堅旗幟時,莊嚴的情感油然而生”。魯迅用這些描述幾乎把原文的長度拓展了一倍,這樣做的原因,一是為了渲染一種科學使生活更美好的氣氛,二是為了做必要的普及:普通民眾很可能不知道巴爾的摩,甚至可能不知道美利堅,即使知道,也可能沒有意識到它們的重要程度。魯迅的思路,就是做一個普及,把這些國家和都市往偉大了寫,先入為主地制造一個“不明覺厲”的閱讀效果。
即使加進了很多“私貨”,但魯迅的成書(中譯名為“月界旅行”)的篇幅比起原文仍舊少了許多。但是魯迅的“豪杰譯”并沒有使故事本身的魅力降低,美籍華裔科幻作家劉宇昆讀過魯迅的譯本,點評它是“生動而優雅”的。雖然《月界旅行》能否被看作《從地球到月球》的一個譯本尚需討論,但魯迅很好地實踐了他在《月界旅行》序言中的觀點:“蓋臚陳科學,常人厭之,閱不終篇,輒欲睡去,強人所難,勢必然矣。惟假小說之能力,被優孟之衣冠,則雖析理譚玄,亦能浸淫腦筋,不生厭倦。”魯迅試圖用科幻小說這種更容易被人們接受的方式傳播科學,加之中國原本沒有科幻小說的基礎,他能有如此洞見,實屬不易。
除了翻譯外國著作,20世紀初,晚清的文人們還自己創作了許多科幻小說。比如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等現實題材小說聞名的吳趼人,創作了一部名為《新石頭記》的小說——這是曹雪芹《紅樓夢》的續寫,書中講述賈寶玉出家后進入清末“野蠻世界”和誤入“文明境界”的故事,甚至還有賈寶玉坐潛水艇的情節,也為當時的中國科幻小說增添了一抹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