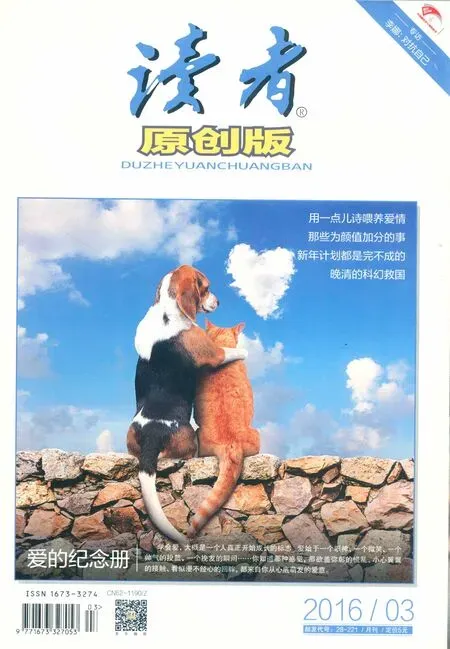流年
文_閆 晗
?
流年
文_閆晗

小時候過年家庭聚會,大人忙碌著人情往來,孩子們經常陷入無所事事的狀態。爺爺的兩三個外甥,也就是我的遠房叔叔,每年過年都來做客,幾個人把炕坐滿了,姑姑和大媽要忙著下灶做飯,我和表哥表妹在屋里屋外轉來轉去,插不上嘴,也插不進腳。電視機通常整天開著,但節目的聲音被說話聲淹沒,什么也聽不到。
有時候我們會走出院子,在村子里閑逛。冬天,到處都是灰黃色的,家家門前都堆著干掉的玉米秸、花生蔓,干冷的空氣里混合著鞭炮的氣味,混著積雪的土路被凍得很硬。有一些小男孩拿著拆散的鞭炮和點鞭炮用的香,在角落里冷不丁發出噼啪的響聲;有的拿一種摔在地上就會響的炮仗,突然就朝你腳邊扔過來,嚇人一跳。我不喜歡聽鞭炮響,覺得既聒噪又危險,便常常躲在表哥身后,遠離那些調皮的小男孩們。
有一年,我們走出了村子,過了村子南邊的河,走到種莊稼的田地里。田地里的作物都被收回了家,裸露的土地一派蕭索,道路兩旁的樹下堆積著落葉和枯黃的草。有一戶人家的田里豎著一塊墓碑,還有隆起的墳包,墓碑上刻著繁體字,那字我并不認識,卻默默悲傷了一會兒。
算不上什么奇特的經歷,我卻對那天的場景印象很深,想起冬季,腦海中就會閃現出那些樹、田野、枯草和墓碑。
對于過年,即便在童年,有對穿新衣服的期待和見到親戚家同齡小孩的喜悅,我還是有很深的寂寥感。一大家子的飯做起來費勁,常要挨到下午三四點才能吃上飯,飯到桌上也涼了一大半。吃完飯再七手八腳地收拾,姑姑、大媽們能歇下來說說話就已經天黑了,大人們又開始張羅著全家穿上大大小小的棉衣,準備騎車回家。按照慣例,爺爺會對外甥們拿來的禮物推讓一番,讓他們帶走,禮物無非是一些餅干、奶粉、麥片、芝麻糊之類的。但爺爺有次說了句“這么一點兒東西,我哪兒還能都留下”,讓場面陷入了尷尬,于是,那回遠房叔叔們就不好意思把禮物帶走了。之后許多年,爺爺的這句話都常常被拿出來調侃。
我不喜歡分離的時刻,從天開始變黑的那一刻起,我就陷入了莫名的憂傷中。我希望表妹和我可以留下來,在爺爺家住下,看爺爺燒炕、放鋪蓋、焐被子,穿著奶奶超級沉的大棉靴,躺在被窩里,在昏黃的燈光下,望著黑漆漆的窗外聽爺爺說家族軼事……可惜這愿望從來沒有實現過,表妹總是很想回自己家,她家離得遠,往往最先走。
有一年過年下了大雪,姑姑全家坐公交車去爺爺家,回去的時候等不到車,爸爸便騎著摩托車分兩趟把她們全家送回去了。雖然爸爸那天穿著厚羽絨服,但也被寒風吹透,渾身冰涼,病了一個多月才好,后來每年冬天他都會感冒很久。如果能穿越回去,我一定攔住他,讓姑姑她們住下來。
現在,爺爺奶奶不在了,我們各自長大,奔向遠方,即便是那樣寂寥的團聚,也無法得到。我努力回想,還是有許多美好的時刻的。記得有一年,我扎著長馬尾,有個不會聊天的遠房叔叔說我個子矮,不適合留長發,表妹個子高,留長頭發會很漂亮。我訕笑著,不知如何回應。爺爺卻表示不愛聽這話:“誰說的?我覺得我們丫頭長頭發挺好看的。”奶奶也附和,還說我比表妹好看多了。我心里明白那并不是實情,卻很感動,他們這樣愛我,而且如此理直氣壯地偏愛。
突然很想念從前那些歲月,即便寂寥,也是獨一無二、難以復制的好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