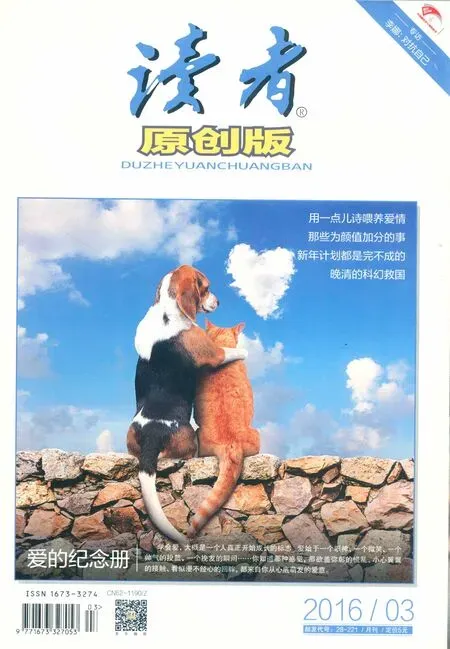穿越歷史的人
文_亢 霖
?
穿越歷史的人
文_亢霖

2016年1月22日,我的外公以90歲高齡辭世。他是個普通人,前半生是個普通的軍人、軍官,后半生是個普通的地方干部。像許多先他而去的人一樣,他不乏叱咤風云的過往,終究歸于平淡。
但他穿越了歷史。
現在是個多元的時代,從“50后”到“00后”,所有人都在激烈地爭議歷史,更爭議著因歷史而形成的現狀。而那些真正經歷過、見證過歷史的“20后”,幾十年來卻保持著沉默,似乎從未發聲。其實那一代人不是沒有發言,只是現在的人不愿聽他們講。在沉默中,那一代人在慢慢凋零。我外公的離去不是個時代事件,在我心里,卻是一個時代的終結。
外公是第一個教我“至今思項羽,不肯過江東”的人。他告訴我,老家宿遷是項羽的故鄉。他去世了,我沒有想象中那樣難過,不知道這沒心沒肺的狠心,是承繼自家鄉的楚地風氣,還是他本人堅強的基因。
但我怎能不難過。他不止將親歷的血與火打造成我童年里的一個個童話,更以樸素的言行滋養我的成長。講了那么多戰斗故事,他從來沒有向我灌輸過無節制的盲目仇恨。那些燒砸日系轎車的反日“愛國”分子從沒有在戰場上放過一槍,而外公親歷過抗日戰爭、解放戰爭和抗美援朝,親手擊斃過許多敵人,卻常說戰爭是復雜的,是所有人的不幸。他說一定要將日本軍國主義和日本人民區分開來,不該將戰爭變成民族間的仇恨。他會從軍事內行的角度評價——日本人作戰也算勇敢,美軍裝備精良、戰術素養高。他是志愿軍軍人,說老統帥彭德懷最光榮偉大的一刻,不是在抗美援朝中與美軍打了個平手,而是在廬山會議上說真話。他念叨著埋骨異國的戰友,可又會說:“現在看來,‘南朝鮮’比‘北朝鮮’搞得好。”他一直有著骨子里堅持的簡單和真實。
這簡單和真實讓外公付出了代價,即便他后來不再覺得那有什么。他離開了軍隊,內里卻始終是個軍人。后半生,進入體制內的他是嚴重不適的。他雖是一個普通的軍人,卻有著項羽一樣的軍魂,在漫長的日子里,他像完成一場場戰斗一般,艱難地穿過了人生的泥沼。
因為外公早就流露的生死觀,讓我能夠沒心沒肺地狠心著。在離去前不久,外公得到抗戰老兵勛章。他說,自己那些犧牲的戰友更應該得到這個,不久后,他就可以拿去給他們顯擺了。他應該不記得了,幾十年前,他拿出解放勛章給一個剛脫掉開襠褲不久的小男孩看時,就說過類似的話。
對我而言,外公留下最大的財富,是“反省”。反省是個人的,也該是家國的。他每講出一種看法,常說這只是他一時的想法,還要“經過實踐檢驗”。他總強調要“設身處地”。我知道,我們都有太多需要反省的事情。一個人,在要求他人反省時,首先應該自我反省。一個民族,更該自我反省。
外公和我之間有一個小秘密。所有人都覺得,他最終敗在了自然規律之下,只有我知道,他是這最后一仗的勝利者。像深入陣地一樣,他深入了死亡。“身既死兮神以靈”,他會親睹那些風景和人情,找機會告訴我們。在寒風中,我捧著他的遺像,只覺山巔上的白云很美,只覺他仍在歲月深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