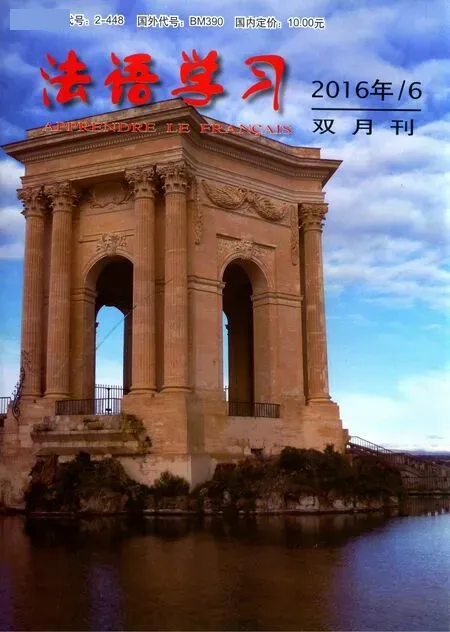當代法國小說創作與“自我虛構”
● 法國南特大學 菲利普·福雷斯特 (正文)● 華東師范大學 蔣向艷 (引言)● 華東師范大學 張晨蕊 (正文翻譯)
當代法國小說創作與“自我虛構”
● 法國南特大學 菲利普·福雷斯特 (正文)● 華東師范大學 蔣向艷 (引言)● 華東師范大學 張晨蕊 (正文翻譯)
引言
自20世紀下半葉以來,法國文壇繼續引領著世界文壇,呈現出一派精彩紛呈的熱鬧景象:“新小說”派作家羅布-格里耶、米歇爾·布托爾,“新寓言派”小說家米歇爾·圖尼埃、勒克萊齊奧、帕特里克·莫迪亞諾,還有標新立異的女作家瑪格麗特·杜拉斯和弗朗索瓦絲·薩岡,以及移民作家米蘭·昆德拉和華裔作家程抱一等。在這眾聲喧嘩中,一個一致的聲音是:新生代的作家們決心與19世紀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決裂,致力于探索新的文學樣式。他們傳達了“先鋒派”立意文學革新的聲音。
這一運動即使不能說是轟轟烈烈,也可以說是聲勢浩大的:那些當得起杰出作家之名的羅布·格里耶、瑪格麗特·杜拉斯、克勞德·西蒙、菲利普·索萊爾斯等人都在這一行列中。持續二三十年后,1977年,法國作家塞爾日·杜布羅夫斯基(Serge Doubrovsky)在其處女作《兒子》中提出了“自我虛構”(autofiction)這一概念,直到20世紀末,這一術語及其所指稱的小說創作逐漸成為一種新的文學潮流,取代了原先存在的“自傳體小說”。1997年開始小說創作的法國當代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Philippe Forest)以其處女作《永恒的孩子》(L'Enfantéternel)獲得法國“費米娜”文學獎(獲該獎的“處女作小說”獎)。他后來出版的小說也連續在法國獲獎:《然而》(Sarinagara)2004年獲法國“十二月”文學獎;《整夜》(Toutelanuit)2007年獲“格林扎內卡武爾”(Grinzane Cavour)文學獎;《云的世紀》(LeSiècledesNuages)2011年獲“法國飛行俱樂部”文學大獎,同年也獲“布列塔尼和盧瓦爾河地區科學院”文學大獎。隨著創作的豐富和成就及影響的擴大,福雷斯特逐漸被公認為“自我虛構”小說這股新浪潮運動中當仁不讓的代表作家。
那么,繼“先鋒派”之后,“自我虛構”小說要表達什么內容?它是否如一些批評者所宣稱的那樣,是向傳統的“投降”,向新自然主義寫作的回歸?它對哪種世界文學傳統有所繼承?它在小說創作上又是否具有新的立意,對法國文學乃至世界文學有著新的擔當?
下文是福雷斯特這位法國“自我虛構”代表作家對“自我虛構”的論述。
一
我不知道,對法國之外的批評家、學者、讀者、作家來說,“自我虛構”這個詞是否熟悉。“自我虛構”這個詞最早于1977年由一個法國小說家在其處女作《兒子》中提出,意指虛構和自傳相結合的文學作品,恰好他還是一個在美國的學者,在紐約大學教了40多年法國文學。
但是直至20世紀90年代末期,并且是在經常不提及術語的發明者杜布羅夫斯基的情況下,這個術語才為文學批評界廣泛使用,小說家自己有時候也以此來指稱以前的“自傳體小說”,并成為法國當代文學的一個主要特征。
“自我虛構”以及它的文學價值引發了各式各樣的論斷,但是人們一致認為,這個術語指稱出一個理解和評價當代法國文學就不得不考慮的現象。與此同時,這個術語開始向其他歐洲國家散播——意大利、西班牙、德國,以及一些歐洲以外的國家,巴西、日本。三年前在紐約組織了一個國際會議,集結了一些美國和法國的小說家們(包括丹尼爾·門德爾森(Daniel Mendelsohn)、瑞克·穆迪(Rick Moody)、希瑞·阿斯維特(Siri Hustvedt)、凱瑟琳·米雷(Catherine Millet)、卡米耶·洛朗斯(Camille Laurens),還有我),探討對大西洋兩岸的當代作家來說,法國的“自我虛構”是否能夠意味著什么。
就我而言,在法語環境中,盡管自1997年我的第一部小說《永恒的孩子》出版以來,我的作品就被認為是繼承了“新浪潮運動”,但是我一直在批評“自我虛構”以及它通常表示的意義。
我已經厭倦了總是被視為我本不屬于的一場文學運動中的一員,事實上,這場文學運動從未存在,我試著要提出一個另外的術語,不是“自我虛構”,而是“Roman du Je”,聽起來像是英國和美國的“I-novel”(自我小說),其實是源自于日本的“私小說”,之后我會解釋原因。我必須承認我很不成功。所以我決定仍使用“自我虛構”這個詞,同時又要強調出它對我的特殊意義,今天我會試著再次解釋。
當然,“自我虛構”在這個術語被提出之前,就已經存在很久了。開玩笑地說,對“自我虛構”的概念存有疑問的法國結構主義批評家熱奈特認為,既然意大利詩人但丁在《新生》和《神曲》里向讀者訴說了他與年輕的貝阿特麗切的際遇,以及他在地獄、煉獄、天堂的經歷,而且這些經歷都被呈現為是真實的,那么但丁就該被視為一位“自我虛構”作家。
在我看來,“自我虛構”只是對舊內容的一種新說法,每當虛構作品直接地或間接地、明確地或含糊地、用這種方式或是那種方式保持它的自傳成分時,就能夠使用“自我虛構”這個詞。這就是為什么“自我虛構”隨處可見,或者至少可以說,這就是為什么在那些被視為“自我虛構”代表作家的作品之外也能發現“自我虛構”的原因。
我會舉兩個例子,第一個是詹姆士·喬伊斯(James Joyce),第二個是大江健三郎。4年前,我受邀為一個新的系列叢書《一書 / 一生》(LeLivre/LaVie)供稿。這個創意來自于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他在人生的最后階段想象自己花整整一年的時間一遍一遍地重復閱讀同一本書,每一天都寫和那本書有關的東西,于是那本書和他每天的生活相交相融,并且形成了一部新的文學作品,展示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聯,并且令真實與虛構成為了同一現實的兩個方面。我選擇了喬伊斯的《尤利西斯》(Ulysses),因為我知道這部現代文學的杰作已經被很多人研究過,所以我只有站在一個主觀角度才能提出一些如果不算新的,那也算是個人的見解。我的目的是對《尤利西斯》進行自傳式的閱讀,從而令小說的自傳成分顯現出來。對我來說,這就意味著突出喬伊斯小說的其中一個方面,因為,這個方面恰好也是我自己小說的核心:我指的是喬伊斯創作的哀悼、哀慟的經歷,尤其和是孩子逝去的哀慟和文學之間的關系。喬伊斯認為,莎士比亞創作《哈姆雷特》也是源自于這樣的經歷,正如書中斯蒂芬·德迪勒斯在都柏林的國家圖書館所作的著名演講中解釋的那樣,而布魯姆也有著相同的經歷,這是喬伊斯所塑造的這一人物的中心線索。
當然,喬伊斯的作品從《英雄史蒂芬》、《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到《尤利西斯》、《芬尼根守靈夜》都有明顯的自傳成分。然而不止如此。盡管喬伊斯是個小說家,但是他堅持的是自傳總是優于虛構。在法蘭克·巴金(Franck Budgen)的書《詹姆士·喬伊斯以及〈尤利西斯〉的誕生》中就能找到依據。這個場景在1918或1919年發生在蘇黎世。喬伊斯正在進行小說創作,巴金問他最喜歡的作家是誰,以及他是否喜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喬伊斯回答說:“不,盧梭承認自己真的偷過銀勺子,要比陀思妥耶夫斯基書中的一個人物承認一樁從未真正發生過的謀殺案要有趣得多。”
喬伊斯支持“自我虛構”嗎?當然這個問題是很荒誕的。但是在我看來,由于我個人對“自我虛構”的定義非常寬泛,也相當模糊,我不會反對將《尤利西斯》的作家算作是這種文學類型的其中一個先驅者,或者說預言者,在法國,這種文學類型在杜布羅夫斯基之后,我們稱呼它為“自我虛構”,但是它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別處,并且早已存在。
我的第二個例子是大江健三郎。1999年我第一次見到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時,將他的小說冠以“自我虛構”之名——這個概念對他來說是全新的,他表現出了很大的興趣。這很容易理解。自20世紀初,在歐洲文學,尤其是盧梭的《懺悔錄》的極大聲譽的影響下,在日本有一類文學稱為“私小說”:shsetsu的意思是小說,watakushi是日語中一個表示第一人稱的詞。因此,Watakushishsetsu翻譯成英語就是“I-novel”(自我小說),翻譯成法語的話我建議翻成“Roman du Je”。就像“自我虛構”一樣,“私小說”用虛構的方式表現自傳中的事件。從最早期的作品到最近的作品,大江健三郎的一個主要關注點就是在改變、顛覆、更新這個概念。正如莫里哀的著名戲劇《貴人迷》中,茹爾丹先生突然意識到他從出生時起說的就是枯燥的散文而不是韻文,大江才意識到自己寫了半個世紀“自我虛構”,卻從來不知道它的名稱。
在1977年杜布羅夫斯基提出這個術語之前,沒有人知道“自我虛構”的存在。現在我們知道了,那么會產生什么影響嗎?當然會。這讓我們更了解這樣一個事實:現在和過去的每一個真正的作家,比如說喬伊斯和大江健三郎,他們都已經深知:真正的文學總是基于個人的經歷,但是這種個人經歷需要一種詩意的實驗來呈現,它才能真正存在。
二
我想要說明一下我剛才用的詞(實驗)。Expérience在法語中是個非常簡單常見的詞。遺憾的是,這個詞很難翻譯,因為它有很多不同的意義。其中一種意義就對應于英語的experience。但是,它也可以指experiment表示的意義。在英語中,experience和experiment有區別,同樣德語中也有這樣兩個詞:Erlebnis和Versuch。但是法語中沒有,單單只有一個詞expérience,具有兩種不同的意義。
當然,通過這樣觀察就下結論未免有點太輕率了。但是,這教給我們一樣東西:“經歷”并不通過自身存在,也不存在于自身中,只有通過“實驗”才能抓到。而這恰恰就是我們從“自我虛構”中學到的:我們生活中最基本的東西,我們最真實的部分,我們的“經歷”,只有當我們用詞句呈現出這樣一個實驗,才能存在。或者,換一種說法,只有當我們將生活轉化成一部小說,我們的生活才算存在。這件事很容易完成,因為從一開始,我們的生活就是一部小說,它以小說的形式在我們腦海里一遍又一遍地講述,這樣我們才感知到了自己的生活。
三
“自我虛構”在法國有很多貶低者。如果福樓拜要寫一版新的《庸見詞典》(Dictionnairedesidéesre?ues),他一定會表示其中一條必須是對“自我虛構”的“抨擊”,因為這種形式的寫作經常被說成是法國文學衰落的主要緣由,是法國小說在美國、在世界上被讀者們擱置一邊的主要原因。對反對者們來說,“自我虛構”是我們的文學在“先鋒派”時代過后衰落的一個征兆,是向新自然主義寫作的回歸,產生出自我陶醉的,無法解決哲學上、政治上,甚至是文學上的重大問題的小說作品。奇怪的是,也是同一批批評家在“新小說”和“原樣派”時代不遺余力地批判先鋒派作家們,時代翻頁后,他們以再一次毀掉了法國小說的托辭來指責“自我虛構”。阿蘭·羅布-格里耶、瑪格麗特·杜拉斯、克勞德·西蒙、菲利普·索萊爾斯發起了對法國文學的第一次沖擊,那么我們(如果我可以這么說的話),我們現在發出的是致命一擊。
他們就是這么說的。
事實當然并非如此。通常我并不愿意說支持或者去贊揚“自我虛構”,因為在過去的大約30年里,很明顯“自我虛構”創作出了一些非常低劣的作品,一些以自我為中心的、反映現在出現在德波(Guy Debord)的《景觀社會》(LaSociétéduspectacle)一書中的人與人之間疏離程度的故事。但是,我堅信“自我虛構”,或者說至少是當代歸入這一領域的作品,具有一個全然不同的目標,因為,“自我虛構”并非是一個新自然主義概念的復興,而是繼承了真正的現代性,并且堅持成為實驗文學的一種新形式。
杜布羅夫斯基的作品就是一個例證。但是如果我們的視野更開闊一點,那些19世紀90年代開始在“自我虛構”名義下創作和出版作品的小說家確實受到了一幫先鋒派作家的影響,先鋒派作家在一二十年以前指出了道路:他們中最早的當然是羅蘭·巴特(《羅蘭·巴特論羅蘭·巴特》),還有瑪格麗特·杜拉斯(《情人》《痛苦》)、阿蘭·羅布-格里耶(《重現的鏡子》)、菲利普·索萊爾斯(《天堂》《女人們》),還有許多其他的作家,包括一些前代作家,比如米歇爾·萊里斯(《游戲規則》)、馬爾羅(《反回憶錄》)和阿拉貢(《布蘭琪或者遺忘》《死刑》)等。
如果有人要編寫“自我虛構”的譜系,那么就必須包括所有這些名字,還要包括其他很多來自美國、歐洲、中國、日本文學界的名字,他們對這個一直被誤認為是源自法國本土的文學現象有著重要影響。在這樣一個譜系的基礎上,“自我虛構”的實驗性成分就會清晰地顯現出來。雖然“自我虛構”提出的是真實與虛構之間關系的老問題,但是用了一系列的新方式,將寫作本身的問題放到了小說的中心位置,提出了一個更為復雜的“我”的概念,考慮到了哲學、精神分析學和文學本身,因為浪漫主義時代就已經教給我們主體的真實而對立的本質。
四
這種采用了多種形式的實驗,就像我剛才說的,如果傳統的自傳確有其事的話,它基于并導向的是一種與傳統自傳的基點非常不同的事物的視域。
這個觀點可能會令人很驚訝甚至荒謬,那就是“自我虛構”并不像我們通常理解的那樣,它并不關心“真實生活”。它聚焦的并不只是構成我們生活表層故事的那些事實,也不只是發生在每個人身上的那些或小或大、或悲或喜的事件,而是更深層的、更難捕捉、更難表達的東西,唯一合適的詞語就是experience,它始終是任何形式的文學作品的唯一目的。就像喬治·巴塔耶為其主要著作之一《內心體驗》所取的標題一樣,這里我指的也是“內心體驗”,巴塔耶稱為“不可能”的東西中夾雜著些許狂喜,在他和一些現代思想家之后,我們也可以稱之為“真實”。
關鍵在于,在這種情況下,主體面對的是真實,他因經歷這種心醉神迷而松懈了對自我的任何感知。因此自我的概念也被剝奪了意義。自我消失了。“自我虛構”進行的這個實驗的結果就是一種最終有著詩性本質的經歷。“自我虛構”中的我不再是任何人,卻在為文學中的所有人發聲。
“自我虛構”和自傳一樣,它的基礎是人生活中發生的事實和事件,但是它根據實驗的方案將這些事件結合起來,從而導向一個令自我消失而讓不可能的真實存在的經歷。這就像艾略特(T. S. Eliot)詩中的著名表述,一個“人格解體的過程”。然而別忘了,盧梭已經知道了一切:難道他不是在《懺悔錄》之后寫了《孤獨漫步者的遐想》嗎?
五
我并不準備對“自我虛構”提出一個新定義。我先前的評論旨在得出一個更有限更溫和的結果。我對“自我虛構”所說的,正是我所見的,也就是,正是如我在我的書中所經歷和實驗的。從《永恒的孩子》到《云的世紀》,還有目前唯一有英文譯本的小說《然而》,我的所有小說都是基于我親身經歷的一個事件,就是我孩子的死亡。這樣的事情讓人難以面對:它令人無法理解,這就是為什么它需要被一遍一遍地用不同的方式訴說,并且毫無希望發現一種最好的、最終的方式,因為這樣一種方式根本不存在。因此,這些小說中的實驗性的內容,每一本都在尋求另一個角度,每一本都在嘗試接近不可能的真實,并且深知失敗不可避免,每一本小說都融合了作者親身經歷的故事以及其他故事,而其他的故事又有關于居于所有文學作品核心的那些共同的欲望和悲傷(例如我的第一本小說《永恒的孩子》,詹姆斯·巴里的《彼得潘》和雨果的《靜觀集》,還有馬拉美的《阿納托爾之墓》;《然而》,小林一茶的詩,夏目漱石的小說,還有日本文學的其他作品等等),嘗試著拉近那些與我相似的故事,來進行延伸,正如我在《然而》和《云的世紀》中那樣,也包括了歷史本來事件,給予這個故事一個普遍的意義,因而就是非個人的意義。
我的每一本小說都指向一種同樣的虛無,讓思想停留在虛無的邊緣,在這種虛無中,那些一早提出的、伴隨文本而生的問題都渾然無解。令作者去直面一個無解的謎題,一個現實的謎題,正如我最新的小說《薛定諤之貓》(LeChatdeSchr?dinger)中呈現的,這些借自于矛盾教義和物理空想的謎題雖然無法破解,但是卻必須通過小說家創作的故事講述出來。誰在講述?我自己嗎?作者嗎?我并不覺得。就像我之前說的,在真實經歷中,人出于對虛無感覺的神往而拋棄了自我。這就是為什么我一直反對“自我虛構”是在追尋自我的觀點。或者說,如果“自我虛構”是在追尋自我,那么它真正的目的就是去迷路,去迷失。就像我在《然而》中引用過的夏目漱石的話,作家的真正箴言是:“追隨天空,拋棄自我”。在空曠的天空之下,在云層的景致之中,我的小說《云的世紀》就這樣結尾了。在薛定諤為他的貓所創造的盒子里,生與死同在,而自我最終也消失了。對于文學作品而言,不存在其他終極的措辭。
?注釋?
本文正文是法國南特大學文學教授、作家菲利普·福雷斯特于2016年3月25日在華東師范大學對外漢語學院所作講座的英文發言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