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絡化知識時代關于圖書館的暗喻與明示
——溫伯格《知識的邊界》中文版評論
王錚
網絡化知識時代關于圖書館的暗喻與明示
——溫伯格《知識的邊界》中文版評論
王錚
《知識的邊界》是美國互聯網思想家戴維·溫伯格論述互聯網知識形態的著作。文章主要從圖書館工作和研究角度,對該書中文版進行評介。首先介紹該書作者的背景及視角,繼而對該書的主題進行闡述,最后對全書中的圖書館意象和表述進行分析,并提出對圖書館的啟示。
知識的邊界 書評溫伯格 網絡化知識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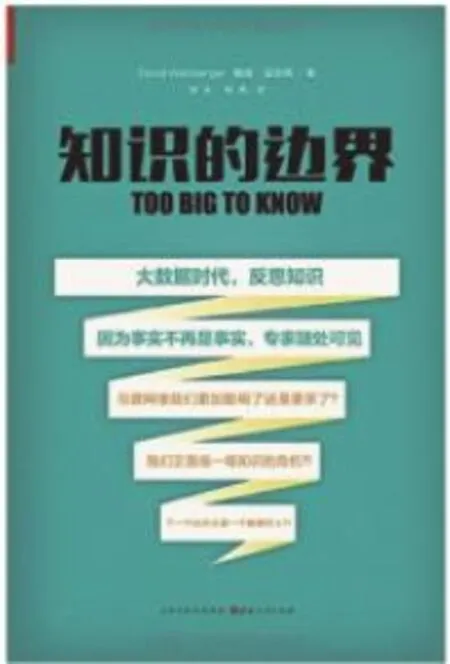
《知識的邊界》[1](英文原版書名Too Big to Know[2])的作者戴維·溫伯格(David W einberger)曾任哈佛大學圖書館創新中心(The Harvard Library Innovation Lab)聯合指導人。該書英文原版在2012年面世后,獲得了當年“世界技術獎年度好書”[3]、“getAbstract國際圖書獎年度好書”[4]等獎項和榮譽。2014年末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其中文引進版,由傳媒學者、財經作家胡泳及高美翻譯,引進版譯為《知識的邊界》。
1 作者的身份標簽:“互聯網+”圖書館的背景
1.1 互聯網思維
溫伯格是哈佛大學貝克曼網絡與社會研究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曾擔任美國總統候選人的網絡政策顧問[5];也是科技評論家和專欄作家,長期在美國公共廣播公司擔任時事評論員[6],其評論多以網絡科技與社會為對象,多有前瞻性和預見性,如在20世紀90年代末談到互聯網智能家居及情感計算的應用,在2005年的節目中提出“標簽”(tag)能夠讓普通用戶組織互聯網信息[7]。溫伯格還經常為《連線》《哈佛商業評論》《經濟學人》《科學美國人》等知名管理和科技刊物供稿[5]。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溫伯格開始在一些初創的網絡創新公司擔任顧問或管理者,在大多數人還不知道網站主頁為何物時,已成為一位網絡公司企業家[8]。進入21世紀以來,溫伯格的幾部評論性著作都與互聯網有關,主要討論互聯網對人類社會、組織、文化及商業的影響,均取得不錯的反響,用時髦的話講,頗具“互聯網思維”。
1.2 哲學視角
溫伯格早年獲得多倫多大學哲學博士學位,受存在主義哲學創始人、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影響較大,其博士論文即與此有關[9],這或許也影響到《知識的邊界》一書的哲學基調。后現代主義哲學者常被稱為理性的批判者,而該書在哲學層面所探討的即為人類理性是否足以理解我們的世界。書中引用了后現代主義的五種觀點來解釋互聯網呈現給訪問者的世界:所有知識和經歷都是一種解讀;解讀是社會性的;解讀沒有高下之分;解讀發生于話語之中;在某種話語之中,某些解讀是備受青睞的[1]142-143。作者認為,互聯網向我們證明后現代主義者的以上觀點是正確的。作為經過哲學訓練的研究者,溫伯格在該書中展現了較為深厚的哲學積淀,常用哲學理論來闡釋網絡議題,并善于從文化意義和社會視角對互聯網生態進行解讀,這是溫伯格的寫作特色。
1.3 圖書館關照
溫伯格與圖書館界的關系可謂密切。他在哈佛大學圖書館任內與同事引入新的圖書館網絡平臺,即Library Cloud[10]。在參與圖書館實踐的同時,溫伯格也有很多關于圖書館的論述,代表性論文《作為平臺的圖書館》(Lib rary as Platform)[11]發表后引起不少反響,至今仍經常被美國圖書館界引用[12]。
需要指出的是,圖書館界也不乏對溫伯格論點的非議。首要的質疑即認為他對圖書館學情報學領域(LIS)和實踐中一些傳統方式和基礎理念的論斷過于草率。此外,溫伯格一些看似新穎的觀點實際已經被圖書館界的前人有所論述甚至實踐。但無論如何,溫伯格每一次觀點的系統發表——無論是“圖書館應該作為平臺(Platform s)而非門戶(Patrol)”[11],還是“圖書館的未來并非創造于圖書館”(The future of librariesw on’tbe created by libraries)[13]——都能促使圖書館人進行一番審視與思索。
在我國圖書館界,溫伯格的著作早有人關注,其2007年的著作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就被冠以“圖書館員最好不要閱讀的書”,由幾位知名博主相繼加以介紹和解讀[14-15],《知識的邊界》英文原版也在早前入選“建中讀書”的推薦書單[16]。
總之,可以說溫伯格既是一位“具有圖書館背景的互聯網人”,也是一位“具有互聯網思維的圖書館人”。在這一點上,具有多重身份標簽的他確實能為圖書館界提供一個貫穿內外群體認知的難得視角。
2 該書主題的解讀:知識與邊界
2.1 從“越亂越美麗”到“越大越無知”
本書中文譯名《知識的邊界》并非是對英文原標題Too Big To Know的直譯。筆者在沒有翻閱該書內容前,曾試著將原書名直譯成“大而致知”或“大而無知”,讀罷后才發覺《知識的邊界》恰當地傳遞了該書主題。與之類似的還有作者2007年的Everything is Miscellaneous[17],我國中信出版社2008年中文引進版譯為《新數字秩序的革命》,之前網上曾出現好幾個風格迥異的中文譯名,如“一切皆混雜”“一切皆商機”乃至“越亂越美麗”。國內譯名同樣選擇了避虛就實的意譯方式。
總之,從2007年的“越亂越美麗”(Everything is M iscellaneous)到2012年的“越大越無知”(Too Big to Know),我們或許可以窺測出溫伯格描繪網絡化知識形態的脈絡,貫穿其中的是一系列“打破——重新建構”的過程。Everything is M iscellaneous打破的是基于傳統實體世界的信息搜集、標注與組織的方法論體系,在網絡環境下,數字內容能夠根據用戶的需要被自由開放地解析、整合、關聯、融匯,接下來Too Big to Know所要重新構建的則是知識的本質。
2.2 何為“知識”?
在《知識的邊界》中,作者開宗明義指出“知識已經變得不再像以前一樣”,至少變得不再像傳統教科書中的定義,也不再遵循長期以來圖書館對知識的傳統認識方式和組織模式。知識正在面臨危機——有些知識,我們曾經堅信不疑,視它們為權威機構最堅不可摧的基礎(本文中著重號均為筆者所加),如今這知識遇到了質疑[1]8。由此產生的更為深遠的影響是:建立在傳統知識形態上的知識機構和知識系統都受到了沖擊。溫伯格列出了一些典型變化領域的例子:大學在討論是否應該將其科研成果全部免費發表在網上(而非發表在期刊上),是否要以在網絡社交媒體上的影響力來衡量一位學者(而非完全看他是否在高質量期刊上發表了足夠的論文);圖書館在疑惑除了搜集那些經過“認證”的知識,該如何衡量分散于“大眾”的知識;咨詢公司在嘗試除了向客戶提供書面的咨詢報告,還要給客戶提供擁有多元觀點的專家網絡入口;美國的情報機構在猶豫如何在舊式的“需要知道”(need to know)和新式的“需要分享”(need to share)之間尋求平衡;科學界在思考如何既保持科學知識的權威性和專業性,又發揚科學的開放性和社會性;企業決策者在探索如何基于分散的網絡化知識建立一種新的“去中心化”的分布式領導模式;傳統媒體在憂慮自身未來的定位和發展前景,因為網絡資訊生態正在逐步弱化傳統媒體“編輯”的角色……以上領域和行業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屬于“知識密集型行業”。這些行業的形成和發展根源于知識的生產、交流和傳播——無論這些行業的工作對象被稱為“成果”“圖書”“著作”“報告”“情報”還是“新聞”。當然,變化的內容不僅僅局限于以上列舉領域,各行各業的變革最終會傳導到生存在當今社會的每一個人身上。在紛繁復雜的時代變局背后,溫伯格為我們提供了一種解釋變化的視角,那就是“知識的網絡化”(the netw orking of the know ledge)。
“知識”已經變得不再像以前那樣。借用書中經典的一個比喻:當知識變得“網絡化”之后,“房間里最聰明的那個,既不是站在講臺給我們上課的那位,也不是房間里所有人的群體智慧,而是房間本身”[1]11。這個房間就是網絡。
2.3 “邊界”何在?
當我們對一個事物進行定義時,首先會明確其“范疇”和“邊界”,即所謂“界定”。而這一方法用于界定網絡化的知識時,卻出現了一個悖論:網絡化知識的最大特征就是其“邊界的消失”。
以前“知識”存在于圖書館、博物館和學術期刊里,存在于個人的大腦里。作者從歷史、哲學、科學等多個角度回溯了傳統知識概念的產生和發展;回顧了笛卡爾、狄德羅、萊布尼茨、培根、達爾文等人在歷史上對于知識的表述和典型實踐;復習了知識公認的一些特點,如知識和信條、真理、事實的關系,當然還有著名的DIKW(數據-信息-知識-智慧)金字塔模型;更為重要的是,作者揭示了傳統知識與實體(最典型的實體如紙張)之間的關系:“傳統知識是紙的意外之物。”[1]72
按照路徑依賴理論,人類社會中的技術演進或制度變遷均有類似于物理學中的慣性,一旦進入某一路徑,就可能對這種路徑產生依賴。“紙張的邊界”也在過去的歲月中逐漸塑造著知識的邊界。紙張作為媒介,不允許輕易糾正錯誤,知識就會被十分小心地審查;紙張印刷資源十分有限,就會產生某種機制讓大家競爭“出版的資格”;如果印在紙上,就要創造集中的場地來堆積書籍,以至于人們頭腦中的知識也遵循著無形的紙張邊界。正如書中的子標題所示:“狀如書籍的思想。”[1]154紙張構成書籍,書籍承載知識。因此,狀如書籍的知識就是A到Z的漫長旅程,狀如書籍的思想就是一種單向的長形式(long-form)論證模式(盡管知識和思想的形狀本不必如此)。
延伸溫伯格的觀點,可以將傳統的知識邊界理解為一紙文本的字里行間格式的界限、一本書刊的封面封底之間厚度的界限、一層書架長寬之間容量的界限、一個圖書館館舍之內空間的界限,乃至我們在這些實體知識界限中養成的單向、線性、長形思維范式的局限。
以上可以作為該書論述的前提和起點,在此基礎上,作者真正要闡釋的是:在互聯網時代,當知識載體逐漸從紙張轉移到網絡時,傳統的知識邊界將不復存在。知識一旦脫離原有界限,繼而與網絡結合,將更加貼近知識的本質——這個世界太大,大到“書本”上的知識體系根本容不下——Too Big to Know。
3 書中的圖書館意象:暗喻與明示
3.1 書中的圖書館語境與表達
《知識的邊界》出現了很多不同類型的知識機構,如新聞媒體、咨詢公司、大學校園、研究機構、圖書館。圖書館在書中出現的頻次和占有的篇幅遠高于其他機構。在這本以“互聯網”為背景的書中,“圖書館”一詞遍布全書各章節,與圖書館工作、圖書館學和情報學相關的表述更是不勝枚舉。引用“圖書館”的案例和佐證是該書的一個特色。
從上文對作者身份的介紹中,我們可以理解圖書館在本書中為何有如此高曝光度,也可以理解為何每次溫伯格的新書一出,都能得到一些圖書館員的“追捧”或“追討”。溫伯格談到圖書館時,不是“就事論事”地討論圖書館,而是將“圖書館”從形象的實體升級為抽象的指代。
其實在討論網絡時代的著作中,以圖書館作為隱喻并不鮮見。比如,凱文·凱利的《失控》[19]中第十四章專門以圖書館命名:在形式的圖書館中(in the library of form)。在該章中,凱文·凱利以阿根廷著名詩人作家博爾赫斯的圖書館為起點,討論空間、形式與智能的命題。博爾赫斯本來就是一個用圖書館作比喻的大師,“博爾赫斯的圖書館”本身就是一個內涵深遠的隱喻。
與凱文·凱利對圖書館晦澀嵌套的隱喻相比,溫伯格作品中圖書館的象征意義更容易理解。尤其是溫伯格擁有圖書館實務經歷,這使得圖書館界在看到溫伯格“拿圖書館說事兒”時更能理解其言下之意或弦外之音。
圖書館界對溫伯格的爭議也來源于此。以《知識的邊界》中的圖書館意象為例,“追捧者”認為它們揭示了圖書館的未來,而“追討者”則認為它們是對圖書館職業根基的誤解與冒犯。筆者看來,《知識的邊界》中的圖書館的確很好地體現了傳統知識形態和知識機構的特征,這或許還恰恰證明了圖書館在舊式知識體系中的權威和地位。溫伯格在該書中并沒有強烈的感情傾向或價值判斷。同時,書中的圖書館形象也并非刻板的,而是豐富多元和動態變化的。
圖書館意象在全書中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首先是作為傳統知識系統的代表;其次是作為網絡化知識系統的比照。筆者簡要摘取該書中出現的圖書館形象樣本,加以說明和評論。
(1)作為傳統知識系統代表的圖書館。按照作者的觀點,新的網絡化知識強調“知識的無界”,而傳統圖書館則恰恰體現“知識的邊界”,作者眼中代表傳統知識系統的圖書館形象具有以下屬性:
——作為知識“過濾器”的圖書館。比如,作者以2008年美國圖書出版量較1990年增加30倍為例,指出任何圖書館的館舍也無法容納如此多的館藏[1]19。同樣,當今時代任何讀者都無法消化吸收如此多的知識。此時圖書館通過書目控制、文獻采購、文獻加工以及閱讀指導等不同手段,能起到某種程度的過濾和篩選作用。
——作為知識“停止點”的圖書館。比如,作者舉出例子:用戶為了獲得某地人口數,在圖書館查閱工具書,獲得一個權威數字之后就不用再查閱其他材料,由此指出“知識是一套停止點系統”[1]33-34。用戶在圖書館檢索到某一文獻,并從中獲得某一事實知識,這往往意味著一系列檢索行為和知識獲取行為的完成和終止。這樣一個獲知的停止點傳統上往往位于圖書館。
——作為知識“認證”的圖書館。同樣以上述查詢人口數據為例,用戶之所以會把在圖書館查詢到工具書上的有關知識作為“停止點”,是因為工具書上的數據經過了專業認證和發行,并且作為一種“證書”存放在圖書館[1]34。
——作為知識“回聲室”象征的圖書館。比如,作者將舊式的回聲室比作一個無聲社區之中的安靜圖書館[1]136。這里的回聲室來自“回聲室效應”(Echo Cham berEffect),是指在一個“封閉系統內”,一種信息或信念經由反復傳播而得到加強或放大,導致與之不同或具有競爭性的信息或觀念受到審查、加以否定或無法得到充分表達[20]。作者在這里借傳播學概念將回聲室比作圖書館是值得玩味和闡發的,其共同點或許不僅僅在于“安靜”。
——作為知識“實體集合”象征的圖書館。比如,作者指出:“我們會想念知識的實體,我們喜歡將知識描繪成真理的集合,這個集合形象一點就像一個圖書館。”[1]70這可以作為以上幾點的集成,圖書館提供給受眾經過“加工”“篩選”“認證”的知識集合,受眾在其中獲得求知過程的停止點,獲得權威的印證。
(2)作為網絡化知識系統比照的圖書館。既然圖書館是傳統知識系統的代表,就會和新的網絡化知識系統形成參照。作者眼中網絡化的知識系統較之傳統圖書館具有以下屬性:
——新的過濾和篩選機制(如鎮圖書館采購委員會需要增加多少人手,才能過濾網上數萬億的頁面,舊有的機制無法滿足當前的過濾要求[1]20)。
——豐富關聯(如科研人員在線獲取文獻,只要通過點擊鼠標,就能實現在同一作者的不同版本間切換,這在實體圖書館中總是無法實現的[1]275)。
——可獲取性(如用0.27秒能夠在谷歌搜索上得到千萬個結果,而在傳統圖書館中什么也得不到[1]275)。
——知識情境(如一部作品置于網絡公共空間中,其具有的情境含義是把它放在圖書館的書架上所不能比擬的[1]281)。
針對以上屬性,我們從圖書館角度加以解讀:在網絡社會,新的知識過濾和篩選機制開始形成,過濾與篩選活動的主體從權威機構和專業組織擴展到更大的群體和所有用戶。豐富關聯表現為知識內容以數字化、網絡化的形式呈現,并能夠實現鏈接、關聯、融匯等功能。事實上,揭示和建立知識之間的參照與關聯一直是圖書館學、目錄學研究與實踐的重要目標,而在數字圖書館時代,圖書館界關注的焦點早已從建立印本文獻實體之間的關聯深入到建立知識本體之間的關聯。在可獲取性方面,用搜索引擎和圖書館作比對來說明網絡的優勢和強勢,這種比較極為常見,也深具說服力。網絡技術確實大大降低了知識獲取的成本和壁壘,也驅使圖書館采取新的工作與服務模式。當然,在網絡時代,對可獲取性的評價也有了新的標準,如果僅僅以1秒之內搜索到千萬個結果作為可獲取性高的表現,而不考慮獲取的內容、質量和潛在限制,那么也有可能陷入可獲取性“虛假繁榮”的陷阱。最后,在知識情境方面,筆者對網絡化知識的這一屬性表示認可。當圖書館工作的對象從文獻層面深入到知識層面時,工作和服務模式需從基于文獻的情境走向基于知識的情境。這一點在大學圖書館和研究型圖書館的工作中體現得尤為明顯。比如,從傳統的文獻服務和基本信息服務拓展到嵌入用戶工作場景,進而打造用戶的知識環境。而大眾標引、社區營建、社交網絡、開放平臺、APP開發、用戶產生內容等基于網絡的新服務方式也正在持續幫助圖書館塑造網絡公共空間的知識情境。
該書作者和筆者都無意將圖書館和網絡化知識系統置于截然不同的對立面,相反,我們都相信圖書館在網絡化知識時代有機會更好地發揮自己的職能和優勢,那就是把自己打造成為網絡化知識基礎設施,成為網絡化知識時代不可或缺的要素。
3.2 該書對圖書館的啟示:向成為網絡化知識基礎設施邁進
在《知識的邊界》中,作者并沒有對舊式的具有邊界的知識系統作激烈的批判,也沒有對新式的網絡化的知識系統過度溢美。況且他還憂心,既然房間中最聰明的已經是房間本身,那就需要打造好這些房間,因為一旦做砸了,網絡反而會使我們變得更笨[1]12。在這種情況下,傳統上處在“邊界之內”的知識機構在網絡化知識時代可以發揮更為重要的價值。面向未來,溫伯格在全書最后一章提出5條利用知識的新策略。作者最終是以一個互聯網人的立場提出這些策略,但如果隱去上下文,這些策略也完全可能是一個圖書館戰略規劃的內容,因為它們無疑可以被視作對當代圖書館使命和活動的陳述、契合和肯定。這一組策略是:
——開放知識獲取通道;
——提供知識描述和知識定位;
——鏈接所有內容;
——將制度化的知識納入網絡;
——教導所有的人。
針對這組策略,可從圖書館角度加以解讀:
(1)開放知識獲取通道。當前最為典型的表現是圖書館參與各類開放運動。在開放獲取運動中,圖書館界與教育科研界攜手打破商業機構對學術信息資源的壟斷和限制,將科學知識開放給所有的研究者乃至社會大眾;在開放政務(Open Governm ent)運動中,圖書館界積極參與政府信息公開,保障公民權利;在開放數據運動中,圖書館搭建平臺,貢獻在信息組織和信息服務領域的智慧與力量,推動全社會接入,利用數據資源。圖書館更進一步通過建立學習共享空間、創客空間,整合開放空間(Open Space)、開放工具(Open Tool)、開放硬件(Open Hardw are)和開放內容(Open Content),拓展公眾獲取和利用開放資源的范圍和渠道。
(2)提供知識描述和知識定位。當前最為典型的是圖書館界對語義網、關聯數據的研究與應用,將揭示與組織的對象深化到知識本體層面,更好地實現知識發現乃至知識創新。
(3)鏈接所有內容。當前要求圖書館打破傳統上紙質資源和數字資源的界限,打破“本地收藏”和“外部獲取/鏈接”的界限,打破“自產/原生”和“訂購”之間的區隔,打破技術壁壘(如接口、格式的不統一)和商業上的人為限制及不合理規定(如商業出版機構對內容范圍和內容使用方式的不合理限制),從而最大限度地建立開放的鏈接和知識組織體系。
(4)將制度化的知識納入網絡。一方面強調圖書館在知識傳播交流體系中原有的“控制”與“認證”等職能,另一方面將圖書館作為一種機構所具有的功能融入到網絡知識環境中。這些活動可以是將古老的文獻進行數字化,和原生數字資源一起納入到統一的知識庫,以更好地進行知識挖掘;也可以是將傳統的文獻計量學和基于網絡的補充計量學相結合,建立衡量評價網絡知識的方法。
(5)教導所有人。這在過往和未來都是圖書館最有價值的工作之一,圖書館界引領著數字素養的教育,致力于消除信息貧困并推進信息公平和數字包容。教育職能是現代圖書館自誕生之日就具有的使命,在新的網絡化知識時代,也沒有哪一種專業的知識機構比圖書館更有能力和意愿向全社會推廣信息技能和信息素養。
知識治理理論中有兩個基本邏輯:知識的獨特屬性需要相應的被組織和被協調的方式;組織設置和技術規則又會影響知識活動的效果和知識的特性[21]。按照知識治理的這種邏輯,當網絡化的知識變得更加開放,當知識的邊界逐漸消失時,必然需要相應的知識組織與協調方式。筆者既非溫伯格的“追捧者”,也非“追討者”,但筆者認同溫伯格在《知識的邊界》中提出的命題:知識的屬性已經發生變化。但這只是命題的上半段,命題的下半段需要圖書館界提出并且作答——我們是否已經做好準備。這個時代的所有圖書館人都是這一命題的親歷者和見證者。
[1]溫伯格.知識的邊界[M].胡泳,高美,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2]David W einberger.Too Big to Know:Rethinking Know ledge Now That the Facts Aren't the Facts,ExpertsAre Everywhere,and the SmartestPerson in the Room IstheRoom[M].New York:BasicBooks,2014.
[3]Theworld technology summ it&awards2012[EB/OL]. [2015-02-09].http://www.w tn.net/summ it2012/finalists.php.
[4]getAbstractInternational Book Award[EB/OL].[2015-02-09].http://www.getabstract.com/en/pages/web/ BookAward.jsp.
[5]Harvard University.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Society.David Weinberger[EB/OL].[2015-07-21].https://cyber.law.harvard.edu/people/dweinberger.
[6]David W einberger.NPR Commentary[EB/OL].[2015-07-21].http://www.hyperorg.com/m isc/npr.htm l.
[7]'Tagging'Lets O rdinary Users O rganize the Internet [EB/OL].[2015-07-21].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4856924.
[8]David W einberger.National speaker bureau[EB/OL]. [2015-07-21].http://www.nationalspeakers.com/speakers/speaker_print.php?id=94.
[9]溫伯格.Too Big to Know[M].王年愷,譯.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4.
[10]Harvard Library Lab.Library Cloud[EB/OL].[2015-07-21].https://osc.hul.harvard.edu/liblab/projects/library-cloud.
[11]Library as Platform[EB/OL][2015-07-21].http://lj. libraryjournal.com/2012/09/future-of-libraries/bydavid-weinberger/.
[12]Library as Infrastructure[EB/OL].[2015-07-21].https://placesjournal.org/article/library-as-infrastructure/.
[13]Let the Future Go[EB/OL].[2015-07-21].http:// www.thedigitalshift.com/2014/09/digital-libraries/letthe-future-go/.
[14]西北圖客.一本圖書館員最好不要閱讀的書《新數字秩序革命》[EB/OL].[2015-07-21].http://blog.sina. com.cn/s/blog_4c683f990100c4de.htm l.
[15]編目精靈III.讓計算機替代我們吧──讀《新數字秩序的革命》[EB/OL].[2015-07-21].http://catw izard. net/posts/20090210122242.htm l.
[16]建中讀書的博客.推薦與科技創新有關的新書[EB/OL] [2015-07-21].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586 b810101hnxu.htm l.
[17]David W einberger.Everything Is M iscellaneous:The PoweroftheNew DigitalDisorder[M].New York:Holt Paperbacks,2008.
[18]溫伯格.新數字秩序的革命[M].張巖,譯.北京:中信出版社,2008.
[19]凱文·凱利.失控:全人類的最終命運和結局[M].東西文庫,譯.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20]胡泳.新詞探討:回聲室效應[J].新聞與傳播研究,2015(6):109-115.
[21]丁魁禮,鐘書華.從知識問題到創新集群知識治理:一項新的研究議題[J].自然辯證法研究,2013(5):62-66.
The M etaphor and Indication of Library in Networking Know ledge Age——Book Review on Weinberger’s Too Big To Know in Chinese Version
WANG Zheng
Too Big To Know iswritten by American Internet thinker David Weiberger,which describes the form of networked knowledge in Internet age.This paper reviews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book from standpoint of librarianship.The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author’s background and viewpoint,and then interprets the theme and structureof thework.At last,the paperanalyses the profile and contextof“library”in the contentofwhole book,and bringsup the inspiration to the librarianship.
Too Big to Know;book review;DavidWeinberger;networking knowledge;library
格式王錚.網絡化知識時代關于圖書館的暗喻與明示——溫伯格《知識的邊界》中文版評論》[J].圖書館論壇,2016(1):115-120,封三.
王錚,男,中國科學院文獻情報中心、中國科學院大學博士研究生。
2015-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