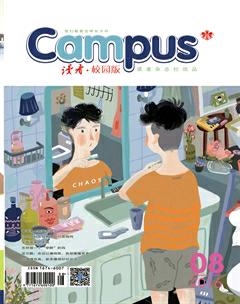我們不說再見

張蕓欣,青年作家,著有《月光漫過珍珠夏》《天亮之后,就會很美》《這世間所有紙短情長》《未見螢火蟲》《云朵上的歌》等書。
我十八歲之前,一直生活在福建沿海的一座叫邵武的小縣城里。
我是地質部門職工的小孩,住的是單位的家屬大院。
在我們家屬大院,一模一樣的場景每天都在上演。我媽每天上班前就拿著飯盒去食堂蒸飯,然后走五分鐘路去上班,中午下了班去食堂拿飯打菜,后來有了液化氣才開始在家煮飯,晚上洗臉、泡腳、看電視劇。
那時候,每天一到天黑我們家樓下的路燈底下,就會聚集一幫人打“八十分”,有人打幾把就回家煮飯,馬上有人頂替上來,不打的人也喜歡站在旁邊看。
對于在小縣城長大的孩子來說,很少有人將來想留在這里,這里太小了,小到給不了任何有能力的人施展的機會。
對于這個殘酷的社會現象,我一度非常恐慌。
因為當年,我是一個長得不好看、成績很差也沒有任何特長的小孩。
更糟糕的是,我們大院里和我同屆的小孩成績普遍都很好,相較之下我的愚鈍更為突出。那時候我媽常說的一句話是:“你要是有人家詩穎一半的成績,我就開心死了。”
詩穎就是那個所有父母口中“別人家”的小孩。
詩穎從小學開始就是班里的學習委員,成績優秀,長得可愛、甜美,就連性格都溫柔可人。
我們讀同一所小學,后來讀同一所初中,她媽媽和我媽媽是特別好的朋友,她爸爸和我爸爸都被一起調派到上海工作。從小建立的友誼讓我對她實在嫉妒不起來。
小時候,閑來沒事我就喜歡去她家玩兒,吃完飯樂顛顛地跑過去。那時候家家戶戶都喜歡裝兩扇門——一扇鏤空的鐵門和一扇實心木門,為了方便,經常開著木門,所以我時常走到她家門口,聽她和她媽媽在客廳邊吃飯邊聊天。
她們會聊學校里的事情,例如老師今天又發脾氣了、誰又考了第一之類的小八卦。讓我吃驚的是,她還會講哪個同學喜歡哪個同學,哪個同學和哪個同學好上了。
這些對于我來說是極為隱秘的事情,我是絕對不會與我爸媽討論的。
所以我喜歡偷聽她們聊天,像是在看另一種生活狀態。
我從小就是那種心性很奇怪的小孩,或許是因為父母離婚的關系,我的心里像是有著一個永遠也填不滿的黑洞,我渴望用各種各樣的事情把這個黑洞填滿。
初中的時候詩穎在我的隔壁班,我們還經常約在一起玩兒,她特別喜歡看日本漫畫,《天是紅河岸》《不可思議的游戲》這些漫畫全是她推薦給我的,她會把她買的漫畫書偷偷塞在一個箱子里,藏在房間的隱秘位置。
那時候,我開始喜歡騎車到學校附近的書店去看“免費”的雜志和書,一看就停不下來。
好像就是在那時候,我找到了生活的樂趣——看書以及寫小說。我開始嘗試給雜志社投稿,只不過所有投出去的稿子都石沉大海,杳無音信。
由于我成績太差,中考后去了離家非常遠的一所普通高中讀書。
失去了相同的學習環境,就失去了共同的話題,我和詩穎的關系漸漸沒有以前那樣好,一是見不到面,二是就算偶爾見到,也不知道要說什么。
清楚地記得高二的某天,我在公交車上與她偶遇,許久不見面,我們彼此都很尷尬,像是最熟悉的陌生人。
那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友情疏離的惆悵。
我從高中開始積極參與學校所有的社團和活動,從廣播站到文學社,但我一個社團也沒考上,不過,因為報考社團我認識了我高中時期的一個好朋友——婷婷。
我們相逢在學校廣播站,她考上了我沒考上,我站在榕樹下郁郁寡歡,她買了兩根雪糕,給我一根,那時候沒有“和路雪”“八喜”這種高級的雪糕,只有我們縣里自己生產的巧克力脆皮,便宜卻親切。
吃完雪糕,我拉著她去操場上跑了兩圈,累得大汗淋漓。躺在塑膠跑道上,我問她:“我是不是挺差勁的?”
她笑著說:“偷偷告訴你吧,我初中復讀了一年還是沒考上一中,是調劑來四中的。不過我也不遺憾,至少我很努力地又讀了一年。”
她的話讓我豁然開朗,接受自己不優秀的事實的確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是也特別勇敢。
婷婷和我一個班,她是學畫畫的藝術生,我們整個班里百分之八十是藝術生,我屬于剩下的那百分之二十。
我樂于在那些學藝術的同學身上觀察他們的生活狀態。
學藝術的學生有他們自己的腔調、難掩的小驕傲和獨特的氣質,他們不愛學習,但喜歡音樂,他們寫歌詞、畫畫、跳舞,敢和老師吵架,敢和年級主任對著干,他們是大家眼中的不良少年,可是我覺得他們活得挺瀟灑的。
我依舊上課認真聽講,但是依舊考得出奇的差。
上了高中的數學后,我不得不承認世上有種東西叫天賦,你不具備的話,就算讀死了也沒用,老師上課講幾何,我回去想了半個月,也不能理解為什么立方體的虛線是那樣畫的。
我老老實實地認識到學習這條路不適合我,我沒有那個智商,更沒有那個天賦。
好在我也沒有什么別的興趣,唯一的興趣就是寫點小說。閑來沒事我就寫小說,用活頁紙、用作業紙,寫了很多稚嫩青澀的小故事。我依然堅持不懈地給雜志社投稿,盡管多數石沉大海,不知道投了多少次。終于,在我不抱期望的某一天,突然接到了某家雜志社打來的電話,通知我稿子被采用了。
我當時聽到這個消息,覺得有點不可思議,在我看到自己的文字被印成鉛字發表在雜志上的時候,才確定這是真的。
我沒把這件事告訴別人,只是拿著雜志跑回家給我媽匯報,我媽一把把我摟在懷里,笑得眼睛都彎起來了,她說:“你太棒了!”
這是我長大后第一次聽到我媽說我太棒了,我有一種說不出的開心和滿足。
第一次發表文章之后,我陸陸續續發表了很多文章,不僅僅是雜志,還有報紙。我媽的同事偶然在報紙上看到我的名字,驚訝得下巴都要掉了。要知道在那個年代的小縣城,發表文章還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兒,讀書好的人有好多,可是能發表文章的小孩卻沒幾個。
班主任也知道了我小說發表的事情,他找到我,讓我承包了班級所有和文字有關的比賽,特別神奇的是我在很多比賽中頻頻拿第一,無法想象成績差到倒數的我,竟然有機會在周一的晨會上,代表年級念我寫的環保主題的稿子。
念完之后我在學校里變成了名人,在我所在的普通高中,優秀的學生沒有一中那么多,出了一個會寫小說還能上雜志的學生是件稀罕事兒。
文學社的老師特意找到我,邀請我進文學社做社長;廣播站的站長也特意邀請我,去廣播站負責稿件審核。或許是經歷了很多的失敗,我更加明白要真正做好一件事有多不容易,我謝絕了老師的邀請,繼續開開心心地寫我的小說。
那時候,由于學校離家很遠,我中午住在離學校不遠的婷婷家的老宅子里,那是一棟木制的兩層小樓,很大也很破,還帶一個種菜的小院子。中午我們吃完飯就坐在陽臺上,她畫畫,我寫東西,下面是窄窄的馬路,馬路兩旁有很多的店家在賣東西,喧鬧的聲音混合在水彩的油墨里,聞起來都帶著陽光的美好。
她姐姐會把切好的水果端給我吃,我們在一起討論未來要去哪里讀書,要過什么樣的生活,我們憧憬著所有的一切。
那時候,我們沒有想過我們會有告別的一天,好像高中的生活永遠都不會過完,那些慵懶愜意的時光永遠不會結束,我們會一直在一起,一直是少女。
當然那都是我們少女時期對青春最天真的想象。
高三那年,作為藝術生,婷婷為藝考去福州參加培訓,我在老師的推薦下,參加了西安舉辦的一次作文比賽。初賽的人很多,沒想到我入選了。
決賽要在西安舉辦,還有為期一周的夏令營,拿到入選通知書后,我立刻跑到班主任的辦公室,要請假去西安。班主任皺著眉頭說:“你現在是高三啊!”
我看著她說:“我一定要請假!”
班主任看我態度堅決,便問我:“那你媽同意嗎?”
我說:“她同意。”
其實,那時候我還沒有問過我媽同意不同意,我心里只有一個聲音,就是我一定要去,這是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不去我一定會后悔。
最后我如愿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車,第一次一個人坐了近三十個小時的火車,去一座陌生的城市。
那趟旅程是我記憶里非常重要的一次旅程,我認識了來自全國各地喜歡寫作的朋友,我們每天聚在一起。聽他們討論文學、討論讀書,講得口沫橫飛,我才知道我目前所看到的、所學到的知識,不過是別人的九牛一毛,他們的才學比我不知道強了多少。如果我在那座小縣城算是一顆小小的星星,那么在他們面前,我只不過是一粒小小的沙礫。
本來內心還有一點點驕傲的我,在那趟旅程后意識到了自己的渺小。
從西安回來之后,我開始投入到緊張的高三生活,我依然寫文章,可是心態完全不同了,變得更加謙遜和認真。
高考后我上了一所大專,雖然在很多人眼中這個成績實在太差了,但是對于我自己來說,已經是盡了最大的努力。婷婷因一分之差沒考上她心儀的大學,她不接受調劑,干脆直接參加工作,詩穎毫無懸念地考上了復旦大學。
陪伴我走過青春的一些朋友,都要陸續離開這座我們生活了十八年的小縣城,去往外面的城市,我們在學校的榕樹下告別,喝得爛醉,倒在操場上看星空,聊我們高中三年的點點滴滴。
后來我還是一直寫小說,十幾年過去了,我出版了十本書。對于文字,依然如同第一次發表文章一樣充滿喜悅和敬畏。
后來我常常想起我們當初的誓言,想起我們在鴿子飛過的藍天下說要永遠在一起,可是一眨眼我們已經好久不見。
可是那些鮮活地出現在我的生活里、陪伴我走過挫折的青春和陰暗的童年,陪伴我守候夢想和堅持努力的歲月,卻永遠地鐫刻在我的心上。
它教會了我在未來的歲月,如何與喜歡鬧別扭的自己握手言和。
如果可以,請讓青春永恒,讓相遇過的我們永不說“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