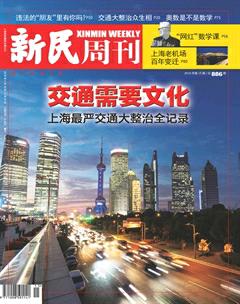圖書如何打贏二戰?
吳興文
當《日瓦戈醫生》多種語文版本在西方出版、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獲得諾貝爾文學獎之際,蘇聯組織國內批判運動,引起從海明威到尼赫魯不同領域的人物出面保護,造成美國中情局秘密印了俄文版偷運蘇聯。那是冷戰時期美國以《日瓦戈醫生》為武器,對抗蘇聯意識形態的戰爭,卻比不上1933年柏林倍倍爾廣場的焚書活動。戈培爾登上掛有納粹卐字布垂講臺,將馬克思、弗洛伊德、愛因斯坦等一一唱名,書本也一本本燒毀,成為二次大戰的前兆。
為了確保柏林焚書行動,現場實況廣播并拍攝成影片,消息傳開后又引發另外九十三場焚書行動。全國風聲鶴唳,許多人先發制人銷毀可能有問題的資料和書籍,納粹進一步公布燒毀的書單。被列入禁單的海倫·凱勒,向德國學生團體表達她的震驚,在倫敦的H.G.威爾斯則舉辦演講,和凱勒的態度相呼應,美國社論撰寫人紛紛加入抗議的行列。
納粹在1939年對波蘭宣戰,英、法依據條約同時對德國宣戰。希特勒卻舍軍隊直接對地面攻擊,先以空中廣播頻道開啟對法戰役。這種巧妙設計的宣傳攻勢,不到一年時間,先后擊敗波蘭、丹麥、挪威、比利時、荷蘭、盧森堡和法國。凡落入德國手中的國家,圖書館往往首當其沖。在東歐總共燒毀375間檔案室、402所博物館、531個教育機構和957家圖書館。被占領國家中能夠繼續開設的圖書館,基本上只收藏納粹允許的圖書。
法國迅速投降證明德國廣播宣傳戰的成功,促使美國圖書館協會認為有責任阻撓希特勒對美思想戰,1941年他們決定舉辦全國性募書活動,捐給美國軍人。原本敵對的出版公司則在1942年3月組成戰時書籍委員會,會中以“在思想的戰爭中,書籍就是武器”作為口號,共享彼此的資源和專業技術,為美軍印制涵蓋各種題材和表達各種觀點的書籍。
戰時書籍委員會發現,希特勒發動戰爭以來,最厲害的武器并不是飛機、炸彈或重型坦克,而是《我的奮斗》。如果美國志在追求勝利與世界和平,必須比敵人所知所想的更多、更深入,這場戰爭是書的戰爭,書是我們的武器。因而產生“戰爭書籍遴選小組”,負責提出能讓美國人明白他們參戰的原因、什么價值受到威脅,以及什么是結合戰爭條件的書籍名單。
出版商首先碰到的難題就是紙張配給。為了印制出最多的書,確保戰士版書籍可以貼近軍人的生活形態,委員會采用史無前例的版式設計和新的印制技術。版式采用平裝本形式,除了節省空間和重量外,平裝書具有柔韌度,容易塞進行李當中。同時研究制式軍服口袋的維度后,才確定較大版本能夠擺入士兵的褲袋,較小本也能塞得進上衣口袋。沒有一家印刷廠能夠印制如此小開本的書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委員會轉而求助雜志印刷廠。由于雜志印刷廠不是設計生產口袋大小的出版品,所以改采“雙聯式印刷”:每個頁面印有兩本書,一在上另一在下,印完后再橫切成上下兩小頁。
據統計超過一億冊書籍消失在戰爭期間,除了遭焚毀的外,還包括因空襲和爆炸毀壞的書籍,經過戰時書籍委員會努力,超過一億兩千三百萬冊的戰士版書被印制出來,加上募書活動募集一千八百萬冊圖書,發送給美國武裝軍人的書比希特勒銷毀的還多。參戰士兵大多是臨時征召的百姓,造成戰士版創造出全新的讀者群,引起世界第一波平民閱讀風潮。茉莉·戈波提爾·曼寧為了紀念出版史上最為動人卻已經被遺忘的篇章,在2014年出版《書本也參戰》,隔年發行漢語繁體字版,探究這個來龍去脈。
當希特勒發動全面戰爭,美國不僅以士兵和子彈打回去,還以書反擊。雖然圖書裝載世上最強大的思想和觀念,但到了二次大戰這些知識寶庫才被真正拿來當作戰爭武器。
《中日古代文學交流史稿》
此書是當代中國比較文學主要奠基人嚴紹璗先生的代表作。作者認為日本文學是典型的變異體文學。在近代以前,中國文化與日本相比較,長期處于高層次階段,因此,中國文化、文學上所獲得的成果與經驗,成為日本古代文學實行自身變異的主要材料。本書通過對日本從原始文化到江戶文化中的中國原素的考察,以詳盡的史料清晰勾畫出日本如何接納、汲取、融匯、改造中國文化,并最終形成以“物哀”、“幽玄”為核心的自身文化這一歷史進程。全書史料豐富、剪裁得當,洋溢著唯美的和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