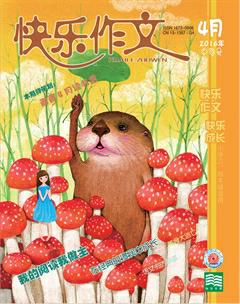亂翻書
雷抒雁
小學到大學,是人生的基本成長期。那種讀書是強制性閱讀,每每有懲罰跟在后邊。考試是一根鞭子,轟羊一般,趕你從一個圈進另一個圈,一層層往所謂高處去。那時的讀書,只為充饑,難甘其味,是“苦讀”,有“頭懸梁,錐刺股”的折磨。小時候,每一次升級后,要做的第一件快事是燒舊課本,以釋心恨。
參加工作之后,才真正體驗到“書到用時方恨少”。急急忙忙地翻書,為實用而讀居多,既不系統,又難集中。半世編輯生涯,亂七八糟讀了一肚子書,世上事物,人間道理,也都知道一些,但比不得學者們,業有專修,學有專攻。
但若問起此生還有什么抱負,有什么興趣,古人說,“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這“萬卷”、“萬里”,只是言其無盡。這“讀”與“行”,樂趣也專在“自由”二字。成名成家,治國平天下,已非我輩所能,早不在念中。
兩年前,終于熬到退休,心愿遂矣。
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買來中華書局新版《二十四史》。把書架上那些讀之無味、棄之可惜的書,一并棄了,給這厚厚的《二十四史》擠出鋪位。買《二十四史》,并非要當史學家,也非是要鉆故紙堆,是將其視為工具書。過去看書看報每有談史的,一掃而過,現在偏要較較真。有許多章段過去也讀過,這回只是“補讀”、“查讀”。
還要做的一件事,重讀經典著作,包括國外的經典。上大學時讀書,多當“仰讀”。以為作家寫的,必好;以為書上的,必對。幾十年人生經驗、寫作經歷之后,再讀經典作品,多當“俯讀”,也能以挑剔的目光視之。偶爾,還能讀出一些欠缺來。另外,更懂得了經典著作,何以為“經典”,拿自己的作品與之相較,知道缺了些什么。這叫“重讀”,是“驗讀”,驗證也。
所謂“自由”讀書,即一切隨心。讀有趣的書,讀有益的書,讀曾經想讀、未找到的書,讀友人寫出的書,讀敵人的書。
如此讀書,難免書桌凌亂,各類書呈各種姿態。有讀到幾章,因故停讀的,夾一紙條,伺機再讀;有讀了幾頁,又有另一書需翻,信手覆在那里的;也有正攤開桌上,覺得其中幾句使人醒悟,需要隨手摘出的。枕邊有書,是送人入夢,或讓人清醒的;廁中有書,是有益輕松排泄的。亂家中風景、亂我生活秩序者,唯書而已!每有家人清掃房間,總叮嚀其凡物皆可動,只書不能動,亂就亂著,我知其亂中之治。如別人胡亂收拾整齊了,其實,反倒是亂了我的思緒。
亂翻書,樂趣在以我為主,書為我使。有書做伴,隨心所欲,保持一種思想自由,精神獨立。一如李白之看山:相看兩不厭。
清人不敢說:“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我則說:人生愜意處,恰在亂翻書。
(有刪節)
微鏈接:
一本書像一艘船,帶領我們從狹隘的地方,駛向生活的無限廣闊的海洋。
——凱勒
書籍是屹立在時間的汪洋大海中的燈塔。
——惠普爾
讀書時,我愿在每一個美好思想的面前停留,就像在每一條真理面前停留一樣。
——愛默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