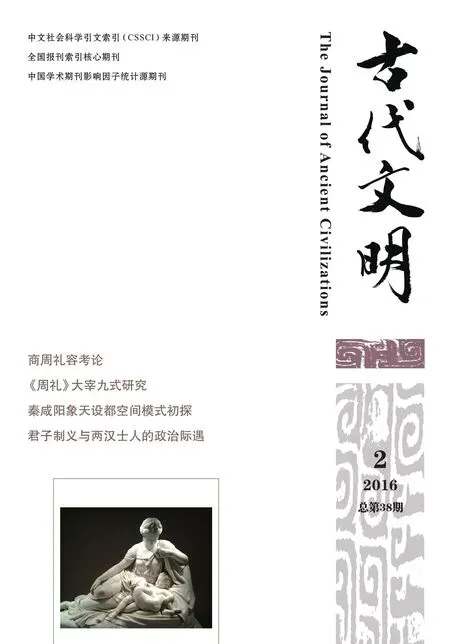明代漕運監(jiān)兌官制初探
胡克誠
?
明代漕運監(jiān)兌官制初探
胡克誠
提 要:監(jiān)兌官制的出現(xiàn)根源于明代漕運制度變遷過程中“兌運法”的施行,并于成化年間“改兌”后趨于定制。“監(jiān)兌”即監(jiān)督軍民之間的漕糧交兌過程,一般由戶部每年選差五名本部主事或員外郎充任,分派山東、河南、浙江、江西、湖廣和南直隸六大有漕省區(qū)。總體看來,有明一代的監(jiān)兌制一直在戶部外差與歸并地方糧道之間搖擺不定。其屢遭裁、并的根本原因,除收受賄賂、濫用職權(quán)等腐敗現(xiàn)象外,當(dāng)歸因于晚明戶部監(jiān)兌官在監(jiān)兌漕糧本職之外,增加了兼催地方錢糧逋賦的職能,以致同地方稅糧征解體系間形成了一種難以調(diào)和的博弈關(guān)系。明清鼎革之后,清廷吸取明代經(jīng)驗教訓(xùn),使監(jiān)兌官完全規(guī)制于地方,而不再具有戶部外差屬性。
關(guān)鍵詞:明代;漕運;監(jiān)兌官;戶部
* 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xué)研究青年項目“逋賦治理與明代江南財賦管理體制的變遷” (項目批號:15YJC770013)階段性成果。
明代自永樂北遷,“軍國之需皆仰給東南”,為保證每年四五百萬石漕糧北運京師,明廷建立起由諸司衙門協(xié)同參與的龐大漕運體系。其中,督理漕運的官員主要有總督﹑把總﹑監(jiān)兌﹑攢運﹑押運﹑理刑六種,而所謂“監(jiān)兌官”則主要由戶部司官外差。據(jù)萬歷《明會典》規(guī)定:“監(jiān)兌,戶部主事五員。每歲于漕運議事畢,選差請敕,分詣山東﹑河南﹑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督軍民有司,依期交兌,催攢起程。南運督至儀真,與攢運官交接明白,即將各兌完起程并交接日期,報部查考。回日,仍將兌完日期具奏。”1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第196頁。“凡各處兌運糧,每歲本部(指南京戶部)選差員外郎或主事,(南)直隸一員﹑浙江一員﹑湖廣一員﹑江西一員,督同各司府州縣掌印官,并分巡分守管糧官員,依限征兌。”2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42,《戶部?南京戶部?糧儲》,第297頁。當(dāng)然,上述史料只描繪出了一個大概情況,事實上,明代戶部通過外差監(jiān)兌官參與漕運乃至直接行使對江南等地田賦解納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控之權(quán),存在一個復(fù)雜的演變過程。
目前,學(xué)界對明代戶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戶部機構(gòu)的總體性介紹﹑戶部官吏的用人限制﹑戶部尚書的任職情況﹑主要職掌及其職權(quán)評估等方面,但對其在具體財政管理環(huán)節(jié)中的實際運作方式和扮演的角色,特別是戶部外差的研究則相對薄弱。3關(guān)于明代戶部外差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范傳南﹑趙毅:《明代管糧郎中建置沿革淺論》,《東岳論叢》,2012年第1期;王尊旺:《明代九邊管糧郎中述論》,《福建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2014年第2期。此外,學(xué)界對明代漕運體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文武總漕等高層官員和漕軍﹑水手﹑幫會等基層組織,而對包括監(jiān)兌官在內(nèi)的中層官制的研究相對薄弱。4關(guān)于中層漕運官制的研究成果主要有丁明范:《明代的巡漕御史》,《明史研究專刊》第14期,宜蘭:明史研究小組,2003 年8月;李俊麗:《明清時期漕船的趲運》,《許昌學(xué)院學(xué)報》,2012年第4期。另,漕運研究學(xué)術(shù)史參見高元杰:《20世紀(jì)80年代以來的漕運史研究綜述》,《中國社會經(jīng)濟史研究》,2015年第1期。鑒于此,本文擬整理存世文獻中明代漕運監(jiān)兌官制的相關(guān)記載,爬梳其創(chuàng)設(shè)沿革﹑基本職能,并分析其屢遭裁撤的原因,以期促進明代財政史和制度史的研究。錯漏之處,還請就正于方家。
一、明代監(jiān)兌官的出現(xiàn)及廢置沿革
“納糧當(dāng)差”是帝制時代社會成員對于朝廷(帝王)最為重要的義務(wù),1王毓銓先生認(rèn)為“納糧也是當(dāng)差”(《史學(xué)史研究》,1989年第1期)。趙軼峰先生在肯定此說深刻揭示了帝制時代所有賦役都具有強制性的本質(zhì)之外,更強調(diào)二者在實際生活中對于社會成員的意義有所不同。詳見氏作:《身份與權(quán)利:明代社會層級性結(jié)構(gòu)探析》,《求是學(xué)刊》,2014年第5期。也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而漕運制度則是歷代王朝為保證居于核心地位的賦稅收入——漕糧的有效征解,制定并不斷調(diào)整的一系列組織和管理辦法。清修《明史》曾總結(jié)有明一代漕運法之三變,曰:“初支運,次兌運﹑支運相參,至支運悉變?yōu)殚L運而制定。”2張廷玉:《明史》卷79,《食貨三·漕運》,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第1915頁。明人顧起元的解釋則更為詳細(xì):
漕運舊例,軍民各半,互相轉(zhuǎn)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轉(zhuǎn)運于通州、天津二倉,往返經(jīng)年,多失農(nóng)月。于是侍郎周忱議,將民運糧儲俱于瓜洲、淮安,補給腳價,兌與運軍,自是轉(zhuǎn)運變?yōu)閮哆\。至成化七年,右副都御史滕昭議,罷瓜、淮兌運,令南京各衛(wèi)官與直、浙等處官,徑赴水次州縣交兌,民加過江船費,視地遠(yuǎn)近有差,自是兌運又變?yōu)殚L運矣。3顧起元:《客座贅語》卷1,《轉(zhuǎn)運兌運長運》,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第2頁。
雖然明清以來關(guān)于明代歷次漕運法轉(zhuǎn)變的時間﹑地域﹑首倡人及其具體內(nèi)容解釋的觀點不一,學(xué)界對此也頗有爭論,4[日]清水泰次著﹑王崇武譯:《明代之漕運》,載于宗先﹑王業(yè)鍵等編:《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史論文選集》,臺北:聯(lián)經(jīng)出版事業(yè)公司,1980年,第309—328頁;李天佑﹑蒿峰:《明代漕運的幾個問題——<明史·食貨志·漕運篇>札記》,《山東師大學(xué)報》,1982年第1期。但總體而言,其制度演變趨勢當(dāng)可概括為軍﹑民之間在漕糧長途運輸過程中責(zé)任配比的不斷調(diào)整:由民運為主,向軍民合作,到軍運為主的過渡。換言之,即軍運逐漸取代民運,兌運逐漸取代支運的過程。而“監(jiān)兌官”的設(shè)置,當(dāng)與“兌運法”的施行息息相關(guān)。
何謂“兌運”?明人何喬遠(yuǎn)曰:“兌之為言易也,軍與民交易也”。5何喬遠(yuǎn):《名山藏·漕運記》,《續(xù)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26冊,第446頁。軍﹑民之間的漕糧交接過程,即民間支付運軍一定錢糧(包括道里費和耗米,成化年間“改兌”后又添過江“腳米”),換取運軍代為長途運輸,也可視為一種交易。歸有光還將兌運法施行后的軍民交接過程解釋為一種雇傭關(guān)系:“民之所以得宴然于境內(nèi),而使軍自至者,非能使役之也,實增加耗之米雇之也;軍之所以不得不至者,實厚受其雇,而為之役也。”6歸有光:《震川先生集》卷8,《遺王都御史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66頁。
但是,在漕糧交兌的實際操作層面,軍﹑民之間常常發(fā)生矛盾沖突,進而影響漕運進度或米色質(zhì)量。而由于明代軍﹑政分屬不同系統(tǒng),地方文官往往難以協(xié)調(diào)軍民糾紛,甚至官﹑軍之間也常有沖突,是故需要朝廷派設(shè)戶部專員監(jiān)督﹑協(xié)調(diào)軍民兌運。如嘉靖初年曾監(jiān)兌山東河南漕糧的戶部主事高汝行所云:
國家定都幽燕,供億惟漕粟是賴,歲運四百萬石……皆陸輸而舟運。陸輸者,民也,而理之在守令;舟運者,軍也,而統(tǒng)之在衛(wèi)所,勢相軋而心相違,于是紛爭之患起矣。弘治初,廷議遣部使者監(jiān)之,而爭者始定,然而猶后期也。正德十三年,又賜之璽書,以重其權(quán),而事易濟矣。7嘉靖《德州志》卷2,《公署·戶部監(jiān)兌分司·跋》,《天一閣藏明代地方志選刊續(xù)編》第57冊,上海:上海書店,1990年,第372頁。
隆﹑萬年間總理河道萬恭亦云:
舊制,各省兌運,屆期分差部臣監(jiān)兌,蓋以各總領(lǐng)運官多厚軍而薄民,而各省有司官多厚民而薄軍故。今部臣操兌運之權(quán),制軍民之便,法至善也。8萬恭:《酌議漕河合一事宜疏》,載陳子龍等輯:《明經(jīng)世文編》卷351,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第3777頁。
上述史料均揭示出明代戶部監(jiān)兌官之設(shè)的由來及其在兌運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明代監(jiān)兌官制的創(chuàng)設(shè)時間,如上文推斷,當(dāng)遲于“兌運法”出現(xiàn)的宣德中期。《明實錄》﹑《明會典》等官方文獻中明確以戶部司官監(jiān)兌漕糧的記載,最早見于英宗正統(tǒng)十一年(1446年)冬十月,時任漕運總兵官都督僉事武興奏:“各處軍民兌糧之際,因官司不相統(tǒng)屬,以致爭兢者多。乞遣戶部主事一員,提督各該軍民官員公同交兌,庶免爭兢。”從之。1《明英宗實錄》卷164,正統(tǒng)十一年冬十月。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年。但此后直到正德七年(1512年)之前,《明實錄》中再無關(guān)于戶部司官監(jiān)兌漕糧的記錄。2《明武宗實錄》卷95,正德七年十二月辛亥。萬歷《明會典》則在正統(tǒng)十一年的最早記錄后,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再次出現(xiàn)了“令每年戶部差官一員于山東﹑河南,南京戶部每年差官四員于浙江﹑江西﹑湖廣﹑南直隸地方,督同各司府州縣正官并管糧官征兌”的記載。而在上述兩個時間點之間,尚有景泰五年(1454年)“令河南﹑山東布﹑按二司官督理兌運”和天順元年(1457年)“令各處監(jiān)兌民糧司府州官,每歲承委后,先行本部知會,徑赴總督漕運官處比較”的兩條記錄。3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以此推知,正統(tǒng)十一年后戶部監(jiān)兌官的派設(shè)并未形成定制,且曾于正統(tǒng)十一年至天順元年間的某一時刻遭裁撤,監(jiān)兌之權(quán)歸并于地方司府州級“管糧官”,直至成化二十一年才又恢復(fù)。這輪監(jiān)兌官制的調(diào)整,可能跟正統(tǒng)十四年(1449年)爆發(fā)的“土木堡之變”有關(guān)。當(dāng)時北京面臨也先蒙古大軍圍困,臨危受命的景泰君臣一方面積極組織北京保衛(wèi)戰(zhàn),一方面征召包括漕軍在內(nèi)的地方軍事力量赴京勤王,致使宣德以來逐漸穩(wěn)定的漕運制度暫時恢復(fù)到民運狀態(tài)。而隨著北京保衛(wèi)戰(zhàn)的勝利和景帝皇位的穩(wěn)固,明廷也開始重整漕運體系,包括文官總漕兼巡撫淮揚都御史的創(chuàng)制4胡克誠:《明代漕撫創(chuàng)制事跡考略——以王竑為中心》,《聊城大學(xué)學(xué)報》,2015年第3期。和地方司府州級管糧官參與漕糧征兌的創(chuàng)設(shè),5胡克誠:《明代江南治農(nóng)官述論》,《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明代蘇松督糧道制考略》,載《明史研究·第14輯》,合肥:黃山書社,2014年,第11—25頁。到成化初年“改兌”的實行,以及漕﹑白二糧財政數(shù)額的確定等制度變遷,使明代漕運管理制度進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中央加強對漕糧解運管理的制度訴求也提上日程,此即戶部監(jiān)兌官復(fù)設(shè)并趨于穩(wěn)定的重要背景。
在成化二十一年戶部監(jiān)兌官復(fù)設(shè)之后,弘治三至六年(1490—1493年)又出現(xiàn)過一次短暫停罷,并將監(jiān)兌之權(quán)歸并于地方司府州“管糧官”的記載:“(弘治)三年,取回各處監(jiān)兌主事等官,止令各該管糧官監(jiān)兌。七年,令兩京戶部,仍差主事等官于湖廣﹑江西﹑浙江﹑山東﹑河南及南直隸各府,催督監(jiān)兌民糧。”6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另據(jù)嘉靖《德州志》中的“戶部監(jiān)兌分司題名記”所載,德州戶部監(jiān)兌分司初設(shè)于“弘治初年”(恐系成化二十一年或弘治六年復(fù)設(shè)之誤)。7嘉靖《德州志》卷2,《公署·戶部監(jiān)兌分司題名記》,第372頁。而乾隆《德州志》中則進一步說明:
監(jiān)兌分司署。按,此署有二,明初在北廠,正統(tǒng)間移城內(nèi),天順間改管糧分司,今現(xiàn)在為督糧道署者,此其一;明弘治間復(fù)設(shè)監(jiān)兌分司,建署于州治東,萬歷間復(fù)裁監(jiān)兌分司,今現(xiàn)在為三官廟者,此又其一也。8乾隆《德州志》卷5,《建置·衙署·廢署》,《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10》,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年,第108頁。
這里明確提出弘治初為“復(fù)設(shè)”,德州監(jiān)兌分司創(chuàng)設(shè)于“明初”,至天順年間始改為管糧分司。不過,乾隆《德州志》關(guān)于“監(jiān)兌分司”的記載恐怕也是混淆了戶部監(jiān)督分司和監(jiān)兌分司的差別,前者專管德州倉,設(shè)置時間當(dāng)在明初永樂通漕前后,而后者則是管理漕糧征解過程中的軍民交兌事宜,大概在正統(tǒng)至成弘間創(chuàng)設(shè)。嘉靖《德州志》中分別載有戶部二分司的《題名碑記》,即是明證。
總體看來,成﹑弘以后的數(shù)十年間,每年選派兩京戶部主事(或員外郎)四到五人,分往山東﹑河南﹑湖廣﹑江西﹑浙江﹑南直隸等南北六大有漕省區(qū)監(jiān)兌漕糧的制度日趨穩(wěn)定。如撰于嘉靖初年的“德州監(jiān)兌分司題名記”所載監(jiān)兌山東河南漕糧戶部主事的派設(shè)情況,從弘治六年至嘉靖七年(1493—1528年)的35年間,共曾派設(shè)戶部監(jiān)兌主事34位,1嘉靖《德州志》卷2,《公署·戶部監(jiān)兌分司》,第369—371頁。幾無間斷。這當(dāng)歸因于成化“改兌”以后,漕運制度趨于穩(wěn)定,故戶部監(jiān)兌官制也日益趨于常態(tài)。
隨著監(jiān)兌官在漕運過程中的作用日益明顯,戶部曾于嘉靖十九年(1540年)提出,“監(jiān)兌官,錢糧所系,職任最重,宜賜關(guān)防,以便行事。”2《明世宗實錄》卷242,嘉靖十九年十月乙亥。不過這一提案在當(dāng)時未獲批準(zhǔn),監(jiān)兌官仍需每年領(lǐng)敕赴差。直到嘉靖四十四年(1565年),明廷才正式批準(zhǔn)鑄給監(jiān)兌官關(guān)防,這也是戶部監(jiān)兌官由臨時性差派轉(zhuǎn)變?yōu)榉ㄒ?guī)定制的重要標(biāo)志。3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
嘉靖之前,戶部每年派往南直隸的監(jiān)兌官只有一人,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十二月,總督倉場戶部左侍郎劉體乾奏:“監(jiān)兌部臣宜重其事權(quán),毋令阻撓。南直隸道里闊遠(yuǎn),宜增一員以管蘇松常鎮(zhèn)四府,一管上江﹑江北。”此議得戶部支持。4《明世宗實錄》卷566,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丙申。次年(隆慶元年·1567年),鑄給江南﹑江北二監(jiān)兌主事關(guān)防。5《明穆宗實錄》卷2,隆慶元年正月戊辰。至此,南直隸監(jiān)兌一分為二。隆慶三年至五年間(1569—1571年),明廷又裁革各省區(qū)戶部監(jiān)兌官,并將浙江﹑南直隸二省區(qū)所在各府州漕糧監(jiān)兌統(tǒng)屬關(guān)系重新調(diào)整歸并,分別由所在專職御史兼任:其中,江北廬州﹑鳳陽﹑淮安﹑揚州四府及徐﹑和﹑滁三州糧務(wù)改由兩淮巡鹽御史兼管,上江所在的應(yīng)天﹑太平﹑寧國﹑安慶﹑池州五府與廣德州糧務(wù)改由南京巡屯御史兼管,而江南蘇﹑松﹑常﹑鎮(zhèn)﹑杭﹑嘉﹑湖七府漕務(wù)則統(tǒng)一歸兩浙巡鹽御史兼管。至萬歷五年(1577年),明廷又重新恢復(fù)了蘇松常鎮(zhèn)四府的戶部監(jiān)兌主事,九年(1581年)恢復(fù)浙江監(jiān)兌主事。6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十一年(1583年),戶部以浙江漕糧,杭州數(shù)少,嘉﹑湖數(shù)多,奏將監(jiān)兌主事衙門移駐湖州,以便督催。7《明神宗實錄》卷136,萬歷十一年四月庚辰。十二年(1584年),又令兩浙巡鹽御史仍帶管江南七府漕糧,止行文督催,免其押送鎮(zhèn)江。8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三十七年(1609年)以后,再次裁革浙江等五省戶部監(jiān)兌主事,歸并糧儲道。9《明神宗實錄》卷454,萬歷三十七年正月乙未。四十年(1612年),蘇松監(jiān)兌主事再度遭到裁革。10《明神宗實錄》卷498,萬歷四十年八月庚午。
萬歷四十年之后至崇禎朝之前的十余年間,隨著漕運各環(huán)節(jié)中的諸多弊病日益凸顯,復(fù)設(shè)戶部監(jiān)兌官制的呼聲再度響起。崇禎二年(1629年),戶部尚書畢自嚴(yán)覆奏稱:“自監(jiān)兌裁后,有司不如期開征,船到尚且無米,不肖運官就中希圖折干,糧道﹑糧廳漫不稽查,水次既已短少,抵倉豈能足數(shù)?”為緩解日益嚴(yán)重的財政危機,明廷再次調(diào)整了監(jiān)兌官制:除復(fù)設(shè)蘇松﹑浙江﹑江西﹑湖廣四監(jiān)兌主事,并仍責(zé)令南京巡屯御史和兩淮巡鹽御史分別領(lǐng)敕兼管南直隸上江﹑江北漕糧監(jiān)兌舊例外,還有一條不同以往的制度調(diào)整,即將之前山東﹑河南二省共設(shè)一位監(jiān)兌主事的傳統(tǒng)(其中山東漕糧于德州兌運,河南漕糧于小灘兌運),改由德州﹑臨清二倉原設(shè)戶部管倉主事分別領(lǐng)敕兼任。11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云南司》卷1,《題覆倉院宋師襄議復(fù)監(jiān)兌并應(yīng)行事宜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72—75頁。不過這次復(fù)設(shè)也僅僅持續(xù)了三年時間,自崇禎五年(1632年)又裁革戶部監(jiān)兌官,各省漕糧監(jiān)兌再次歸地方糧道兼理,“此后監(jiān)兌之事,即糧道之事,監(jiān)兌之職掌,皆糧道之職掌。”12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云南司》卷12,《題請申飭糧道料理漕兌疏》,第577頁。
二、戶部監(jiān)兌官的基本職能
明代漕運制度自兌運法出現(xiàn),特別是成化改兌以后,整個稅糧解納環(huán)節(jié)大致歸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由各省直司府州縣管糧官督并糧里,將征解到的稅糧運至臨近水次倉,等待漕船抵達(dá),加耗運兌與運軍。該階段由各地?fù)岚纯傮w監(jiān)督,司府州縣各級管糧官具體負(fù)責(zé),以額定稅糧按時按量解運到倉支給運軍為旨?xì)w。第二階段,則是赴各地水次倉接運漕糧的運軍駕船北運,終至京﹑通二倉。該階段由文﹑武總漕負(fù)責(zé),各督運官軍實際押運。而戶部監(jiān)兌官則在期間扮演了監(jiān)督﹑協(xié)調(diào)兩階段交接的橋梁紐帶角色。如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戶部議上漕運新定事宜:“凡違限有司﹑軍衛(wèi)官,俱聽監(jiān)兌主事于兌完之日會按臣彈奏,本部分例題覆。有司則屬各按臣逮問,軍衛(wèi)則屬督漕都御史發(fā)理刑主事治罪。”1《明世宗實錄》卷342,嘉靖二十七年十一月戊寅。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戶部奏請如御史顏鯨建議,令“各監(jiān)兌主事與巡按御史嚴(yán)查有司過限無糧﹑大戶私囤插和﹑軍船過期不到﹑官旗故意刁難等弊,徑自逮問,每年俱于四月內(nèi)類奏”。2《明世宗實錄》卷516,嘉靖四十一年十二月乙亥。崇禎初年,畢自嚴(yán)曾總結(jié)監(jiān)兌官職掌:
監(jiān)兌一差,專為漕糧而設(shè),初督州縣開征,則宜修復(fù)水次倉厫,俾令米盡入倉,務(wù)以干圓潔凈為主;次督旗甲開兌,則宜盡除綱私話會及勒耗折干等弊,務(wù)以兩平交兌為主。兌完之后,俾令刻期開幫,尾押前進,直至瓜、儀,過淮而止。沿途查點漕艘,毋令攙前落后,裝載私貨,延挨時月。若夫內(nèi)供白糧,亦令緊接漕幫,絡(luò)繹前進。把總運官,仍須分別殿最,揭報勸懲。則監(jiān)兌之職業(yè)盡矣。3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云南司》卷1,《題覆倉院宋師襄議復(fù)監(jiān)兌并應(yīng)行事宜疏》,第75頁。
由此可知,監(jiān)兌官的主要職能,當(dāng)是以水次倉為中心,監(jiān)督軍民交兌,并考評地方官和運軍兩方工作的完成情況,以保正漕糧及時足額解運。
首先,是監(jiān)督考評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的完糧入倉情況。如正德五年(1510年),時任總漕邵寶疏請“仍敕本部,毎年例差監(jiān)兌官員,務(wù)選精煉之人,令其親詣各水次,從實查勘,除依限交兌外,若有遲誤者,必根究所由,或在軍,或在民,或在官吏,指實參奏,系軍職行漕運衙門,系民職行各該巡按御史,提問如律,照例發(fā)落,不許視為泛常,茍且塞責(zé)。”4清高宗敕修:《御選明臣奏議》卷13,《舉糾漕運官狀(邵寶)》,《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45冊,臺北:商務(wù)印書館,1986年,第207頁。七年,戶部提出:“各處兌運稽遲,請遣戶部官四員,領(lǐng)敕監(jiān)兌,申嚴(yán)期限,違者罪之”。5《明武宗實錄》卷95,正德七年十二月辛亥。同年,戶部會議巡撫官,詳細(xì)規(guī)定了地方運糧到倉的期限,及監(jiān)兌官的相應(yīng)考察事宜:“各處兌糧稽緩,宜令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十月內(nèi)開倉征完,十二月內(nèi)運送交兌。仍敕監(jiān)兌官,于十一月內(nèi)至水次,督并兌完,赴京復(fù)命。次年正月終未完者,監(jiān)兌官劾治之。”6《明武宗實錄》卷116,正德九年九月庚申。此即明確了監(jiān)兌官對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交兌漕糧情況的監(jiān)督參劾權(quán)。嘉靖以降,隨著漕糧部分折銀逐漸成為慣例,漕運銀的比例大增。為適應(yīng)這一趨勢,戶部于嘉靖四十一年又出臺了“改折糧銀違限降黜例”:“自今年始,各撫按及監(jiān)兌主事嚴(yán)督各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依限征完改折糧銀,同本色解部。四月終折銀不完者,同正月無糧例,府州縣官各提問,住俸半年;五月終不完者,同二月例,各提問住俸一年;六月終不完者,同三月例,各提問降二級;七月終不完者,同四月例,不分多寡,并布政司掌印管糧官一體提問,各降二級,送部別用,俱監(jiān)兌官同巡按御史查參。”7《明世宗實錄》卷507,嘉靖四十一年三月甲午。萬歷中,戶部又題準(zhǔn)“各府州縣掌印正官,查將本年份應(yīng)征本折漕糧及輕赍等項銀兩,逐一先期催辦,在十月以里,漕米起運,銀兩貯庫,方許離任。若糧銀不完,及雖完而米色粗惡者,各掌印官雖經(jīng)離任,仍聽監(jiān)兌主事會同巡按御史指名題參,照例降罰”。8《明神宗實錄》卷385,萬歷三十一年六月乙巳。以上規(guī)定明確了戶部監(jiān)兌官與巡按御史有對地方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解納錢糧情況的監(jiān)督參罰權(quán),而監(jiān)兌官對府州縣官任內(nèi)稅糧完解情況的考評參劾,則成為其升轉(zhuǎn)降調(diào)的重要依據(jù)。
其次,是監(jiān)督考核兌糧上船后漕運官軍押運漕糧之情弊。如弘治十二年(1499年),戶部奏準(zhǔn),令監(jiān)兌﹑攢運官,將各衛(wèi)所掌印并運糧官賢否,遞年開送漕運都御史﹑總兵官,三年匯送,以憑考察。9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正德九年(1514年),戶部規(guī)定:漕運過程中,如因運官刁難,導(dǎo)致征收逾期,則罪在運官,監(jiān)兌官有權(quán)開其揭帖,送戶部及漕運衙門,年終會議,具奏罷黜。1《明武宗實錄》卷117,正德九年冬十月癸丑。十六年(1521年),針對漕運過程中出現(xiàn)的運官科斂軍士財物﹑侵盜官糧等犯罪行為,戶部接受總漕陶琰等人的建議,申明懲罰措施,其具體監(jiān)察彈劾,則交由各監(jiān)兌﹑巡按官及京通二倉坐糧巡倉并薊州管糧官,“將各該運官遷延違限,有司征收過期者,指實參奏提問,查照住俸降級事例,著實舉行。”2《明世宗實錄》卷9,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庚辰。到嘉靖七年,戶部與南京后軍都督同知楊宏議定考選漕運把總新規(guī),改一年一考為三年一考,具體辦法是:“令撫按官會同監(jiān)兌官將運官賢否,每歲一報,積候三年,領(lǐng)運到京,該部照例考選,疏請去留。”同時再次強調(diào),“運官有妨漕政,若運官坐奸贓者,聽漕運衙門及巡按御史﹑監(jiān)兌部臣指實參問。”3《明世宗實錄》卷93,嘉靖七年十月甲寅。
除了監(jiān)控地方有司和軍衛(wèi)按時按量解納漕糧(漕限)外,監(jiān)兌官還要對漕糧質(zhì)量(米色)進行監(jiān)測,保證入京漕糧“干圓潔凈”。如嘉靖四十四年,戶部明確提出:“水次米色,專責(zé)有司,嚴(yán)行監(jiān)兌主事查驗;臨清米色,專責(zé)運官,嚴(yán)行通判﹑管糧郎中查驗。各分等則,呈報總督及巡倉衙門,如有濫惡及插和等弊,參究罰治。”4《明世宗實錄》卷552,嘉靖四十四年十一月己酉。萬歷七年(1579年),戶部更嚴(yán)格規(guī)定,不許有司另行差人解納,必經(jīng)監(jiān)兌官檢測樣米后,再令運官帶解,“以防官旗插和之奸”。其具體辦法是由監(jiān)兌官在每船“摘取樣米二升,分別紅白二色,印鈐米袋”,5《明神宗實錄》卷83,萬歷七年正月乙丑。以備核查。當(dāng)然,經(jīng)監(jiān)兌官檢測過的漕米如再出現(xiàn)數(shù)量或質(zhì)量問題,監(jiān)兌官也要一體治罪。比如,萬歷七年,有儀真運糧指揮劉大材等盜賣漕糧,插和粗惡,事發(fā)被戶部參奏。朝廷認(rèn)為,“漕糧爛惡,罪不專在運官,還查原差監(jiān)兌部官,從官參處。”于是,相關(guān)監(jiān)兌主事陳宣遭到降一級處罰。6《明神宗實錄》卷88,萬歷七年六月辛卯。萬歷十九年(1591年),以浙﹑直漕糧黑潤數(shù)多,臨倉掛欠又甚,蘇松監(jiān)兌楊應(yīng)宿﹑浙江監(jiān)兌黃璜,及蘇松﹑浙江糧道俱各罰俸。7《明神宗實錄》卷242,萬歷十九年十一月戊辰。
值得注意的是,嘉靖以前,監(jiān)兌官的本職工作為監(jiān)督漕糧兌運,并無催督地方錢糧逋賦之權(quán)。但自嘉靖中葉“北虜南倭”同時侵?jǐn)_,國家財政日益緊張,明廷被迫向江南等“財賦淵藪”開刀,嚴(yán)督逋賦,一方面于地方添設(shè)蘇松督糧參政等司道級管糧專官,8胡克誠:《明代蘇松督糧道制考略》,載《明史研究·第14輯》,第11—25頁。另一方面則通過頒給原屬漕運系統(tǒng)常設(shè)機構(gòu)之一的戶部監(jiān)兌主事等部院外差官新的敕書,授予其兼催地方錢糧逋賦之權(quán),充當(dāng)“督逋使”。如嘉靖三十年(1551年),時任蘇州府吳縣令的宋儀望在所撰《吳邑役田碑》中有記:“比者,丑虜犯順,方動兵革之議,大司農(nóng)遂告帑藏殫竭。江南逋負(fù),動至數(shù)百萬,其在蘇吳,十居其五,部使者更至無寧歲,邇又添置藩司,專督逋稅,征斂之議,益猬毛而起矣!”9宋儀望:《華陽館文集》卷6,《吳邑役田碑》,《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6冊,第674頁。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題準(zhǔn):“南直隸﹑江西﹑浙江﹑湖廣各監(jiān)兌主事,合照先年兼催錢糧事例,請給敕四道,仍會同各該撫按官,將嘉靖四十年﹑四十一年額派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四省錢糧,盈開納事例,并節(jié)年會議條陳等項銀兩,其四十二年份,并帶征三十六年份錢糧,完者起解,未完者嚴(yán)催,候一年滿日通算,約以十分為率,未完四分者,布政司掌印﹑管糧官,俱降俸二級,移咨吏部,不許推升。追征完日,準(zhǔn)照舊支俸。未完六分者,俱照不及事例,降一級,起送吏部調(diào)用。未完八分以上者,俱革職為民。其余府州縣掌印﹑管糧官,亦照此例。監(jiān)兌主事,催督錢糧,通以一年為限。查將未完錢糧應(yīng)參官,照依前例,分別參奏,以憑戶部議覆施行。”10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9,《戶部十六·征收》,第216—219頁。四十三年(1564年),又敕遣戶部主事董原道﹑楊楠﹑張希召﹑蔣凌漢往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監(jiān)兌兼催錢糧。11《明世宗實錄》卷539,嘉靖四十三年十月戊子。四十四年,鑄給監(jiān)兌主事關(guān)防,加強其催督漕糧逋賦的權(quán)威。12申時行等修,萬歷朝重修本:《明會典》卷27,《戶部十四·會計三·漕運》,第196頁。四十五年,又“以南直隸﹑浙江﹑江西﹑湖廣積逋未完,更賜各處監(jiān)兌主事敕,令其督催額派及條議事例銀,限一歲中完解不及四分者,布政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降俸二級,六分者,降一級,八分者,削籍為民。”1《明世宗實錄》卷564,嘉靖四十五年閏十月辛卯。隆慶元年十月,再命巡漕御史蒙詔﹑監(jiān)兌主事劉佩﹑賴廷檜﹑顧養(yǎng)謙﹑程文著兼催各省逋負(fù)錢糧。2《明穆宗實錄》卷13,隆慶元年十月丙戌。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戶部題差主事王階往浙江﹑郭惟寧往江西﹑趙世德往湖廣﹑魏可簡往蘇松﹑沈榜往山東,各監(jiān)兌所屬府州縣,盡數(shù)解完本年錢糧,方許離任,若果拖欠于布政司,庫銀借支起解,催征補完,有未完者,照例參治,俱載入監(jiān)兌。3《明神宗實錄》卷297,萬歷二十四年五月戊辰。可見,地方司府州縣錢糧逋賦均在監(jiān)兌參罰之列。
此外,明代戶部監(jiān)兌官為“歲差”,嘉靖之前,工作簡單明確,堪稱“清閑”。戶部曾多次強調(diào)“監(jiān)兌主事,事竣回京,不必候交代”。4《明世宗實錄》卷28,嘉靖二年六月庚戌;卷32,嘉靖二年十月戊戌。監(jiān)兌官也經(jīng)常借機開小差,比如,正德年間曾發(fā)生過因監(jiān)兌官過境回家,漕軍無人監(jiān)管,導(dǎo)致漕卒斗毆致死的事情;還有監(jiān)兌官私自過境回家時弄丟了敕書,引起朝廷震怒。5《明武宗實錄》卷173,正德十四年夏四月己丑。到嘉靖十九年,戶部根據(jù)武定侯郭勛條陳,為限制漕運途中各閘壩留難盤剝,奏準(zhǔn)令本部主事“各詣水次監(jiān)兌,俟兌畢,仍令押赴京﹑通二倉”。6《明世宗實錄》卷236,嘉靖十九年四月辛巳。則監(jiān)兌官除了于水次監(jiān)兌外,還要跟船押運。萬歷中,戶部明確規(guī)定:“監(jiān)兌部臣,原系督理漕務(wù),兼催起運錢糧,二者均國家惟正之供,須糧銀盡完,方云竣事。宜通行省直撫按及監(jiān)兌部臣,以后部臣糧完日,押至交割地方,即速回任,照舊督催,不許回家自便。其交代之期,改于九月終旬,務(wù)將京儲盡數(shù)報完,方準(zhǔn)回部。”7《明神宗實錄》卷385,萬歷三十一年六月癸卯。可見,隨著監(jiān)兌官被賦予催逋之責(zé),其清閑日子也走到了盡頭。
三、戶部監(jiān)兌官屢遭裁撤的原因
有明一代的監(jiān)兌官制雖以戶部外差為主,但其間置廢不定,屢遭裁撤。究其原委,似乎是戶部監(jiān)兌官群體中普遍存在的玩忽職守,乃至濫用職權(quán)﹑收受賄賂等腐敗現(xiàn)象。如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戶部主事王嘉言﹑韓珊因“監(jiān)兌失期罪”而分別被奪職閑住和降調(diào)外任:“時二臣已承委年余,尚未至水次。尚書高燿等劾其怠玩曠職,因并發(fā)嘉言管銀庫時,受商人賄,擅發(fā)金價三千,故嘉言得罪獨重云。”8《明世宗實錄》卷555,嘉靖四十五年二月丁亥。同年七月,南京吏科給事中張崇論劾奏直隸監(jiān)兌戶部主事龐瀾貪賄不職,詔黜為民。9《明世宗實錄》卷560,嘉靖四十五年七月甲寅。崇禎初年,戶部尚書畢自嚴(yán)曾反思其置廢不定之因,曰:
人臣設(shè)官分職,總期展采宣猷,況監(jiān)兌一差已設(shè)而復(fù)裁,既裁而又復(fù),其故可思也。裁者因前官之?dāng)∪海藉θ径?fù)氣,復(fù)者望新官之砥礪,務(wù)拮據(jù)而奏功,故戒前車而策后效,亦在各官之自為計耳。開往日監(jiān)兌濫受州縣有司交際等項幣帛、下程心紅紙札之類,一概弗辭,而不才有司,又轉(zhuǎn)取之大戶糧長,頭會箕斂,剝肌椎髄,即有不收,多飽有司囊槖。其庸闇監(jiān)兌,又有縱容下役恣為朘削而弗問者。叢怨讟而騰蜚語,職此之由。10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云南司》卷1,《題覆倉院宋師襄議復(fù)監(jiān)兌并應(yīng)行事宜疏》,第76—77頁。
故強烈建議要“滌除陋規(guī)”。但監(jiān)兌官之裁,除了諸如上述“濫受州縣有司交際等項幣帛﹑下程心紅紙札之類”陋規(guī)和“縱容下役恣為朘削而弗問”等腐敗問題外,是否還存在某些更為深層﹑本質(zhì)的原因?筆者認(rèn)為,其中最為重要的一項,當(dāng)歸因于戶部監(jiān)兌官在制度創(chuàng)設(shè)過程中,同糧儲道存在一定的職能重疊,特別是同整個地方稅糧征解體系間形成的一種難以調(diào)和的博弈關(guān)系。
明代自仁宣以降,各省區(qū)地方逐步建立起一套司(道)府州縣各級佐貳專職的管糧官體制,它們同撫按對接后,形成一種新型地方財賦征解體系。11胡克誠:《明代蘇松督糧道制考略》,載《明史研究?第14輯》,第11—25頁。如萬歷十五年(1587年)五月,戶部覆南京戶科給事中吳之鵬奏時所稱:“國家設(shè)督糧﹑水利道以總理于上,設(shè)同知﹑通判﹑判官﹑縣丞﹑主簿等官以分理于下,而修筑疏浚之,以備旱澇。”1《明神宗實錄》卷186,萬歷十五年五月丙辰。一定程度上描繪出晚明以“專務(wù)道——府州縣佐貳”專司地方稅糧﹑水利的管理模式。2胡克誠:《明代江南治農(nóng)官述論》,《古代文明》,2012年第2期。這套體系再同漕運系統(tǒng)接軌后,共同肩負(fù)起包括漕糧在內(nèi)的地方財政轉(zhuǎn)運功能。而與此同時,明廷還不斷向地方派設(shè)如戶部管糧郎中﹑監(jiān)兌主事等專職官員,代表中央監(jiān)控其實施效果,并同上述體系構(gòu)成一種平行交叉結(jié)構(gòu)。如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戶部尚書潘璜疏云:“今后一應(yīng)錢糧,在外責(zé)成各布政司督糧參政﹑參議,在內(nèi)責(zé)成各邊腹管糧郎中﹑主事。”3潘潢:《會議第一疏》,載陳子龍等選輯:《明經(jīng)世文編》卷198,第2055頁。這里所謂“內(nèi)”﹑“外”即分別代指了中央戶部外差和地方管糧道兩套體系。其中,在漕糧征解環(huán)節(jié),二者關(guān)系大概如下圖所示:
正是由于明代地方管糧司道官的設(shè)置及其在漕糧解運過程中扮演著愈加重要的角色,某些職能又同戶部監(jiān)兌官發(fā)生重疊,故而明中后期,視戶部監(jiān)兌官為冗員﹑主張裁省的呼聲不斷涌現(xiàn)。如隆萬之際的總河萬恭即認(rèn)為,戶部監(jiān)兌官權(quán)力有限,且與地方漕儲道之間彼此掣肘,導(dǎo)致兌運愆期,已成為整個漕運系統(tǒng)運轉(zhuǎn)不靈的重要因素之一。建議仿效浙江的辦法,撤銷戶部監(jiān)兌官,歸并兌務(wù)于地方糧道(漕儲道),并責(zé)令巡按御史監(jiān)督審核。如此,則使官﹑民﹑軍三方均獲便利,其云:
今議早運,征發(fā)期會,急如星火。而部臣亡殿最之權(quán),亡催督之柄,多發(fā)一令則大吏以為侵官,多差一人則小臣以為壓己,部法令非行也,其勢必求糧儲道矣。糧儲道催壹單則兌壹單,否則坐而待之,部臣無如之何矣。兌運愆期,率由于此。夫兌既愆期,而欲開幫如期,過淮過洪,入閘抵灣,悉如期,胡可得哉?浙江近以御史帶理兌軍,官民稱便。今各省宜照此例,悉令糧儲道兌運,而巡按御史間壹親核之。夫以本省之官兌本省之糧,則民便,以過洪之官兌過洪之船,則軍便,以所催之糧給所兌之軍,催其所兌而兌其所催,則官便。而又臨之以巡按,董之以重權(quán),了此不壹月耳,則官與軍、民俱便。孰與部臣者,有司慢而軍衛(wèi)易,且又轉(zhuǎn)求糧儲,煩難為也!4萬恭:《酌議漕河合一事宜疏》,載陳子龍等輯:《明經(jīng)世文編》卷351,第3777頁。
明人李樂亦指出,戶部監(jiān)兌官與地方糧儲道職責(zé)重疊,故裁﹑并監(jiān)兌職權(quán)順理成章:
京差監(jiān)兌,本省糧儲,職名雖異,其為兌軍一也。糧儲奉有專勅,官職尊于監(jiān)兌,若不高坐省城,而徧歷兌軍各州縣,則監(jiān)兌之可無差,萬分不須商榷,況止浙西三郡,其勢易于徧閱乎?自多設(shè)此差,浮費何止千金?有司又處饋送常儀,不無有損監(jiān)兌名節(jié),誰為惜之?又誰為之?罷也?萬歷二十五年題革。5李樂:《見聞雜紀(jì)》卷5,《四十七》,《續(xù)修四庫全書》,子部第1171 冊,第625頁。
甚至連崇禎初年一度贊同復(fù)設(shè)監(jiān)兌官的戶部尚書畢自嚴(yán),也很快對這一議案提出反思和質(zhì)疑:
去年(崇禎二年)為漕事大壞,該巡倉御史宋師襄欲復(fù)監(jiān)兌之舊,奉有明旨,諭令臣部差委司官。臣部深慮,當(dāng)事體久廢之后,司官人微權(quán)輕,不能返極重之勢,司官亦多卻步,但無可奈何耳。夫司官能治運弁而不能束百姓。責(zé)成糧儲道臣,軍民兼管,似可永久無弊。且當(dāng)日設(shè)立司官之意,不過欲以地方米數(shù)之完欠、起運日期之遲速,時時申報,臣部得以與聞耳。前科臣解學(xué)龍論漕運疏中,各省糧儲道押運至津門方許回省,其起運日期數(shù)目亦當(dāng)報部,則監(jiān)兌司官可以不設(shè)。1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新餉司》卷8,《覆科臣裴君賜條議催征禁革疏》,第586頁。
而實際上,明代歷次裁革戶部監(jiān)兌官后,也都將兌務(wù)歸并于地方糧道,故有明一代監(jiān)兌之權(quán)一直處在戶部外差與地方糧道間搖擺不定。
此外,更為重要的是,由于監(jiān)兌官慣常的中央戶部屬性,與地方撫按司道分屬不同系統(tǒng),彼此間并無直接統(tǒng)轄關(guān)系,故而在行使職權(quán)過程中難免互相掣肘。隆慶五年(1571年),總督倉場侍郎陳紹儒提出:“每年兌運事宜,當(dāng)專責(zé)各處巡撫,而令監(jiān)兌官揭報遲速,庶事權(quán)歸一。”2《明穆宗實錄》卷61,隆慶五年九月辛酉。此即指明了巡撫與監(jiān)兌官在監(jiān)督稅糧征解過程中的責(zé)任分工。萬歷三十一年(1603年),戶部奏稱:“兌糧入船之后,國家令甲,即各巡撫按關(guān)分司俱不得干預(yù),一切大小事皆備行漕司,發(fā)理刑主事,俱待完糧日,照例問擬。故盤詰之責(zé),水次有監(jiān)兌,沿途有糧儲,至儀真有攢運御史,過淮有理刑主事,天津河西務(wù)有臣部分司,逐程分責(zé),條例森然。”3《明神宗實錄》卷389,萬歷三十一年十月癸卯。可見,兌糧入船前后,正是地方撫按同監(jiān)兌主事等漕運官系統(tǒng)的權(quán)責(zé)分界線。
不過,因監(jiān)兌官對地方有司起運錢糧的交兌情況負(fù)有監(jiān)督考評之權(quán),特別是嘉靖以后,又被賦予催逋之責(zé),導(dǎo)致監(jiān)兌官在一定程度上打亂了以巡撫為核心的原有地方權(quán)力構(gòu)架。因此,戶部監(jiān)兌官制難以長期穩(wěn)定存在的本質(zhì)原因并非其職權(quán)行使的效果不佳或腐敗問題,而是因為其催征地方錢糧逋賦的新職能,侵奪了原有地方權(quán)力體系的威權(quán),故而遭到強烈抵制。
任內(nèi)錢糧完欠情況,是地方掌印﹑管糧官升遷降調(diào)的主要依據(jù),一旦無法完成,他們往往以天災(zāi)﹑人情為借口,推卸責(zé)任,希圖朝廷暫緩參罰。而在明代,“總理糧儲”的巡撫這個原本欽差的身份,在明代中后期儼然成為地方利益的最高代表,每每袒護地方官的失職行為。這在中央政府看來,正是所謂“人情易玩,或借口于災(zāi)傷;吏道多庸,反沽名于撫字”。4《明神宗實錄》卷57,萬歷四年十二月庚午。
而與之相對,戶部作為主管全國財政的中央機構(gòu),秉承“量入為出”的原則,以保證地方錢糧如期足量輸納為最重要的職責(zé)與施政基礎(chǔ)之一。當(dāng)監(jiān)兌官作為戶部外差時,相對于地方有司來說,恰如掌握其生殺大權(quán)的又一欽差。如萬歷三十九年(1611年),蘇松監(jiān)兌主事顧四明對蘇松二府自萬歷十八年(1590年)以來逋欠錢糧等項逐一匯報,并對責(zé)任有司的種種推諉借口大肆抨擊。他要求地方各級政府嚴(yán)格督催完納,“以后屬縣解貯庫錢糧逐計季造冊,申送撫院按院,以便查盤,仍報監(jiān)兌衙門,以便督催,一項清而項下各注收繳,一年完而年終匯送考成,如有積慣吏役仍踵故智,盡法究遣,以懲將來。”5《明神宗實錄》卷483,萬歷三十九年五月癸卯。從中可見,當(dāng)時蘇松監(jiān)兌官對于地方官錢糧完納情況的管轄權(quán)限,一定程度上已經(jīng)凌駕于撫按之上。
這種職權(quán)訴求本質(zhì)上的差別,導(dǎo)致戶部同巡撫之間形成某種程度上的“對立”關(guān)系。如隆慶四年,戶科左給事中張國彥有鑒于戶部同地方撫按彼此掣肘的尷尬局面,曾指出:“各處稅額日虧,由戶部不能操黜陟之柄,動為撫按掣肘,有今日參降而明日薦擢者。自今請著為令,凡系逋賦有司,令督糧道以報撫按,雖賢者毋得概薦,戶部以咨吏部,雖賢者毋得概擢。有能招流民,墾曠土,完積逋,佐度支之緩急者,不拘官級超拜,要在彼此一體,賞罰信明,然后人知趨避,而法可修舉也。”6《明穆宗實錄》卷45,隆慶四年五月乙酉。萬歷四年(1576年),戶部尚書殷正茂則強調(diào):“追征逋負(fù),其職在有司,若皆推諉不前,國用何以取辦?”如地方催逋不力,“不惟司府州縣印糧官降罰,而撫按官亦難免怠緩之責(zé)。”但他也不得不承認(rèn),“各省地里遼邈,查催動經(jīng)歲月,各撫按官身臨其地,法既易于遍及,權(quán)尤便于鼓舞。”1《明神宗實錄》卷57,萬歷四年十二月庚午。十二年(1584年),戶部尚書王遴奏請嚴(yán)督地方錢糧逋賦時甚至提出要殺一儆百:“伏睹《大明律》內(nèi)一款:凡收夏稅秋糧,違限不久者,杖一百,受財以枉法論。若違限二年以上不完者,人戶﹑里長杖一百遷徙,提調(diào)部糧官吏處絞。今各撫按司道府州縣等官,逋欠山積,豈以遷徙處絞之律不能行耶?不懲一恐無以戒百也!”神宗批復(fù):“錢糧拖欠,令立限督催,其余并與各部院相關(guān)者,俱令上緊議行。”2《明神宗實錄》卷156,萬歷十二年十二月辛酉。可見,中央已對地方逋欠錢糧忍無可忍。三十三年(1605年),戶部尚書趙世卿對包括撫按在內(nèi)的地方政府肆意拖欠﹑挪借已征在官之錢糧,導(dǎo)致中央財政緊張的情況大為不滿,抱怨道:“竊惟人臣比肩而事一主,合而視之,皆為公家之事,分而屬之,各有職守之常,如其職雖踵頂捐糜,罔敢自愛,非其職雖纖毫錙銖,罔敢或侵,是故明乎此者,可為事上小心,可為同寅協(xié)恭,而彼此不至于相病矣。不謂今日諸臣其陵夷決裂,有月異而歲不同者!”3趙世卿:《司農(nóng)奏議》卷4,《督逋·題飭省直借用錢糧疏》,《續(xù)修四庫全書》,史部第480冊,第216頁。中央與地方財政間的博弈,簡直勢同水火。崇禎初年,戶部尚書畢自嚴(yán)曾分析地方與中央財政的關(guān)系:“軍民額供所當(dāng)按時輸納者,太倉視省直為灌輸,亦猶邊鎮(zhèn)視京運為接濟,京運不至,責(zé)在臣部,而臣部于省直有司雖有內(nèi)外統(tǒng)轄之體,實無撫按臨蒞之權(quán)。凡有催督,移咨撫按,行司府,而后下及州縣,轉(zhuǎn)屬為隔,呼吸難通,視若弁髦,藐如充耳,即簿書期會,嘔心扼腕,亦徒托空言耳。”4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堂稿》卷2,《申飭京邊考成疏》,第57—58頁。可見,這種內(nèi)外職責(zé)上的差異,導(dǎo)致戶部對撫按催督不力,甚至以“借”為名截留上納錢糧的行為既憤慨又無可奈何。
與之相對,作為“封疆大吏”的巡撫以及對地方錢糧征解負(fù)有實際責(zé)任的司府州縣掌印﹑管糧官,對于戶部外差監(jiān)兌官侵奪﹑壓制其權(quán)的情況也難以容忍,彼此矛盾不斷。如晚明名臣朱國禎在《涌幢小品》中所載一事:
萬歷九年十一月,主事袁某狂誕,為(張)江陵所喜。監(jiān)兌浙中,盛儀從,呼叱同知以下,無所顧忌。一州守稍與抗,至欲與杖,太守解之而止。視二司蔑如也,人皆惡之。省下出,與巡撫吳善言相值,不引避。巡撫捶其隸人,起奪之,不可得,大罵被髪而走,隨與沖至柵門,拉之仆地,吾郡董宗伯在杭城為之調(diào)解。未幾,告歸,墮水死。5朱國禎:《涌幢小品》卷25,《二主事》,北京:文化藝術(shù)出版社,1998年,第606頁。
此監(jiān)兌浙江戶部主事袁某與地方司府州縣官乃至巡撫沖突不斷,雖有性格“狂誕”或有靠山(張居正)倚仗等主觀因素存在,但其背后的制度運行矛盾也溢于言表。而晚明幾次裁革監(jiān)兌官,也幾乎都來自地方大員的彈劾與倡議。如萬歷二十四年,浙江巡撫劉元霖就上疏強烈建議裁撤各省戶部監(jiān)兌官。6《明神宗實錄》卷302,萬歷二十四年九月丁巳。萬歷帝起初并未同意,還特別強調(diào):“監(jiān)兌部臣,專敕特遣,體統(tǒng)與親臨上司不異,該府州縣掌印管糧等官有故違漕規(guī)的,從實查參,不許顧忌依違,自取廢事,爾部申飭責(zé)成,通行各省直知道。”7《明神宗實錄》卷396,萬歷三十二年五月乙丑。再次重申了戶部監(jiān)兌官對于地方掌印管糧官違規(guī)情況的參劾之權(quán)。但至萬歷三十七年,浙江監(jiān)兌還是在地方撫按一再要求下裁撤,歸并兌務(wù)于糧儲道。與此同時,蘇松﹑山東等地?fù)岚匆菜艡C而動,疏請裁﹑并所在戶部監(jiān)兌官。8《明神宗實錄》卷454,萬歷三十七年正月乙未。至三十九年,山東﹑河南監(jiān)兌主事被劾遭裁,明廷聲言“以后不得再請設(shè)立”。9《明神宗實錄》卷488,萬歷三十九年十月戊子。次年,在應(yīng)天撫按的強烈抵制下,蘇松監(jiān)兌主事也終以“裁冗省費”的名義裁革,據(jù)當(dāng)時戶部覆奏:
漕、白二糧既有鹽、漕二院專督,又有道府州縣分任,綜理有人,則監(jiān)兌似為閑員,且曾革于隆慶三年,復(fù)于萬歷七年,則知非可久之制,允當(dāng)裁省。其兌運漕糧、催攢京儲等項事宜,凡屬監(jiān)兌衙門者,俱改屬糧道管理,頒給敕書、明諭兩道,各照所屬應(yīng)兌正耗本折漕糧及輕赍銀兩、運軍行糧等項,設(shè)法督催,盡數(shù)完報。仍將開倉開兌日期、管糧運糧官職,具揭送部。見運各官賢否,應(yīng)舉應(yīng)剌,核實具呈撫按題請。有船糧遲誤及抗違阻撓,照例分別參究,府州縣見征帶征京邊錢糧并商稅契等項銀兩,照依題準(zhǔn)考成新例,開報撫按參處。水利一節(jié),并乞敕責(zé)兼管,至于裁省諸費,大約每省每年不下千金,撫按宜檄行道府查革減編,就于賦冊除明,張示曉諭,使百姓共知,所謂省一分民受賜一分者也。1《明神宗實錄》卷498,萬歷四十年八月庚午。
崇禎二年,在巡倉御史宋師襄等人建議下,戶部監(jiān)兌官雖再度復(fù)設(shè),然而時任戶部尚書畢自嚴(yán)有鑒于此前戶部監(jiān)兌官同地方官之間勢同水火的關(guān)系,對其復(fù)設(shè)前景并不樂觀:“惟是簡查議裁之因,皆各省撫按題行,其說主于省官省費,甚至以贅旒為辭,恐裁革日久,而一旦復(fù)之,萬一各省撫按又有后言,事體未便。此臣部所為趦趄而未敢輕舉也。”因此,他提出對復(fù)設(shè)后的監(jiān)兌官“崇重事權(quán)”:
監(jiān)兌司官以含香之清署,膺皇華之特遣,其責(zé)任亦隆重矣。無奈邇來法紀(jì)凌夷,部使體統(tǒng)且漸輕漸褻也。銜命而往,操功令以從事,而有司或以贅員視之,其何以展布四體耶?是必查照舊例,請給敕書關(guān)防,各府正官以下相見之禮,查照恤刑義節(jié),無得分庭相抗。至于衙宇使令供億等項,昔年俱有規(guī)制,簡查原案,逐一修復(fù)。在司官不妨厚自挹損,在地方不得過為菲薄,其要尤在撫按司道,各從國儲起見,協(xié)裏相成,刮目相待,庶不至委君命于草莽,而軍儲國計胥有禆益矣。2畢自嚴(yán):《度支奏議·云南司》卷1,《題覆倉院宋師襄議復(fù)監(jiān)兌并應(yīng)行事宜疏》,第76頁。
不過,這次被寄予厚望的監(jiān)兌官復(fù)設(shè)也僅維持了三年,期間不斷遭到各方質(zhì)疑,特別是地方撫按司道的強烈抵制,終于在崇禎五年再遭裁革,歸并其權(quán)責(zé)于地方糧道。至此,明代戶部監(jiān)兌官退出了歷史舞臺。
明清鼎革,在漕運官制上亦有損益,其中清代監(jiān)兌官制不同于明代慣常的戶部外差屬性,而專委各省糧道及府州管糧推官﹑同知﹑通判兼任,史稱“監(jiān)兌督糧道”或“督糧監(jiān)兌道”3“監(jiān)兌督糧道一員。駐德州,參政銜,道屬庫大使一員。按,糧道初駐濟南府,康熈十六年移駐德州,舊設(shè)常盈倉正副大使各一員,又常豐倉副大使一員,俱康熈十六年裁。”雍正《山東通志》卷25之二,《職官二》,《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540冊,第549頁。﹑“監(jiān)兌推官”﹑“監(jiān)兌同知”﹑“監(jiān)兌通判”4李文治﹑江太新:《清代漕運》第六章,《漕運官制和船制》,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出版社,2008年,第149頁。另,張政主編《中國古代職官大辭典》中的“監(jiān)兌同知”/“監(jiān)兌通判”條,即解釋為“同‘管糧同知’/‘管糧通判’”。開封:河南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第849頁。等。如清高宗敕修《欽定歷代職官表》所載:
(清代地方)管糧同知六人,正六品,通判三十三人,正五品,掌監(jiān)兌漕糧。凡米色之美惡,兌運之遲延,及運軍橫肆,苛求衙役,需索奸蠧,包攬攙和等弊,皆司其禁戢之政。初,漕糧以府推官監(jiān)兌,康熙六年,各府推官既裁,改委同知、通判……謹(jǐn)案,明時以各司府州正官及管糧官征兌漕糧,又遣主事五員分督之,見于《明會典》者如此。國初,以府推官監(jiān)兌,乃沿明末之制。蓋明之監(jiān)兌主事,萬歷十六年以后嘗罷遣,而專以府佐監(jiān)兌也。5永瑢等:《欽定歷代職官表》卷60,《漕運各官表》,《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02冊,第351—370頁。
由此可知,監(jiān)兌官在明代主要指戶部主事,而清代則由地方司道府州管糧專官充任。這種制度調(diào)整,當(dāng)是充分吸取明制經(jīng)驗教訓(xùn)的結(jié)果。
[作者胡克誠(1981年—),聊城大學(xué)運河學(xué)研究院講師,山東,聊城,252059]
(責(zé)任編輯:李媛)
【中國傳統(tǒng)學(xué)術(shù)】
[收稿日期:2015年8月20日]
DOI:10.16758/j.cnki.1004-9371.2016.0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