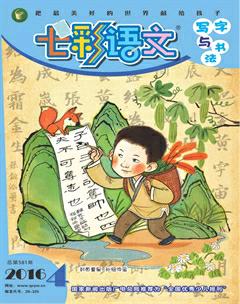石鼓文
安然
《石鼓文》是先秦時期的石刻文字,距今約有2500年。因為文字是刻在十個鼓形的石頭上,故稱“石鼓文”。每石在腰部環刻詩一首,都是類似《詩經》的四言詩,記載秦國國君游獵之事,因此又稱“獵碣”。石鼓文在唐初發現,歷代名家題詠甚多,而書學著錄、題跋、研究都一直未曾間斷,書壇千載盛事,無過于此。原石現存北京故宮博物院。
《石鼓文》上面銘刻的是春秋戰國時期秦國的文字,為籀(zhòu)文大篆。字體上承西周金文,下啟小篆,具有獨特的個性風貌。筆畫飽滿圓潤、骨力雄強,起筆收筆均為藏鋒,蒼茫高古;線條自然淳厚、質樸遒勁,豎畫有垂露的直線,左右線條有相背、相向和對稱弧線等形態,橫線則粗細均勻、內含骨力,圓潤流暢。
結構造型上,《石鼓文》略呈長方形,勻稱自然、舒展大方。有些文字雖然還保留象形、表意構造,如“魚、栗、射”等,但大部分已蛻變為圖案化,有方、圓、欹側等姿態。與春秋戰國時期,特別是秦國一些器物上的銘文相比,《石鼓文》明顯要規范、嚴正,顯現出高超的書寫技藝。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其中有些重復的字,如“吾、君、可、車、既”等,居然沒有明顯的差異。
現代人寫書法刻意將相同的字寫得不一樣,而在先秦時期在重要器物上書寫,則力求工整、規范,保持筆畫和結構的一致與和諧,努力體現出莊重感。
章法上,《石鼓文》布白均勻,字距行距基本相等,整齊一律,呈現出鮮明的布局特色,既有金文的渾厚雄強、氣度非凡,又造就了后來小篆的工穩、勻稱之勢,這些在先秦刻石中有無法替代的審美意義與價值。
《石鼓文》在書法史上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自被發現以來,就受到重視,經過杜甫、韓愈、韋應物等人作詩頌之,更是名噪一時。同時,它被歷代書家視為習篆書的重要范本,特別對清代書壇影響甚大。唐代書法理論家張懷瓘就稱它為“小篆之祖”,它是從金文向小篆發展的一種過渡性書體。
清末的吳昌碩更是對《石鼓文》推崇備至,他學《石鼓文》,并不亦步亦趨,往往以畫筆入書,以行書筆意寫篆,寫得淋漓盡致,雖然乏于法度甚而狂野,但意態生動有神采,氣息沉郁雄壯,自具新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