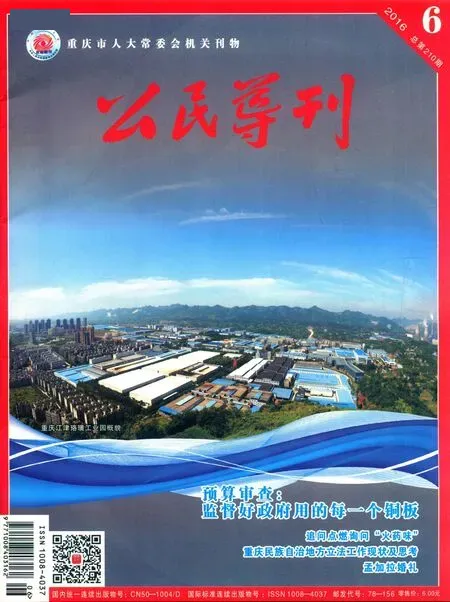淺談對民族立法變通權(quán)的認識
李樹林
民族立法權(quán)是憲法和法律賦予民族自治地方人大的一項重要職權(quán),體現(xiàn)了中央對民族自治地區(qū)的政策關(guān)懷。如何用好、用活、用足立法權(quán),對提高民族立法質(zhì)量,促進民族地區(qū)經(jīng)濟、政治和社會各項事業(yè)全面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在立法法公布實施前,我國立法變通權(quán)的法律規(guī)定主要散見于民法通則、刑法等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中的授權(quán)性法條之中,且只有關(guān)于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變通權(quán)的規(guī)定。人們僅是從這些法律的規(guī)定中,推定民族自治地方立法主體和經(jīng)濟特區(qū)立法主體享有立法變通權(quán)。
立法法第75條第2款規(guī)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shù)孛褡宓奶攸c,對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作出變通規(guī)定,但不得違背法律或行政法規(guī)的基本原則,不得對憲法和民族區(qū)域自治法的規(guī)定以及其他有關(guān)法律、行政法規(guī)專門就民族自治地方所作的規(guī)定作出變通規(guī)定。”
這是我國第一次對民族自治地方立法變通權(quán)作出了限定性規(guī)定,也是我國目前唯一關(guān)于立法變通權(quán)不能變通事項的法的規(guī)定。
自治立法面臨“兩難”
首先,“立”還是不“立”?作為民族立法主體的自治地方人大常常為此糾結(jié):不“立”是失職,對不起自治地方的人民;而“立”好像又是在“等、靠、要”。
如果要“立”,是照抄上位法簡單“立”還是結(jié)合實際變通“立”?如果照抄照搬價值不大,反而浪費立法資源;如果變通“立”,自治地方在人才儲備、立法技術(shù)等方面又很難達到要求,還不易通過。
“立”好之后,也面臨“兩難”:執(zhí)行還是不執(zhí)行?這句話說起容易做起難:如某自治縣的自治條例規(guī)定,上級國家機關(guān)安排的需要縣級配套資金的建設(shè)項目,免除自治縣的配套資金(其實國務(wù)院也有相關(guān)規(guī)定),但不少的上級政府投資項目仍然要求自治縣配套資金;或者給自治縣的同志明說,“你不配套可以,我把項目拿給其他能夠配套資金的區(qū)縣”,以致自治縣爭取項目的同志提都不敢提自治法規(guī)。
筆者以為,民族自治立法的這種“難”,客觀上體現(xiàn)了國家治理之難,改革推進之難,法治建設(shè)之難;主觀上體現(xiàn)了我們一些國家機關(guān)工作人員對民族區(qū)域自治政策,特別是對自治地方立法變通權(quán)的認識到位難。
為什么有人不理解、不認可自治地方的立法變通權(quán)?細究起來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原因:一是認為自治地方行使立法變通權(quán),有可能破壞國家法制的統(tǒng)一;二是需要上級國家機關(guān)對相關(guān)政策作出調(diào)整,形成了“以下管上”的權(quán)力僭越;三是獲得了有別于其他非自治地方的優(yōu)惠政策,破壞了政策統(tǒng)一性。
事實真的如此嗎?當然不是,否則憲法和立法法等法律也不會作如此規(guī)定。
變通與法制統(tǒng)一
我們知道,現(xiàn)實生活中,法律沖突是廣泛存在的法律現(xiàn)象,錯綜復(fù)雜、形式多樣。既有縱向的不同層級的法律、行政法規(guī)、地方性法規(guī)和政府規(guī)章之間的沖突,也有橫向的同位法、準同位法之間的沖突;既有違法的法律沖突,也有合法的法律沖突。
立法法第75條第1款規(guī)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民代表大會有權(quán)依照當?shù)孛褡宓恼巍⒔?jīng)濟和文化的特點,制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同時在第2款中規(guī)定,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可以依照當?shù)孛褡宓奶攸c,對法律和行政法規(guī)的規(guī)定作出變通規(guī)定。
可以看出,民族自治立法因為變通規(guī)定而產(chǎn)生的法律沖突,屬于上下位法律之間的縱向沖突,但因為經(jīng)過了特別的法律授權(quán),而具有存在的正當性基礎(chǔ),所以屬于合法的法律沖突。同時,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適用范圍僅限于自治地方,既經(jīng)過了憲法、立法法授權(quán),又切合了自治地方的實際,是我國法律體系的有益補充和重要組成部分,體現(xiàn)了法律的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統(tǒng)一的原則,是堅持黨的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更高層面的法制統(tǒng)一,而不是相反。
舉個例子,原來國家的人口與計劃生育法提倡一對夫婦只生育一個孩子,針對全國而言,特別是人口稠密地區(qū)來說非常必要,但如果在西藏、南疆這些人口特別稀少的民族地區(qū)也嚴格實施這樣的人口政策,后果將非常嚴重。所以根據(jù)憲法和法律賦予民族自治地方的立法變通權(quán),他們通過民族立法,變通執(zhí)行了計劃生育政策,多生或不限制生育,實現(xiàn)了人口的有序有效增長。
變通與權(quán)力僭越
民族立法中的變通規(guī)定是不是對上級機關(guān)形成了約束,從而產(chǎn)生了權(quán)力僭越?表面上看好像是,但仔細了解法律的規(guī)定和立法的程序,我們將得出不同的結(jié)論。
首先,民族立法屬于授權(quán)性立法,他的立法權(quán)的獲得不在自治縣,也不在省級機關(guān),而是在國家層面,是中央賦予了自治縣的立法權(quán)。
其次,各自治縣在立法規(guī)劃和上報環(huán)節(jié),都非常注重程序。既要制定立法計劃,報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作為省級立法的批準項目;還要履行黨內(nèi)報批程序,由自治縣黨委報上級黨委批準。
再次,各自治縣在立法的起草階段,都要反復(fù)征求上級國家機關(guān)、特別是有變通事項的上級國家機關(guān)的意見,必須取得上級國家機關(guān)認可的書面回復(fù),這個過程非常艱難,是各方利益反復(fù)博弈的過程。
最后,自治法規(guī)在經(jīng)過自治縣人民代表大會審議通過后,必須報省級人大常委會審查批準。我們常說,自治縣只擁有半個立法權(quán),還有一半在省級人大。自治法規(guī)在一定意義上說也是省級法規(guī),因為它是省級人大常委會審查批準的。既然是省級人大常委會批準的,也就不存在“以下管上”的權(quán)力僭越問題了。
變通與平衡發(fā)展
民族自治立法中的變通是不是容易導(dǎo)致民族矛盾和區(qū)域發(fā)展的不平衡,破壞政策的統(tǒng)一?顯然不是。我們黨歷來講求實事求是,也從來沒有一成不變的政策。在民族地區(qū)依據(jù)立法變通權(quán),實施更加優(yōu)惠的財政、經(jīng)濟、資源管理等政策,本身就是為了促進區(qū)域的平衡發(fā)展,促進各民族的共同團結(jié)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
眾所周知,由于歷史的原因,我國各少數(shù)民族絕大多數(shù)都生活在邊疆地區(qū)、山區(qū),或者沙漠化、石漠化嚴重的地區(qū),自然地理條件惡劣,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滯后,處于相對落后的發(fā)展階段。而與民族地區(qū)毗鄰的漢族地區(qū)地理環(huán)境相對優(yōu)越,經(jīng)濟發(fā)展也相對較好,不應(yīng)該強求獲得與民族地區(qū)一樣的政策。退一萬步說,如果毗鄰的漢族地區(qū)確實一樣貧窮落后,甚至更為落后,那么我們可以采取扶貧或者其他措施予以扶持,而不是來爭民族政策。
當前,距離實現(xiàn)我國第一個百年奮斗目標已為期不遠,民族地區(qū)是實現(xiàn)脫貧奔小康的短板。各級各部門特別是各自治地方的上級國家機關(guān),有責任有義務(wù)為推動民族貧困地區(qū)的發(fā)展采取更加優(yōu)惠的政策措施,同時也有責任和義務(wù)將一些行之有效的優(yōu)惠政策通過民族自治立法的形式固定下來,持續(xù)推動民族貧困地區(qū)實現(xiàn)跨躍式發(fā)展。可以說,幫助民族地區(qū)更好行使立法變通權(quán),不但不會導(dǎo)致民族矛盾和區(qū)域發(fā)展的不平衡,反而會彌合民族分歧,凝聚發(fā)展共識,促進共同進步。
張德江委員長在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說,改革和法治如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相輔相成、相伴而生。對民族地區(qū)而言,變通體現(xiàn)改革,立法體現(xiàn)法治,只有依法行使好立法變通權(quán),才能推進民族地區(qū)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xiàn)代化,才能有助于各民族地區(qū)與全國各族人民一道,共同脫貧致富,共同奔向小康。
(作者單位:重慶市石柱自治縣人大常委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