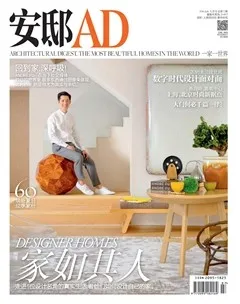設計面對面











每年的米蘭設計周都是設計界最大的派對,新思考。新趨勢、新技術在這里爭相亮相,設計界新老朋友興奮相聚……數碼時代的今天,這樣的面對面尤其顯得必要而珍貴。
米蘭設計周開幕前一晚,我們潛入城里的一個小院子,穿著時髦的人們正忙進忙出,一家買手店似乎正要舉辦活動,我們探頭張望,一位身材高挑的金發姑娘笑著走來招呼我們進去看看。原來這是米蘭資深“網紅”、知名設計記者JJMartin創辦的古著網站的線下活動。熱情、歡喜、分享,這便是設計周的氣息。當然,還有數碼時代里線上、線下的相互交錯。
設計周就像是一張江湖召集令,五湖四海的設計界老炮兒、新鳥應聲而來。曾經電子郵件上那個念不流利的外國名字,正是對面這個有血有肉的設計同行。一聲Ciao,就不再是陌生人。這在數碼時代顯得尤為珍貴!事先做了再多功課,也不如一位朋友跑來分享剛見過的精彩展覽令人心動。
經濟持續不怎么景氣,設計師反而更能沉下心來思考與實踐,究竟是推陳出新,期盼引燃設計界的下一次“革命”;還是回首經典,用新面料和色彩圖案升級未被時間淘汰的大師作品;或者索性像藝術家那樣,以家具為載體,把功能放一邊,創造引入思考的限量版作品……多元,才是設計周的聲音。除了設計師,藝術家和建筑師甚至時裝品牌也愿意來設計周上露個臉。畢竟,這里是設計的江湖所在。米蘭設計周,一周不眠,一年初始。
馬巖松設計周“熱身”
設計師是米蘭設計周當仁不讓的主角,但在意大利,建筑與設計很少被嚴格劃分,因此,在威尼斯建筑雙年展之前兩個月舉辦的米蘭設計周,總會吸引不少建筑師前來“熱身”。今年,意大利老牌雜志Interni向各國建筑師發出“打開邊界”(Open Boarders)主題邀約,其中就包括中國建筑師馬巖松和他的LRD建筑事務所。
拿到這一“命題作文”后,馬巖松決定在米蘭大學的中央庭院里搭建一個幕帳裝置。“建筑師一直熱衷于討論‘邊界’,社會上也存在各種有形無形的‘邊界’。”馬巖松表示,“相對于打破邊界,我們想在傳統的庭院空間和室內空間的邊界,創造一個模糊傳統和當代、內和外的新型公共空間。”他和團隊運用ETFE材料——種常被用作大型場所穹頂材料的聚合物,以長條形式拼接出漸變橘色幕帳,從古羅馬式樣教學樓的陽臺向下延展到庭院的草地上,圍合出開放式的三角形空間,取名“無際”(Invisible Border)。
當微風吹過,輕盈的幕帳便形成起伏的漣漪,陽光則透過幕帳長條之間的縫隙在地上留下變幻的陰影。裝置搭起后,周圍的師生不知不覺都被吸引了過來,搬幾把椅子坐下聊天。當馬巖松再次造訪自己的作品時,他欣喜地發現這里竟已自發成了一處公共空間!
Patricia Urquiola溫故知新
今年是現居米蘭的西班牙設計師Patricia Urquiola擔任Cassina品牌藝術總監以來首次參加米蘭設計周。在Patricia身上總能夠瞥見一種自由不羈的色彩,這也在Cassina展館內一覽無遺。整個展館絲毫不見“流行”元素,灰色水泥磚墻面不禁讓人聯想到1955年荷蘭設計師GerritRietveld為Cassina在荷蘭修建的展廳。在Patdcia的推動下,Cassina的經典作品經歷了一次技術和色彩方面的大革新,其中也包括Rietveld于1930年代設計的Utrecht扶手椅,發行了全新限量版。椅身特別運用了荷蘭設計師Bertjan Pot創作的五色提花面料。盡管Cassina擁有很多曾在設計史上掀起革命的經典作品,背靠這些大師之作,Patricia卻表示自己正蓄勢待發,會指導品牌持續出品新作,因為“只有這樣,才可能引發設計界的下一次‘革命’”!
Jaime Hayon升級舊作
西班牙設計師Jaime Hayon的走紅離不開BD Barcelona Design。10年前,出道不久的他為后者設計了“Showtime”系列作品,也將自己“秀”了出來。這是他設計生涯中的第一個國際大牌客戶。今年,品牌通過更換顏色、軟包、材料等方式升級這批舊作,紀念雙方合作10周年。在Jaime看來,“這10年間,我成長了很多,品牌也改變很大”。要知道道,當他剛和BD Barcelona Design合作時,品牌主打戶外家具,“他們從那時起開始向室內家具轉變,這是非常大的變化!”這次推出諸多舊作升級版也令Jaime高興,“如今大家總想看到新東西。品牌愿意繼續推廣舊作,說明只要設計好,就能一直存在!”剛在荷蘭、以色列舉辦個人回顧展的Jaime還透露,他正和一位中國藝術家進行合作,也令人充滿期待。
如恩設計墻外開花
如果用米蘭設計周作為設計師新一年開始的話,那么今年可謂如恩設計的大豐收年。在設計周不少展覽上都會偶遇他們,他們幾乎每天都在和不同品牌開會,聊聊這次展出作品的接受度,更洽談接下來的合作。今年,他們展出了為意大利家具品牌Poltrona Frau設計的“Supporting Ren”(配角)系列;為西班牙地毯品牌Nanimarquina設計的地毯“街JIE”;為西班牙燈具品牌Parachilna設計的燈具“Bai Family”(白家族),為瑞典家具品牌Offccct設計的衣架“Mr.O”(O先生);為意大利燈具品牌Viabizzuno設計的燈具“SulSole Va”;為由他們擔任藝術總監的Stellar Works設計的多件產品和全新的“Bund”(外灘)系列……他們還為丹麥面料品牌Kvadrat設計了名為“The Cut”(簡裁)的展覽空間!如恩設計的兩位夫妻檔創始人、擁有國際建筑教育與工作背景的郭錫恩與胡如珊,也因為和這些國際著名家具品牌的合作,無可爭議地與諸多國際大牌設計師站在了同一陣營,那些你叫得出名字的大師,和他們也是交情甚好。懂得用設計師的語言,而非“中國設計師”的語言,可能正是他們贏得業界信任與尊重、得以“墻外開花”的原因。
AD:你們和Poltrona Frau合作的最大挑戰是什么?你們并沒有設計這個品牌為人熟知的大體量的皮革家具?
如恩設計:主要的挑戰在于我們的物理距離,但一旦互相了解對方的需求,一切就變得簡單多了。Poltrona Frau以沙發和椅子為人所知。我們想要避開他們所擅長的,通過創作一些“配角”來“支持”大師和經典設計。要知道,大牌通常會忽略體量小一些的家具。
AD:你們這次為Kvadrat設計了展位,這和設計產品是否不同?
如恩設計:展位設計與產品設計、建筑設計都相當不同。你不得不去考慮第一印象、組裝技術和成本。我們考慮最多的是如何讓展位的設計和品牌本身有關,如何最好地展示品牌的個性、陳列和產品。在這個項目上,我們想要為參觀者打造一個舒適的空間,可以隨意坐下、享受空間,同時看看面料。我們甚至還把面料隱藏了起來,從展場外很難第一眼看到里面展示的產品。我們在天花板上做了開口,內部使用Kvadrat的織物包裹,在很遠處就能看到,從視覺上強化了織物的質感,讓展陳更具有吸引力。此外,這個展位可以輕松組裝、拆卸,隨時都可以用于Kvadrat之后參加的其他展覽。
AD:你們這次展出的不少作品都取了和中國相關的名字,這是一種強調你們中西方背景的策略嗎?
如恩設計:并不是特別的策略,我們只是覺得,中文和英文一樣好,為何英文才是為作品取名的唯一選擇?
AD:你們如何在米蘭同時展出那么多作品?在數碼時代,你們如何看待設計的速度?
如恩設計:我們試圖放慢一切,其實我們真的不想做太多事情。比起很多同行,我們已經算是做得比較少的了。然而,在這樣的時代,速度無疑是一個問題。我們只能盡力做好。我們甚至經常回絕一些有趣的項目提議,這也是完全可以的。我們現在不急于完成事情,設計師的生命周期是很長的。
AD:你們可能是參展米蘭設計周最頻繁的來自中國的設計師,你們怎么看今年的設計周?
如恩設計:展覽本身對我們來說并沒有太大變化。這仍然是家具設計里最好的展覽。對大多數設計師來說,它仍然令人興奮。
AD:你們接下來有什么項目?
如恩設計:我們為Poltrona Frau設計的巴黎展廳剛開放。我們還在為施華洛世奇、Lema、ClassiCon、雪花秀、Hem、Axor、Gan、Parachilna、Agape等品牌進行設計。
愛馬仕平衡之美
在米蘭維特拉劇院,愛馬仕新上任的家居藝術總監CharlotteMacauxPerelman和Alexis Fabrv為大家呈現了品牌全新的家具系列、藝術擺件系列及面料與墻紙創意。他們更特別邀請了墨西哥建筑師Mauricio Rocha設計了展覽現場。在原始的土磚墻隔斷內,幽暗的暖黃色燈光下,愛馬仕基調“平衡”的產品成為當仁不讓的主角。
AD:這次推出的新系列靈感來自何處?
CharlotteAlexis:平衡是自然萬物遵循的生存準則,也是家的核心。作為庇護身心的港灣,家將活力、幸福與和諧融合在一起,賦予人身心上的平和與愜意。我們希望通過作品實現這樣一種“平衡”。不論家具、擺件還是面料,平衡都很重要。我們不想制造任何噪聲或煽情。
AD:你們在米蘭也展廳,為伺這次邀請Mauricio Rocha在維特拉劇皖內設計展覽空間,發布新品?
CharlotteAlexis:我們選擇Mauricio是因為他的理念非常貼近愛馬仕的精神。他在墨西哥經常將當地原始的、傳統的材料用于當代建筑中。他對傳統的尊重正是吸引我們的地方,因為愛馬仕也很重視手工藝人,與他們合作創作當代物件。我們很喜歡Mauricio建筑中體現的力量和樸素,具有一種無聲的魅力。他為我們創作了粗獷的展示空間,和我們的產品形成一種美妙的對比。
AD:能具體說下剛剛提到的愛馬仕的精神嗎?
CharlotteAlexis:我們的作品是沉靜且有活力的。每個物件,不論大小,都呈現出精湛的手工藝。即便是非常小的物件,也需要花費很久的時間來制作。
AD:你們在意流行趨勢嗎?
CharlotteAlexis:不要問我們這樣的問題,我們相信愛馬仕是一個具有延續性的品牌,對我們來說,更重要的是創造可以抵御時間的作品。我們堅信我們的價值,我們也相信,應當和趨勢保持一定距離。AD:你們都不是家具背景出身,擔任愛馬仕的家居藝術總監感覺如何?
CharlotteAlexis:我們兩人一位是建筑師(Charlotte Macaux Perelman),一位是出版人(Alexis Fabry),我們合作時有很多不同的想法,會發生不少互補。我們處于一個跨界的時代,我們的強項也在于整合。
Lasvit大放異彩
在米蘭市區的塞爾貝羅尼宮曾是拿破侖在米蘭的行館,古典、華麗,金碧輝煌。今年的設計周期間,這里成為捷克玻璃品牌Lasvit的展覽“Via Lucis”(光明之路)的舉辦地。
這個成立于2007年的年輕品牌,在過去一年里有許多大動作。他們在塞爾貝羅尼基金會的支持下,修復了塞爾貝羅尼宮內的4盞水晶吊燈。這些曾經屬于拿破侖的吊燈生產于18世紀末。為了確保能夠保留吊燈的原始特色,每盞吊燈都被拆解后海運到捷克進行修復,它們恰好也是由18世紀的波希米亞水晶玻璃手工制作而成的,也因此通過這次修復完成了一場歷史的創造性輪回。
修復了塞爾貝羅尼宮內的吊燈之后,Lasvit就開始著手準備另一段獨特的現代作品之旅。品牌和多達18位設計師或組合合作,包括Arik Levy、Daniel Libeskind、Campana兄弟、AndéFu、MaurizioGalante等在業界頗為活躍的設計師,以及捷克傳奇人物和年輕設計師,請他們用現代方式重新詮釋新古典風格枝形吊燈。而為了展現這些新作,Lasvit在古典大廳里搭建起立體幾何造型半包圍式的展示空間,構建出傳統與現代對話的契機。
盡管Lasvit出品的多數燈具都體量較大,富有戲劇性的視覺震撼力,生于香港的設計師AndréFu卻為品牌創作了一系列內斂含蓄的作品,這也是具有豐富室內設計經驗的他首度操刀燈具設計。在André看來,燈飾本身代表著一種體驗。他為作品取了“tactile”(觸覺)相似的名字“TAC/TILE”,正是為了強調自己對觸感的探索,比如手指觸碰材質時的體驗。“設計室內空間要通過家具、光線、材質、氣氛等多種元素來講述故事。而設計一件單品時,我想挑戰自己是否也能達到同樣效果。”他將不同風格、時代的建筑元素反映在作品中,精準的三角形玻璃磚可成垂直與水平兩種形態。垂直時,呼應了具有現代審美的都市建筑;水平時,又讓人聯想到東方式的屋檐。光從朦朧的玻璃磚透過,令玻璃與黃銅材質構成的燈飾變成了簡潔內斂的發光體,有別于品牌之前的風格。
其他設計師在自己的作品中一方面凸顯了個人風格,另一方面探索了玻璃材質的特點和工藝上的可能。比如,現居巴黎的時裝設計師Maurizio Galante為品牌設計了名為“Ludwig”的吊燈,以此尋找科技與情感、歷史與現代之間的平衡。奧地利藝術家Raja Schwahn-Reichmann則帶來具有巴洛克田園風格的作品“Omnia Vincit Amort”(愛無所不能)。Lasvit的創意總監Maxim Velcovsky以捷克知名“入骨教堂”的尸骨吊燈為靈感,用玻璃材料重塑了入骨的形狀,象征了出生、死亡以及代代相傳的歐洲工藝的消亡。來自巴西的Campana兄弟繼續他們和Lasvit的合作,推出了“candy”(糖果)桌上器皿,在設計師看來,“糖果代表著一種趣味和天真”。
相比椅子、燈具,凳子可能并不能夠引起很多人注意,而這也正是Michael Anastassiades為之著迷的原因。這位居住在倫敦的塞浦路斯設計師最廣為人知的作品莫過于他的同名品牌黃銅架空結構燈具。當然,他為Flos設計的極簡主義燈具也為他贏來不少關注。今年,受到已有百年歷史的美國家具品牌Herman Miller邀約,Michael首度設計了凳子“Spot”與小桌“Stasis”,由胡桃木與橡木制成,一根黃銅管、一根木管連接起圓形的底座和頂部,與Michacl的燈具共同營造出極簡與神秘的環境。可以說,這是一位將線條和材料的節制,以及物品的無時間性置于一切之上的設計師。這也昭示著他加入了一個神秘設計師俱樂部,包括CharlesRay Eames、Georges Nelson、Isamu Noguchi(野口勇)等國際大師都曾是Herman Miller為數不算太多的合作對象。
AD:這一項目是如何開始的?
Michael:Herman Miller曾和Eames夫婦、Georges Nelson等大師都合作過,一直想要創作具有永恒性的設計。這也是他們的設計要求。他們請我設計凳子,我自己也挺喜歡凳子的。設計本身非常單純,對我來說,最好的贊揚就是沒人發現這些物件。我曾在多年前為倫敦的一座東正教堂設計了枝形吊燈,我的朋友去了教堂,站在燈下,都沒發現這是我的作品!這意味著我的設計成為環境的一部分,這很棒!我也用這樣的思路來設計凳子。
AD:您為何喜歡凳子?
Michael:我一直都為凳子著迷,還收藏了很多小凳子。我從eBay和很多地方把它們買回來。這是一種富有力量和挑戰的物件。至今尚未有過第二張像Alvar Aalto的“Stoo160”凳子那樣風靡全球的凳子,這不正是凳子的迷人之處嗎?
AD:您的家怎么樣?
Michael:我住的房子不大,每個房間都只有25-30平方米。但也正因為此,你可以一眼看到所有物件,以及它們如何共處一室。我家也沒有很多東西,而且我自己的燈具在其中占了大頭。對我來說,把作品放在真實的居住環境是一種有趣的練習。
AD:您會為Herman Miller設計燈具嗎?
Michael:不會,他們并不是因為燈具而知名的。而且我已經和Flos合作了,我也只想和幾個品牌合作。
MarcelWanders叛逆和諧
歷來天馬行空的荷蘭品牌Moooi,今年以“叛逆的和諧”為主題,一口氣推出了22件新品。光是入口處的藝術出版物Rijks,Masters of theGolden Age就足以令人屏息。這是Moooi創始人Marcel Wanders花費3年多時間完成的向17世紀荷蘭藝術巨作的致敬之作。他特地找到為梵蒂岡教廷印刷書籍的公司進行印刷。“這本書呈現了藝術巨作如何影響了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Marcel說。步入展廳,幾乎直立的“Charleston”沙發絕對是視線焦點,“你想跳舞嗎?它會是最佳舞伴!”Marcel這么評價自己的這件新作。若要比重量,那么英國設計師Paul Cocksedge為Moooi創作的“Compression”沙發則可能是最重的家具,用了足足6噸大理石!另一件吸引眼球的作品則是英國設計師Umut Yamac的“Perch”燈具系列,包括落地燈、桌燈、壁燈等6款,正如它們的名字,燈具看起來猶如棲息在枝頭的折紙小鳥。而最令MarcelWanders激動的莫過于Moooi Carpets在去年基礎上推出了更多逼真的大幅數碼印花地毯系列,并可接受網上定制。Marcel不僅親自為這批地毯站臺,還興奮地在電腦上向參觀者們一一演示操作方式,“你還能直接在網站上設計圖案、尺寸,實時看到環境里的視覺效果。點擊發送,我們就能為你打印。這絕對是地面設計界的創新!”這次也是Moooi的新任CEO Robin Bevers上任以來的正式對外亮相。“今年‘叛逆的和諧’的主題和我們的理念一致。在Moooi,我們總是想方設法平衡創意和生意、混亂和秩序。”據悉,Moooi還將在倫敦和東京開設全新的展廳,進一步發展荷蘭之外的市場。
Studio Job符號帝國
歷來幽默荒誕、特立獨行的Studio Job,今年在米蘭設計周推出了為馬賽克品牌Bisazza設計的全新鑲嵌瓷磚系列。正如他們此前為NLXL創作的墻紙和為Seletti設計的戶外家居,這批作品也同樣使用了工作室的部分檔案圖案符號。Studio Job將巨型像素和馬賽克表面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也映照了我們充滿各種圖案和表情符號的日常生活。
AD:你們曾在2007年時和Bisazza合作過大型“Silverware”塑料系列,這次又緣何為品牌的核心產品馬賽克設計了5款圖案?
Studio Job:上一次的雕塑作品猶如一次高級定制項目,我們也愿意把我們的標志性圖案分享給Bisazza,用于馬賽克設計中。這些圖案來自我們的檔案,但用于馬賽克是第一次。其中,我們延續之前不斷從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中提取符號的做法,設計了“Industry Amber”,運用了蒸汽機、機車輪、工具等那個時期的象征性物件。我們想要通過在圖案中創造象征性語言,用富有秩序的無秩序來象征力量和危險。
AD:你們如何定義Studio Job?
Studio Job:我們處于各種事物的邊緣。在過去15年間,設計越來越跨界。我們與藝術、音樂、時尚有很多交集。這猶如文藝復興時期的做法,對我們來說就是“設計”這個詞的定義。不論我們做什么,我們有自己的風格。我們更像是公司內部的客座藝術總監。
AD:你們的這種風格是否也受到成長環境的影響?
Studio Job:我(Job Smeets)的父親是一位古董商,從小家里有很多古董家具、時鐘、畫作。我可以不假思索地用5秒鐘畫出一個18世紀的拿破侖櫥柜。我想這些都對我現在有很大影響。Nynke則在一個更為現代的環境中長大。她學習面料和平面設計,我則更喜歡古董,更具有概念性。所以Nynke負責電腦制圖,我負責一些大的框架和方向,這就是我們的分工。
AD:那你們的團隊構或呢?
Studio Job:我們有25人,是一個比較大的作坊。這個規模對我們來說足夠了,否則就會失去和員工交流的機會。把團隊做到越大越好是個瘋狂的想法。生命有限,我覺得應該把時間花在質量而不是數量上。我希望和藝術與設計中的其他小公司一起,向大家傳達一則信息:發展壯大并非一切。
COS光之森林
米蘭設計周可不只是家具品牌的事,時裝品牌COS今年已是第五次參展。這次,COS請來日本建筑師藤本壯介,在一棟建于20世紀30年代的荒廢意大利劇院Cinema Arti內,上演了一出光影交錯的裝置作品“光之森林”(Forest of Light)。
穿過前臺,再掀開黑色的幕布,參觀者便進入了漆黑的劇場式空間。多個圓錐形聚光燈從天花板上照射下來,更妙的是,它們會隨著人的移動路線,忽明忽暗變化!在這個過程中,特別設計的聲音、薄霧和鏡墻營造出立體無盡的空間,圓錐形聚光燈則化身為樹木,形成一個明明滅滅的“光之森林”。
出生于日本北海道的藤本壯介從小生活在大自然中,他的建筑作品大多強調虛空間和自然感,也成為COS近年來的設計靈感。受到品牌邀請后,藤本壯介感受到時裝與建筑的共通之處,“COS的時裝中蘊含著極簡主義美學,基本、優雅、具有永久性的美感。”于是,他決定用一種非物質的材質表達COS的這些特性,從品牌z016春夏系列獲得靈感,最終選定了用光、影、聲音構成的“光之森林”來呈現結構、空間、身體之間的關系。“對我來說,森林是一個非常好的空間,簡單、有活力。”參觀著聚光燈構成的虛幻空間里,從明走向暗,從暗通向明。現場的座椅又給人一個停下來休息的地方。“聚光燈成了時裝、空間與由光影構成的建筑之間的接口。”
Nendo從漫畫里跳出來的椅子!
在米蘭市區的一處庭院里,舞臺上布滿了閃耀著銀色光芒的椅子,有的似乎在模糊抖動,有的仿佛被肢解扭曲,有的則被加上了射線,似乎隨時都可能丟下你跑路,還有的被安上了一圈弧線,仿佛正要打轉起舞……這些猶如漫畫表情和動作的椅子,正是近年來備受關注的日本設計事務所Nendo的創作,也是多產的Nendo事務所目前正在進行的400多個項目的其中之一!放射線、速度線、集中線等效果線,都是日本漫畫中慣用的繪畫手法,有助于表現情感、聲音和動作,讓漫畫更具視覺沖擊力。Nendo的創始人佐藤大將這些技法轉化成家具設計的語言。原本靜止不動的椅子加上了夸張的視覺效果后,立刻成為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主角。全部鏡面設計,令人恍惚究竟身處二次元的漫畫中還是三次元的真實世界里。當然,這50張“漫畫椅”都是限量設計,也并不是真正用來“坐”的。今年9月,這些還將在紐約Friedman Benda藝廊展出,這也是Nendo最近在設計藝術方面的傘新嘗試。
AD:您怎么會想到做這些“漫畫椅”的?
Nendo:在我很小的時候,我成天喜歡看漫畫,父母常常為此生氣。而一旦我去參觀博物館和美術館,父母就變得特別高興。我就納悶,看漫畫和去美術館之間有什么區別呢?最近,我認真研究了日本漫畫,發現它其實也凝聚了日本文化的精華。于是我就想,是否可以將漫畫的元素轉化到家具和物件中?
AD:您是如何發展出這一系列的?
Nendo:我們先打造了一把沒有任何變化的正常的椅子,然后就開始做各種漫畫變體。但和漫畫一樣,我故意避開了顏色、紋理等效果,采用不銹鋼來制作椅子,并且使用光滑的鏡面效果,這樣就能在空間里形成新的層次。鏡面可以反射出真實的外部世界,正如漫畫反映生活日常一樣。為了達到最好的效果,這些椅子都在日本手工打磨,用了4個月時間!
AD:這50把椅子里,您最喜歡哪一把?
Nendo:我最喜歡布滿放射狀線條、似乎隨時都可能爆炸的那一把。但它特別沉,需要六七個人才能搬得動!當它抵達米蘭時,很不幸,一些線條斷裂了。我們不得不從日本飛來的制作者,并且租了一臺焊接機,在展覽現場進行修補。
AD:您的靈感究竟從何而來?
Nendo:我發現關注日常生活中的常規就能帶來非常多的啟發。如果你每天都做同樣的事,你一定會發現其中細微的區別。這些細微的區別正是我的靈感來源。
巴卡拉開箱生輝
法國水晶品牌Baccarat巴卡拉的紅色包裝盒甚是經典,當你拆開盒子的那一刻,是期待與驚喜。今年米蘭設計周上,CEO DanielaRiccardi想把這份驚喜和“盒子”的概念擴大。于是,就有了在Brera美術學院內這場名為“紅匣子外那一抹流光溢彩”的展覽。若干大型木頭集裝箱內,璀璨、華麗的枝形吊燈被固定其中,像一個個正準備打包、運送的隆重的禮物。要知道,幾個世紀以來,Baccarat巴卡拉吊燈正是被放在木匣中運往世界各地的!
這些熠熠生輝的“禮物”的創作者也個個來頭不小。其中,以創作大型裝置藝術聞名的荷蘭藝術家Hans van Bentem重新演繹了著名的大理石美第奇花瓶,全球限量8件。值得一提的是,美第奇花瓶的水晶版本也是由Baccarat巴卡拉在1909年時制作完成的。另一位荷蘭設計師Marcel Wanders則在品牌著名的Zenith吊燈基礎上,重新設計的輪廓,柔化了棱角,并加入虬枝、流蘇及八角形,現代感十足。這盞吊燈被取名“Le Roi Soleil”(太陽王),致敬法國路易十四君主。Marcel還富有革命性地將他兩年前為Baccarat巴卡拉設計的復古花瓶上下顛倒,加上面板,變成了茶幾!茶幾內藏LED充電系統,夜間看起來猶如懸浮在空中,為周圍籠罩上一層神秘的光環。以色列藝術家、設計師Arik Lew則進一步發展了他同品牌于2013年合作的Tuile de Cristal系列,借助建筑學的演繹方式,磚塊的雛形為多種設計的組合提供了遐想的空間。
幾乎每次參加米蘭設計周,Tom Dixon總會帶來一點兒新奇的點子!從在博物館里重構19世紀火車站發布新品,到把廢棄劇院改造為“電影院”售賣產品,今年,Tom大叔開起一家“餐廳”!位于米蘭市區17世紀的古老回廊里,這家臨時餐廳只在本屆設計周期間對外開放,全天提供食物,晚餐則需預約。這里也是Tom大叔發布新品的所在地,推出了運用金屬、塑料、玻璃等材料創作的“Materiality”系列,以及小型組裝家具“Offcut”系列。這家臨時餐廳的合作對象是石材品牌愷薩金石(Caesarstone)和意大利食物設計工作室,Mabeschi di Latte。Tom大叔為愷薩金石設計了4款廚房,Arabeschi di Latte相應策劃了空氣、土地、火、水4種不同主題的晚餐菜單,供應富有實驗性又營養健康的食物。從菜單到服務員,這里的一切看起來都是一家如假包換的餐廳!在馬不停蹄地參觀設計周期間,逛到這里,可以隨手切下一片面包、鑿開一塊巧克力,Tom大叔貼心地解決了很多參觀者的溫飽問題!
AD:您是然后和想到在設計周期間搭建一家臨時餐廳的?
Tom Dixon:在意大利,食品與生活藝術是緊密相連的。很多決定都是在進餐時談攏的,而不是像在英國或美國,非得在一場會面中才能敲定。此外,米蘭設計周已經變成了一場馬拉松,或者說“設計競技場”,人們以一種毫無節制的節奏消費著新鮮事物。我認為有必要創建一些場所,讓人們能夠感受到緩慢的節奏和冥思的喜悅。這就是我創建臨時餐廳的初衷。
AD:您在倫敦的商店里也開了一家餐廳?
Tom Dixon:我在倫敦的餐館之所以誕生,首先是因為我熱愛下廚。下廚與設計非常接近,兩者都是將一些簡單的原料進行轉化的過程,比如把面粉轉變成面包。這一過程對我而言至關重要,即將平凡無用的東西轉變成極具價值的東西。當然,不得不承認,由于市中心越發昂貴的店面租金,對于一個設計師而言,很難光靠銷售設計品維持一家后面的盈利。我們可以在自己的餐廳里展出作品,這點大大有助于銷售。在決定買下一件價值不菲的家具或者燈具前,人們都希望能夠切身感受一下這些家具在現實生活中的效果,這是人之常情。
AD:您設計的燈具也受到室內設計師的青睞,被廣泛應用于餐廳中?
Tom Dixon:我們的強項在于既能滿足住宅市場的需求,也能滿足“合同”市場的期待。因此,對一盞燈具或一把扶手椅的設計,我們既應該讓其適應大酒店的環境,也應該讓其適應私人住宅的環境。室內設計師的確很喜歡用我們的燈具來裝飾餐廳或舞廳,這或許是因為黃銅制品的暖色調比運用新技術的冷色調照明更容易令人感到舒緩吧!
Gam Fratesi大腦奧秘
在米蘭市區一棟19世紀建筑內,一個巨大的底座上鋪滿了深紅色地毯,上面的圖案猶如大腦細胞組織。底座緩慢旋轉,跟著旋轉的是其上陳列的各種家具。這正是由丹麥藝術基金會支持的Mindcraft16展覽。延續去年,由當紅丹麥意大利設計組合GamFratesi策展。Gam Fatesi的兩位創始人——丹麥人Stine Gam和意大利人EnricoFratesi曾同在意大利學習建筑,2006年合作成立工作室。他們在位于哥本哈根的工作室里處理著日益精進的設計工作,就在5個月前,還迎來了他們的第二個孩子!不同于去年用鏡面反射效果策劃的Mindcraft15,今年Gam Fratesi用猶如大腦運作的裝置強調設計背后人腦的思考過程,整個展覽概念性十足,又充滿些許喜劇色彩。此外,在米蘭設計周期間,這個已經在業界建立響亮名號的組合還展出了為家具品牌Porro、曲木家具品牌Thonet、衛浴品牌Axor(雅生)等多個品牌設計的作品。
AD:能介紹一下這次展覽的主題嗎?
Gam Fratesi:展覽所在地Cimle Filologico曾是語言學習和研究院,所以我們展覽的主題是“頭腦”(Mind)——就像每次開始設計前都要先思考一樣。展覽的設計模仿了抽象的大腦。我們覺得人腦工作起來猶如發條:想法一個接著一個,這也啟發了我們令展臺旋轉起來的設計。每一位設計師都是獨立的個體,但他們不免受傳統、文化和環境的影響。
AD:你們如何選擇參展作品?
Gam Fratesi:我們選擇設計師,而不是展品,每一位設計師都被要求根據主題設計作品。對Mindcraft來說,通常新銳設計師和知名設計師各占一半。同時,我們希望每一件參展作品都有自己的特點,這樣展覽會更多元化,也就不會有20件同一類型的展品。
AD:你們的作品常被描述為意大利和丹麥設計的聯姻,你們自己怎么看?
Gam Fratesi:丹麥設計在很大程度上基于手工藝,因此忠于材料,也注重功能。意大利則更注重創新,但創新并不是在材料上,往往是在作品的概念或設計想要傳達的訊息上,功能不一定是設計的重點。我們在合作上保持誠實和開放的態度,經常展開熱烈討論,不同的背景也促使我們對事物進行更深入的分析。所以我們的設計中并不會存在割裂的意大利或丹麥設計。
AD:丹麥設計現在很熱門?
Gam Fratesi:現在對丹麥設計來說確實是個好時機。我們有20世紀50年代開始留下來的很棒的設計,但這多少為后來的設計師帶來了挑戰,當代設計師也開始摸索新的方向。當然,不論方向如何不同,作品一定仍是“以人為本”的。意大利的設計有時會傳達一種“只看別摸”的訊息,而丹麥的設計更人性化,始終強調人們會在實際生活中享受設計,這是丹麥設計的原則之一。在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任何設計都要實用、能夠為人們帶來快樂。我們做設計也是這樣。
現居倫敦的以色利設計師Ron Arad是設計師中的另類。他曾在眾星云集的英國AA建筑學院師從建筑大師Pete Cook和Bernard Tschumi,和不久前去世的建筑師Zaha Hadid是同班同學。如果不是因為Moroso,也許Ron會更以“建筑師”的身份為外界所知。自1991年,他與Moroso開始了一系列家具設計合作,將粗糙的金屬鑄造為富有戲劇感的家具,這成為他富有標志性的設計語言,也令他成為米蘭設計周上的常客。而在這25年間,Moroso也成長為業界最重要的設計品牌之一。今年,Moroso特別在城里的展廳為Ron舉辦了一場回顧特展“Spring to Mind”(思春)。
AD:為何這次展覽取名“Spring to Mind”?
Ron Arad:我和Moroso的合作源于總在春天舉辦的米蘭設計周,這是原因之一。另外,我經常在家具里運用彈簧(Spring),這也是一個原因。
AD:您和Moroso的合作是怎么開始的?
Ron Arad:這一切都始于一個玩笑!我坐著的這把“Big Easy”扶手椅其實是我在米蘭設計周開的玩笑。它看起來很柔軟,卻是金屬做的!前來看展的Patrizia Moroso就問我能否由Moroso生產這把椅子。我當時這么回答她:“不行,我不能只給你一件。我要做一個系列,否則就不干。”沒想到Parrizia欣然答應了。當時她剛從博洛尼亞大學畢業,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我們開始合作時,Moroso家族的其他人還有些猶豫,但patnzia表現出決斷和勇敢。Moroso也從當年名不見經傳的品牌發展為一線當代家具品牌。
AD:合作25年后感受如何?
Ron Arad:通常,你和一家公司合作,就真的是和一家“公司”合作。但和Moroso合作不一樣。你能感受到Patrizia Moroso在其中的用心,仿佛她的姓氏只是碰巧和公司名字相同而已。你能感受到“人”。不僅是Patrizia,整個團隊都仿佛是我的家人,這種關系非常特別。
AD:您對這次展覽滿意嗎?
Ron Arad:在這里我就像是客人,因為展覽全是Patrizia和她的團隊來設計和執行的。如果你在Instagram社交平臺上搜索標簽ronarad,你會發現參觀者們上傳了數以千計的展覽現場圖片!
Atelier Biagetti家具的隱喻
去年,觀察到現代人對追求“完美身形”的著迷,Atelier Biagetti的兩位創始人Alberto Biagetti和LauraB aldassafi,同策展人Maria CristinaDidem聯合在米蘭設計周推出了Body Building系列。今年,他們再度聯手打造了全新系列:No Sex。“Body Building系列與身體相關,而NoSex與心理相關。我們感興趣的并不是設計一把新的椅子或一張新的桌子,而是想要了解物品放在家里產生的效果,因為家是人最親密的地方。”Alberto Biagetti說。而策展人Maria Cristina Didem這樣看待Atelier Blagetti的創作:“我覺得他們的工作性質有些像小說家。他們從現代生活中提煉出主題,再進行詮釋。只不過,作為設計師,他們是以立體物件的形式來詮釋的。如果他們是電影工作者,說不定就用電影來表現這些主題了。”No Sex系列所有作品都采用設計藝廊的方式,每款限量7件,都具有巧妙的隱喻。比如,當你坐上多層折疊皮質軟墩時,它仿佛嘆了一口氣:那盞圓形落地燈則令人錯覺進入了婦科診所。值得一提的是,野獸形狀的地毯、粉色和香檳色的十字形鏡子已被Seletti相中,將由后者制作與銷售。這無疑也有助于Seletti加強品牌自與Toilet Paper雜志合作以來的設計藝術推廣者的形象。
Airbnb早餐會的遇見
繼去年的“暖房派對”之后,這次網絡房屋短租平臺Airbnb在Marta de Rossana Orlandi餐廳辦起了“早餐會”。擔當策展人的是DesignMiami的創始人Ambra Medda,她設想出一場“請盡情觸碰”的展覽“MakersBakers”(匠人和面包師)。25位設計新人圍繞著共掣甓物制作了不少富有手工藝感的食器和裝飾。在Ambra看來,這更像是“策劃了一次體驗”,填飽肚子也充盈頭腦:“人們可以在這里相會交流,而這不正是大家來米蘭看設計周的原因之一嗎?”不妨坐下來吃塊點心、喝一口小酒,認識些新朋友吧!
Kvadrat童話森林
丹麥面料品牌Kvadrar最為人熱議的莫過于品牌和Christian Dior前創意總監Raf Simons的合作,將高級定制的魅力延續到面料上。誰能想到,Kvadrat竟然還有一顆“童話心”!在今年的米蘭設計周上,他們就推出了與日本面料設計師皆川明合作的作品,極具溫暖、放松的童話色彩!其實這源于10年前雙方首次合作時的一條約定,便有了10年后再度合作一套作品的理由!熱愛北歐設計的皆川明將自己創作的圖案、精致的刺繡細節和微妙的色彩層次運用于3款面料、1款窗簾和限量靠墊配飾品上。他采用樹枝、雨滴和花卉等抽象圖案敘述自己想說的故事,令人聯想到靜謐的森林和結滿果子的樹木。這些面料還被皆川明的好友、日本設計師深澤直人用在Murani品牌的家具上!皆川明為展覽取名“Forest comes Homes”(森林回家),對他來說,“城市離不開自然,希望能用一片‘森林’為人們創造一種安心和舒適。”
施華洛世奇水晶的無窮可能
奧地利水晶品牌施華洛世奇今年在米蘭的展覽刷新了人們對于品牌的固有印象,在首飾和裝置之外,首度推出了全新家飾品牌“Atelier Swarovski Home”。品牌邀請Daniel Libeskind、Ron Arad、AldoBakker等著名設計師為其設計首批作品,包括餐桌擺飾、娛樂和家庭辦公器物。設計師們結合大理石、金屬、樹脂等材質,運用前沿精妙的水晶切割技術,淋漓盡致地表現出水晶的特性,也賦予水晶更多可能性。從今年秋季開始,這一全新品牌將在全球部分獨立零售商店內售賣,價格設定在150~2萬歐元之間。
Marni跳支舞吧!
自2012年以來,時裝品牌Marni每年都會在米蘭設計周期間展出一系列由哥倫比亞婦女團隊手工制作的塑料戶外椅子,所得收入部分捐贈給一家旨在支持兒童保護的印度慈善機構。今年,Marni將這一展覽升級成“舞會”,令這一跨文化、跨年齡的分享更為光彩奪目。“我們希望可以更面向公眾,”Marni創始人Consuelo Castiglioni的女兒、特別項目總監Carolina Castiglioni告訴我們,“由此便誕生了設計周期間的Cumbia舞蹈課程。這是一種帶有非洲元素的哥倫比亞舞蹈,需要穿著寬松的圓擺裙。我們特意為前來‘舞會’的人們,用Marni的歷史面料定制了一批這樣的裙子。”結果呢?一場既像家庭聚會,又像期末匯報演出的活動應運而生!Consuelo和她的孫女一起跳起了舞,孫子則坐在爺爺的肩膀上。這樣其樂融融的場面在時裝品牌的跨界活動中難得一見,洋溢著真誠又時髦的波希米亞氣息,而這不也正是Marni的風格嗎?至于展出的那些帶點兒復古味的戶外椅,也正日益受到針對年輕人群的設計酒店的追捧。
今年已84歲高齡的德國“光之詩人”Ingo Maurer在米蘭市區SanPaolo Converso教堂里展出剛剛研發的新作品。教堂內文藝復興后期的壁畫前,各種現代構成感十足的燈具,創造出令人震撼的視覺效果。金箔、陶瓷碎片、羽毛、鋁箔、刀叉……都曾被Ingo Maurer用在燈具上,化平凡為神奇。每一個看似隨性偶發的細節處理,其實都經過嚴謹精確的計算,才能給空間帶來豐富的感性特征。今年推出的“Keep Balance”(保持平衡)系列也是此前作品的延伸,由可以全角度旋轉的60厘米高的平衡軸構成。平衡軸一頭是沒有任何裝飾的燈泡,另一頭則是一個白色“大雞蛋”。“我喜歡那些需要一點兒解釋的簡單事情,”Ingo Maurer說,“白熾燈泡一直是我的最愛,我也一直嘗試把好玩的形式加入其中,比如蛋。這一切都始于文藝復興早期的著名畫家Piero della Francesca,這樣做你就會一直盯著作品不放。”有著知識分子外形與哲學家氣質的Ingo Maurer相當擅長用理性的科技呈現出極具人文感性的燈光,無時無刻不給人帶來震撼。這不,教堂穹頂上還掛著兩個大型吊燈,可以直接通過智能手機里的App進行控制!至于說到為何以“保持平衡”為名,IngoMaurer坦然表示:“平衡和有趣同樣重要,在嚴肅中保持玩樂的詼諧態度,能讓很多可能性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