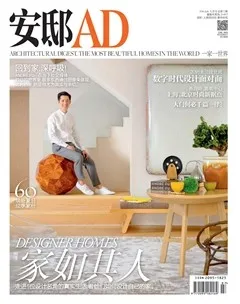不安分的美猴王



最近,鄔建安的展覽“萬物”正在前波畫廊展出:在一個單獨的展覽空間內,近1500塊被切割出不同紋路的舊磚組成《淺山》,顯得氣勢恢弘;而在另一個空間內,由泛著珍珠磷光的海螺殼所組成的大骷髏裝置《大骨架》,看上去既驚悚,又有著細節處的恍惚美感。此外,最顯眼的便是由密集手工剪紙疊加形成的裝置《萬物》、將水墨筆畫拆解又拼貼而成的《五百筆》,以及角落里由鹿角和蛇骨組成的極小型恐龍、掛在鹿角上的《仙家》和36塊大理石排列成的《三十六劃》,它們都在變幻演繹著個體與整體的關系。
“它的故事線索是孫悟空被壓在五行山下,‘五行’在中國古代哲學里象征了世間萬物,孫悟空則是一個不服從整體規劃的叛逆者,被鎮壓500年后出來了。”在位于環鐵藝術區的工作室內,鄔建安向我們通俗地解說這次展覽,這位曾被人稱為“不安分的美猴王”的藝術家,大多時候說話嚴肅、理性,但偶爾激動、戲謔的語氣里又透露出他骨子里的叛逆。在他的作品里,我們不難看出美猴王的影子,就連工作室的門簾上也有張彩色的猴臉,而周圍他收集的唐卡、動物頭顱標本和皮毛,以及印第安人頭像木雕,都使得這里多了幾分原始洞穴的感覺。他將展覽中的裝置作品《大骨架》——一件由許多個拋光海螺組成的大骷髏和它后面的空間想象為一張大網,“象征曾經關住孫悟空的空間,磚的作品就是五行山,就像我們小時候抓蛐蛐玩兒會搬開磚頭看,萬物有些七十二變的氣象,五百筆就像一個個體和整體關系的推演:組成字的筆畫被拆開了,再任意拼貼,最后也可形成一個混沌又完整的小宇宙,而恐龍是蛇骨和鹿角的再組合,‘仙家’中影的存在也會改變鹿角底座原有的身份”。
個體和整體的神秘關系,一直是吸引和困擾鄔建安的根本問題,也激勵著他去尋找藝術語言來表達。比如2011年,他運用傳統剪紙藝術做的大型裝置作品《七層殼》,“用360個小人物形象組成7組作品,試圖讓個體形成明朗的整體形象,但做到后面非常疲勞”。2014年,他又做了大規模展覽“白猿涅槃”,“好像故意嗆著來,不組成任何整體,只有個體,但最后自我感覺有些情緒化,那么到‘萬物’,不再是簡單的整體大于局部,或局部要戰勝整體的兩極化思路,整體和個體各有多種存在的樣本,它們可以演化出復雜豐富的關系”。其中,與展覽同名的作品《萬物》是用上萬個浸蠟鏤空剪紙組成的“三聯畫”,畫面中隱隱約約可見各類形象:骷髏、鳥、魚、獸、神仙、鬼怪和羽人等,它們形成的整體卻好像混沌的煙霧,既有手掌、山體、猴臉,也有盤旋的通道和云煙,層層疊疊,說不清、道不明,讓人聯想到宇宙內萬物共生又如謎一般的關系。
奇妙的是,這件作品雖然工藝復雜,但將鄔建安所擅長的剪紙藝術發揮得淋漓盡致。實際上,他對民間藝術的迷戀始自在中煙美院讀研期間。他學的是民間美術,2003年鬧“非典”,他待在家里,在窗也不敢開的恐懼感里,突然剪出一系列富有遠古圖騰意味的“白日夢”剪紙系列,之后一發不可收拾。根據上古神話剪出數百種形象,造型雖有傳統氣息,但又借鑒西方解剖人體學的圖像和自己的想象,使得它們自成一個荒誕志怪的小世界。再之后,他陸續嘗試過結合牛皮鏤刻、夾宣鏤刻和皮影戲等民間藝術創作,由此催生出極具個人色彩的藝術面貌。對他來說,民間藝術手工質感的不完美、不確定,如同蘊含在個體身上的神秘、閃爍不定的質感;另一方面,嚴謹和精細化的工藝流程操作又仿佛無數個體匯集成整體,某種神秘力量會帶來無法預料的演化,這兩種矛盾特質的融合就像一個謎,“神秘的東西往往潛藏著巨大的能量,就好像你自以為想要個人主義,但內心其實都藏著整體,藝術最有魅力的地方就在這里,它會帶著你求索,跟潛意識對話,來讓你看清內心深處的那個整體,也會帶來做些事情的愿望和勇氣”。
今年春節,鄔建安先后在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和波士頓美術館邀請觀眾互動,一邊“揭開咒符、解放美猴王”,一邊體驗做中國的剪紙拼貼,而在不久前,他剛剛去往日本考察大地藝術節藝術項目的實施環境,同時,他還在美院執教,風風火火地身兼多重角色,與許多藝術家安于創作的作風迥然不同。實際上,他很樂意體驗不同的藝術表達,“有時在藝術機構,有時在鄉村,有時在課堂,都是將藝術思考和工作成果與眾分享的方式,而且不同環境會帶來不同的結果和思考”。說到底,他是在以知行合一的方式來解開生命這道大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