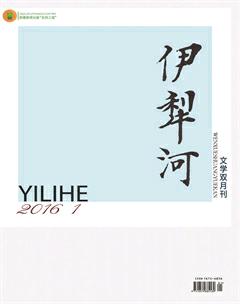阿爾山的態度(外七章)
周慶榮
1
我投宿的地方是一座山,它有一朵花的名字。當陽光有了傍晚的溫柔,我想向玫瑰峰要一個高度。
如果誰告訴你,玫瑰長在高山,你不要僅為玫瑰而登攀。你要在高處看一條河,看河畔的草原和仿佛畫中的羊群。
我喜歡這樣的黃昏,哈拉哈河的氣質憂郁而深沉,在夕陽下。
我喜歡站在玫瑰峰一尊像極了思想者雕塑的石峰邊,向下眺望。目光遼闊,全部的山河暫時都屬于思想者。當地的詩人李巖說,石峰與一位領袖很像。
我堅持把高處的光榮給予思想。
當我們站在山頂,我們就一起把思想投向山下的事物,真實并且具體的事物。
2
在野韭菜個性固執的味道里,我從藍柳花的美麗背后,看到大片的趴地松。
它們是這里最樸素的比喻。
不長高,但氣宇不凡。它們在石叢里扎根,石頭黑里透紅,這段地形里河流名叫柴,提醒曾經的樹木與火的關系。
愛著愛著就選錯了方式。
久遠的地心之火,它推翻作為一塊整體石頭的山脈。大石太霸道,它壟斷了土地的形象還是禁錮了生命的豐富?
液體的火,土地深處的脾氣?
我理解一切革命的理由,石頭裂開,舊雨加上新雨,時間沉默為永恒的伴侶。我現在看到的新事物生長在陳舊的石頭之上,聽到河水汩汩流淌,黑褐色的存在似乎重新美麗,草、野花與樹木覆蓋住最初的傷痕。
美麗,在疼痛之后。
3
哪一塊土地能夠如此袒露內心?
在阿爾山,我看到大峽谷深深的往事。如果時間允許,我會一塊一塊地數,數幾十萬年前森林里每一棵樹,數樹枝上每一只松鼠和天空中飛翔的鷹,數野動物公民般的眼神。
這里是石頭的世道。被地火煮沸熏黑的環境,我看到火熱的心。
一些水證明著這片土地上純凈的濕潤,我愿意把這種濕潤形容為希望的情感。
高處的水就叫天池吧,低處的依然是地池。再大一些的我們習慣用湖來命名,阿爾山湖泊眾多,邊上有鹿就叫鹿鳴湖,邊上有杜鵑就只能是杜鵑湖了。
這些靜止的水是我印象中一篇篇散文,天空、山脈和山脈上郁郁蔥蔥的樹木是文章里吸引眼球的內容。
但我想讓水流動。
4
阿爾山確實有一條流動的水。
它就是我在玫瑰峰看到局部的那條河——哈拉哈河。它核心的意味有兩點:一段河可以說服嚴酷的寒冬,不讓厚冰封住水的口;更長的路程屬于歷史的回顧,家里家外都是馬背上的英雄,如果你聽到水聲,那不是一條河的嘆息。當愛無奈時,我同意它最后把愛留給親人。
河畔,草原廣大,山脈逶迤。
戰爭不是全部的歷史,金戈鐵馬、圓月彎刀,英雄魂歸何處?
我熱愛哈拉哈河,愛邊上蒙古包里真誠的兄弟姐妹,愛長調類的牧歌。
一切暴力應該溯流而上,到火山噴發的地方接受培訓。
哈拉哈河,我聽到阿爾山人稱呼你為他們的母親河。
5
深秋季節,我建議你們讀懂阿爾山。
阿爾山,溫泉之源。
在冷冷的北方,我尊重有溫度的水。
溫泉,是土地的良心。
當季節進一步深入,深入到冰與雪,陌生的人也可以在這里從容。我珍惜有良心的土地以及土地上一切事物和事物中間的人們,我在別處如果神情緊張,就選擇在這里放松。
放松,像自由的人一樣自由;自由,像溫泉的溫暖一樣相信世間的依戀。
我不知道溫泉是否為火山噴發后土地對自己態度的反思,我此刻被溫泉溫暖,相信自己走出臥牛潭的忍耐,走出虎石潭里的咆哮,只記住悅心潭的哲學。
植物和時間,它們不是給土地的創口療傷。它們今天的態度很好,人與自然,你們要善待對方,如果累了,阿爾山就是疲倦的人的遠方。
我在黑暗中繼續寫詩
黑夜說:要寬容。
所有的燈光隨后熄滅。
我的孤獨需要訓練,詩歌比黑暗更加孤獨。
蝗蟲吃光了苞谷,它們感嘆土地的貧窮。黑暗沒收了它們的眼睛,我不能為它們寫詩。
光明里的人云亦云,我要提防把詩里的抒情用錯。哪里的泥土讓樹木開花,夜鶯就應該歌唱。宵小的人在黑暗的遠方,他們濫用著光明。他們讓你走近,然后無視你,世界如果不傾斜,那是因為你從來不懼怕卑鄙。
我繼續寫詩的時候,已經不虛榮。
當學問里沒有了人的骨頭,我不寫諂媚;當計謀遠離了人性,我不寫嘆息。
我寫黑暗中的原諒,寫早就決定好了的堅強。
倘若還要寫下去,就給漫無邊際的自由寫下幾條紀律:如果遇到黑暗,即便是天使的翅膀也要首先寫下忍耐的詩行。
子 夜
空氣里沒有我的態度。
呼吸里有。我關心呼吸如同關心人們的整體命運,急促或者舒緩,一定是截然不同的存在方式。
子夜,大部分燈光已經投宿在客棧,而旅人的寂寞里存在著親人的期待。
我在子夜踱步,空氣豐富,一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似乎與太陽的方向一致。許多人脾氣暴躁,他們沒有從空氣里聽出親人的呼吸。
不共命運,不同呼吸。
什么樣的人吐氣如蘭?什么樣的人口氣污穢?
一切的不喜歡,深刻著頓悟。
感謝實踐,它提攜真理。偽裝的面孔也認真讀書,它們閱讀的模樣極似蠹蟲,把文章啃掉,試圖愚昧別人。
我的文章寫給空氣。
空氣在山河里,誰也不能忽視誰。子夜是最好的時刻,一切安靜,而我任意豪邁。
豪邁給予看不見的微小,揚眉吐氣的抱負與自以為是者較量,最后的呼吸屬于慈祥的星星。它們是子夜的歌,歌詞關于人間的自覺。
忘記孤獨,更好地呼吸子夜的全部。
陰險的人,你在干嘛?
這是我的子夜。我的子夜,不考慮它和你的關系。
月光下的經驗
天空的一枚好月亮足夠征服我。
苗條的月和豐滿的月敘述高處不同的營養,夜深時的經驗讓我安靜地尊重更加安靜的月。
多少人在月色下走過,從月缺走到月圓,一個月的時間不是歲月的完整,但它似乎總結著生命全部的蒼茫。
愛恨情仇被月光安慰,月照亮我們,仿佛什么也沒有發生。已經發生的它都接受,講故事的可以繼續講,如果故事關于愛情,會說到別處。
嫦娥走遠,她的啟示誰能懂?
也有關于現實的詰問,存在過的往事,心是最好的歸宿。是非遠去,批判和贊美也同時遠去,近處的不是心事,而是如月光一樣博大的從容。
后半夜的月光簡直寵辱不驚。
換一種方式就可以忘卻憤怒,可以把被憤怒留給時間。我的一切決定都有理由,只是我不忍在如此大好的月色下嘮叨。月光的沉默里泊著信任,所有金屬的聲音與人生中的嘈雜都會成為經驗。
此刻,月光是經驗。
我不要秋天的房子。
我想站在秋夜的月光下,該去的去。該來的,我只把信任和友善留給慷慨。
我這樣地尊重玉米
初秋的雨水冷靜了昨日的夏天,一些人的拜金主義讓我想起短暫的冰。它曾經封住水的嘴,真實的聲音在深處哽咽,地面上的繁華似乎誘惑我去誤判。
是在這個時候,我看到玉米。
我承認讓我認真對待的事物不少,當我坐在后院的石頭上感謝時光的安靜,我發現玉米棒上的胡須由紅變紫。一襲青蔥的長衫從古典的含蓄開始占領我的一畝三分地,它要代表玉米發言。
其實,我是如此尊重大地上每一個平凡的細節,玉米穗剛探出頭時的靦腆,掛著夏天的風走過季節的陰晴。炎熱的空中一陣陣蟬鳴比玉米更高,我真的厭惡這些復雜的喧鬧,它掩蓋蒼白的勢利,如同講臺上教授的虛偽。
我尊重一個玉米棒緣于簡單的發現。所有的玉米粒整齊排列,如同紀律嚴明的軍人,它們服從大局,壓制著任意一個成員的虛榮。說起榮譽,與集體分享。這就是玉米,牙關緊咬,克服青蟲的嚙食,創新的豐收屬于兄弟,若是遭遇黑斑病或者形勢的萎縮,它有核心的棒子,責任留下,錯誤在我。
我對玉米的感動就這么簡單。
第一定律獻給陽光,第二定律給予土地。它是第三,謙恭地站在兄弟的身后,不是因為躲避人間的暗箭,而是遜讓成功的輝煌。
玉米比我的兄長好。
好玉米啊,我熱愛每一寸土地就像熱愛整個山河。
沒有月亮的夜晚
不贊美、不惆悵。
夜晚,如果沒有了月亮,將黑得徹底。
不去想水一樣的光,不想千里之遠。共嬋娟屬于神話,現實主義地在一起,看看天空,微弱的星星足以安慰。
沒有了月亮的夜晚,心理陰暗的人無法行走。
所以要心靈發光。
所以要靈魂豁亮。
無邊無際的地理的黑,我要感謝。
秋天的樹木:掛著果實的、沒有果實的,葉子綠的或者已經枯黃的,都只是一團又一團影子。它們證明夜晚的龐大與公平。
我反對那些把仇恨和黑暗等同起來的人。
你恨得咬牙切齒別人也看不見,這樣的結果比白天笑里藏刀要好。
何時的月初照何年的人?
失去月亮的天空,慨嘆是多余的。
重新思考一下黎明:
早起的人和無眠的人,黎明是你們的。
我決定和沙河一道冷
河面飄滿了落葉的時候,水還沒有安靜。
夏天錯估了形勢,因為秋天已經深入。野鴨們任性的愛正被成熟的蘆葦觀察,風變涼。
我站在岸上,立場堅定。
我知道自己無法把沙河的環境裝修成溫暖的夏天,炎熱的蟬鳴遠去,鷺鷥整裝待發。
哪里有溫度,它們就飛向哪里。
我決定和沙河一道冷,因為沙河在冬天會結冰,因為我也準備好了理性的忍耐。
慚愧啊,我不能將太陽固定在沙河的上方,沙河是北方的一條河,我是常年居住在河畔的人。
我同意河水的自由是永恒的真理,為此,我憐憫不自由的一切。借助夏天的暴雨,我理解一條河的水位上升,兩岸是怎樣的規矩?洪水的自由表達應該服從法律,法律在秋天起草,在冬天結冰生效。
我決定和沙河一道冷。
我的溫度是堅強的沉默。
水鳥飛走后,我在。河面依舊會結冰,我的血液依舊是熱的,一個多情的人,是河畔不敗的暖。
觀徐家康《雙青圖》
一棵青松能夠承載多少人世的風雨?如果風雨不夠廣泛,就再長出一棵。
兩棵樹在一起,可以是父子,可以是伴侶。
互相注視,互相攙扶,有時又互為安慰與希望。
因為真情的存在,風雨過后,我們依然相信人間是真的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