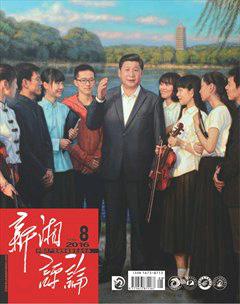404 Not Found
404 Not Found
韜奮的婚事家事與國(guó)事
陸其國(guó)
2009年鄒韜奮被評(píng)為100位為新中國(guó)成立作出突出貢獻(xiàn)的英雄模范之一。今天,我國(guó)的新聞編輯皆以贏得和進(jìn)入長(zhǎng)江韜奮獎(jiǎng)·韜奮系列為最大榮耀
1926年,由鄒韜奮主持的《生活》周刊從一份不起眼的小刊物,一躍發(fā)展成為“風(fēng)行海內(nèi)外,深入窮鄉(xiāng)僻壤的有著很大影響的刊物”,發(fā)行量最高達(dá)到15.5萬(wàn)份,“創(chuàng)造了當(dāng)時(shí)期刊發(fā)行的新紀(jì)錄”。《生活》周刊自鄒韜奮接辦的那一天起,就敢于同邪惡、黑暗勢(shì)力作斗爭(zhēng),力圖“求有裨益于社會(huì)上的一般人”。1935年11月,他在上海創(chuàng)辦的《大眾生活》周刊,對(duì)風(fēng)起云涌的抗日救亡運(yùn)動(dòng)給予了強(qiáng)有力的輿論支持和援助,銷售量達(dá)到20萬(wàn)份,超過(guò)原來(lái)的《生活》周刊,創(chuàng)造出當(dāng)時(shí)我國(guó)雜志發(fā)行的最高紀(jì)錄。1936年鄒韜奮和救國(guó)會(huì)的其他領(lǐng)導(dǎo)人沈鈞儒、李公樸、沙千里、史良、章乃器、王造時(shí),因主張團(tuán)結(jié)抗日被社會(huì)各界譽(yù)為“七君子”,他們呼吁蔣介石及國(guó)民黨政府,“應(yīng)該趕快起來(lái)促成救亡聯(lián)合陣線的建立,應(yīng)該趕快消滅過(guò)去的成見(jiàn),聯(lián)合各黨各派,為抗日救國(guó)而共同奮斗”,因此而被南京國(guó)民政府關(guān)押入獄。在243天的獄中生活里,鄒韜奮始終以一個(gè)堅(jiān)強(qiáng)的愛(ài)國(guó)民主戰(zhàn)士的姿態(tài),表現(xiàn)出無(wú)畏的革命風(fēng)范及英勇的斗爭(zhēng)精神。
婚 事
鄒韜奮原名恩潤(rùn),韜奮是他的筆名。他祖籍江西,于1895年11月生于福建。
沈粹縝生于1901年,蘇州人,她是家中長(zhǎng)女。10歲那年隨大姑母到北京,讀完小學(xué)后進(jìn)刺繡學(xué)校學(xué)習(xí)。她20歲時(shí),被蘇州女子職業(yè)學(xué)校校長(zhǎng)楊衛(wèi)玉選中,被聘為校美術(shù)科主任。此時(shí)的沈粹縝風(fēng)華正茂,青春美麗。一時(shí)間上沈家為粹縝說(shuō)媒的人絡(luò)繹不絕,對(duì)方多為家道殷實(shí)的商人。可沈粹縝偏偏看不上商人。直到1925年的一天,校長(zhǎng)楊衛(wèi)玉給她介紹對(duì)象。楊校長(zhǎng)說(shuō),對(duì)方“是一個(gè)文人”,身上決無(wú)銅臭,“和他組織小家庭,可以完全擺脫封建禮節(jié)的束縛”。這樣的對(duì)象應(yīng)該是沈粹縝愿意接受的。但楊校長(zhǎng)告訴她,對(duì)方有過(guò)短暫婚史,現(xiàn)喪偶。他請(qǐng)沈粹縝鄭重考慮后再?zèng)Q定。楊校長(zhǎng)介紹的正是韜奮。
此后不久,楊校長(zhǎng)乘火車去上海公干,沈粹縝同行。車抵上海,出站時(shí),楊校長(zhǎng)一邊張望,一邊對(duì)沈粹縝說(shuō),韜奮今天要去昆山辦事,他現(xiàn)在車站,你們可以先認(rèn)識(shí)一下。話音剛落,沈粹縝就見(jiàn)一個(gè)戴著眼鏡、目光深邃、一臉文氣的男子匆匆向他們走來(lái)。事前毫無(wú)所知的沈粹縝,對(duì)這次“相親”也沒(méi)怎么介意,只是覺(jué)得“十分可笑”。她揣測(cè)楊校長(zhǎng)和韜奮一定早有“預(yù)謀”。她對(duì)韜奮印象不錯(cuò),而韜奮對(duì)她卻是“一見(jiàn)鐘情”。沈粹縝后來(lái)回憶道,“此后不久,楊衛(wèi)玉先生陪同韜奮到我工作的蘇州女子職業(yè)學(xué)校和我第一次正式見(jiàn)面”。“這時(shí)正是蝶飛鶯囀、落英繽紛的江南暮春時(shí)節(jié)。”
韜奮的感情則更熱烈。自這次見(jiàn)面后,他常給粹縝寫(xiě)信,幾乎一周兩封。沈粹縝說(shuō)“他在愛(ài)情方面,不僅熱情洋溢,而且也能體貼人,還很風(fēng)趣”。比如韜奮有時(shí)會(huì)用蘇州話給粹縝寫(xiě)信,后者讀起來(lái)難免要連蒙帶猜來(lái)領(lǐng)會(huì)信中意思,閱讀時(shí)常常忍不住啞然失笑,平添不少情趣。相信在這樣的互動(dòng)交流中,韜奮也會(huì)告訴粹縝他曾經(jīng)的經(jīng)歷,包括第一次婚姻。
韜奮父親和一位姓葉的同事曾同在福建省政界共事,“他們因自己的友誼深厚,便把兒女結(jié)成了‘秦晉之好”。但韜奮一不滿意葉小姐沒(méi)進(jìn)過(guò)學(xué)校,二不滿意包辦婚姻,他與葉小姐都沒(méi)見(jiàn)過(guò)面、說(shuō)過(guò)話。
可是韜奮反對(duì)沒(méi)用,雙方家長(zhǎng)不同意,葉小姐本人也秉持“詩(shī)禮之家”的訓(xùn)誨,表示非韜奮不嫁。由于彼此堅(jiān)持,事情一直擱著。直到韜奮離開(kāi)學(xué)校進(jìn)入職場(chǎng),對(duì)于那位癡情女子于心不忍,終于同意結(jié)婚。后來(lái)舉辦婚禮,雙方家庭都接受了韜奮的“新派”——不舉宴、不收禮、婚禮用茶點(diǎn)。韜奮事后很感念老岳父對(duì)他的包容。當(dāng)然,尤其讓韜奮內(nèi)疚和感動(dòng)的,是婚后“天性本來(lái)非常篤厚”的妻子對(duì)他的一腔真愛(ài)。令人扼腕的是,這對(duì)年輕人步入婚姻殿堂還不到兩年,妻子卻因一場(chǎng)突然襲來(lái)的傷寒癥,不幸香銷玉殞,英年早逝。
妻子病逝后,韜奮才真切地感受到她在他心中的分量。他回憶:“她死后的那幾個(gè)月,我簡(jiǎn)直是發(fā)了狂,獨(dú)自一人跑到她的停柩處,在靈前對(duì)她哭訴!……這種發(fā)瘋的情形,實(shí)在是被她待我過(guò)厚所感動(dòng)而出于無(wú)法自禁的。我在那個(gè)時(shí)候的生活,簡(jiǎn)直完全沉浸于情感的激動(dòng)中,幾乎完全失去了理性的控制。”
韜奮這種真誠(chéng)對(duì)待感情的態(tài)度,深深打動(dòng)了沈粹縝。1925年7月,他倆請(qǐng)了幾位雙方家人,先到蘇州留園照相,然后按當(dāng)?shù)亓?xí)俗,交換訂婚戒指,舉行了訂婚儀式。訂婚后,韜奮去蘇州更勤了,每周必去看望粹縝。有時(shí)早車來(lái),晚車走。大多是周六晚到蘇州,夜借宿旅館;星期天和粹縝游蘇州園林,晚上趕回上海。沈粹縝后來(lái)回憶道,“這大約半年左右的戀愛(ài)生活,在韜奮一生中,是絕無(wú)僅有的……”半年后的1926年元旦,他倆假座上海永安公司樓上“大東酒家”,舉行了婚禮。
家 事
婚后,為妻子考慮,韜奮原想在蘇州安家,而且已租下房,甚至都布置好了。但此時(shí)粹縝覺(jué)得,韜奮每周一次奔走在上海與蘇州之間太費(fèi)時(shí),她知道丈夫惜時(shí)如金。所以在她的堅(jiān)持下,最后決定退掉租房,到上海安家。為此粹縝還毅然辭去在蘇州女子職校待遇不錯(cuò)的每月六十元薪水的職務(wù)。她說(shuō):“命運(yùn)既然把我和韜奮結(jié)合在一起,從此以后,我和韜奮也就共著同一個(gè)命運(yùn)了。”
婚后不久,韜奮開(kāi)始接辦中華職業(yè)教育社辦的機(jī)關(guān)刊物《生活》周刊,并任主編,正式從事新聞工作。其時(shí)韜奮堪稱“光桿司令”:既是“老板”,又是“伙計(jì)”,還兼任其他多種重活,如采寫(xiě)文章、寫(xiě)各種專欄、跑印刷廠、校對(duì)……“他對(duì)這個(gè)刊物真可說(shuō)像一個(gè)母親對(duì)嬰兒那樣傾注了全部感情、心血和精力。”(沈粹縝語(yǔ))
韜奮不喝酒不抽煙,唯一的嗜好是讀書(shū)。而且生活有規(guī)律,愛(ài)整潔,每月薪水全數(shù)交給妻子,依賴妻子理家。而在妻子眼里,放下工作,韜奮在家里是一個(gè)說(shuō)話風(fēng)趣、喜歡逗樂(lè)、和藹可親的人。尤其是他倆有了孩子后,每天晚飯后總要和孩子玩一會(huì)才進(jìn)工作室。孩子長(zhǎng)大一些,一日三餐韜奮便要其自己動(dòng)手。但在有些方面,如何教育孩子,他與粹縝也有矛盾。如粹縝不讓孩子吃零食,不贊成給零花錢。韜奮則認(rèn)為應(yīng)該給孩子零用錢,這可以讓他們隨時(shí)買一些學(xué)習(xí)中需要的東西,可以從小培養(yǎng)他們獨(dú)立生活的習(xí)慣和能力。在教育問(wèn)題上,韜奮也是責(zé)無(wú)旁貸,二兒子嘉騮有一次因古文沒(méi)背出被老師責(zé)打哭鼻子時(shí),韜奮認(rèn)為老師做得不對(duì),他沒(méi)有責(zé)怪孩子,連晚飯也顧不上吃,就去學(xué)校向老師提意見(jiàn)。
韜奮在這類事上特較真,而在另外一些事上,則特別“天真”。比如他不會(huì)數(shù)錢(銅板),乘電車辨不清站點(diǎn),他要求孩子生活自理,自己卻很不會(huì)料理……沈粹縝為此也檢討自己“在婚后長(zhǎng)期的共同生活中間”“把悉心為他(韜奮)料理一切看作是自己應(yīng)盡的責(zé)任,這樣也就愈發(fā)增長(zhǎng)了他的依賴程度”。當(dāng)粹縝一旦意識(shí)到“人是需要在實(shí)際生活中鍛煉的”,她就開(kāi)始有意識(shí)對(duì)韜奮“放手”。果然,這樣一來(lái),尤其是1941年12月8日日本侵占香港,韜奮先于家人被迫流亡到東江縱隊(duì)后,他不但學(xué)會(huì)料理自己的生活,還幫助粹縝到山溪中為孩子們洗衣服和做其他各種雜事,以至讓妻子覺(jué)得“他好像突然變得能干多了。”
在妻子的精心打理下,那時(shí)出入韜奮家的朋友,都贊譽(yù)他們家充滿溫暖和幸福。沈鈞儒曾回憶道,那時(shí)沈粹縝“隨時(shí)隨事,協(xié)助(韜奮)先生,平時(shí)家庭融和快樂(lè),故(韜奮)先生得一心專注于著作”。沈粹縝也覺(jué)得,他們“那時(shí)的家庭,對(duì)韜奮來(lái)說(shuō),就好像一個(gè)美麗而平靜的港灣,他安靜地泊在那里,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路子,專注地孜孜不倦地從事著自己心愛(ài)的感到興趣的工作——編輯他的《生活》周刊,一直要到他自己摸索著前進(jìn)的道路走不通的時(shí)候,尤其是九一八事變的炮聲,才把他從原來(lái)狹隘的圈子中震驚過(guò)來(lái);敵人的刺刀和鐵蹄把他愛(ài)國(guó)主義的熱情大大激發(fā)了起來(lái)。”似乎到了這時(shí)候,韜奮才猛然驚醒,從此毅然走出小家庭“和煦平靜的港灣,迎著風(fēng)暴,一往直前,再也沒(méi)有回頭。”
國(guó) 事
韜奮接手《生活》周刊前,該刊每期發(fā)行量只有2800份,且多為贈(zèng)送。后來(lái)在韜奮手上發(fā)行量猛增至逾15萬(wàn)份!以至它所從屬的中華職教社“深知道這個(gè)周刊在社會(huì)上確有它的效用,允許它獨(dú)立”,于是《生活》周刊脫離職教社,另組合作社,產(chǎn)生了生活書(shū)店。它的業(yè)務(wù)發(fā)展到全國(guó)分支店達(dá)42所,先后出版書(shū)籍1050余種。這樣的業(yè)績(jī),韜奮是如何做到的呢?且聽(tīng)他自述:“我接辦(《生活》周刊)之后,變換內(nèi)容,注重短小精悍的評(píng)論和有趣味、有價(jià)值的材料,對(duì)于編制方式的新穎和相片插圖也很注意。”“每期的小言論雖僅僅數(shù)百字,卻是我每周最費(fèi)心血的一篇,每次,必盡我心力就一般讀者所認(rèn)為最該說(shuō)幾句話的事情發(fā)表我的意見(jiàn),其次,是信箱里解答的文字。”又說(shuō)“也許是由于我的個(gè)性和傾向和一般讀者的要求,‘生活周刊漸漸轉(zhuǎn)變?yōu)橹鞒终x的輿論機(jī)關(guān),對(duì)于黑暗勢(shì)力不免要迎頭痛擊。”
當(dāng)然,更主要的是,韜奮辦刊,把握住了如何契入社會(huì)脈搏。如九一八事變,國(guó)難臨頭,全國(guó)震動(dòng);東北義勇軍喋血抗戰(zhàn),消息傳到上海,生活周刊社代收讀者捐助前方款項(xiàng),數(shù)量達(dá)12萬(wàn)元,創(chuàng)下抗戰(zhàn)中以刊物代收民眾捐款先例,這些就是“時(shí)代的要求”和對(duì)“社會(huì)的問(wèn)題和政治的問(wèn)題”的回應(yīng)。簡(jiǎn)言之,《生活》周刊在韜奮手中,它的內(nèi)容就是和時(shí)代所需緊密結(jié)合,并與民眾訴求息息相關(guān)。而在具體工作中,處理稿件時(shí),他直白“我只知道周刊的內(nèi)容應(yīng)該怎樣有精彩,不知道什么叫做情面,不知道什么叫做恩怨,不知其他的一切。”
1943年春開(kāi)始,前一年韜奮被發(fā)現(xiàn)的右耳慢性中耳炎癥日益嚴(yán)重,在上海經(jīng)醫(yī)生詳細(xì)診斷,確定為癌癥。當(dāng)年5月進(jìn)行手術(shù)。關(guān)于術(shù)后情況,醫(yī)生并不樂(lè)觀。此后雖做鐳錠治療,但病痛一直折磨著韜奮,劇烈時(shí)他面部肌肉都會(huì)牽動(dòng),并且掉淚。胡愈之回憶道,有一次他們幾位朋友去醫(yī)院看望韜奮,彼此正交談著,忽然就見(jiàn)韜奮臉上出現(xiàn)痛苦表情,并吃力地安慰朋友們說(shuō),我又要痛了,你們不要害怕。接著嘴里發(fā)出“哎哎”的呻吟,隨即就見(jiàn)他眼淚奪眶而出。韜奮不想讓朋友們?yōu)樗麚?dān)心,邊忍著劇痛,邊安慰大家說(shuō),“我的眼淚并不是懦弱的表示,也不是悲觀,我對(duì)于任何事情從來(lái)不悲觀。只是痛到最最痛苦的時(shí)候,用眼淚來(lái)和病痛斗爭(zhēng)!”韜奮說(shuō)他“從來(lái)不悲觀”決非虛言,即使在有時(shí)不得不用麻醉劑止痛的情況下,他仍對(duì)前來(lái)看望他的同事說(shuō),希望病愈后再和大家繼續(xù)努力二三十年,他還想完成三件事:第一,恢復(fù)生活書(shū)店;第二,為失學(xué)青年辦一個(gè)圖書(shū)館;第三,辦一份日?qǐng)?bào)。
為避免敵偽加害,韜奮曾換過(guò)五家醫(yī)院,并一度住進(jìn)朋友家。此時(shí)沈粹縝一雙善刺繡的手,又學(xué)會(huì)了為丈夫打針,以隨時(shí)護(hù)理丈夫。這一切似乎都給了韜奮力量,他在病中以頑強(qiáng)的毅力,將自己的經(jīng)歷,結(jié)合國(guó)事,寫(xiě)作《患難余生記》。但最后因病體難支,完成三章后,再無(wú)力終篇。
1944年九月,韜奮在病榻上口述,由他人筆錄,完成 《對(duì)國(guó)事的呼吁——韜奮最后遺囑》一文。念茲在茲的,還是他仍在戰(zhàn)亂中的祖國(guó)和同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