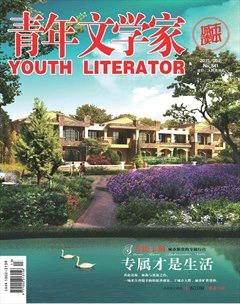常換 常新

先生Yann Francioli(楊帆),25年前,帶著對神秘東方文化的向往,來到中國學習,如今是法國高端瓷器銀器品牌Ercuis & Raynaud品牌中國總裁,與從事藝術工作的太太文嘉、女兒Oceane及兒子Thomas生活、工作在北京。文嘉,出生于上海,做過西門子藝術項目部負責人、香格納畫廊北京負責人,現在是藝術家曾梵志的藝術品顧問,元?空間執行總監。
這是距離都市30分鐘車程的隱居之地,Yann和文嘉夫婦以及他們的一對兒女就生活在這里。已在中國生活22年的法國人Yann,曾在餐廳、使館和電臺工作,2002年他從上海換到了北京工作,太太文嘉隨著他搬來了北京。從事藝術工作的文嘉說:“我喜歡上海的飲食和街道,但北京的藝術人文氣息更濃厚,更有活力,我最有意思的朋友都在北京。”
“我們不是一對特別善于規劃的夫妻。”當年去法國旅行,除了知道要去看望爸爸媽媽,其他一切都是未知。“我們更喜歡這種突如其來的樂趣,這比一切都按照規矩安排好更具驚喜。”這些年,他們在上海搬家3次、北京兩次,像遷移的候鳥。“這是一種常態,當房租漲價的時候,我們就搬家,”Yann開玩笑說,“直到我們買下了這個房子。”3層小樓,空間并不很大,細節卻處處體現著品位。雖然家是固定下來了,但家具和擺設也是常換常新。
夫婦兩人都喜愛上世紀50年代丹麥風格,所以家具基本是同樣風格。再進行一點一滴的填充,收藏各種小東西,收集自己熱愛的藝術品……“我們所有的大件家具都是零零散散帶進來的,有意思吧?”文嘉奶奶的沙發、老北京的柜子、被別人拋棄的桌子、15年前在上海買的容易入睡的沙發……居然配合得相當和諧。
丹麥復古家具,有一種中國明式家具的線條簡潔、無時間感的配合度,它可以和所有的家居風格相匹配,優雅簡潔,耐人尋味。“最好玩的就是把這些家具重新配合在一起。”比如文嘉曾經定制過一盞帶佛像的燈,“我選擇了顏色、材質、樣式……自己設計的嗎?好吧,也可以這樣說。”并沒有佛教信仰的文嘉之所以選擇在客廳內安放一些佛像,只因它們讓人感受到靜謐和舒適。在佛像燈后面的墻上,掛著一幅年輕藝術家唐茂宏動畫作品的靜態版,工業設計化的桌子又位列其下,它們各司其職,各得其所,互不沖突。
一個很大的木制寫字臺,是曾經混跡于798的法國朋友留下的,至今還保持了它工作臺式的原貌。“他最喜歡的桌子都留在了我們家。”文嘉說。它曾經被文嘉和家人用作餐桌,后來被Yann當成了Show Room的瓷器展示桌,現在再度回到家中。兩人的趣味如此一致?“確實,好像我們沒什么分歧。”在客廳左手邊的餐廳,造型各異的摩天大樓的蠟燭是來自設計師李鼐含的圣誕禮物,新上海最著名的地標建筑,“她的想法是這些蠟燭要燃燒掉,像城市的毀滅進程。這是比較悲觀主義的,而在我的家,它們被樂觀地擺放在了餐桌的旁邊作為裝飾。”
豐富的藝術收藏也是文嘉家中一個很大的特色。在上海,上世紀90年代,中國當代藝術剛剛變得興盛,文嘉和Yann就認識了許多藝術家,包括香格納的老板勞倫斯先生。“我們和勞倫斯都是老朋友了,結婚時他還來參加了我們的婚禮。”但當時也沒有想做收藏規劃,哪怕和藝術家們的關系非常親近要好,比如周鐵海、丁乙。他們最早收藏的一幅徐震的作品被放在了洗手間內,家常而輕松。自從將家搬到了北京,文嘉開始和Yann每年有規劃地采買藝術品,最多的就是畫作。“最開始買的,是曾經在798的一個小而有趣畫廊的法國藝術家的作品,然后是唐茂宏,接著每年都會有一部分預算投入買畫。”例如陳維、陳曉云、顏磊的作品。
“我們會按照自己的預算和審美收藏作品,不會買非常昂貴的。我個人喜歡年輕的、有時代感的藝術家作品,不僅僅是照片或者畫作。我們有一套趙要的酒瓶,很早的時候,他還在香格納幫我們設計請柬。他還有一組照片,黑色的,米粒一直在動,但是和這里的環境不是特別合適,我就放了起來——總有一天會用上。”文嘉娓娓道來。按照Yann的說法,他們總是會買一些“沒有用的”東西。
顏磊的作品本來放在別的地方,因為買了照片又進行調整,因為購買了柜子又再度調整,反復的調整讓家人體驗到的全是趣味,“家過了一段時間會有一種舊了的質感,重新漆一下墻或者調整家具,就會讓藝術品和家具的布局再次融合。這好像在畫廊中做展覽的感覺。”
利用率超高的廚房,是Yann做西餐、文嘉做中餐、孩子做甜品的樂園。因為空間有限,成為這個家唯一的遺憾。“太小了,本來想把車庫改成廚房的另一部分,但工程實在浩大。”家人經常聚在廚房旁的小餐桌上,吃一頓簡單午餐,或者閱讀一兩本書,度過一個溫馨的午后。
女兒Oceane的房間像個藝術空間,隨性,色彩豐富,在凌亂中有自己的一套秩序。時髦的她其實很愛喝茶,家庭觀念也很強。她在倫敦學藝術,“她的選擇或多或少都和父母有關,女兒要做藝術家了,壓力很大。”Yann逗趣道。文嘉則補充著他們的憧憬,等14歲想學建筑的兒子Thomas上了大學,兩人準備去環游世界,“那時候也一定會收集到更多好玩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