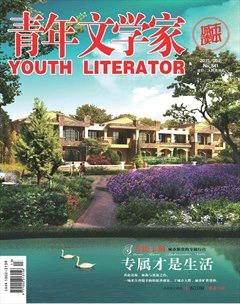越痛苦越要愛
倪曼德
說到愛情的痛苦,可能不得不談到的一部小說是英國女作家艾米莉·勃朗特的《呼嘯山莊》。和現在許多歌頌浪漫愛情的敘事作品不同,這里面沒有一對男女的愛情是幸福的,愛情與相引發的嫉妒乃至仇恨成了小說敘事的主要推動力。不過在那個講究財產與地位的年代,這樣寫倒是符合一貫的文學傳統的——愛情是一種具有顛覆性的、危險的力量。主人公希思克利夫和凱瑟琳青梅竹馬親密無間,但卻因為家庭和財產的原因不得不分開,凱瑟琳嫁給了來自另外一個莊園的青年埃德加,他在社會地位上更合適。這讓人想起《少年維特之煩惱》里面的情節設置,激情澎湃的男主人公能夠得到女主人公的芳心,卻不能令她和他結婚,在許多類似的小說里,總有這么一個理性、文靜的,來自另一個莊園的白凈情敵。當希思克利夫偶然聽到凱瑟琳說,和他結婚似乎有辱家門,勃然大怒憤而出走。后悔的凱瑟琳遍尋不著自己的舊情人,悲痛欲絕。此后她郁郁寡歡,婚姻一點都沒有給她帶來幸福,反而在婚姻的結果——分娩中死去。
《呼嘯山莊》在中文世界里有許多模仿作品,其中甚至包括不少肥皂劇,某個人物偶然聽到一句話然后憤而出走過了幾年回來報復這種橋段在今天已經毫不新鮮。希思克利夫和凱瑟琳當然懷著典型的痛苦,而另一種痛苦我們也很熟悉,即《包法利夫人》中的那種無聊。福樓拜在這部小說里寫了一個心腸不壞且頗有姿色的外省女人愛瑪,她整天想著浪漫小說中的橋段,而她的丈夫根本不能滿足她這方面的需求。愛瑪后來和巴黎來的羅道耳弗子爵發生了一段三年左右的婚外情,在這段戀情終結的時候,子爵給她寫了一封矯揉造作的信,還故意在信紙上滴上一滴水冒充眼淚,但這封信卻真的給愛瑪帶來了極大的痛苦。盡管福樓拜在處理這個人物的時候體現了高超的諷刺技巧,在這一處卻流露出了同情:
“她靠著窗臺,拿起信來又念,氣得直發冷笑。不過她越用心看信,心越亂。她恍惚又看見他,聽他說話,兩只胳膊還摟住她。心在胸脯里跳得像大杠子使勁撞城門一樣,不但不勻,而且一次緊似一次。她向四周掃了一眼,恨不得陷下去。為什么不死了拉倒?”
她和羅道耳弗子爵的戀情失敗使她很不甘心,反而加重了她之前的心理癥候。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版的《包法利夫人》(李健吾譯)中,愛瑪在107頁后死去。她始終不滿于自己的小資產階級身份,渴望進入上流社會,最后瘋狂地借債消費(她不是沉迷物欲,相反她總是在追求精神層面的愛情),不得不服毒自殺。盡管距離小說寫作時間已經有100多年,我們現在看凱瑟琳和愛瑪,依然很容易理解她們的痛苦。
不過我們作為現代人,很可能不會有她們那樣的命運。在今天與婚姻、愛情有關的社會話語里,門第、財產這些都成了政治不正確的詞語。人們只需要聽從心的召喚,跟著感覺走。即使像凱瑟琳、愛瑪這種婚后不幸福的女人,也不會像小說里那樣一直沉淪下去,社會有一整套機制來幫助她們:心理醫生、仲裁專家、離婚律師……打開電視機甚至都能看到調解夫妻矛盾的節目。如同福柯所說,人們的身體都被納入國家規訓的范圍,成為生產工具的一部分,那么她們的痛苦也不再是簡單的情緒,后現代的社會仔細閱讀了這些痛苦,把它們納入了社會再生產的軌道。即使人們不想要這些機制的幫助,也可以很簡單地找到人傾訴,在互聯網的時代,埋藏秘密的樹洞簡直唾手可得。我們這個時代的凱瑟琳和愛瑪一樣會傷心失望,但她們絕對不會那么容易得憂郁癥和自殺。“療傷”這個詞經常被人提及,它幾乎專指在愛情挫折后的恢復心情(一般來說,如果人們在事業上受挫,不會選擇這個詞),有一整套專門的自我恢復技術來針對愛情的痛苦。因為愛情去自殺、皈依宗教這些都不是我們當今文化中的選項,如果說在過去這么做的人還帶著一些驕傲,那么今天這種做法近乎恥辱,這說明一個人已經完全無法控制自己了。
對于現代人來說,愛情中的痛苦意味著什么呢?可能在找到真正的公主/王子之前,我們吻過太多的青蛙,每一次都很不舒服。尋找伴侶如同西緒福斯推石上山,每次都不是同一塊石頭,但過程都一樣艱辛,即使到得山頂牽到戀人的手,接踵而來的也可能是無聊、嫉妒、自卑甚至壓抑。
進入戀愛狀態從來都不是終點,美國哲學家詹姆斯·卡斯寫過一本《有限和無限的游戲:一個哲學家眼中的競技世界》,有限游戲的目的在于在一個有限的邊界內贏得勝利,而無限游戲卻旨在讓游戲永遠進行下去。有限的游戲具有一個確定的開始和結束,擁有特定的贏家,規則的存在就是為了保證游戲會結束。
無限的游戲既沒有確定的開始和結束,也沒有贏家,它的目的在于延續游戲。我們可以把愛情中的追求過程看成一個有限游戲,而真正的戀愛階段(包括婚姻)是一個無限游戲,能夠追求到心愛的人,并不能保證能與他/她相守,因為一旦有限游戲有一方勝利,除非勝利者是一個唐璜式的登徒子,游戲一般都會自動進入無限階段,不但規則變化了,游戲的目的也變化了,追求者已經不能靠討對方歡心來博得好感,他必須要維持相處中的快樂狀態,并且把自己定位成合作姿態。雙方必須合作把這個戀愛游戲玩下去,否則就會兩敗俱傷,就像瑪麗娜·阿布拉莫維奇的行為藝術作品《潛能》。這是藝術家和她的戀人烏雷在1980年橫貫歐洲的作品。兩個人面對面站立著并專心地注視著對方,手里還同時拉著一個緊繃的弓,在烏雷的手里緊拉著一支帶毒的箭,正對著阿布拉莫維奇的心臟。由于弓箭的張力使他們的身體都向后傾斜,他們稍不留神,那支毒箭就會離弦射出,同時,他們心臟急劇加速的跳動聲也通過擴音器播放出來。
莎士比亞的《仲夏夜之夢》里,喜劇性是通過愛情的前現代性體現出來的。和人們通常認為的不同,這位《羅密歐與朱麗葉》(與《仲》寫于同一年)的作者對于純浪漫愛情持著一種揶揄態度。《仲夏夜之夢》“亂點鴛鴦譜”的故事模式被后人廣泛模仿,即一種非自然非社會性的魔藥會導致人們盲目地愛上陌生人。在后來歌德的《浮士德》里,浮士德也是喝下了魔女的藥湯才愛上了格蕾琴。魔藥的存在暗示了一種非理性狀態,用我們現在的科學話語來說,也許這種狀態是激素和大腦神經運作的結果,但在當時,這意味著人們不需要在精神層面上為自己的選擇負責,一切都會歸結到以財產和權勢為標準的婚姻上來,在《仲》的結尾秩序恢復,各位情侶都各司其位,仙后當然不會和織工真正相愛,這不符合時代精神。但在現代這件事就是可能的,各種敘事作品都在講述跨越門第超越物質的愛情,人們全都在聽從潛意識的呼喚,舊秩序的打破當然提供了很多愛情上的可能,但也同時意味著如果愛情失敗,那么不是社會、家庭的問題,而是自己出了差錯。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的年代,人們常說的話是“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如果一個人在經濟上很窘迫,那么多半是他自己的“問題”,或者懶惰,或者道德敗壞。同樣道理,弗洛伊德主義成了與之相應的心理學說,雖然在嚴格的心理治療領域,弗洛伊德主義早已經淡出舞臺,但它的心理學簡化版卻成了最流行的意識形態。既然人們已經不得不對自己的愛情失敗負起責任,那么曾經言聽計從的潛意識現在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了罪魁禍首。人們從報紙雜志、心理節目和電視劇中得到的教訓是:那當然是因為我自己有問題。問題不在于顯而易見的貧富、美丑,而在于性格和欲望,這些謎一樣的問題都可以追溯到童年那段早已經記不清的時期。無法確定癥結是否真的存在,但這種泛弗洛伊德主義的心理趨勢卻使許多人不得不對自己的內心感到懷疑,這種懷疑本身是無法治愈的。
在現代愛情關系中,人們總是呼喚想象力,別開生面的表白或者富有巧思的禮物都會使人開心。人們越過了物質匱乏的年代,覺得送99朵玫瑰不再浪漫,反而顯得俗氣,因為這種到處都可見的禮物除了貴,本身并沒有被注入更多意義,它的意義就是表面一層那么多,是消費主義給玫瑰涂上的含義。但想象力同時也是危險的,它是欲望的工具,在付諸實現之前,它始終都是以白日夢的形式存在。一方面,想象力營造了一種事先準備好的現實,真正的情感經歷可能是對這種現實的代入;另一方面,這種先驗的現實會影響人們對當下現實的判斷。麻煩的是,人們很難保證自己的想象不被消費主義的各種觀念侵入,欲望從來就不是獨立存在的。我們這個時代鼓勵欲望,把身體的各種欲望納入了社會再生產的循環里,它成了類似能源一樣的東西。
和資本主義興起時期的清教倫理不同,現代社會里如果一個人沒有過剩的欲望,如果沒有不滿足,反而是不正常的。欲望和消費密不可分,因此想象力的風險在于,一個人要有足夠的抵抗和反思意識,才能夠成為想象力的主人而不是為之所役。《包法利夫人》中愛瑪的想象力把她送進危險的境地,批評家們說這是因為她看了太多愛情小說,腦子里充滿不切實際的幻想。在17世紀,印刷術的發展確實導致了知識的大量傳播,也解放了很多人的想象力。這些例子不勝枚舉,在奧斯丁的《諾桑覺寺》里,凱瑟琳的想象力也來自哥特小說,以至于在認識真實世界的時候出現了偏差,多荒誕的話也會相信;普希金的《歐根·奧涅金》里,塔季揚娜是個“精神世界相當狹隘”的鄉村姑娘,充滿對文化的幻想,極其渴望奧涅金這樣的知識分子來注入自己的愛情。想象力既是私人的,也是社會的,是經濟秩序的一部分。如果一個人的想象力不加辨別地受到外界的過多影響,那么就會如同鮑德里亞所說,他本該有的、自發的想象力被掏空,真實世界反而成為模仿,虛構成為比生活更加有趣的真實。愛瑪如果活在現在,在想象的模式上可能不會有什么太大的改變,倒反而在社會意義上變得合理,除了浪漫小說,還有更多電視劇和電影,同時互聯網加速了這一切。她也不需要借高利貸,因為有信用卡。人們常常把愛瑪和堂吉訶德相提并論,但不同的是,堂吉訶德并未因為想象力放棄任何責任,而愛瑪卻背棄了自己作為母親和妻子的身份。她是比堂吉訶德更加嚴重的病人。
現代人意識到想象力的危險性,想要躲避它。美劇《欲望都市》一集里,女主人公凱莉輕描淡寫地說:“如果有男人和我說,他要和我開始一段浪漫的愛情,我就要尖叫了……這么說的意思是,如果有男人對你有什么浪漫的幻想,那么不久當你們熟悉了,你就會變得真實,你也不會再是他幻想的來源,那就沒意思了。浪漫的人都很可怕,離他們遠點兒。”劇中的四位女主人公都年過三十,顯然這代表著許多在愛情上“有經驗”的人的一種類似自省的態度:對愛情不要期望太多。這是她們和愛瑪·包法利最大的區別。現代個體在關于愛情的經驗上(不管是直接還是間接經驗)遠遠超過他們在18世紀和19世紀的前輩,分手、欺騙遠不是什么致人于死地的痛苦經歷,現代人更有懷疑精神也更享樂主義,這幫助他們在應對愛情的痛苦的時候更有力量,他們的想象力也更加面向未來而不是過去的創傷記憶。然而這種力量也使人們更有可能敞開心懷去迎接新的戀愛經驗,其中也包括新的懷疑和絕望。總的來說,現代人處于彷徨的境地,更有想象力、更敏感,也更加知道如何保護自己。但防衛意識和愛情經驗的廣度和深度處于反比關系,因此如何去面對愛情,每個人都必須做出自己的抉擇。
每一對情侶也就是一個小共同體,他們之間的互動是社會關系的反應,但也是這兩個人之間的創造性活動。他們要用自己的方式將這個游戲永遠推進下去,每一個決定都將重新定義這個共同體的性質。在此過程中,想象力依舊是最好的工具。譬如浪漫,不應該在對方身上尋求,它應該是雙方互相作用、自然產生的結果。避開意識形態的陷阱,想象最獨特的自己和對方,只有這樣,愛情才不愧為當代最有魅力的文化理想,為它遭受的痛苦也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