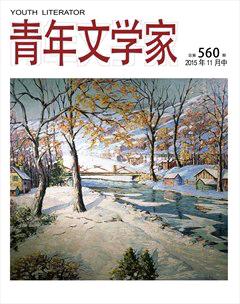美麗中國:中國夢的鄉(xiāng)土美學(xué)維度
摘 ?要:有關(guān)鄉(xiāng)村的詩意想象,或鄉(xiāng)土烏托邦的書寫一直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一種重要傳統(tǒng),通過這種傳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展現(xiàn)了以鄉(xiāng)村為依托的中國想象。但現(xiàn)代性所開啟的鄉(xiāng)土規(guī)劃僅僅將鄉(xiāng)土作為一種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實(shí)體,忽略了鄉(xiāng)土在中國人的集體經(jīng)驗(yàn)與情感中的豐富多義性。也許我們不僅要通過城市來改造鄉(xiāng)土,也需要通過鄉(xiāng)村文化來反思城市化進(jìn)程中所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
關(guān)鍵詞:美麗中國;中國夢;鄉(xiāng)土美學(xué)
作者簡介:陳雪(1980-),女,重慶人,湖南吉首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傳播學(xué)院講師、博士,研究方向:文學(xué)史、美學(xué)。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2-0-02
在十八大之后,“美麗中國”成為我們理解中國未來建設(shè)的關(guān)鍵詞,但“美麗中國”到底有什么樣的具體內(nèi)涵呢?“美麗”到底美麗在哪些層面了?我想自然美、人性美與藝術(shù)美的統(tǒng)一是“美麗中國”的題中應(yīng)有之義,三者缺一不可。我想,這種美麗中國的圖景,以及自然、人性與藝術(shù)的統(tǒng)一性可以放到鄉(xiāng)土美學(xué)的視野下進(jìn)行觀照。不僅因?yàn)橹袊哂杏凭玫霓r(nóng)耕文化傳統(tǒng),更重要的是鄉(xiāng)土美學(xué)的旨趣與美麗中國夢想具有內(nèi)在的相通性。
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華文明是一種鄉(xiāng)土文明,而中國古典美學(xué)是一種以鄉(xiāng)土意識為基礎(chǔ)的美學(xué)。這種鄉(xiāng)土意識彌漫于中國古典繪畫、詩歌、戲曲、音樂、建筑等各門類藝術(shù)之中。這些藝術(shù)中所表達(dá)的去國懷鄉(xiāng)之感、羈旅思婦之愁、山水田園之趣、窮通出處之思,無不與這種鄉(xiāng)土意識息息相關(guān)。鄉(xiāng)土文化還影響到中國古典藝術(shù)的表現(xiàn)方式,那樣一種長期與土地,與土地上生長的草木莊稼,與山水、與自然界的風(fēng)云變幻打交道的方式,使得中國古人的思維方式從來都具有某種與自然物象相互感應(yīng)的特征,無論是“立象盡意”還是“托物言志”,中國藝術(shù)從來都與那些圍繞著人的鄉(xiāng)土風(fēng)物血肉相連。這一點(diǎn)使得中國古典藝術(shù)從來沒有走向某種抽象表達(dá),也沒有過于細(xì)碎的刻畫與羅列。藝術(shù)所呈現(xiàn)的世界始終是一個我們身體所感受到的生機(jī)勃勃的大千世界。這就是中國古典世界觀中所謂的“萬物”、“天地”。很顯然,中國古典美學(xué)精神背后所依托的終極性的存在正是這種整體性的自然-生命共同體。人總是將有意義的生活落實(shí)到自然天地中,中國藝術(shù)所表達(dá)的理想也正是這種天人合一的境界。
隨著現(xiàn)代性的開啟,這種共同體意識被打破了。建立在現(xiàn)代技術(shù)基礎(chǔ)上的空間觀念使得自然不在成為與人冥契一體的存在,而成為操控和規(guī)劃的對象,“即自然以某種可在計(jì)算上確定的方式顯露出來,并且作為一個信息系統(tǒng)始終是可訂造的。”[1]與此相關(guān),自然被祛魅,鄉(xiāng)村也不在成為詩意的家園,而是整個國家的現(xiàn)代性設(shè)計(jì)的某個可以操控的某種幾何學(xué)空間,某種可以加以利用的資源。城市與鄉(xiāng)村進(jìn)一步分離和對立。在傳統(tǒng)社會,無論是農(nóng)民還是讀書人往往有著深刻的鄉(xiāng)土生活經(jīng)驗(yàn),有著與鄉(xiāng)土世界的血脈相連的關(guān)系。而在現(xiàn)代性規(guī)劃中,城市雖然不得不依賴于從鄉(xiāng)村提供的種種資源(人力、物產(chǎn))而得到發(fā)展,但是城市生活卻更多地建立在資本的流動上,資本抽空了人與土地的感性聯(lián)系,也抹平了人與人之間的具體的身體化的關(guān)聯(lián)。現(xiàn)代性的空間意識源于笛卡爾從幾何學(xué)的角度對空間的界定,在這里,沒有什么不能被納入一個可計(jì)量的幾何學(xué)的框架下被計(jì)算,在幾何學(xué)的模式中,空間不再是含混多義,而是清晰透明,均質(zhì)化的,“天上和地下的物質(zhì)都是一樣的,而且世界不是多元的。”(笛卡爾)正是在笛卡爾這里,世界才不再是人生在世的場域,而成為擺置于人面前的一個客體。
現(xiàn)代性的普世價值威脅著前現(xiàn)代那種扎根于土地的具體經(jīng)驗(yàn),使之貶值。人不再通過與空間建立起某種本源性神話聯(lián)結(jié)而獲得生活的價值與意義,現(xiàn)代性帶著其“瀝青理智主義”(asphalt intellectualism)不斷祛除源自鄉(xiāng)土、故土的神話、詩性與情感的力量。這種均質(zhì)性的空間觀念在金錢資本夷平一切差異的流動中現(xiàn)實(shí)化(西美爾),并隨著印刷資本主義對古典書寫神圣性的消解而走向那種以語言為聯(lián)結(jié)的現(xiàn)代民族國家意識(想象的共同體,)。在一種以金錢、共同語言為中介形成的共同體經(jīng)驗(yàn)中,那種人與其環(huán)境所本有的那種直接的“人身”關(guān)系被抽象化(或被某種普遍性所“中介”)了。現(xiàn)代性空間經(jīng)驗(yàn)最終取代了前現(xiàn)代那種空間感知。于是,在現(xiàn)代視野中,鄉(xiāng)土的美學(xué)維度被鄉(xiāng)土的經(jīng)濟(jì)學(xué)維度所取代,以此為基礎(chǔ),鄉(xiāng)土不再是生存的家園,而是國家經(jīng)濟(jì)發(fā)展的手段和對象。
中國鄉(xiāng)土的現(xiàn)代性改造從晚清、民國時期所推行的一系列鄉(xiāng)村行政改組,再從抗戰(zhàn)到新中國成立后所實(shí)行的一系列土地改革政策,特別是1950年實(shí)施的這次土改旨在為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發(fā)展和國家工業(yè)化開辟道路。這些政策無疑大大地解放了農(nóng)村生產(chǎn)力,使得國家得以迅速地發(fā)展工業(yè),并為經(jīng)濟(jì)發(fā)展、城市建設(shè)打下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這也使得農(nóng)村逐步喪失其在傳統(tǒng)社會中那種相對的獨(dú)立性,而成為整個國家宏觀規(guī)劃的一個環(huán)節(jié),農(nóng)業(yè)合作化政策的實(shí)施最終是為了實(shí)現(xiàn)整個國家的工業(yè)化目標(biāo)。而再到后來隨著改革開放,農(nóng)村進(jìn)一步為城市化建設(shè)提供大量剩余勞動力和生產(chǎn)資源。大量農(nóng)村人口背井離鄉(xiāng)涌入城市,他們居無定所,往返于于城鄉(xiāng)之間,為推進(jìn)中國的城市化進(jìn)程做出了巨大的貢獻(xiàn),也付出了自己的青春和汗水,但在心理和情感上卻很難融入城市生活。與此同時,大量婦女兒童及老弱病殘則留守鄉(xiāng)村,帶來了眾多的社會問題。而且,在這種城市化進(jìn)程中,田地閑置、荒蕪,鄉(xiāng)村的生存環(huán)境被破壞。
有關(guān)鄉(xiāng)村的詩意想象,或鄉(xiāng)土烏托邦的書寫一直是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中的一種重要傳統(tǒng),通過這種傳統(tǒng),中國知識分子展現(xiàn)了以鄉(xiāng)村為依托的中國想象。但在近20年來,鄉(xiāng)村文化在現(xiàn)代化進(jìn)程中所遭受的摧毀和破壞成為一個重大的主題,我們看到森林被大面積的破壞(阿來《空山》),地下的土地資源被一點(diǎn)一點(diǎn)地耗盡、淘空(張煒《九月寓言》),更重要的還有那種鄉(xiāng)土倫理被消解, 像閻連科、劉震云、賈平凹、尤鳳偉、劉慶邦等人的一些作品中,呈現(xiàn)了鄉(xiāng)村整體性的破敗淪陷、人心不古,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guān)系被資本所異化。在所有這些作品中比較有代表性的是賈平凹的《秦腔》。這部作品呈現(xiàn)了一個被耗盡、被遺棄的鄉(xiāng)村圖景:農(nóng)田被現(xiàn)代化的高速公路、農(nóng)貿(mào)市場、酒樓等侵蝕,清風(fēng)街的老農(nóng)們放棄了他們傳統(tǒng)的生活方式,從事經(jīng)商,而年輕勞動力則放棄土地進(jìn)城打工。整個鄉(xiāng)村世界一篇凋零,只剩下一個老人、一個啞巴、一個瘋子在賣力氣。傳統(tǒng)的藝術(shù)形式秦腔不得不以走向市場的方式茍延殘喘。女人們成為引誘者和偷奸者,兄弟親情被金錢所征服。這是鄉(xiāng)村圖景的全面的破敗,現(xiàn)代化所帶來的是城市的發(fā)展與鄉(xiāng)村的淪陷。可以說,鄉(xiāng)村所遭受的重創(chuàng)不僅是現(xiàn)實(shí)生存層面的,更是一種文化層面的整個延續(xù)了幾千年的集體經(jīng)驗(yàn)、情感與想象的瓦解、分裂。它使得我們對我們心靈歸宿、對家園的想象變得失去了現(xiàn)實(shí)依托。
可以說,現(xiàn)代性所開啟的鄉(xiāng)土規(guī)劃僅僅將鄉(xiāng)土作為一種物質(zhì)、經(jīng)濟(jì)實(shí)體,忽略了鄉(xiāng)土在中國人的集體經(jīng)驗(yàn)與情感中的豐富多義性。雖然中國經(jīng)濟(jì)得到了飛速發(fā)展,但是也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空氣污染,水資源短缺,土地荒廢,荒漠化,溫室效應(yīng),以及貧富分化、拜金主義等問題。海德格爾在對現(xiàn)代性的“空間的祛魅”所導(dǎo)致的虛無主義進(jìn)行反思時,借助于古希臘神話中有關(guān)土地崇拜的神話,試圖重新賦予土地某種原生性力量。海德格爾對現(xiàn)代性的均質(zhì)性空間體系,及其帶來的普遍主義、都市主義、世界主義的后果展開了批判。在他看來,土地不是地理意義上的某種坐標(biāo),或法律、經(jīng)濟(jì)范疇,而是人生在世的基礎(chǔ)、根基、本源:“因?yàn)槿祟惥幼≡诖蟮刂希麄兙蜆?gòu)成了一些空間,這些空間的輪廓并不僅僅是領(lǐng)土性的(在拉丁詞terra的詞源學(xué)意義上),并不僅僅是作為人類在其中設(shè)置邊境的空白圖表。毋寧說,‘大地變成了古希臘人所謂的‘chthon,在那里人們居住著,并形成了一個故鄉(xiāng)(homeland)。”[2]同樣,對于中國文化而言,鄉(xiāng)土不僅是一個現(xiàn)實(shí)的地理空間,而且也是詩性的想象空間,還是人與自然相互協(xié)調(diào)的生態(tài)空間,而且它還意味著一種神話的本源。
也許我們不僅要通過城市來改造鄉(xiāng)土,也需要通過鄉(xiāng)村文化來反思城市化進(jìn)程中所出現(xiàn)的種種問題。需要在一個更大的均衡的視野中來處理鄉(xiāng)村與城市的關(guān)系。中國的發(fā)展并不僅僅體現(xiàn)在GDP指標(biāo)上,也體現(xiàn)在都市與鄉(xiāng)村、人與自然、人與人、身與心之間的和諧程度上。“鄉(xiāng)土美學(xué)通過詩性鄉(xiāng)土、審美鄉(xiāng)土、神性鄉(xiāng)土的建構(gòu),直接為下述三部分人籌劃著人的全面發(fā)展,啟迪著詩性人生、審美人生的高遠(yuǎn)追求,營構(gòu)著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3]因此,中國夢不僅僅是都市夢,不僅僅是發(fā)財致富之夢,而且美麗中國夢也是一個美麗鄉(xiāng)土夢,它追求的是一種整體、全面的發(fā)展,是一種自然、人性、藝術(shù)的統(tǒng)一所形成的大美之境。在這種“大美”的追求中,鄉(xiāng)土美學(xué)能夠給我們啟迪,在發(fā)展“生態(tài)文明、綠色經(jīng)濟(jì)”的語境中,我們不僅要意識到鄉(xiāng)土的經(jīng)濟(jì)維度,更需要在這種語境中恢復(fù)鄉(xiāng)土的詩性維度,生態(tài)維度,和神話維度,只有這樣才能實(shí)現(xiàn)中華民族偉大復(fù)興的中國夢,才能找到我們賴以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園。
注釋:
[1]海德格爾.海德格爾選集[M].上海:上海三聯(lián)書店,1996,第941頁.
[2]美查爾斯·巴姆巴赫.海德格爾的根[M].上海:上海書店,2007,第42頁.
[3]簡德彬.鄉(xiāng)土美學(xué)何為?[N] .文藝報.2005(05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