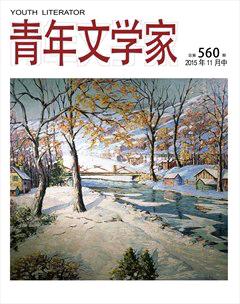自知無路之“后”
作者簡介:朱奇瑩(1986-),天津職業技術師范大學講師,研究方向為日語語言文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5)-32-0-01
2015年夏,楊慶祥的《80后,怎么辦》[1]由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出版,不僅受到北島、李陀、閻連科等的贊賞,甚至引起了諸如“80后是否是失敗一代”的討論。也許是因為之前看過發表于2013年第6期的《天涯》雜志上“勵志”版的《我們可以找到那條路》[2],或者因為關于“新窮人”、“新工人”的問題,在其他方面有過一些關注和認識(如呂途或者汪暉等都曾對此有過專門研究或論述)[3],所以再讀楊慶祥(以下略稱“楊”)的該部著作時,新鮮感和沖擊力并不那么強烈。然而對其中的誠懇描寫和嚴肅思考,以及通過面對面訪談等形式而呈現出的八零后多樣的個體經驗,同樣作為一名“80后”的我,對照自己這些年生活的城市,回想每個迎來送往的平凡日夜,在一定程度上的確切膚而具體地體會到了那些文字背后夾雜的苦悶、掙扎和焦灼,更佩嘆作者“把社會現實、作品分析和批評家的個人經驗融合在一個整體性的批評實踐當中”的姿態之可貴。
無論是楊在作品中提及的汶川大地震、奧運會,亦或是世博會、達沃斯、自貿區、天津8·12大爆炸、2015年大閱兵……這幾年,身處在GDP高速領跑世界的中國,生活在GDP高速領跑中國的城市,在八零后的個體生命里,從來都不缺乏宏大的時代敘事。但同時,無論是暫時性的參與,還是被代表被表征,正因為這種一體兩面的狀態存在,才使得我們不能輕易斷言,認為這個時代推陳出新的宏遠話語完全與自己無關。這不是自我安慰和牽強附會,畢竟每天吃穿住行,日常開支用度,生活的每張小碎片都早已交織和被擺布在所有的大敘事里。八零后不管以何種方式,無論是被塑造還是主動充當,無論是光鮮放大還是被陰暗屏蔽,都不能否認自己作為一名當事人置身于幻景流年的事實。因為有時恰恰是憑借這一消隱被動的立場,而得以從另一角度返觀歷史的現場和察悟其中的吊詭,站在被排斥的邊緣兜住大敘事的網眼下滲漏的被認為微不能道的一切。發現自己的不堪抵抗、轉瞬即逝、欲說還休。
其實,何止是八零后呢?看看霧霾中天橋下老老小小早出晚歸的身影,有誰能太過認真地只專注于生之艱難的思考,而絲毫懈怠下拼命生活的本身呢?畢竟不置可否地遭遇著大敘事和艱難于小生活的,從來就不限于八零后,與集體呈現被剝離關系的,也并非只是殷切相信個人奮斗之夢的年輕人。當社會構造本身堅持了以資本和權貴來計算成功的邏輯時,大多數人只能在少數成功者之外,再努力尋覓和建構起一種 “仿成功”式的幻影,以求安放自己倉皇虛弱的身體和不斷縹緲揮發的靈魂。
但是,對于年輕一代的歷史虛無感,我愿意相信這畢竟是一種偏向于外在的被動,因此不會根本性地成為妨礙年輕人自身去做內面努力,從而歷史性地進行自身認識、解構、重構或思考的障礙。相反,若沒有虛無體驗的真實存在和親身經歷,一切所謂的歷史感覺難道不是更容易陷入輕浮?當下歷史指向八零后的直接經驗,就是切實而徹底的去歷史化的過程。在虛無的重返中我們出生,與越來越大的虛無學會共處、互動、曖昧、妥協。這構成八零后一代的“歷史與生活的同一性”,是與五零后那種厚度與韌性兼具的“世故和權術”不同的另一種“更圓滑自足的世故”。這也許源自上一輩青年們關于“潘曉討論”未得深層繼續和真正完成的后遺癥,然而在資本力與特層話語起決定作用的空間內,只怕任何企圖再進入歷史之內的努力都會望而卻步。這也許就是楊所謂的“對于歷史存在已經失去了信任,所幸徹底放棄了這種歷史的維度,而完全生活在‘生活之中”的八零后普遍性。
無論是前幾年相親節目的火爆,還是近年真人秀節目的盛行,都如楊所觀察的那樣,小時代中雀躍的演員或者觀眾,無一不是“都處在一個凸顯的平面上,鏡子和攝像機成為最重要的媒介,只有通過它們,我們才能看到或讀到自己。或者說‘鏡子和‘攝像機已經成為主體,寫作者和閱讀者都必須通過這樣的主體把自己‘物化,并找到存在的實感”。有的人投入忘我地出演著某種不真實的“真實”,有的人迷醉沉溺并輕快地接受了那些被送到眼前的真實的“不真實”。為了達到自我完成而需要進行的與整體關系的調整變得越發困難,而與整體達成某種合謀,僅僅只對自己的立場做出稍微的妥協與改良卻相對容易實現得多。發現問題的同時,也變成了問題的寬容接受者和承受人。
“怎么辦”作為一個懸置的疑問搖擺在我的面前。要去哪里尋找到足夠支撐起八零后一代自我完成的內在力量?在一邊拒絕和抵抗被同質化的同時,還必須時刻警惕不會在另一個側面沿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鏈條,去建構起一個自以為特立獨行的虛幻自我,這種實踐的可能性或者說與他者連帶的可能性,應由誰、如何來提供保證和對接?又該如何“自覺”而“結實”地探索和堅持?當“小資產階級之夢蘇醒”之時,當自覺的主體逐漸學會將個體的失敗,慢慢置于歷史的現場中重新加以復雜化考量之時,“怎么辦”會更加成為一個無所逃避的問題急迫地呈現眼前吧。
無路之處會有路嗎?至少,自知無路與不知無路的區別,或者才是更要緊的問題。
注釋:
[1]楊慶祥,80后,文學博士,中國人民大學副教授。其著作《80后,怎么辦?》出版于2015年6月。
[2]楊慶祥在作品“附記二”中敘述文章的發表經由時,表示該文章最初“給了《天涯》雜志,但是《天涯》顧慮比較多。……后來還是發了,但題目改了,叫做《我們可以找到那條路》,很勵志,里面一些比較敏感的詞語也作了相關處理”(參見《80后,怎么辦》第116頁)。
[3]參見呂途著《中國新工人 迷失與崛起》(2013年1月,法律出版社)、《中國新工人 文化與命運》等(2015年1月,法律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