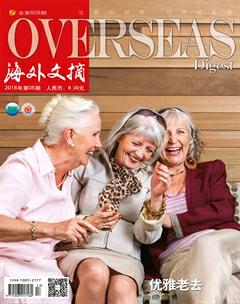臉書“吸塵器”
佩內洛普·格林馬士
凱特·斯科洛芙是奧勒岡州波特蘭市的品牌策略師。對于她來說,和已經相處了3年的前男友分手,是一時沖動的決定。她說:“那時候我們才分手15分鐘左右吧,可能他的車還停在我的樓底下,他臉書的狀態就改為‘單身了。”
這意味著他們共同的臉書好友,還有她那些還處在青春期的孩子們,立刻就知道了這件事。“我無處可藏,甚至都沒來得及哭一會兒。”斯科洛芙女士說,現在她已經55歲了。
她通知了她的朋友們,把各自相冊里面所有有關她和她前男友的照片全部刪掉。她說:“真希望臉書有一個網絡吸塵器,能把我和我前男友在網上留下的痕跡全部清理掉,尤其是合照。就在昨天,還有老照片突然跳出來。”
去年11月份開始,臉書社交網絡上就出現了類似的功能,這類功能可以管理、追蹤那些記錄戀愛關系的數據。“這就像是吸塵器。”凱利·溫特斯說,她是臉書公司愛心團隊的產品經理。這個富有創新力量的團隊中有產品經理、產品設計師、工程師、社會學家和心理學家。她說:“你想要丟掉所有與快樂無關的事情。”她的這番話剛好印證了日本家政女皇近藤麻理惠的觀念。
已經有300萬用戶開始使用這項功能,這個功能叫作“分手流程”。一方面,他們盡量回避所有與前任相關的信息,另一方面,也把自己分手的那些狀態、感受隱藏起來。因為考慮到用戶在將來可能會和前任復合,“分手流程”允許用戶進行反向設置。
想要還原網絡吸塵器刪除掉的內容(這是借用了斯科洛芙女士的話,網絡吸塵器是一個很厲害的網絡編程,能使用分析師運算方法,來鎖定那些有可能勾起用戶不快樂回憶的照片),那更是個體力活兒。
擁有15億用戶的大型社交網站上魚龍混雜,社交網絡環境的運行規則一直處在變化當中,想要把握這個規則,你必須既有賈寶玉那樣的細膩敏感,也要有劉備那樣的厚臉皮。
作為一個局外人,我想說,很多多愁善感的人,分手后在網站上細細地記錄了自己分手后的內心歷程,他們低估了社交媒體“好友”們的居心叵測,倒不如簡單粗暴地發一句:我在所有平臺上都取關了我的前任。
愛心團隊的任務就是讓臉書上的人際互動越來越有人情味兒。溫特斯女士和她的團隊一直在研發能夠解決社交障礙、欺凌、網絡攻擊(或潛在的網絡攻擊)、飲食失調或者高中生不良習慣的應用軟件。她還和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的至善科學中心、耶魯大學情感智能研究中心及其他學術機構有所合作。
新的項目能夠在網民的博客中識別出自殺傾向,并且向他們提供相應的援助,預防自殺。有團隊專門研究如何處理已死亡用戶的賬號,也有團隊研發了平安軟件,來幫助受到自然災害的用戶快速地找到親友。
門羅帕克市是臉書的總部所在地,在一個初春的星期二,臉書的員工們成群結隊地騎著淡藍色自行車,在園區內通行,他們看上去就像是一群健康活潑的大學生。
大約6000名員工在這里工作,在新城市主義小鎮(之前是太陽微系統公司的總部,在2011年時被臉書買下)和濱海公路另一邊的43萬平方英尺的開放式設計總部之間往返。總部由弗蘭克·蓋里設計。
在臉書辦公區里,到處都是數字形狀的聚酯薄膜氣球靜靜地飄在員工的桌子上,那是每一個員工的入職紀念日。自動售貨機里面擺放的是鍵盤和充電器,而不是小食品,粉紅色的凸版印刷海報上寫著“我是技術宅”等樣式的鼓舞人心的標語。
會議室被布置得主題感極強,而且各有特點。一些會議室被布置成《星球大戰》主題,一個標牌上寫著“盧克,我是你表哥”。其他的會議室風格就更獵奇了,比如“奧林匹克魚”。記者們很喜歡破解這些會議室命名背后隱藏的東西。比如,房間中“升序與降序”、“繪畫的手”、“魔法帶綁著的禮盒”采用了M.C.埃舍爾作品的名字,向他致敬。
25歲的埃爾伯特女士,開朗外向,最開始她一直學習芭蕾舞,后來去了羅德島設計學院。她跟我們講述了她和大學時交往的前男友之間因為社交網絡動態而產生的糾葛。
“我看著一條又一條自己曾經發布的狀態,”她說,“我很難過,就跟我的朋友們一樣。當網上還記錄著你和前任的點滴時,你并沒有真正離開他。或許,臉書能夠幫助我們從痛苦中振作起來。”
埃爾伯特一直在想,如何讓用戶在網上減少和前任的互動,怎樣才能既不需要不留情面地拉黑,又能切斷跟前任的網絡聯系。有一天下班的時候,她突然有了一個點子,這個點子大有可為。她說:“很多人都會因為突然聽到前任的消息而感到心痛。”

左起依次為臉書愛心團隊的:凱利·溫特斯、喬治·威爾士、艾米麗·埃爾伯特、丹·穆瑞羅。
有的人在分手后有嚴密監視前任網上狀態的傾向。一些調查研究分析了這種傾向和依戀類型之間的關系。研究表明,這種網上監視確實和強迫性的關系入侵(想與他人保持親密關系,但是他人不接受)之間存在聯系。
一些調查表明,使用臉書的人,更有可能在戀愛關系中出軌。這引出了進一步的研究,這些研究顯示,使用臉書有可能是離婚的預警信號。
有的研究表明,使用臉書會令人沮喪,而有的研究則剛好相反。有些研究人員斷言,使用臉書會刺激到多巴胺反饋回路,從而導致一種神經性上癮。當你收到用戶狀態更新或者跟進一個朋友的主頁的時候,天然的類阿片物質會大量分泌。有研究甚至表明,用戶在網上展示感情生活的行為,和這段感情的健康程度之間,存在著聯系。
西北大學一年級新生摩根·史密斯認為,分手這件事,對人的傷害可以劃分為幾個階段。
“如果你在每一個社交平臺上都拉黑了自己的前任,那真是下了狠心了,”她說,“如果我在臉書上拉黑自己的前任,那等于是把消極的情緒都留給自己了。我想至少保持禮貌,為將來留有余地。同時我并不想每天都看到他的狀態。不過要是他被選上了海外交換生項目,或者當選了班長,我還是愿意祝賀他。臉書更像是對生活的長期記錄。”
37歲的馬修·考費勒是在新奧爾良工作的廚師,盡管他盡職盡責地刪掉了所有和前女友的合照,并且在每一個平臺上都取消了對前女友的關注,他還是被臉書折磨得不輕,僅僅是因為,他忘記取關了前女友開辦的網店。(他前任開了一家售酒的網店,天天都在網上曬店、曬酒、曬生活。)
他說:“有些讓人眼見心煩的東西總是被推送給我,隨時隨地準備在我心上插一刀,雖說時間能治愈一切,但是臉書總是哪壺不開提哪壺。更惱火的是,我的小狗兩個月之前去世了,臉書竟然提醒我每周都分享一次它的照片。”
西北大學新聞系20歲的學生瑪德琳·考夫曼在臉書上的分手就像是一場游戲。她花了整整4個月的時間跟她的男友在網絡上斷絕聯系,雖然他們在現實生活中已經提了分手。
“他的‘戀愛中狀態延續了2個月,”她說,“分手之后看到這個狀態我一直覺得怪怪的,不過,既然是我先提了分手并更改了狀態,我覺得在某方面來說我是贏家。”
42歲的艾麗西亞·阿迪娜是舊金山的一位訓狗師。直到現在她還沒辦法釋懷臉書給她的傷害。2008年,她聯系上了自己的生母和一大家子人。從此,她把社交媒體當成了和這個家庭保持聯系的通道。
她說,隨后,她跟她生母發生了爭執,那個家庭所有的人都對她取消了關注,這意味著,某天阿迪娜登錄臉書的時候,發現自己一個好友都沒有了。“我跟這一家人就好比是待在了一個虛擬的房間里,現在這個房間里就剩我一個人了。”
幾年之后,她在網上獲悉自己的生父已經因病離世了,她說:“我強烈地感覺到臉書是個神奇的東西,它蘊含著很強大的情感力量,這股力量讓人憂喜參半。”
邁克爾·瑞奇是波士頓兒童醫院的兒童健康中心主任,兼任哈佛醫學院兒科專業的副教授,他從社交媒體技術誕生之日起就開始研究社交媒體對兒童心理的影響。
上周,在他自己經營的論壇“有事找醫生”上,有一位女士向他咨詢,這位女士的癥狀特別典型,她雖然已經取關了自己的前任男友,但是她還是情不自禁地想要監視她前男友的網上狀態,她說這種情況在她的朋友中很常見。
“我們見過很多這樣的人,在現實生活中,他們絕不會如此緊盯自己的前男友,但是在網上,卻情不自禁,”瑞奇醫生說,“我們發現,在戀愛的初期,這種跟蹤行為就已經出現了,這可能是源于嫉妒,因為社交媒體的存在,這種傾向有可能被放大,也可能最終消失。”
幾年前,瑞奇醫生帶著他的團隊,和波士頓公共衛生中心一起,組織了一個針對未成年人的論壇,論壇的標語就是“走出網絡,直面生活”。
瑞奇醫生說:“當你敢直面你的戀人,告訴他‘咱倆走不下去了,這意味著你敢于追求有品質的戀愛生活。‘走出網絡,直面生活這個標語是想讓人們在戀愛生活中投入更多的感情,而不是動動手指發條狀態什么的。我擔心的是,設計這些社交軟件的初衷都是好的,但是這些軟件很可能會讓人越來越傾向于逃避現實。這些軟件發展得太快了,我們必須保持學習,才能跟得上時代的節奏。”
埃爾伯特連續工作了24個小時來完善“分手流程”這個工具,臉書公司在研發新產品時有這種連續工作的傳統,很多創意因此得以實現。她說這更像是極客們的通宵派對。接著,她在很多測試平臺上實地演練。很多工程師對這個軟件進行了優化改進和功能擴展。終于,2015年4月,他們在玻璃幕墻會議室里把研發成果以兩分鐘短片的形式展示給扎克伯格。(臉書的參觀向導模糊地指向了一個方向,那里有許多外形相似的辦公室,哪一間是扎克伯格的,他卻并不告訴我們。)
“我自己就克服過許多困難,”埃爾伯特女士說,“小的時候我患有厭食癥,在單位我參與到飲食失調專題活動中時,我感覺自己不光是工程師,更是一個能呼吁大家關注這件事的人,當你從痛苦中走出,并且幫助別人克服同樣的痛苦時,這種感覺太令人欣慰了。”
在產品研發過程中,功能說明的正確措辭是非常關鍵的。埃爾伯特說,語言的運用特別重要,“分手流程”功能說明的用詞靈活性極大,既適合那些剛和男朋友分手的14歲女孩,也適用于那些帶著孩子,經歷了多年婚姻生活的離異夫婦。
用詞必須保持中立,不能表現出任何傾向性,也不能表現出任何形式的引導。“如果說產品設計師們致力于給人們帶來驚喜和快樂,”埃爾伯特女士說,“那么生活中有關痛苦的回憶,又應該如何應對呢?”
無論如何,臉書上應用的語言不應是抒情詩,但是這些語言又必須起到幫助用戶理解功能的作用。如果你某一天終于很不幸地要使用到“分手流程”(目前只有美國地區的用戶可以使用),你會發現這里有許許多多的功能可以使用,就像溫特斯女士說的那樣。
“分手流程”采用了這樣的功能描述:“歇息一下,我們可能會幫上你的忙,我們不會向他顯示你的任何動態,同時也會少向你推送他的消息,只有你主動訪問他的主頁時,你才能看到他的動態。”等等。語言的運用就像是說明書一樣,“為你標注過的狀態和照片開啟標簽許可功能。”不過到了最后,“分手流程”的描述還是轉向了提醒用戶關愛自身:“找好朋友傾訴、保持活躍……”
有一些想法,用埃爾伯特的話講,就是:“讓你暫時無法出現在某個人的賬號當中,以此來防止網上跟蹤。”技術上來講,這是一個很難實現的目標,而且,這會引發更大的爭議——臉書在生活中究竟應該扮演什么角色。但她說:“這沒什么,就像是星巴克不接受人們用信用卡付賬一樣。”
有些人的確容易被網絡跟蹤困擾,但是,如果臉書上面全是嬰兒搞笑視頻,或者唐納德·特朗普拉選票的推文,那么臉書是無法盈利的,它必須保持自己作為一個社交平臺所獨有的特點。
一直要求推出“網絡吸塵器”功能的品牌策略師斯科洛芙女士想要知道,清除一段感情里所有的痕跡,是否需要付出感情成本。“從本質上來說,如果我們能夠像電影《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里描繪的那樣,直接抹去悲傷的回憶,那么我們會不會在治愈的過程中損失掉什么。”
雪莉·特克的新作《重新重視對話:數字時代中交談的力量》中探討了“技術是如何讓我們忘記生命中重要的細節的”。
特克博士是麻省理工學院技術和自我創新中心的主任。長期以來她一直在觀察人與機器之間的互動,她想起了互聯網剛剛興起時的一件事,那個時候人們在探討“互聯網將如何給世界帶來生機”。
特克博士說:“手機應用能為你創造一條……比如……通向星巴克的道路,你可以繞過你的前任戀人,或者繞過任何你不想見到的人,沒有摩擦地,順順利利地買到你想要的摩卡星冰樂。”
“沒有摩擦”這個概念一直困擾著她。“可能一整年之內,你都不想開始一段新的感情了。”她說,她確確實實看到了臉書幫助人們走出失戀陰影的功能。“有的人可能會在分手之后強迫自己閱讀那些舊情書、舊日記,翻翻老照片,心有所動,寫下許多詩歌、小說。”換句話說,有的人就是通過緬懷過去,來進行藝術創作的。
“也不是說臉書就不應該推出這類幫助人們走出分手陰影的功能,”她說,“我們之所以會閱讀舊情書,是因為我們正努力從過去走出來,我們必須意識到,這個過程里面充滿著人性的光輝,并且要對自己抱有同情,人生本來就是豐富多彩的。”
幾周之前,埃爾伯特女士和男朋友一起去巴塞羅那度假,在旅行的最后幾天,他們去了哥特區,在巴塞羅那大教堂前面,他向她求婚了。兩位隨行攝影師全程記錄了這個過程。
盡管如此,他們還是在一天之后,才更改了自己在臉書上的情感狀態。
[譯自美國《紐約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