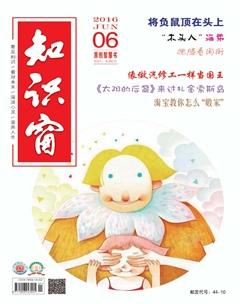把相機交給你
真正的幫助,不是帶著施舍感的憐憫,而是在平等立場上的尊重和關照。

1992年出生的楊凱芩畢業后,打算前往倫敦藝術學院讀碩士。出國前,她到甘肅山區支教,開了一門名為“山間暗房”的攝影課,成了孩子們的“羊老師”。
教完拍照的基本方法,楊凱芩讓孩子們拿著相機自己練習。一聽說能自己拍照,孩子們興奮得手舞足蹈。她待的這所學校位于縣里最偏遠的山區,平均海拔2400米,大多數孩子都住校。在此之前,他們只是鏡頭中被拍的對象,從未摸過相機。
孩子們究竟能拍出什么樣的照片,楊凱芩并不抱什么期望,就當是讓他們玩游戲吧。
孩子們四處尋找拍照對象。夜晚,幾個男孩子頭抵頭躺在路上,仰望著燦爛的星空。付鵬斌覺得小伙伴們簡直像星星一樣美,趕緊舉起了相機;王李燕打算用相機拍下自家羊圈里的羊,因為它們解決了家人的生計問題,她打開閃光燈,鏡頭里的羊群眼睛發亮;大雪過后,大地銀妝素裹,李晉在雪地里邊跑邊喊:“太美啦,我要和美景拍一張。”于是“咔咔咔”拍下一連串清晰度不一的自拍。
孩子們的照片讓楊凱芩深感意外。在外界的鏡頭中,貧困兒童總是一群被憐憫的弱勢群體。但在孩子們的鏡頭里,這里有善良可愛的人、美麗純真的笑臉、看不完的美景。孩子們的世界沒有悲苦,甚至美好得讓人羨慕。
盡管這些照片很難用傳統的藝術標準來評判,甚至談不上構圖,但楊凱芩的心被深深觸動了。也許,貧瘠的不是孩子們的生活,而是人們的眼睛。
付鵬斌想拍下家人挖土豆的照片,又怕爸爸責備,走過去匆匆拍完一張就跑。楊老師鼓勵他告訴爸爸,他想拍一張做紀念。于是,鵬斌鼓足勇氣又拍了一次。爸爸發現后問他:“拍這些有什么用?”鵬斌窘迫得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這個貧困的農家,“有用”是值不值得做的唯一標準。
楊凱芩將一切看在眼里,耐心地告訴鵬斌爸爸,拍照確實沒什么用,但能讓孩子體驗生活的快樂。樸實的農家漢看著楊老師,若有所悟。臨走時,他告訴楊凱芩:“歡迎老師以后多帶鵬斌拍照。”
在楊老師的鼓勵下,這些山里娃越來越會玩。捐贈來的器材有限,孩子們便自己想辦法。光線不夠,他們拿鏡子反射陽光,或者用手電筒照明;三腳架不夠,他們就用木頭做支架。每個拿到相機的孩子都準備了一套拍照“武器”,有手電筒、閃光燈、正方形或橢圓形的鏡子、三腳架等。
孩子們的思維也越來越活躍。有一回,楊老師和二龍踩空掉進了溝里,一旁的李晉趕緊照下來,小李子一邊迅速移動,一邊念念有詞。事后,還得意地宣稱自己是“危急情況下的記者”,弄得楊老師哭笑不得。
孩子們用自己的視角觀察、感受、體會、表達和記錄生活,記錄他們眼中珍貴的人和事。楊凱芩問他們最喜歡拍什么。一個女孩走到她跟前,認真地說:“老師,我不希望別人把我拍得苦兮兮的,然后給予我幫助。”孩子的眼睛明亮得像一汪清泉,清澈見底。楊凱芩看著她,一時竟說不出話來。
“把相機交給你,請你把自己交給世界。”楊凱芩在日記里記下這句話。外界總是將貧困地區的孩子當成不幸的對象,刻意營造落寞、悲慘的氣息,再施以援手。而在楊凱芩看來,真正的幫助,不是帶著施舍感的憐憫,而是在平等立場上的尊重和關照。
“把相機交給你”,我還給你全世界的美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