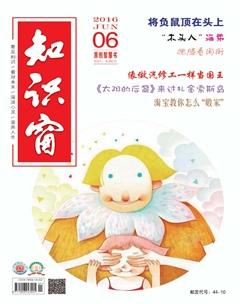真愛和真不愛
吳曉波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東西變得越來越重要,那就是“態度”。凡認真思考過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絕的,都不必說服。
一
二十多歲的時候,我寫過一篇專欄,題目叫《一個春天早晨的敲門聲》。
1908年,正在哈佛大學讀二年級的沃爾特·李普曼已經是《新共和》刊物的撰稿人,一個春天的早晨,他忽然聽到有人敲門。打開門,發現一位須發花白的老者正微笑地站在門外。老人自我介紹:“我是哲學教授威廉·詹姆斯,我想我還是順路來告訴你我是多么欣賞你昨天寫的那篇文章。”
很多年里,我一直沉浸在這樣的幻想里,希望自己的文字能走得更遠,希望更多的人喜歡我的作品,希望在某個春天的早晨也能聽到敲門聲。
年復一年的寫作,把一個好端端的少年逼成了“著名財經作家”。到今天,我寫出的書從地板上往上壘,已經超過膝蓋了。照這個速度,也許有一天,真的能“著作等身”。
也是到今天,我才漸漸意識到,文字也許是寫給所有人看的,可這個世界上真的有很多人不喜歡你的文字,不喜歡你的態度、立場和價值觀。
像枚硬幣有兩面,一面叫“真愛”,另一面叫“真不愛”。
二
海明威在巴黎街頭匆匆而行,南美青年博爾赫斯隔著馬路,沖他大聲喊“大師”。這個細節,被成名后的博爾赫斯津津樂道了無數次。而在夏志清的文學史講義中,海明威是一個被高估的作家,他的小說世界“只有男人,沒有女人”,文字“一清如水,多讀沒有余味”。
博爾赫斯是“真愛”,夏志清是“真不愛”。
25歲時,尼采癡迷上了56歲的瓦格納,認為他的音樂代表了“人類美學的高度”,可是在7年后,隨著瓦格納改變音樂風格,尼采與之決裂,稱“他是一個狡猾的人,聽他的音樂使人致瘋”。
25歲的尼采是“真愛”,7年后的他是“真不愛”。
而后世對尼采本人的評價,也鮮明地搖擺于天才和瘋子之間,有無數的“真愛”和幾乎同樣數量的“真不愛”。
那天,我壓低帽檐走進影院,去看《小時代》。坐在漆黑的空間里,一次次地想站起來走人,然而在四周,卻時不時地響起清脆而會心的笑聲。在這個影廳里,你分明可以猜測出,哪些角落坐著的是像我這樣的誤入者,而在哪幾個角落里坐著“小四粉”。那些“梗”是郭同學專門埋給“自己人”的。
很多批評和嘲諷小四的人,從來沒有讀過他的作品,而我不同。我看過兩部《小時代》,還翻閱了《悲傷逆流成河》,我以后大概再也不會讀他的作品了。對于小四的文字和審美,我是“真不愛”。
三
這個世界上,有一種東西變得越來越重要了,那就是“態度”。
“態度”是一種價值判斷和身份認同。有態度的人,清醒地知道自己認可什么,反對什么,愿意與怎樣的人在一起,以及不愿意與怎樣的人在一起。
任何一種“態度”,都有因果和取舍。明確的“態度”,讓一個人變得成熟而清晰,從而在蕓蕓眾生中,分隔出不同的社群。
社群之內,因趣味和價值觀相似而其樂融融,溝通成本趨近于零。
社群之外,人人形同陌路,事事爭吵不休,口水無數,終無定論。
沒有一個社群的人比另一個社群的人更傻或更聰明,更高尚或更卑鄙。態度也是一樣——凡認真思考過的,都值得尊重;凡刻意拒絕的,都不必說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