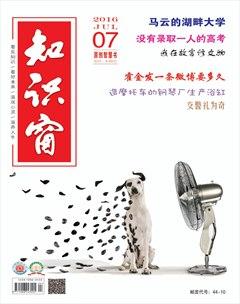漫長的夏日和燃燒的少年
唐歡
一群頭發凌亂的高中生在水泥地籃球場上張牙舞爪地爭搶著褪色的籃球,春日的夕陽照得他們滿頭大汗,精瘦分明的小腿貼著地面追逐交錯,臟亂的球鞋在粗糙的地面胡亂摩擦破洞。晚自習鈴聲一觸即發,班主任的咒罵還未來臨,這是這所還未評上省重點高中的學校一天里最有生氣的時刻。
我和命先一群人在場上奔跑,精瘦的命先眼疾手快,靈活地在人群中貼著水泥地搶到籃球,便立即拋向空中,籃球重重地砸在籃板上,接著又陷入新一輪張牙舞爪的爭搶。
夕陽西沉,人聲鼎沸的球場上人群漸漸散去,球場旁的水龍頭前擠滿了人。命先雙手翻起身上的汗衫朝頭上一抹,蒙住頭麻利地揉搓兩下,索性連手也不用洗了。
1.夏日的籃球場
籃球場隨著濃霧下沉回歸冷寂,旁邊的操場雜草叢生,圍墻邊的刺柏卻郁郁蔥蔥,像新上漆的鐵質圍墻。黑色鐵柵欄繞校一周,繞過人跡罕至的后樹林,在學校北邊的大門像道笨重的閘門重重地合上。
鐵門很久未開,地上的弧形軌道已經生銹。每天早上,命先和我望著這道閘門外飄香的早餐店,面面相覷。學校食堂的饅頭硬得像秤砣,我們每天早上托著不銹鋼飯盒盛著的兩個白色秤砣在食堂里百無聊賴。命先跟我一樣厭倦了這個混雜著消毒水和洗潔精氣味的地方,我們開始盤算著闖過那道閘門,沖向馬路對面飄著煎蛋和肉絲香氣的南昌炒粉店。
早餐店主熱情地招攬著躍躍欲試的住校生們,趾高氣昂的走讀生在早餐店里拎著大食品袋一頓采購,踩著單車飄進校園,提著熱氣騰騰的早餐給交情好的住校生同學們。
我和命先始終不愿意麻煩走讀的女生,堅持自食其力。大門旁重兵把守,他們是學校封閉制管理的中流砥柱。有好幾次,四肢發達的體育生試圖硬闖過重閘,都被保安拎著衣領抓了回來。我們取笑頭腦簡單的體育生,因為每次我們都能瞞天過海,比如謊稱我是走讀生,忘帶走讀證了……屢試不爽。
大大的鐵閘門中開著的不銹鋼小門被高中生們蹭得光亮,搖著笨重的環球牌大鎖在不銹鋼小門上晃蕩,捶擊不銹鋼鋼管發出的清脆響聲,這是困頓的早晨讓人開始一天興奮清醒的聲音。
2.命先和我
和命先的交情,始于我對他名字的好奇。命先說他們家族起名字按排行,“先”字是輩分排行,“命”字則是他爺爺輩給他定的,據說跟他的堂哥、堂弟名字的中間字可以組成一個成語,大概是“福大命大”的意思。這么看來,他那個叫“大先”的堂弟,名字更具獨特性。
重點班的殘酷之處就在于,座位是按成績排的。我和當時并不高大的命先成了同桌,也自然結成了非常堅固的“籃球隊友”和“早餐同盟”。籃球場上,眼疾手快的命先總是能在亂戰中搶到籃板球,給我記憶最深刻的是他每次搶到籃板球之后的詭笑。盡管他投籃的出手姿勢像打太極,盡管他消瘦的身材被壯漢們一碰就摔出底線,但他已經是個具有殺傷力的防守者。
也因為這樣,我笨重的大高個和眼疾手快的命先成為黃金搭檔。我們在無聊的數學課上談論籃球戰術,在政治課上談論NBA,他大概就是休斯敦火箭隊的貝弗利,而我一直以霍華德自詡。可是,在月考試卷發下來的那一刻,我們又開始懺悔。命先頂著連片的“×”開始訂正。他訂正的時候總是一手沉重地舉筆托著下巴,一手手指卷曲玩弄著他凌亂的劉海。有段時間里,他的劉海已經全部卷曲,加上他長期打球暴曬的黝黑皮膚,這才真正開始有點像火箭隊的貝弗利。但是,無論面對多少次連片的紅色對叉,一次酣暢的籃球賽后,我們的精彩談論又風生水起。
班主任的語文課是最漫長的,他熱衷于開批斗會,能把語文早讀開成批斗會,把課外活動開成批斗會,把兩節連上的語文課開成批斗會。批斗會開起來,他雙手叉腰、目光掃射,像兩頂永遠裝滿子彈的機關槍噴著火光,在悶熱的教室里掃射。命先縮著,絕不敢和他目光交匯,我個子高,無法退縮,好幾次被迫和他目光短兵相接,都有種罪大惡極的恐懼感。
有幾次課外活動打球,我和命先玩的忘記了時間。上課鈴一響,班主任準時埋伏在教室的后排,我們抱著籃球滿頭大汗沖進教室,竊喜未被發現,卻在落座的前一秒被老師揪出。
接下來,除了沒收籃球,就是漫長的批斗。夕陽從窗外斜照,晚風吹著課本刷刷作響,我們瞇著眼睛直視著夕陽,又被晚風隔著汗濕的球衣吹得瑟瑟發抖。我們忘了話語的具體內容,只是教室回響的批斗話仍然讓我們耳朵發熱。
3.食物的“垂涎”
封閉制的校園讓我們對“吃”產生了長久的垂涎,好幾次,命先的爸爸提著餐館打包的美食來到宿舍,飯盒打包的食物有“啤酒鴨”和“紅燒豬蹄”,還有很多金黃色的食物上蓋著各種佐料,油光發亮的食物仍然冒著熱氣。命先往往和我一起分享,他知道我和他一樣在饑餓的情況下,對這種流油的食物會陷入某種恍惚的理智消失。
我們的友誼從充滿消毒水和洗潔精味道的食堂到香氣撲鼻的南昌炒粉店,再到回味無窮的宿舍。午后的陽光格外毒辣,宿舍風扇仍舊半死不活,那些金燦燦的食物像饕餮一樣在那個夏天構成了我和命先最久遠的回憶,我們在大飽一頓后陷入綿長的午睡,下午的英語課上還打著飽嗝。
幾年后,我在南方的高校里讀研究生,那么多年盛夏和夕陽斜照過去之后,我感覺很多記憶只能點點滴滴出現,并且轉瞬即逝。昔日出現過的歡笑和痛楚的時光幻化成為同樣的顏色,在泛黃的紙上都是一樣的暗淡,使人難以區分。但關于和命先的那些漫長的夏日,伴隨著食物的香氣和汗水,總讓我記憶猶新,
余華說這就是人生之路,經歷比回憶鮮明有力。回憶在歲月消失后出現,如同一根稻草漂浮到溺水者眼前,自我的拯救僅僅是象征。
那個陪伴我度過整個燃燒的高中歲月的同桌,時常讓我在回憶里笑得發抖,像那個夏天正午熱風吹起的大片樹葉。那些食物的香氣和球場的汗水,隔著學校翻新的塑膠跑道和球場在歲月里閃耀著光芒。那個最終未能成為“少年包工頭”的同桌,和他依然卷曲的劉海是歲月里始終燦爛的陽光,在不論晴朗和蔭翳的日子里,永遠照在燃燒的少年喜悅的臉上。
(作者系暨南大學2014級新聞與傳播學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