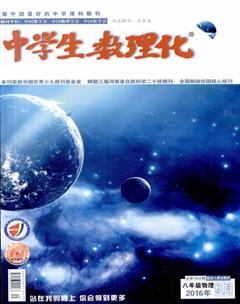經典物理學的重要分支
周華
我國關于聲學最早的科學研究來自于戰國時期的《呂氏春秋》,上記載有“黃帝令伶倫取竹作律.增損長短成十二律;伏羲作琴.三分損益成十三音”.意思是將某一標準音的管長或弦長增加現有長度的三分之一或減少三分之一產生的音律聽起來十分和諧.兩種方法交替使用.各種音調得以輾轉而生.這就是著名的“三分損益法”.1957年在河南信陽出土.現存于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蟠螭紋編鐘,是戰國前期制造的樂器.它一共9件,大小不一,按照三分損益法制成,其音階完全符合自然律.音色清純,可以用來演奏現代音樂.古希臘時代的畢達哥拉斯也曾提出類似聲學定律.不過他是以弦樂作為研究基礎的.
對聲學的系統科學研究始于17世紀初的伽利略.人們很早就懂得區別音調的不同。例如上面所說的利用三分損益法來制作樂器進行表演.但在伽利略之前沒有人能說出決定音調高低的實質是什么.伽利略將他的研究成果記載在他晚年完成的《關于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一書中.伽利略在生活中偶然發現.當他用一把鋒利的鐵鑿刮一塊銅板.在發出強烈尖嘯聲的同時.刮下來的碎屑會在銅板上排成一組纖細的等距離平行條紋.當以不同的速度移動鐵鑿時.發出的聲音越尖利.碎屑條紋排列得越緊密.而當發出的聲音較低沉時這些條紋排列得比較稀疏.他認為條紋排列的疏密程度和銅塊振動的頻率大小有關.這也間接說明了音調的高低和物體振動的頻率有關.伽利略又發現鋼琴的琴弦振動時.與其相差八度或五度的琴弦也會發生明顯的振動.他將這一現象解釋為一根弦的振動在空氣中的傳播激起了另一根具有相同振動頻率的弦發生振動.伽利略于是作出了這樣的總結:“音調與物體的振動幅度無關.而是由物體的振動頻率決定的.即由撞擊到耳朵鼓膜并使其以同一頻率振動的空氣波動的脈沖數目決定.”過去人們知道.對于一根弦.可以通過改變它的松緊程度、改變橫截面積或改變長度來改變它的音調.伽利略的結論使人們意識到原來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改變弦的振動頻率.
18世紀初.一位英國人站在一座教堂的頂端.注視著19 km外正在發射的炮彈.記錄下炮彈發出閃光后與聽見炮的轟隆聲之間的時間.經過多次測量后取平均值.得到的聲速為343 m/s.在當時只能利用人耳和停表的條件下.這一測量結果已十分精確.18世紀中期.巴黎科學院利用同樣的方法測得在0℃的環境下聲速為332 m/s.這與目前最準確的數值331.45 m/s相差無幾.
1827年.瑞士物理學家科拉頓和他的助手分別坐在日內瓦湖相距10 km的兩只船上.他的助手在用錘子敲擊吊在水下的一口鐘的同時.打開船上的閃光燈,坐在另一條船上的科拉頓一手握著他自己設計的喇叭形水下接收器.一手持著秒表.測量從他看見閃光到聽見從水里傳來的鐘聲為止的時間.實驗結束后.他宣布了水中聲速為1 435 m/s.
第一次測量聲音在鑄鐵中的速度也是在巴黎進行的.方法十分巧妙.在鑄鐵管的一端敲一下.在管的另一端聽到兩次響聲,第一聲是由鑄鐵傳來的.第二聲是由空氣傳來的。由于已知聲音在空氣中的速度.利用管長和兩次聲音的時間差便可以計算出聲音在固體中的傳播速度.
其實早在1687年出版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一書中.牛頓就運用復雜而難懂的數學方法推導出了聲速應等于大氣壓與密度之比的二次方根.但根據牛頓的推導算出的聲速只有288 m/s,與實驗值相差很大.直到1816年.拉普拉斯指出只有在空氣溫度不變時.牛頓對聲速的推導才正確.
有關聲學研究的集大成者是英國著名物理學家瑞利.1877年由他著作的兩卷《聲學原理》出版,這部著作至今仍被奉為聲學理論研究的經典.在當時許多人看了《聲學原理》之后都認為有關聲學的所有理論問題都已經被解決.剩下的只是一些工程技術問題.但實際情況遠不是這樣.20世紀.聲學和其他學科聯系得越來越緊密.漸漸出現了專注于聽覺器官、神經系統、聽覺產生機理研究的生理聲學和心理聲學,致力于研究建筑混響、噪聲防治問題的建筑聲學和環境聲學.致力于研究聲電信號轉換的電聲學等.聲學研究已經深深地影響并改變著我們的生產生活.據統計幾乎所有的著名物理學家都研究過聲學.許多諾貝爾獎獲得者都是學聲學出身.聲學已成為經典物理學中歷史最悠久并且仍處于前沿領域的唯一分支學科.
責任編輯 林洋
- 中學生數理化·八年級物理人教版的其它文章
- 開爾文·熱
- “我們恨化學”
- 高分子有機化學的研究先驅
- 談談食品保鮮膜
- 本期練習及綜合測試題參考答案
- 嘟嘟闖關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