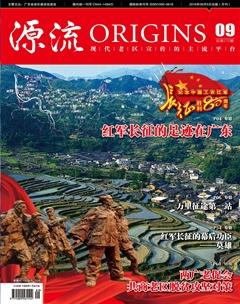秦牧與揭陽老區人民的深厚情誼
楊建東

散文界曾有“南秦北楊”的說法,兩位散文大家,“北”是楊朔,“南”則是秦牧。
秦牧于上世紀50年代末下鄉到揭陽,與云路鎮棋盤老區村人民結下一段不解的情緣。據《揭陽市地名志》記載:“著名作家秦牧于1958年春到棋盤村‘下鄉當農民,住了8個月,寫了《棋盤的變遷》等10余篇文章”。
1958年,全國“大躍進”運動進入高潮,全國作家響應號召下鄉下廠、深入生活,一大批“右派”被下放到農村進行勞動改造。秦牧因寫《地下水噴出了地面》,差點被打成右派,也被下放到原揭陽縣(今揭東)云路鎮棋盤大隊參加勞動。
秦牧來到棋盤大隊,被安排在生產隊長老王家“三同”(同吃、同住、同勞動)。那時干部、作家下鄉“三同”,“萬事開頭難”的就是先要過“三關”,即飲食關、住宿關和勞動關。就拿“飲食關”來說,其時物質奇缺,農民口糧不多,一日三餐都是稀粥、地瓜加咸菜,十天半月吃不上一次豬肉。老王夫婦很難為情,但秦牧卻樂呵呵地說:“我也是貧苦出身,現在有糜有番薯食,就很好了!”說完,拿起熟地瓜大口吃起來。老王夫婦看在眼里,釋懷地笑了。其次是“住宿關”,當時農民普遍居住在逼仄的泥磚房,像老王這樣條件較好的“三同戶”,也只能安排秦牧到臭味難聞、蚊蟲成群的“牛寮間”居住,但秦牧很快就適應了環境。再說“勞動關”,剛開始,他連扛鋤頭這么簡單的動作都鬧笑話,把鋤頭和裝肥料的糞筐放在身后,兩手緊緊抓住鋤頭柄,躬著腰前行,樣子讓人笑話。經農民朋友指點,秦牧很快學到了“功夫”,扛鋤、挑糞樣樣在行。隊里種地瓜又是一個考驗,打壟栽苗,全靠手持鋤頭完成。半天下來,秦牧累得筋疲力盡,雙手也給鋤頭柄磨得起了泡。對這些,秦牧都挺過來了,他的表現,很快得到了廣大農民群眾的認可。隊長和社員們都勸秦牧要量力而行,不要用勁過度,夜班也不要他參加,但秦牧總是爭取多出工,回到住處又不顧疲勞,把當天的所見所聞和感受記下來。就是在如此艱苦的條件下,秦牧創作了大量散文、小品文,如《勤勞》《下鄉當農民》《棋盤寨變遷》等。他在《勤勞》一文中寫道:“我真正體會到‘苦戰兩字的嚴肅意義。”
秦牧有濃厚的貧民情結,他不抽煙、不喝酒,喜歡喝白開水,平常會吃瓜子等零食。他沒有架子,與村民和學生們都合得來。來到村里,他好奇,什么都要問,尤其是民情風俗及村中特殊人物等,問得更詳細具體。
秦牧身體強健,深秋季節還經常到山坑里洗澡。村民見了關心地對他說:“‘白露水,惡過鬼,您就別再洗涼水澡了!”“三同戶”也燒好熱水給他洗澡,他總是微笑地表示感謝,并幽默地說:“我是在煉真功哦!”但還是繼續他的“涼水操”。他的學生陳某回憶說:“秦老師老實厚道,赤色的皮膚,健壯的身驅,簡樸的裝束,與我們農民沒有區別。唯一不同的是,他戴著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
棋盤村創建于清嘉慶靖三十一年,迄今已有460多年的歷史。該村民風純樸,文化積淀深厚,屬山區,又是革命老區。新中國成立后,村民筑庫儲水,引水上山,變旱地為水田,涌現了王木秀這位遐邇聞名的全國勞動模范。中南局書記陶鑄曾“三上棋盤村”,棋盤名揚全國。所有這些,都為秦牧施展才華提供了廣闊天地。
秦牧除自己搞好文學創作外,還不遺余力地培養本土作者。有的村民寫了詩歌、有的寫了小劇本,請秦牧“過目”,他都熱情接待,然后一字一句認真修改。當年,棋盤籍的文學青年王云昌帶回榕城等地的文友前來拜訪,秦牧熱情接待他們,關切地詢問:“大家都寫什么東西?”“創作中遇到何問題?”他鼓勵大家多寫散文、小說。王云昌等人擔心文化程度低寫不好,秦牧說:“不要怕,你們都是工農作者,有生活基礎,只要多學習、多觀察、多練筆,是會寫出好作品來的!”王云昌在秦牧鼓勵和幫助下成長起來,成為鄉土作家,被安排進縣的文化部門工作,出版過多種文學著作。
在棋盤期間,秦牧與全國勞動模范、黨支書王木秀、復員軍人王云德、農業技術員余守信等人創辦“棋盤農業中學”(今為棋盤初級中學),他任教導主任兼語文老師。他上午在生產隊參加勞動,下午到農中上課,夜里還要批改學生作業,但他樂此不疲。
秦牧關心村民的文化生活。1958年中秋節,村里要開展文娛活動,他一下子寫了30多則謎語,供棋盤村舉行“中秋燈謎競猜會”用。他創作的謎語,結合鄉村人名、地名和風俗習慣等來做,如“種樹包活—打一本鄉人名(謎底:木成)”;“冬菜罐—打一民間俗語(謎底:窄嘴)”等,雖然是信手拈來,卻很受群眾喜歡。對那年的中秋晚會,棋盤村老一輩村民還記憶猶新,秦牧的一些燈謎作品被他們傳為佳話呢!
秦牧當年參加了遷移墳墓、平整耕地的勞動以后,創作了散文《遷墳記》,發表在《羊城晚報》上,恰巧被來廣東視察的毛澤東同志看到,稱贊“這是一篇宣傳實事求是精神和集體主義思想的好文章。”《人民日報》副刊版轉載了此文。秦牧也結束了8個多月的下鄉生涯,回到廣州擔任《羊城晚報》副總編輯。
秦牧回穗后,情牽棋盤,曾多次抽空返回棋盤村,探望“三同戶”、鄉親和文友。他與復員軍人王云德是交往至深的“密友”,鴻雁往來頻繁。催人淚下的是,“文革”爆發,秦牧受到迫害,遠在揭陽的“造反派”要王云德提供“揭發秦牧的反叛”材料,被他嚴辭拒絕,從而被“隔離審查”27天之久。抄家時,秦牧贈送他的《藝海拾貝》《黃金海岸》等書,和留給他的熱水瓶、絲巾等結婚紀念品,以及幾十封書信全被當作“罪證”,洗劫一空。十年浩劫過后,他們又恢復了聯系,“劫后余生情更堅”,秦牧寄來的信件及贈書,王云德都視若珍寶,妥善保存著。在此摘錄秦牧在1988年給王云德的一封信如下:
棋盤群眾生活如何?你自己生活又怎樣?是否大家都普遍好起來?頗一為念。你要到茂名省親,很好。你十二三號來廣州,我大概在家。見到時,我將支助你一部分旅費。
孩子們參加勞動,日子就會越來越好了……我在棋盤生活的那一段,是很可紀念的,屈指一算,已三十年了。當時你和老余都未婚,現在有孫子了……
從信中可看到,秦牧問得最多的就是棋盤村群眾和王云德一家的生活狀況,他早把自己當成棋盤村人了。“我在棋盤生活的那一段,是很可紀念的”,這是他的心聲,感人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