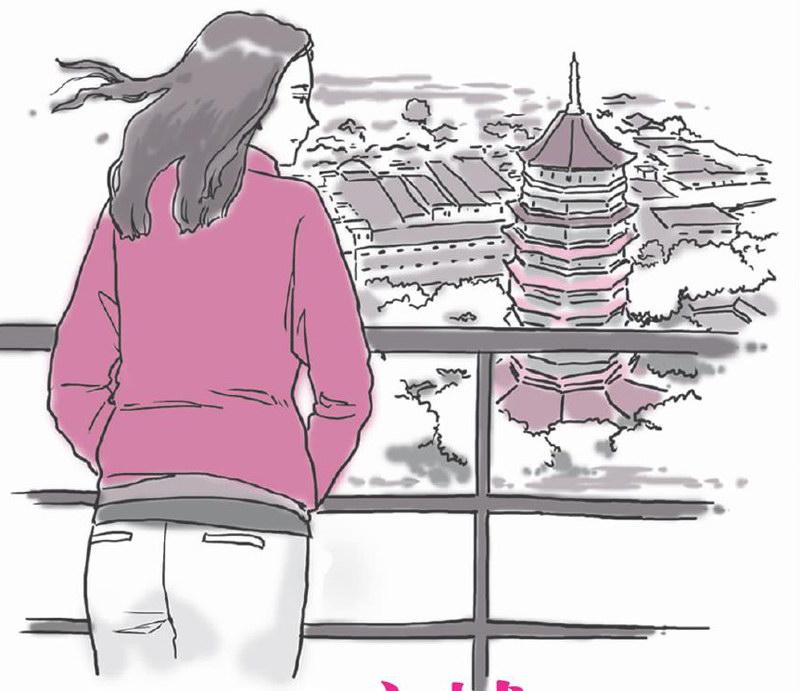琥珀之城
馮可欣
我曾在一篇隨筆中描寫過(guò)初入蘇州外城的感受:“大多數(shù)民居都被漆成米色,如今看去,顏色稍褪。不夠碧藍(lán)的天灰蒙蒙地沉默著,我仿佛正透著茶色的玻璃欣賞這個(gè)城市的側(cè)臉。”劉瑜在《觀念的水位》中有這樣的論述:“第一次到劍橋,我感覺(jué)掉進(jìn)了一個(gè)時(shí)間的琥珀。”“茶色”和“琥珀”在某種意義上被賦予了一種靜謐而穩(wěn)重的形態(tài)。面對(duì)這不約而同的感性認(rèn)識(shí),我會(huì)心一笑。
劍橋與蘇州有相似之處,它們成為無(wú)數(shù)正在更換成相同面貌的城市雞群中的鶴,在歷史所鋪陳的建筑、義化氛圍上站立,比周遭的“完全現(xiàn)代化”們高出一個(gè)下巴頦。每個(gè)城市都有歷史所賦予的輝煌或衰敗,它們的過(guò)去本是深深植根于土地的,只可惜很多被輕易地夷為平地。為了在“發(fā)展”中“繼承”,人們自然保留了一些宏偉且具昭示意義的古建筑。興修各類博物館、展覽館,把散落在民間的文化記憶硬生生歸攏到一處,讓舉著相機(jī)喧鬧不休的游客略讀它們精致的風(fēng)霜。這活像是把形形色色的民間高手和街頭藝人套上革履西裝塞進(jìn)寬敞透亮的會(huì)議室,讓他們個(gè)個(gè)用標(biāo)準(zhǔn)普通話做述職報(bào)告,很多活力和生氣就是這樣丟失的。
劍橋和蘇州盡管程度上有所差異,但都肯定了“活的歷史”這一觀念。對(duì)于建筑遺產(chǎn)的保留,兩者做得都相當(dāng)不錯(cuò)。“除了那些宏偉建筑,普通人生活過(guò)的房子、街道也都值得保留,因?yàn)樗鼈冇涗浀氖菤v史的一個(gè)側(cè)面。”劍橋保留了它15世紀(jì)的圖書館,蘇州保留了它外城的老民居;劍橋保留了它18世紀(jì)的餐廳、17世紀(jì)的墻,蘇州保留了它的古鎮(zhèn)、蜿蜒的古河道。不需要走進(jìn)刻意營(yíng)造的“歷史氛圍”,只要呼吸,你就能感受到歷史的氣味,因?yàn)樗阍谕黄{(lán)天下。
平凡的歷史因?yàn)楹?jiǎn)單,所以不被目光的投射壓得喘息。它具有更大的可以鋪展開(kāi)來(lái)成卷軸畫式的平面結(jié)構(gòu),可以接受來(lái)自不同角度的贊嘆和欣賞。它的歷史是延續(xù)性的,可以自在流動(dòng),而不像于陳列館中從一個(gè)年代開(kāi)始進(jìn)行著一遍又一遍的輪回和循環(huán)。
這樣的城市,因?yàn)樗膫€(gè)性而不僅僅因?yàn)镚DP而著名。而一個(gè)注重尊重過(guò)去、尊重痕跡的城市,它的民眾也因?yàn)槟軌蛎剿牡住⒅浪母⒁?jiàn)證它的成長(zhǎng)、參與它的改善而變得自信而富有創(chuàng)造力。正如伊凡·克里瑪在《我快樂(lè)的早晨》中寫的:“對(duì)于國(guó)外的那種自由生活,因?yàn)槲覜](méi)有參與創(chuàng)造它,所以也不能讓我感到滿足和幸福……我喜歡在布拉格大街的鵝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讓我想起這座城市的古老歷史。”知根知底的優(yōu)勢(shì)其實(shí)可以成為推動(dòng)家園建設(shè)的強(qiáng)心劑。“根”的力量是無(wú)窮的,它讓一切付出和努力都有了著落和盼望,這樣的城市想不發(fā)展都難。
佳作點(diǎn)評(píng)
本文從感性出發(fā),給城市設(shè)定了“靜謐而穩(wěn)重”的基調(diào),也奠定了本文舒緩的語(yǔ)言風(fēng)格;其后,作者進(jìn)一步將自己所要贊美的城市與其他城市在文化認(rèn)識(shí)和評(píng)價(jià)等方面區(qū)別開(kāi)來(lái),并分析產(chǎn)生這一差別的部分根源——“尊重過(guò)去、尊重痕跡”,即保留了該城市的文化之根,為作者的個(gè)體感受提供了理性的分析。
(顧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