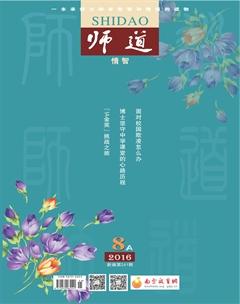“他比其他的學生更需要我”
梁雪菊
他坐在課室一角,最后一排,單人單桌。
他的手舉了好幾次了,每次老師話音剛落他的小手便舉起來,舉得筆直端正。老師看到了,于是說:“請最后一組最后那位同學回答。”可坐在他前面的那位男同學“嗖”地站了起來,而他還是腰板挺直地坐在座位上。老師本想示意請的是坐在最后的那位同學,可站起來的男孩早已經聲音響亮地回答問題了,老師沒有打斷。
接下來的課他仍然積極而堅定地舉著手,老師再次說:“請這一組最后那位同學來朗讀,老師看到你舉起的小手了。”坐在他前面的那位男同學再次“嗖”地站了起來,準備朗讀。這一次老師說:“不急,我請的是最后那位同學。”可全班同學齊刷刷地扭頭看著他,異口同聲說道:“他不會!”已經站起來的那位男同學像得到指令一樣開始流暢地朗讀文句。
老師肯定了前面的男生后,請他來朗讀。他怯怯的,不知道自己該不該站起來。老師走到他身邊,摸著他的頭,鼓勵他把屏幕上的句子讀出來。他讀的聲音很小,小得幾乎連就坐在他后面聽課的我都聽不見。可是老師非常欣喜,目光滿是柔情與鼓勵地說:“你看,你讀出來了!”然后轉過頭對大家說,“誰說他不會呢,請大家把熱烈的掌聲送給他!”
在后面的學習活動中,他一次又一次地舉手,一次比一次讀得響亮。寫字時,老師一次又一次地走到他身邊,握著他的手寫一個,讓他自己獨立寫一個。
下課的時候,我摸了摸他的頭,拍了拍他的肩膀,對他充滿鼓勵地笑了笑。他扭過頭對我靦腆地一笑,露出缺了門牙的一排牙齒。我注意到了這依然怯怯的神色里有了幾分快樂的滿足。
這是校際教研聯誼活動上,小欖鎮菊城小學的蔣老師給板芙鎮一所小學二年級的學生執教《淺水洼里的小魚》課上的細節。
從課室出來,在前往會議室評課的路上,我特意問蔣老師:為什么一次又一次走到這個孩子身邊?在這樣的研討會公開課上,就不怕因此影響教學的節奏嗎?蔣老師同樣給了我靦腆一笑,眼睛里閃著淚花:“他比其他學生更需要我,這與公不公開課無關!”
是什么原因使點名坐在最后的他來發言時,前面的同學一次又一次忽略他的存在而自覺站起?是什么讓所有同學作出同樣的判斷“他不會”?他積極而堅定地舉起的小手和怯怯的表情后面有著怎樣的渴望?當我們坐下來思考這些問題的時候,答案都不難找到。可又是什么使許多老師忘卻了“他比其他學生更需要我”?
蔣老師這句話柔軟而鋒利,觸動了教育情懷那根弦,戳中了教師個體手上教育公平那顆心。
(作者單位:廣東中山市教育教學研究室)
責任編輯 鄒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