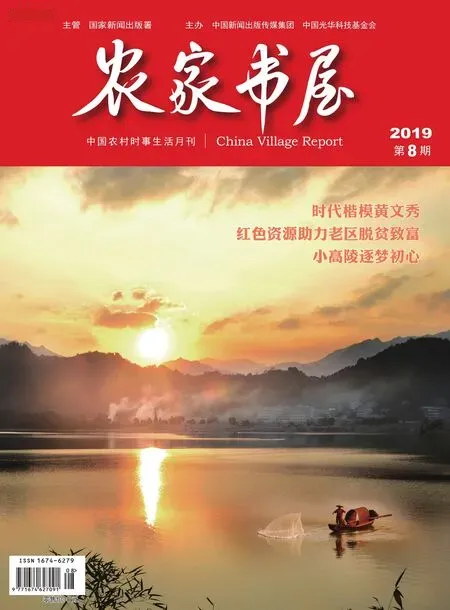給土地流轉上保險
陳曉


“積極發展多種形式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完善對家庭農場、專業大戶、農民合作社等新型經營主體的扶持政策,鼓勵農戶依法自愿有償流轉承包地,開展土地股份合作、聯合或土地托管。”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對扶持家庭農場等經營主體采用了這樣的措辭。在此背后,則是逃不掉也繞不開的土地流轉制度。
土地流轉三部曲
如今,土地流轉正在成為農村經濟發展的重要推手,同時也是農村改革的關鍵一環。
總體看來,我國農村土地使用權流轉的發展,經歷了從禁止到限制、再到開放的“三部曲”,其中的幾個重要節點尤為關鍵。
1984年,原來的禁止政策開了口子,中央一號文件首次提出“鼓勵土地逐步向種田能手集中”,但“自留地、承包地均不準買賣,不準出租,不準轉作宅基地和其他非農業用地”。接下來,1988年的《土地管理法》和1993年的《農業法》規定“國有土地和集體所有的土地使用權可以依法轉讓”。2003年,中國農村土地承包經營制度開啟法制化新篇章,這一年施行的《土地承包法》專門規定:“國家保護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償地進行土地承包經營權流轉”。
2008年,《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允許農民以多種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此后,2009年和2010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均對土地使用權流轉高度重視。這些法律、政策,對農村土地流轉的引導和推進,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
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提出,“賦予農民對承包地占有、使用、收益、流轉及承包經營權抵押、擔保權能,允許農民以承包經營權入股發展產業化經營。鼓勵承包經營權在公開市場上向專業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企業流轉,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這是農村土地制度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農業現代化再進一步。
2014年,“三權分置”被提出,即“堅持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落實集體所有權,穩定農戶承包權,放活土地經營權,實行‘三權分置。”細看近幾年的中央一號文件,土地流轉作為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正在加速推進。
回顧土地流轉政策的演變歷程,全部禁止、部分限制和明確開放的3個階段,已然顯示出土地流轉制度建設取得的巨大成就。
業主跑了,農民虧了
在土地流轉快速推進的同時,問題也是層出不窮。隨著投向農業的社會資金不斷增加,農村土地流轉比例也越來越高,但土地流轉協議非正常性中止的情況常有發生,成為各地土地流轉無法回避的問題。由于土地流轉是一種市場行為,現行政策法律體系中缺乏強有力的監管和約束機制,土地流轉雙方違約的代價輕微,這就使得土地規模流轉的風險居高不下。
成都是全國農村改革試驗區,承擔了11項改革試驗任務,主要著力于農村土地制度、農業支持保護體系、農村金融制度等問題的改革探索。成都邛崍市自2005年金色大地公司出現首例大規模土地流轉單方違約,直至2014年底川之味拖欠土地租金事件以來,共出現較大規模的拖欠租金事件9宗,涉及面積約1.7萬畝,給廣大群眾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邛崍地處成都平原西部,是個典型的農業大縣。全市農村土地確權面積68萬畝,去年流轉面積25.1萬畝,適度規模經營比重達36.78%。在土地流轉快速推進的同時,也存在潛在風險。對農民來說,最大的風險莫過于業主“跑路”,租金“打水漂”。
“我們村都跑過三個業主了!”在冉義鎮九龍村,61歲的村民牟保清掰著指頭細數:“第一個是在2013年,雙流的一家公司來我們村搞鰻魚基地,結果經營不善走了,欠了一年多的租金。第二家公司流轉了我們村、共富村、石子村的3000多畝地,后來老板自己出了問題,每畝地欠了100多元租金。第三個業主流轉了幾個村的1000多畝土地,結果種了不到一年就又撂荒了。”
村里的種糧大戶黃光倫補充:“我原來在外面干工程,回來種地就是因為跑掉的業主是我介紹來的,他丟下的爛攤子我不能不管。”
黃光倫是本村人,村民們不再信任外來的業主和工商資本,而愿意把土地流轉給他,每畝租金都比給外人的便宜100元。
據了解,2012年至2014年間,冉義鎮先后有4家公司的老板跑路,上千畝土地欠下了幾十萬元租金。“這涉及2000多戶村民,雖然后來欠款被追了回來,但留在村民心里的影響卻難以消除。”鎮長張麗說。
不流轉行不行?牟保清搖起了頭。去年8月牟保清搬進了鎮上新建的住宅小區,他和老伴帶孫子,兒子兒媳在成都打工,都勸他們把地流轉出去。
“村里的年輕人都出去打工了,只剩下老人和婦女種地,只要租金有保障,大家還是希望把地流轉出去。”黃光倫說。
冉義鎮農民的集中居住率達到了85%。生活方式變了,生產方式也要改變。就拿九龍村來說,全村800多戶人家,只剩下八九十戶還居住在老村,這其中還有一半是常年在外打工的。
市場化破解土地流轉風險
2014年以來,邛崍探索“土地預流轉+非融資性擔保”模式,就是村集體成立土地股份合作社,村民先把土地“預流轉”給合作社,再由合作社統一招標、流轉。“這個非融資性擔保是由政府來做的,說到底還是由政府兜底。”邛崍市農林局局長陳漢云說。
如何用市場化方式破解土地流轉金融風險?在這一模式的基礎上,2015年邛崍市在冉義等鄉鎮試點土地履約保證保險。具體說,就是引入保險公司開發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產品,保費按土地流轉交易額的3%收取,財政“以獎代補”分攤50%的保費,另一半保費農戶出20%、業主承擔80%。“一旦業主違約,農民的損失都將由保險公司賠付,再由保險公司向承租業主追討。”陳漢云介紹。
2015年12月,中華聯合財產保險公司與邛崍友良種植合作社負責人簽訂保險保單,這成為全國第一單土地流轉履約保證保險合同。目前,中國人保、錦泰保險等多家保險公司都開發了相關產品。
67歲的陳世清是冉義鎮共富村村民,8畝地都流轉給友良種植合作社。“我們只交3元的保費,就可以保障每畝1000元的租金,安心多了。”陳世清很高興。
友良種植合作社負責人汪友良也覺得有保障。“對于合作社來說也是一件好事,以前總擔心,村民第二年不租了,現在有了保險,我們也可以把眼光放長遠了。目前,規模種糧的風險之一在于由于經營者管理不善以及當季氣候等原因,造成糧食大面積減產,經營者損失慘重,農民的租金無法兌現,導致流出方和流入方不信任。”汪友良流轉了6000余畝土地,本人也成為全國土地流轉保證保險第一單的投保人。以土地經營權證和10年的土地流轉合同,經過交易鑒證,每畝可從銀行貸款1000元。他說,“去年稻飛虱嚴重,200多畝田受到嚴重影響,每畝只能收獲200多斤稻谷。當時要是有土地流轉保險就好了”。
黃光倫也說,原來和村民的土地流轉合同只簽了3年,參加了保險后,他又重新簽了10年的合同。“以前有些配套基礎設施不敢建,現在可以放心做了,心里更踏實。”
成都市農委副主任潘斌說,土地流轉保證保險實現了土地規模經營流轉風險可控,填補了農業保險品種在土地流轉領域的空白。今年已擴大到成都市,按照區縣不同,市級財政承擔保費的50%或80%。
今年5月4日,彭軍以每畝每年450元獲得紙房溝村600畝耕地30年的經營權,成為今年邛崍通過農村產權交易平臺公開交易的第一單。給流轉土地“上保險”,邛崍有新規——引入非融資性擔保,為全域范圍內土地流轉中農戶和項目業主的履約進行風險擔保。“一份擔保函,讓農民和業主吃下定心丸。”邛崍市統籌辦相關負責人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