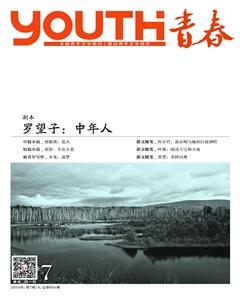存在過的院子
徐方芳
“家屬院!”--無限神往的語氣讓“家屬院”這個本來不具美感的名詞變成了一個輕快活泛的感嘆句。聲音的源頭是三三兩兩站在院門口朝院內張望的人,多半是女性,偶有一兩個小男孩也是母親、姑姑或是姐姐帶來的,表情木然,完全不同于身邊女性的逸興橫飛。那些處在青年、少年和童年時代的女子,也許是恰好經過,也許是故意走到這里,駐足觀望,拘謹又熱切,像站在另一個世界的入口。女性天生對別樣生活的渴望更強烈,或者是容易將欲念表現得更顯露直接一些。
院子里的人過著與他們不同的生活:大院子里一排排干凈整齊的小院落,明凈玻璃窗格后飄著雅致的印花窗簾,窗臺上擺著叫不出名字的珍奇花草,進進出出的大人和孩子衣著光鮮。這里的人們也不用在灶間燒火,爐子上的淡藍火苗總是不緊不慢地起伏搖曳著安閑靜好的燃燒,終日供著熱湯熱水,也燉煮煎炒著她們難得享受的美味食物。
同性別的居民往往是她們關注的焦點,她們悄聲評論著成年女子的發型、妝容、衣飾,有艷羨有加的贊嘆有不以為然的鄙薄,也有少見多怪的驚訝。唯有小女孩一直都是那么養眼:夏天穿雪白粉紅淡黃的連衣裙,春秋天穿天藍淺紫的馬海毛背心,冬天是大紅的滑雪衫和毛呢外套;頭上戴著的鑲著緞帶的發箍,辮稍扎著半透明的蝴蝶結;水晶一般剔透的涼鞋和別致的搭襻小皮鞋,走起來已經夠步步生花,何況還有織著蕾絲邊的襪子;因為白,個個眼睛烏黑嘴唇紅潤。她們在窺看者的眼中是家屬院這座神秘花園里孕育的最明麗的花兒,是城堡里嬌貴的公主,承蒙著想象也想象不出的恩寵,甚或讓其間某些人胸中升騰起宿命的蒼涼和憤然,并且毫不掩飾地宣之于口。
居處此間的女孩,一個人走路的時候,被她們復雜的眼光追隨著,耳朵里聽著她們成分復雜的議論,心中難免有些惶惑不安,腳步也不自在起來。要是兩個三個結伴就不同了,她們(也可以說是我們,因為我也曾參與其間),因為有了同盟者,內心從父母長輩那里沾染來的優越感就約好似的膨脹開來,昂首闊步,目不斜視,眼角的余光里散射著鄙夷和高傲。有時不知誰起的頭,開始笑,笑的原因也許是那些鄉村女子在她們眼中土氣古怪的衣著打扮或者某個人長相上的小小缺陷,有時人家沒什么可挑剔的還是要笑,究其原因還是骨子里的居高臨下。一個笑,其他的都跟著笑,花枝亂顫,讓另外一個群體面面相覷、不知所措,沒有語言肢體的爭斗,家屬院的女孩在精神上已經稍勝一籌,此時的“輸”和“贏”,都建立于不同生活境遇在各自內心投影的自我定位之上。
很多時候,那些女子就那么無所事事地站著,有一搭無一搭地評論,迎接一個,再目送一個,別人在遠處時目光放肆地掃視,待到人家走到跟前又謙卑地讓到一邊,直到索然無味了才悻悻地離開,臉上呈現的是悵然抑或不平的神情。
對于她們,家屬院的居民們往往報以不屑,狐疑、警惕的態度。家屬院并沒有設防,誰都可以自由進出,她們表面看來卻好像總站在門外,矜持而自律的樣子。但失盜的事情還是時有發生,證據確鑿地說明了她們的表里不一。不過丟失的無非是一些衣物玩具之類不值錢的小東西,她們鋌而走險的順手牽羊,其實是羨慕到極致滋生的貪婪。家屬院居民自視處于人群中相對較高階層的優越感和長期被局限窄小空間里壓抑出的促狹,放大了這原本微小的罪惡。家屬院誘惑著她們,也排斥和防備著她們。
另一些人可以在她們羨慕的目光里堂而皇之進入這個排外的院子,他們是此處居民的親朋。有些來自鄉間,拎著一只雞,一兜魚,一籃雜七雜八的菜蔬,扛著半口袋大米或一簍番薯。身份、目的不同,導致他們以全然不同的臉孔出現在這里。單純探望親戚的,有一種夸張的豪爽--這些家里出產的東西實在是不值一提,又有一種貼心的殷勤和周到--這些都是你需要的、最好的、外面買不到的,他們的到來和離開往往都是高聲大氣的,有熟人身處世俗評判中身份高人一等的階層,使得他們心中的榮耀和得意溢于言表。求人借錢、托人辦事的,進來時都訕訕的,走路小心翼翼,待到到了要拜望的人家,連手中的禮物好像帶了討好的謙恭表情。還有一些來自城市,他們的到來往往讓被造訪者受寵若驚,渾然不覺間就在人前表現出炫耀招搖來,引發鄰居多多少少的羨妒,這戶人家的孩子也因為有了來自都市的新奇玩具和小鎮無處購買的包裝精美、味道獨特的糖果糕點成為眾多孩童的中心。那個年代的蕓蕓眾生心中,城市高高在上,鄉村低入塵埃,小鎮家屬院介于城市的“高”和鄉村的“低”之間,處于時而仰視時而俯視的角度,每一天都演繹著世間的沉浮異勢,世態炎涼。
家屬院的格局是封閉的,大院插著碎玻璃的高墻和定時開關的鐵門,一幅倨傲的情態,其間的小院大多數時間也關門閉戶,顯得冷漠而孤僻,然而畢竟還是平面居住的年代,不至于像這個立體居住的年代這樣隔墻而居也互不相識。你家的東墻是他家的西墻,他的前門對著你的后窗,屋舍和院子相互偎依對視,居住其中,自然少不了親密和溫情。鄰墻的孩子常常在晚間來一場彼此呼應的敲墻惡作劇,爐子熄火時可以從鄰家借一塊燒的正旺的煤球,總有孩子端著自家院子里成熟的葡萄、無花果敲開左鄰右舍的門,從墻上接過東鄰從老家菜地里摘來的瓜菜或者西鄰從城市買回的面包、奶糖,心里也是歡喜的。你的母親和她的母親在樹蔭里燈光下討論毛衣的花式,食物的烹調方法,他的父親和你的父親坐在沙發里喝茶、下棋、談時事或者發牢騷……這樣的日月和順,足以在日后追憶起來撫慰人心。
而在鄰里和睦這一片暖色之下,明爭暗斗的寒光也此起彼伏,滋生攀比引發的嫌隙的理由實在太多了,工資、獎金的多少,職位高低,是否評優,孩子的考試成績,家里用的電器,一日三餐的水準,穿什么牌子的衣服--有些是私利之爭,有些純粹是無謂的敵對,那些敵對的理由本身不足以成為敵對的理由,僅僅是別人與自己不同的生活狀態。這些信息往往通過父母的對話、爭吵和主婦之間的嘀咕到達孩子的世界,小小年紀便知曉了人世的虛偽狹隘和險惡,讓我們看世界的眼光過早失去了應有的純凈和溫暖。
家屬院是職工宿舍的民間叫法,這樣的稱呼比官方的命名多了一重人情意味,它是一個機構外延最小的社會背景。這體制造就的居住區,讓工作中的競爭和合作者帶著各自的家庭在工作之外的時間還要在同一個空間生活,一個人諸多生活細節都暴露在他人的視線中,秘密可能成為把柄,隱私可能成為底細,人與人被動地太過靠近在某種程度上抹殺了因距離產生美感的可能,于是便有了那些不該有的芥蒂和齟齬。人們不得不給自己涂上保護色,小心翼翼,謹言慎行。
空間的逼仄壓抑的不止是成人的身心,這樣的沉重的擠壓還波及孩子,尤其是我們這些被旁觀者羨妒不已的女孩。在這高度壓縮的生存區域上,我們進行著她們想不到的艱難成長:自己的小天地只是一個小到不能再小的房間或者客廳里一條布簾隔出的一角,這樣的狹小空間無法保守青春抵達的秘密--在公共的廁所、浴室,成年女性有意無意落到身上的目光,永遠是一種不懷好意或熱情過度的監視和窺伺,她們太過隨意咋咋呼呼的詢問、試探和關心,更讓本來葉芽萌動花苞膨脹那樣悄然隱秘美好的生長發育,因為迫不得已的暴露仿佛成為一種尷尬、羞恥、罪惡的事情,于是每一個女孩走向長大成人的過程都投上了一種驚恐的窘迫的陰影,即便是多年以后回望依然覺得難以釋懷,這樣的經歷是豆蔻年華蔥蘢的花葉上一片無法修復的蟲斑。
院落之間狹窄小路上,人們相遇、寒暄,微笑的面孔下掩藏著各自的心事。腳下粗糲的黃沙咯吱作響,黃沙粉飾的路遠不及城市柏油水泥路的清爽堅固,卻可以在下雨的時候規避村路那樣叫人步履維艱的泥濘,浮動的沙粒每天都被掃帚帶走,也被腳步和車輪碾壓滲進土壤的皮肉,當泥土的面目漸漸浮現,這里便再鋪上一層沙,然后又滿懷優越步履輕盈地走在上面,冷傲地看一眼家屬院門口那些羨慕的面孔。黃沙對泥土的遮蓋,跟家屬院高高聳立的圍墻一樣,以隔絕鄉村濃郁的土地氣息來顯示它接近城市的一面。
房屋低矮,打開門窗戶映入眼簾一堵暗淡呆板的磚墻,沒有村居臨軒而望的廣袤遼遠,也沒有高樓憑欄俯仰的天高地闊,家屬院是城市和鄉村的夾層,它模擬著城市生活方式的又與鄉村血脈相連。這樣貶值的微縮的城市生活,酷似盆栽的農作物,徒有表象的考究與嬌貴,實際上卻失去了盡享陽光雨露的機會,以及在深廣天地間蔓延的自由。
后來,家屬院陸陸續續從人們視線中消失了,再過若干年它就是一個要解釋半天也未必說清的名詞。但是它們確這個是世界上存在過的院子,是一個年代繞不開的物質符號。
毛驢車
一部完整的城鎮生活史,少不了那些毛驢車。幾十年間,越來越便捷的交通運輸工具的日漸普及使得毛驢和毛驢車失去了延續幾千年的大部分功用。而上個世紀最后幾年,一片片新型的住宅小區和職工公寓取代了低矮擁擠的家屬院,也切斷了毛驢車和城鎮的最后關聯。
曾經的家屬院,每個早晨都是在毛驢車吱呀吱呀的聲音中開始的。小毛驢的蹄音很輕,幾乎聽不到,那漸來漸近又漸去漸遠的聲音是板車的車架和車軸摩擦的聲音,聲音越響,負載越重。
只有在晝長夜短的季節才能在早晨看到毛驢車。天寒地凍黑夜漫長的隆冬,當我們經歷了一番思想斗爭掙扎著起床時,只看見小路上的青霜或者白雪上清晰的車轍和蹄印。
負重的小毛驢眼瞼低垂,長長的濃密的睫毛半遮著水潤潤的瞳仁,眸子里的光那么溫厚而和善,瘦長的臉,嘴唇周圍一小片絨撲撲的粉白,小毛驢其實是多么漂亮的生靈,這一點也許只有善良細膩小女孩們才會留心,她們正在讀一本關于小毛驢的書,那頭叫小銀的小毛驢在花瓣、露水和檸檬色的月光下,飲著清澈的河水,咀嚼鮮嫩的青草,主人看它的眼神愛意流動。小毛驢不知道世界上有這樣一頭小毛驢,它的主人也不知道。
小毛驢拖著沉重的板車車廂,無聲無息,心無二志地邁著步子,那般乖巧馴服,這時候看見它,不由會覺得懶、蠢、倔,這樣的評價對毛驢是不公平的。家畜里的毛驢像人群中的老實人,不會如貓狗一樣顯能賣乖,也不會像馬一樣桀驁不馴,偶爾表現出來點頑固偏執,反而被揪住了尾巴。
趕驢車的人,多為中年男子,衣著往往跟毛驢一樣的色調,黑的灰的,至于他們的面容,也許誰都沒留意過,即使無意中視線投射到他們臉上,也會匆匆轉向別處,事實上這樣做也沒必要,因為絕對不會有四目相對的尷尬,他們的眼睛從來都盯著地面,每天都在家屬院的一個角落進行著最骯臟、最繁重的勞作的值得尊敬的人,卻永遠像做錯事情似的表現出一副最謙卑的樣子,這情形跟許多年后,在地鐵里、公交車上看到眾人對那些滿身灰土泥垢的民工避之不及,而民工自己卻一臉歉意、坐立不安一樣,委實是件荒謬而悲哀的事情。
那些跟毛驢車相向走來的人們,蓬亂著頭發,松塌著褲腿,踢踏著拖鞋,拎著痰盂,睡眼惺忪腳步懶散地走著,擦肩而過時無不掩鼻、皺眉,那樣厭惡的神情仿佛是這輛毛驢車帶來了那些叫人作嘔的味道,事實上小毛驢和它們的主人更有權利輕視這些自以為是的人們,家屬院的日常生活中,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可以缺席,而它們和他們卻要是有一天不到場,城鎮里所有的大院子將會方寸大亂。
打掃干凈的公廁散發著消毒水的味道,家屬院的人們神清氣爽地開始了一天的精致生活。傍晚時分,毛驢車還會出現在這里,帶走堆滿垃圾池的垃圾,暮色里的毛驢車搖搖晃晃像一座移動的小山,來往的居民還是害怕受到侵犯似的左右避讓,小毛驢不算強壯的背上沉重地壓著的,恰恰是他們生活中多余出來的東西。
毛驢車日復一日的辛勞讓這里的日常生活安慰有序地繼續,每天清運走的廢棄物,或者歸于土壤經歷是一場神奇的轉換,成為維系生存的菜蔬、瓜果,糧食的養料,或者被回收再利用再次便利人們的生活,那個時代,毛驢和它們主人的勞作是無休止的物質循環鏈條上不可或缺的一環。
坐享它們勞動成果的人覺得一切理所當然,他們永遠居高臨下,趕驢車的人成了他們眼中失敗的人生的典型,常常在教育不努力的孩子時做恫嚇孩子的反面教材。他們無一例外地忽略了這樣一個事實:別人忍受著臟污和辛苦的勞作是他們終日享受的舒適優雅精致生活的一個支點,倘若缺失,他們將陷入難以想象的困窘與狼狽。那些身不由己地處在自以為是的心態中的人們,怎么能意識到潛藏在卑微表層之下的崇高呢?
拉車的小毛驢不是黑色就是灰色,仿佛是舊時衣衫黯淡的平民,不像馬,不是銀白就是棗紅亮黃,如錦衣貂裘的貴族。很多時候,毛驢屬于平民,馬屬于權貴。被高官豪強,惡少土匪驅使,趾高氣昂,盛氣凌人,將喧嚷熱鬧眾生和樂的街市驚擾得雞飛狗跳踩踏的七零八落的是馬。毛驢從來都安分守己,它們為終日為生計奔走的人駕車,為貧窮清瘦善良憂郁的小文人代步,在細雨,冷月,暮色和晨光中,一襲淡青的剪影,小毛驢用不算健壯的四肢和不太寬闊的背,和那些艱辛又堅韌的人們,一起背負起生活的重擔。
許多年過去,誰還記得那些安靜的小毛驢和它們謙卑的主人呢?
泡桐·懸鈴木
那些年在北方小鎮的每個職工宿舍區,成排分布的家除了屋舍和小院還有一些樹,多半是泡桐和懸鈴木,家屬院這樣一直追逐仿效城市生活的地方,選擇當時作為城市行道樹的樹種來做綠化樹似乎順理成章。
也許家屬院的大人們并不喜歡這些樹,城市的樹擔負著凈化空氣、美化環境的雙重任務,這里前者似乎沒有必要,無論來自哪個方向的風都經過大片的原野,浸透了最新鮮的草木氣息,后者,它們又好像做不到,速生的泡桐,樹冠繁茂的懸鈴木,總是將大片的陰影投射本來就不軒敞的家屬院中,老舊的屋瓦和磚墻顯得更加暗淡,也許可以將這樣的幽暗看成一種詩意,但附庸風雅的詩意滋養不了具體、實際的生活,相反它阻斷了居家過日子所需要的飽滿光線和溫度。
泡桐和懸鈴木最被主婦們嫌惡,再明亮硬朗的陽光經過它們闊大的葉片,就被剪碎為一地細碎的光斑,削弱那些小院子作為花圃、菜地和晾曬場地的功能,每到修剪的時候她們就攛掇園藝工人們,多砍點再多砍點,盡量讓樹冠枝葉疏朗,而當溫暖濕潤的季節再次來臨,幾番瘋長之后小院子可能會覆蓋在一片更濃的陰翳之中,對此也只能抱怨,在家屬院這樣一個什么都要遵循整體布局規劃的微縮城區里,誰不可能像在鄉村那樣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隨意種植或者砍伐居所旁邊的一棵樹的。
無論多么不受歡迎,泡桐依舊年年長高長粗,抽枝生葉,開花落花。泡桐花不像別的高高挑在枝端的花朵那樣輕盈,笨笨拙拙的,微微下垂,像一支支音調低沉的小喇叭,沉甸甸地開著,花瓣厚厚的,有絨布的質地,春寒未盡的季節,有種微微的暖意。淺淡的紫色適合月光和微雨,元稹的“朧月上山館,紫桐垂好陰。”是月下的泡桐花的溫馴沉靜,柳永的“拆桐花爛漫,乍疏雨洗清明”是細雨中的爽朗明艷。紫桐花開那幾天,是家屬院最明亮的時光。也只有這個時候人們才對泡桐樹有幾分好感,不由自主去抬頭看花。
沒幾日桐花就謝了,整朵整朵掉下來,像一塊塊舊手絹,落著落著,褐色的花蒂也落下來,終日清掃不盡,叫人生厭,那枝頭毛茸茸的新葉已經迫不及待地遮住了珍貴的陽光。泡桐樹下的每個小院子漸漸淹沒在半明半暗之中。
枝條稠密遮天蔽日的懸鈴木比泡桐更不討人喜歡。它們的球形果實青綠地在枝頭搖曳幾番童話的感覺之后,就毫不猶豫露出一直在膨脹的禍心,果實碎裂、種子四處飛舞,空氣帶了刺,迎面撲來或者粘在晾曬在院中衣物上,結果都是皮膚上令人抓耳撓腮的持久痛癢。相比路人的偶爾中招,與懸鈴木比鄰而居的人要在很長的時間內機率頻繁地深受其苦。
多年的生長,懸鈴木都有了粗粗的可以依靠的主干,樹皮不停地剝落更新,斑斑駁駁,一幅滄桑傷感的模樣。常有孩子闖了禍領了罰或者受了什么委屈,靠著樹干長時間地嗚咽,邊哭邊摳樹皮,新樹皮鮮綠粉嫩,像新鮮的傷痕,這場景總讓人心生惻隱,接下來的情節就是被好心的叔叔阿姨或爺爺奶奶領回家,遞上來一塊擦眼淚的熱毛巾,一只削好的蘋果或者剝開的橘子,最后是父母親氣消了,找了過來,幾番感謝之后,把孩子領回家,懸鈴木們在路旁靜默著,經歷一場雨過天晴的孩子恐怕都沒在意偎依過的樹是哪一棵?
我們忘記一些恩惠,就像當初忽略過它們一樣輕易。人們是在經歷這些年夏天的酷熱難耐之后,越來越懷念那些泡桐懸鈴木掩映之下清涼的日子。
泡桐和懸鈴木對于家屬院居住過的我們來說,跟家屬院生活一樣,既剝奪也給予,慳吝而又大度,殘酷而又溫情,或者這也是生活本身的況味。